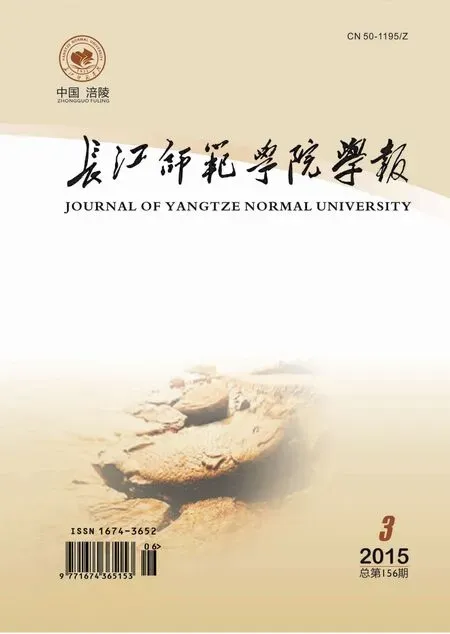褪尽温情现光芒,穿透世相成诗性
——冉冉诗集《朱雀听》的诗性之路
梁平
褪尽温情现光芒,穿透世相成诗性
——冉冉诗集《朱雀听》的诗性之路
梁平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土家族代表性诗人冉冉的诗集《朱雀听》在心理上褪去感情的缠绕,取向理性的思考,给人予以精神上的震荡和摇撼,而情景退隐之后所获得的极富精神力度的“情景”也更能惊醒、提领人心。两者共同构成冉冉诗歌的诗性品质,显示了冉冉在诗歌艺术上独立而有效的努力。
感情;情景;理性;诗性
一、序言
冉冉诗集《朱雀听》共分9辑,辑数之多,在其他诗人的诗集中并不多见;该诗集无序言无后记,只在诗后附有一篇即墨的释读文章,这在诗集的体例中亦不多见。辑数之多,表明诗人涉笔之繁复,分类之细致;体例之简略,表明诗人诗心之素净,诗外之沉默。如此,在繁复、细致与素净、沉默之间,阐释的空间被拉大,而诗人自己并不提供进入这个空间的任何途径,这就为阐释设置了较大的难度。但诗人无论涉笔多么繁复、分类多么细致,出自同一心灵机制的诗歌之间应该隐含某些内在的联系,也无论诗人多么素净,多么沉默,其诗歌却是敞开的,诗人的意指和修为自在其间。诗歌之间的联系让诗歌从各个方向汇成一个整体,而诗人的意指和修为则是这个整体的灵魂。
那么,冉冉诗集《朱雀听》是怎样构成一个整体的呢?这个整体的灵魂又何在?
黑格尔说过,“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朱雀听》不单是在整体上设置了阐释难度,其中多数诗歌超出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经验,读来读去不得要领,无快感,难入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朱雀听》并不与日常情景建立直接联系,而是借由日常情景的稀薄因子去思考、去挖掘、去升华,营造一座精神的高地,凭懒惰的诗法难以抵达、凭浮泛的情感难以抵达、凭轻浅的直观难以抵达。而读者一旦跋涉到这座精神的高地,得到的不是诗法的熟稔、情感的触动和直观的美感,而是精神的轰动与峭拔。《朱雀听》显然不是那种即兴式、自动化、重复性的写作,而是一次次精神历险的诗性表达。
《朱雀听》中有一首《庄严的褪去》,应该是整部诗集的核心诗篇。这首诗借写大地“褪去了它的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和紫色”“褪去了它的声音”“褪去了它的芳香”“褪去了自己的味道”“关闭了眼耳鼻舌”之后在无色、无音、无味且无任何感官作为的本真、宁静甚至封闭状态中“潜心孕育内部光芒”的自然规律,来隐喻性地表达诗人对外在色相的拒绝,对恒常状态的突破,包括对旧有诗歌形态的弃置,进而独向内心新创诗歌的愿望。这个愿望在《朱雀听》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诗集中不仅闪现着诗人内心幽深而明亮的光芒,也发散着诗歌本身独异而精致的光芒,两者共同完成了《朱雀听》的诗性任务。这个愿望在诗集里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有以下两条途径。
二、情感淡化,理性出场
诗歌的外观是情感,内核是理性,是一般诗歌的存在形态。冉冉的诗歌旨趣是主精神的,而精神是理性思考的方向与结果。情感与理性无法截然分离,但大体上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情感的迷雾不仅会缭绕理性使其隐而不现,还会降低理性可能抵达的高度。冉冉深明此理,因此在写作中自觉地淡化了情感因素,转而向理性的高度径直而去。这样的转身背离了常规的阅读习惯和心理期待,读者很难从诗集里获得情感的触动和认知的共鸣。诗集里有一辑《朱雀听》,是诗人写给儿子的诗歌。母亲爱儿子,儿子依恋母亲,是天伦之乐。温情,幸福,这是家庭的一般结构和感情状态,也是亲情诗的一般情感向度。但冉冉在这辑诗里的诗情并不温情,也无幸福感,而是痛心,是心碎。这辑诗之前附有诗人录自旧作的小序,“这么多年/我的公开身份/是朱雀的母亲/而实际身份是痛苦与哀伤的女儿。”这个小序体现了诗人面对儿子时的心理状态,是痛苦,是哀伤,并成为整辑诗歌的情感底色,这已与一般表达母子情的诗歌区别开来。“我们说过的话/尖利的令人心碎的话/都留在楼底的林中/丝丝缕缕不曾消失。”(《仔细听》)这是一种惊心的场景和紧张的关系。“吸附在她们身上的/除了这个城市的苦还有/整个人间的痛”(《弥天大雾》),这是由己及人的猜想和道出的真相,也是诗人痛苦的极度扩张。母亲爱儿子,至少有本能作基础,而紧张的母子关系却让诗人产生了畏惧,“梦和醒都太漫长/那数不胜数的把柄重叠着/爱和怕是两个烫手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把柄。”(《把柄》)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在爱与怕的两重心理元素间游移、踌躇。这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促使诗人进行理性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有些无奈,却是母亲对儿子更深的责任感,“那些苦和痛/雾一样白/雪一样凉/奶一样绵延不绝。”(《弥天大雾》)在苦与痛之间,诗人奉献的依然是绵延不绝的“奶”,这“奶”即是爱,不是物质化、情感式的爱而是精神性的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精神原汁。那么,诗人是怎样以精神之奶滋养儿子的呢?“天穹如幕/雨倾泄向平滑的街面/巨瀑样的水流/在自己身上奔驰/那是雨在书写/就好比你什么也不做/命运仍在写你。”(《我没有要你写诗》)这已然是各有天命的说辞了,而道出这个命运的真相,也许就是诗人对儿子的交底,退到底线了,一个人便再无退路,便会反思,便会忏悔。“我的痛心在于/那些屈辱连着你的血脉/最终在你身上投下了阴影/哪怕它像尘埃那般细小/哪怕你未曾察觉。”(《我不能》)屈辱,大约是生命的必然遭遇,道出这个真相,也是希望儿子作好相应的心理准备,而“那伤痕是我的松香/那血却是我最甜的蜜//重要的是/那蜜也连着你/开初它像针尖那么小/随即/就像涌泉那么多”(《我不能》),这是希望儿子以后能有化屈辱而成蜜的心理能量。如此看来,诗人对儿子的爱,不是溺爱,也不是情感之爱,而是经由苦与痛淬火之后的精神之爱,不是重在儿子的身体,而是重在儿子成人成才需要的生命感悟和人格力量的训练上。冉冉就是这样,在心理上褪去感情的缠绕,取向理性的思考,在诗歌形态上剥去情感的外壳,敞露理性的内核,从而给人以精神之巅的震荡和摇撼。这效应,显然不是表层心理和简单阅读所能企及的。
这样的诗歌意图和理路差不多普及在诗集的每一辑每一首诗中。比如在《公交车上的几十个人》和《他和他们》两辑中,诗歌同样没有集结于温情的吟唱,而是将公交车作为世相的缩影,将他和他们作为全部的人群,从中选取个别的独特的细小人事来揭示生活的真相、变异,由此引发一种普遍性的联想和思考。再比如在《异域》一辑里,诗人并没迷失于异域风情的特异与美好,而是努力在异域为童年记忆寻求印证,或者在神性的国度思考人之何为。这些诗篇穿透了世相的表层和眼前的现实,敞开了人间的本质,拉回了消逝的历史,靠近了神明的胸怀,散发着深刻而丰富的启示。至此,我们才明白,冉冉诗集中不是缺乏情感,而是淡化了情感的色彩,将情感提炼到理性的高度而成为了更内在、更恢宏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核心依然是爱,但不是本能之爱、感官之爱、直接之爱,而是有强大理性作为内在支撑的精神之爱。这种爱是对形而下的取消和否定,对形而上的追索和抵达,然后返回到对人世精神层面的照耀,往往以痛苦、伤怀、幽思甚或反拨、斗争的形式来实施。罗曼·罗兰说:“谁热爱人类,谁在必要的时候就一定要同人类作斗争。”[1]冉冉正是以“斗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深沉而博大的爱。
三、情景退隐,诗性凸显
歌德认为情景是诗歌最重要的元素。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思维是其主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诗歌写作中的运行结果就是情景的诞生。情景既是读者进入诗歌的直观媒介,也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载体。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性要通过情景来完成,意境性要经由情景来营建。同时,情景也是实现诗歌含蓄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诗歌美感度的基本保障。可是,我们在冉冉的诗歌中,几乎找不到完整而鲜明的情景,没有“诗中有画”的感官效果。这为诗歌的解读又增设了一道障碍。甚至我们认为这是诗人阻断读者借由情景进入诗歌的有意而为。撇开那些从题目上看理性色彩较浓的诗篇不说,单是以事物名称或事件形态命名的诗篇,其中就少有关于事物形象或事件动态的描绘。比如《码头》一诗,常规写法应是写出码头的特征和情景,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形象感,以此寓含诗人的诗情与诗思,但该诗只是点明码头这个生发诗情诗思的地点,并且只抓住码头上在诗人看来最显眼的火棘来写,而火棘本身在诗中也只有名称而无形象,诗的主体在于对生命的苦乐与生死的体验和认知。从一般理解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体验与认知移植到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事物。这“断桥式的表达”无疑让读者“莫名就里”。再比如《我们在树下喝加了蜜的茶》,题目告知我们这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然而在诗里,这件事情并未得到正面的铺叙,而仅仅是诗歌得以萌生的一个触媒,诗歌主要生发的是对“闪失”以及由“闪失”引起的人生差别进而对人生偶然性的感悟,并且这个感悟与柿子树上“殷红的果实”给人的甜润感觉毫不相关甚至截然相反,这就容易让读者坠入理解的迷雾,心生茫然。为了解除这些疑惑,我们必须了解冉冉诗歌与一般诗歌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诗写途径。
一般诗歌之所以阅读难度不大并容易受读者喜爱,是因为这类诗歌情景感较强,美感度较高。即是说这类诗歌重在“诗意”的传达,其中诗歌的情景、氛围所产生的美感效果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其蕴含比较适合读者的解读能力,两者相距不远。这类诗歌往往以情感的切近和诗意的浓郁赢得读者的认可。而冉冉诗歌无意于此,她要摒弃诗意呈现诗性。所谓诗性,是指诗歌的内在品质,涉及到诗人的感受能力和言说方式,并进而揭示诗与思、诗与存在的关系。对具有“诗性”品质的诗歌进行解读,自然要求读者具备与诗人一样的感受能力,与诗人的言说方式相适应并知晓诗与思与存在之关系的良好素养。亦即说“诗性”诗歌兼有思考的强度、方式的陌生和精神的向度。这些因素在普通读者那里处于缺失状态,因而对“诗性”很不适应,难入其里。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冉冉诗歌是主精神的,这种精神渗透到诗歌的感受属性层面,便体现为诗性。诗性之诗着意于诗歌的理性张扬和精神提升,就必然将情景视为诗歌的外在因素而加以抛掷,让其退隐至诗歌的主体之外难以寻觅、辨识。也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淡化情感之后所获得的饱含精神因素的情感更能震荡、摇撼人心,情景退隐之后所获得的极富精神力度的“情景”也更能惊醒、提领人心。只不过此时的情景已非可触可感的直观情景,而是抽象却更激烈的心理情景。看看《赶在天亮之前》,“赶在天亮之前/把创口缝好/把蛋壳背在身上//针脚多么柔软/在第一针与第二针之间/藏着剃度的发丝//在最后一针与/倒数第二针之间/藏着一片湖水那静和美/要等到全身的涟漪散尽/才能看出。”人在白天受伤,伤口要到晚上才沉落到心底,晚间的痛苦注定大于白天,因为本已受伤,而想到伤又是伤,并且伤及心灵,然而,无论如何,第二天是新的一天,所以夜晚也是修复创伤的关键时间。缝补创口,这是一个惊心又让人疼痛的情景,诗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苦痛,我们只能想象,诗人并不形象地言明这个心理过程,但读者自有一份难忍的同感。而缝好之后,也只是把“蛋壳”背在身上。蛋壳薄弱、易脆,那么一场缝补到底会有多少功效呢?这表明了人之脆弱和受伤的反复性。但诗人依然在缝补,从“第一针”到“最后一针”,耐心、坚韧。缝补所用的线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诗人是靠什么在平复创伤呢?是“剃度的发丝”,这个意象含有退隐的意思。是的,退隐也许是避免再次受伤的良策。退隐的结果是获得不泛涟漪的“一片湖水”的“静和美”。这就是以退为进获得的完美人生了。整首诗让人感受到人生的苦难,也给人以消除苦难的药方,含有理性的启示性和精神的超越感。我们再回到前文所举《码头》一诗,“这码头上只有火棘/血红的/一树一树的火棘//那是漫长的一生/留下的灰烬/那是一场梦与另一场梦/之间的停顿//那是苦与乐之间的过渡/明与暗生与死/之间的门楣//一树一树的火棘/像迟到的掌声像/寂静的雷鸣。”火棘就是停顿,是过渡,是门楣,是掌声,是雷鸣,这揭示的就是人生的繁复以及对于繁复的思考与应对,是人生繁复过程中应有的标志。从梦到梦,从苦到乐,从明到暗,从生到死,从热烈到寂静,不正如行船吗?而有船必有码头,有码头就有对此岸彼岸的关怀与思虑。因此我们把这首诗的地点换为其他处所显然是不合适的。同理,把象征生命行迹的火棘改成其他植物同样不合适,绝不是因为如诗人所说码头上只有火棘,而是码头上的植物唯有火棘能暗合诗人的生命感触,正所谓此情必此景。而具体情景退隐后,我们看到的是诗人面对繁复人生时内心的痛苦、思谋和寻觅,几乎就是人生的缩图,诗人的内心情景甚是惨烈,但最终归于“迟到的掌声”和“寂静的雷鸣”,表达诗人忍耐、等待和无为而为的心志,启示读者的人生。“刚立冬我就看见/靠近我的死像一对/拾荒的狗熊//还有他的死死是/越来越近的汽车爱/来不及说出来。”(《哑剧》)诗人在这首诗里表达了对死的体验与认知,而死亡的情景在诗里依然被退隐。死像拾荒的狗熊一样靠近,人生多么荒凉,死是一场车祸,多么惨烈,死时来不及说出爱,人生多么短暂。而这一切,诗人视为一场哑剧,台词其实全是多余,就算脚本里有台词,也发不出声音。人生就是一场哑剧,无声地演出,最后离开舞台。死是对生的否定,而这个否定其实一直持续在生命过程中,因此死亡意识有必要伴随生命的整个过程,这看似一种灰色的人生观,实则有助于对人生进行更加通透的洞悉,也有助于一种豁达人生观的形成。“不知死,焉知生”,死是对生的警醒与烛照。
冉冉诗歌中情景的退隐,使其诗歌的诗性特质得以凸显。这种诗性,是诗人在更高层面上对更高意义的追求和接近。伽达默尔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序之中,在显示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和灾难性的迷误中,与远不可及的意义相遇。”[2]这“远不可及的意义”只有借助理性和精神的力量把世界整理成自己满意的秩序后才能抵达,与世界诗性地和解。
冉冉诗歌的理性光芒和精神含量是显著的。其实现的途径就是淡化情感,退隐情景,使理性一路攀升,诗性越发突出。生活中直接的感情和直观的情景已成为冉冉诗歌隐约的背景。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朱雀听》里依然能感受到诗人强烈的情感和在生活中攫取的独特情景,只是为了突进生活的深处,追问自己及人群的生存问题而让理性的思索、冷静的反思掩住了直接的感情和直观的情景。而在比较抽象的情感和稀薄的情景里,诗人的内心体验更切身、更尖锐、更强烈,更见理性抒情直击灵魂的诗性力量。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的关于“诗的生成和运动”的一番话:“越是艺术大师,就越能把某个东西从原来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中抽出来,把它移到另一个序列中去,而且使它所由抽出的原先那个序列只留下最微弱的标记。”冉冉诗歌显示了她抽离情感与情景的序列迈向精神序列的努力,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她更加诗性的表现。
[1][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24.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三联书店,2001:52.
[责任编辑:黄志洪]
I206.7
A
1674-3652(2015)03-0069-04
2015-02-11
梁平,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