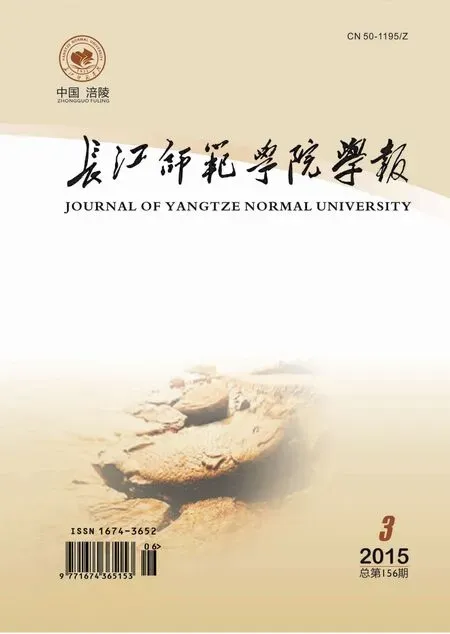特色民族村寨现代性建构的实现:读《人类学视野下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和实践研究》
刘安全
(长江师范学院 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做出有专门指示[1],希望通过各种保护举措,建立起多元的民族特色村寨。其中,旅游开发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传统特色民族村寨与旅游联姻之后,在“民族牌”“特色戏”的标签中,地方性民族文化在“主流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规约和影响下完成了重构与再造。那么,在“民族文化旅游真实性的争论”和“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张力的探讨”中,现代建构的民族村寨文化何去何从?村寨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合理性如何存在?陶少华的《人类学视野下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和实践研究》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特色民族村寨的真实的旅游开发“场域”,从中可以给我们诸多的启发。
一、著作简介
该著作全文36万余字,以“过程—事件分析”的方法,对罗家坨苗寨的旅游开发过程进行了精细化的描述,作者以事件发生过程作为主要线索,详细探索了行为各方对苗寨文化的收集、整理与研判、苗寨开发的可行性研究、苗寨旅游规划、苗寨旅游景点建设等阶段的过程,并对民族村寨文化的传承、现代重构以旅游开发场域中各行动方的诉求与行为,进行了人类学方法的描述与分析。
该著作以一个较为典型的苗族特色村寨的旅游开发过程为研究指向,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具体分析在特色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行动者,即包括政府、村民、规划者、建设者、媒体等各方利益相关者,在各自惯习的推动下,怎样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本,选择怎样的策略,在旅游开发场域中的冲突、斗争、协商和妥协,最终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地的开发。
该著作以“理性”为关键词,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旅游开发可行性论证中的理性、旅游规划中的理性和旅游景点建设中的理性。开发可行性论证中的理性,关照到三个主要行动者——政府、媒体和村民对苗寨文化的收集、整理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研判,最后达成以旅游开发苗寨的共识。旅游规划中的理性,集中体现于旅游规划文本,这个文本是政府、规划者与村民因三个不同利益诉求而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旅游景点建设中的理性,则是政府、村民、建设商、合作社等行动者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的冲突与整合,最终形成合力,推动了苗寨景观建设。这种分析方法,直观地呈现出事件发生的过程,打破了对研究对象静态结构的分析,关照由这个结构而转向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一种独立的解释。可以说是对处于实践过程中的社会生活的研究,而对沟通微观与宏观创造了可能性,达到对实践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真实把握[2]50-52。
二、微型社区研究
民族村寨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实、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物质和非物质的各个层面。透过民族村寨这样一个微型社区,寻找其中特定民族文化特质,来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生活的本质,一直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罗家坨苗寨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鞍子镇新式村,是渝东南一个较为典型的苗族村寨。因其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但其苗族文化传承与保存较好。全村至今仍有木质吊脚楼49幢,被誉为“重庆境内最大的家族苗寨”。罗家坨苗寨保留着吃鼎罐饭、烤火铺等苗族传统风俗,也是“娇阿依”苗歌主要传承地,是全国首批1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村寨之一。作者希望“以小观大的民族学研究范式,探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践过程”[3]4。
对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的研究,也就是选择了当下开始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这一类型的特色民族村寨中的个案,进行“微型社会”精细化研究。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中国微型社区研究,它秉承了西方学术传统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非常重视微型社区的观察与研究,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两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4]304费孝通将这样的微型社区研究的意义总结为“模式”的研究概念,“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5]319对微型社区的描述,作者借用了“场域”一词,罗家坨苗寨的旅游开发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微观世界”“自罗家坨苗寨确立为旅游开发项目村寨之后,它就形成了旅游开发场域,由有关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的行动者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和构造”[4]40。这种“类型”而非“典型”的村寨社区研究,不仅可以体验到一种活态的村寨文化,同时,也通过活态文化在现实社会中运行和冲突的观察,探讨乡村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发生的联系[6]39。
三、人类学“深描”
陶少华对重庆市彭水县的一个偏远苗族村寨罗家坨的研究,花了3年时间,分3个阶段,进行了至少13个专题的实地田野工作。他于2010年8月初次到罗家坨苗寨,从2010年夏季开始到2013年的春天结束,对罗家坨苗寨的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过程进行了跟踪观察与研究;完成了对村民、政府工作人员、规划者、建设者和游客等数百人的深度访谈,拍摄了6 000多张照片,录制了数十个小时的视频和录音资料;对当地的墓碑、庙宇碑刻、契约文书等实物和文字做了收集和整理。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为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过程的民族志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著作对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的可行性论证、规划和开发建设各个阶段进行了人类学“深描”,并用布迪厄“实践理性”作为指导,深刻地探讨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行动者的文化惯习、资本转换关系、行动策略等问题。“深描”方法是“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7]24深描其实是精细的行为主义描写,只有契合文化背景的关注恰如“眨眼”这样细微的细节描写,才可能触碰到研究对象的本质。没有生动的、贴近研究对象本身的理解,任何的民族志描写将是苍白无力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跨文化间比较和抽象分析才是可能的。因而,格尔茨十分强调对行为描写的精细化,“人类学或至少是阐释人类学,其学科进步的标志与其说是达成一致的尽善尽美,不如说是争论的精细化。”[7]33这就要求把文化作为一个文本来看待,深描就是要对该文本进行解释。陶少华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成就了这“一本基于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原创性著作,也是一本难得的村寨民族志”[3]序2。
四、作为一种达成理性的特色村寨现代性建构
在人类学中有一种中国乡村文化研究范式认为,在中国乡村存在着三种基本的社会力量,即“在场”的国家、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由此,型构出一种微型社区研究的“国家—精英—民众”理论结构,这是一种从“小地方透视大社会”的研究取向。在这一种研究模式中,民族村寨文化就与国家、社会的大历史搭上关系,“民族村寨文化由于被强调了所处的具体和主体生活情境,因而具有 ‘作为过程的民族文化生活’和 ‘作为符号的民族文化事象’的双重意义。”[6]40这一研究模式还强调国家、精英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关联,也就是说,民族村寨文化建构所涉的各种主体、关系、空间和时间等因素都要纳入了研究视野,既获得了对研究对象观察与研究的整体性,又突出关照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
作者巧妙地用“达成理性”一词描述了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场域”中行动者各方的行为和博弈结果。苗寨的旅游开发,是“持续性主体相互竞争、妥协形成的行为原则,是各方权利博弈后的全力所指方向,这就是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达成的理性。”[3]250作者指出,在苗寨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在政府与社会强弱对比明显的格局中,旅游建设没有能像政府主导或者没有按照政府意志的假想路线行进,而是在村民、规划者、媒体和旅游开发商、建设商等行动的合力之下产生改变和修正,这是苗寨旅游开发“场域”中各方关系的冲突和博弈下而得到的最终结果。因为,行为中理性的达成也是通过一系列策略和行为而建构的理性。
同时,这种达成的理性,在表面上是苗寨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景观的建设,而从本质上看,则是苗寨文化的变迁和重新建构的过程。“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建构一种适应旅游村寨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是罗家坨苗寨旅游场域中生活文化的再生产,是罗家坨苗寨旅游场域中的社会重新建构。”[3]246
当下社会,民族特色村寨不可避免地步入了现代化过程的快车道,在“多元现代性”的文化图景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对对立排斥的概念,而更多地表现了“地方性知识”在大传统中的流传,以及由族群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而来的国家认同。这样的行为与策略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文化建构的现代形态,“尽管(民族村寨文化现代建构)其中不乏 ‘他者’力量的扶持、引导、再发明和再创造,但作为文化主体的村寨成员始终是复兴再造民族村寨文化的根本力量。”[8]9
[1]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DB/OL].http://www.gov.cn/gzdt/2012-12/10/content_2287117.htm.
[2]谈卫军.“过程——事件分析”之缘起、现状以及前景[J].社会科学论坛,2008(6).
[3]陶少华.人类学视野下的罗家坨苗寨旅游开发和实践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14.
[4][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M]//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M]//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肖青.试论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模式建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8]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J].思想战线,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