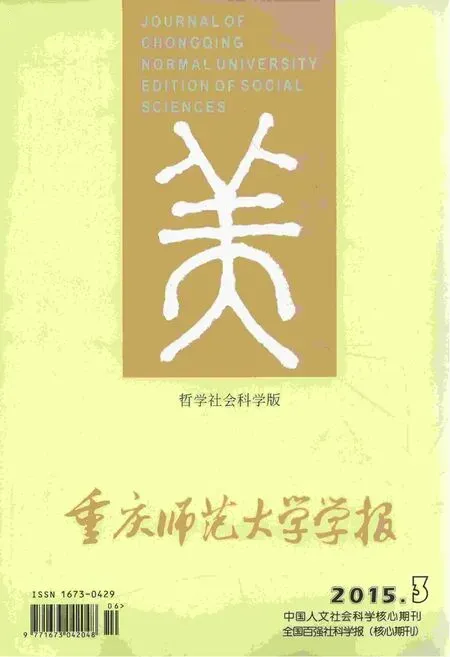金石学视域中的《水经注》金石文献著录考察
郭继红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是为补注《水经》而作。郦道元在补注《水经》的过程中,旁征博引,除征引大量典籍文献外,还征引了350余种金石文献,在时间上上起秦汉,下至北魏,在地域上包罗全国,甚至涉及域外,在内容上涉及政治、民俗、地理、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堪为后世金石学研究之珍薮。“金石”二字并称古来有之,但以“金石”作为一学术名词之始,始于宋代曾巩《金石录》一书。之后,有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金石略》、潘昂宵《金石例》、郭宗昌《金石史》等先后流行于世,其中郑樵的《金石略》把“金石”别列一门,列于二十略之中,使金石学成为一门专门之学。
金石学虽兴起于宋代,但宋之前与金石文献相关的搜集和整理活动已开始。据清人李遇孙《金石学录》,宋以前见之于史籍记载的金石学实践有四十余事,其中《水经注》成书之前的有二十六事,按其实践方式可分四类:一是金石文献之存录,但当时之存录仅属偶然,非有意而为之,如《左传·昭公三年》引《谗鼎铭》、《礼记·祭统》引《孔俚鼎铭》、《礼记·大学篇》引《汤盘铭》、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录载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和会稽刻石等,都是为史料的征引而偶然为之。二是石经刻录与补修,如《后汉书·孝灵帝纪》载,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异同,刻之于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蔡邕传》注引晋陆机《洛阳记》,记有洛阳南开阳门外太学汉石经诸碑等。由于风吹日晒,石刻碑碣会逐渐剥落,石经文字会损毁,不可复识,因而对石经的补修便显得尤为重要。据《北史·崔光传》记载,北魏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崔光曾上表奏请勘补石经,明帝依其奏,“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1]1620,至胡太后主政,遂废。三是金石文献搜集著录,如晋将作大匠陈勰,辑有《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见之于《隋书·经籍志》,今不存。四是金石文献校考,如《史记·封禅书》载李少君见汉武帝,据铜器刻铭考铜器铸造年代;《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时,美阳得铜鼎,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考释文字。综上,《水经注》成书以前零散的金石学实践已经开始,虽然这些实践只是零散地、偶然地进行,与宋代那种系统性的考证实践有很大差距,但正是这些零散的金石学实践考证,为郦道元撰著《水经注》金石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郦道元著录金石文献是站在前人成果之上的,其通过对金石史料的著录变相的对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做了总结,也蕴育出金石学在宋时形成的种子。
一、著录大量北魏以前的金石文献
金、石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古人早已用之,如《礼记·祭统》所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2]732再如《穆天子传》卷二云:“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郭璞注曰:“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类也。”[3]11青铜鼎铭,多见于商周贵族的祭器,因其贵重,传世不多。秦汉以降,刻石之风兴起,大量的石刻文献相继产生,相关著述也不断涌现,据《隋书·经籍志》,魏晋至唐的金石文献著作有:“《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碑文》十卷,车灌撰;又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祐撰)。”[4]1086然以上诸书今多已亡佚,唯《水经注》留存有秦汉以降大量的金石文献359种,为后世学者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郦注所引金石文献就其种类而言,有金文、摩崖、碑碣、界至、画像石、建筑附属刻铭等;就其数量而言,郦注所引金石文献中,吉金文献有4种,石刻文献有355种,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碑刻类达288种,这样庞大的数量即使与宋朝金石学著作著录的金石文献数量相比也不遑多让,如欧阳修《集古录》,所录北魏乃至北魏以前的金石文献仅150余种,而金石学的集大成著作——赵明诚的《金石录》,辑录北魏以及北魏以前的金石文献380余种,故清人钱坫称:“彝鼎之显由二汉,则许洨长言之矣。志碑之著由二魏,则郦中尉详之矣。”[5]10707由此,郦注金石文献的留存价值可见一斑。然至宋欧赵著录金石文献时,道元所引多已亡佚,所存者不过十有四五,如卷二十一《汝水》“又东南过郾县北”条注中《后魏叶公庙碑》,此碑刻有筑修叶公庙缘由事,但后世无著录,仅郦注著录。再如卷二十一《汝水》“又东南过平舆县南”条注中《汉青陂碑》,此碑记述了青陂的地理处所、源头及流向信息,保存了青陂水利工程的相关资料,为后人对其研究提供了线索,但此碑不见于欧、赵著录,已亡佚,唯郦注存。凡此类碑版逸闻,郦注著录有不少,因而被后世金石学者视之为瑰宝,如清人洪亮吉曾称“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凡引汉碑百,魏碑二十,晋及宋魏称是。窃尝谓金石之学,惟道元能见其大。今读其注,如华阴载祠堂碑,巨鹿载神坛碑,则祀典可定也;荥阳石门之铭,沛郡石坡之颂,则水利可兴也;洛阳南界冀州北界之石,则区域可正也;曲江泷中碑,新城大石山碑,则幽远可通也。”[5]10707
对于郦注金石文献的价值,陈桥驿先生在《<水经注金石录>序》中写道:“《水经注》虽然并非记载金石的专著,但它所引及的碑碣石刻等资料,不仅数量多达三百五十余处,而且在时间上上起秦汉,下至北魏;在地区范围上包罗全国,甚至涉及域外;特别是在内容上的丰富广泛,使这些碑刻的实用价值大大提高。历来学者著录金石资料,在内容上往往着眼于人物、墓志、祠庙等,而尤以名人名事为重。在形式上则又常常追求书法字体和雕琢功夫。但郦道元在这方面绝无成见,只要在地区上属于他的著述范围,在内容上符合于他著述的需要,则不论‘石作粗拙不匹’或‘文辞鄙拙,殆不可观’,他都能兼容并蓄,搜罗无遗。因此就大大地丰富了《水经注》的金石资料,为后人利用这些资料带来了许多方便。”[6]523陈桥驿先生的评价允为精当。
二、影响后学的金石文献著录方式
金石文献的著录方式,朱剑心先生认为主要有存目、跋尾、录文、分域、分人、纂字、摹图、义例、分代、通纂、概论、述史、书目等。郦道元著录金石文献是为了补注或考证的需要,而非有意为之,因而其著录方式并非唯一。以《水经注》篇章目次论,其金石文献是以“分域”著之,按照水系河域分布著录,先黄河流域,次淮河流域,最后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水域,且其著录数量长江以北居多而长江以南较少。若以时代论之,则郦道元著录的金石文献上起秦汉,下至北魏,可以看做是“分代”著之。若以其著录内容而言,以“通纂”概之,或为恰当。“通纂”即集存目、跋尾、录文等综合而著录者。
存目,即著录金石文献时著录金石文献名目,不记其他。《水经注》著录金石文献有采用。如卷六《汾水》“东南过晋阳县东”条注中对《晋太原成王之碑》的著录:“太原郡治晋阳城,秦庄襄王三年立。……《魏土地记》曰:城东有汾水南流,水东有《晋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成王之碑》。”[7]98卷十二《圣水》“又东过阳乡县北”条注中对《晋康王碑》和《晋范阳王庙碑》的著录:“桃水又东迳涿县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晋大始元年,改曰范阳郡。今郡理涿县故城,城内东北角有《晋康王碑》,城东有《范阳王司马虓庙碑》。”[7]222此三碑郦道元只著录碑目,其他的未有涉及。
在金石文献著作中,以“跋”的形式著述的金石文献最受后世学者重视,不仅是因为其所含的信息量大,而且也是因为其所含的金石器物信息最为全面。郦道元在著录金石文献时,为了其考证的需要,对于其亲迳所见的碑刻,都有详实的描述。虽然他的目的仅为补注史实需要,但是其对碑刻的描述在客观上已经具有了碑跋的性质。《水经注》所载碑刻的跋尾内容丰富,主要有:(一)记碑刻形制、碑石留存情况。在引用碑碣石刻时,郦道元就自己亲身所见,对碑碣的形制作详细描述。如卷三十《淮水》“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条注中《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593对碑碣石刻存佚的记载,如卷十九《渭水》“又东过霸陵县北”条注中《梁严碑》:“其渎水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迳郿及武功槐里县北,渠左有安定梁严冢,碑碣尚存。”[7]340(二)述碑主字里官位,或立碑年岁。如卷十五《伊水》“又东北过新城县南”条注中《晋宗均碑》:“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7]277再如,卷二十三《阴沟水》“东南至沛为濄水”条注中《汉温令许续碑》:“濄水之北有《汉温令许续碑》,续字嗣公,陈国人也,举贤良,拜议郎,迁温令,延熹中立。”[7]412(三)记碑刻刊立之缘由。如卷四《河水》“又南出龙门口”条注中《晋立司马迁庙碑》,此碑是因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司马迁遗文“大其功德”而“立碑树桓。”[7]55再如,卷三十三《江水》“又东过符县北邪东南”条注《汉孝女碑》:“郡县上言,为之立碑,以旌孝诚也。”[7]583此碑乃郡县旌孝诚而刊立。
录文,即摘录碑刻铭文。《水经注》在征引金石资料时对铭文非常重视,经常会摘录或概述碑碣铭文内容。在摘录铭文时,有时会摘录铭文全部,如卷十五《洛水》“又东过偃师县南”条注中对《晋九山庙碑》和《百虫将军显灵碑》碑文的摘录,郦氏照录碑文,一字不删;有时会根据考释需要,摘录铭文中一句或几句,如卷四《河水》“又南出龙门口”条注中对《司马迁碑》碑文的摘录,郦氏为了考释华池和夏阳城地理位置,只摘录《司马迁碑》碑文中的一句“高门华池,在兹夏阳”[7]55。作为考证例据。
《水经注》金石史料的著录方式影响深远,宋时金石学者对其多有接受和创见。宋时欧、赵、洪诸家对《水经注》著录的金石文献多有征引。在征引过程中,郦道元运用的著录方式他们肯定会有接受,又因他们是专治金石的学者,肯定会对其有所损益,有自己的创见。以《水经注》碑刻跋尾内容为例,通过与欧、赵、洪三家著录的碑刻跋尾包含的信息相类比,可明显发现两者基本相似,如对《后汉殽阬君神祠碑》的记述,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九《渭水》“又东过郑县北”条:“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东南向华岳,庙前有碑,后汉光和四年,郑县令河东裴毕字君先立。”[7]345五部神庙即殽阬君祠,郦氏在此著述了此碑的地理处所、刊立时代和刊立者;欧阳修《集古录》卷三跋云:“右汉殽阬君神祠碑,在郑县。……光和中,(裴)煜为郑县令,始修复之,事见《水经》及《华州图经》。殽阬君祠今谓之五部神庙,其像有石堤西戍、树谷、五楼先生、东台御史、王翦将军,皆莫晓其义。”[8]17860此跋尾内容包含有碑石处所留存,刊立者、刊立时间以及碑文的留存情况等。赵明诚《金石录》对此碑也有跋,并利用《水经注》所载的金石资料对此碑的刊立者是裴煜还是裴毕作了考辨,认为欧氏有误。洪适的《隶释》录有此碑碑文,并跋云:“殽阬君神祠之碑铭,篆额,在郑县。灵帝光和四年县令裴毕字君先立。”[9]32综上,虽然欧、赵、洪三家在碑跋中著述的信息各有侧重,但是其基本内容与郦道元著述差别不是很大,只是欧、赵、洪三家的著述更为规范一点而已。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是以前人的大量实践成果为基础的,金石学的形成也不例外,郦道元在著述金石文献时所运用的方式方法,被后世学者沿袭规范,为金石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学者著述金石文献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例。
三、利用金石资料考经订史的著录意识
金石刻辞,在保存文献方面有其特色。一者可以长久保存,不像纸质文献,一旦遭厄,毁失殆尽;二者具有更高的可靠性,且不易发生错讹和篡改;三者时代较早,且系原始资料,对纠正传世文献错讹、补证文献,有极高价值。宋时金石学兴起,众多学者重视和利用金石资料考经订史。赵明诚《金石录·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0]8799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里也曾谈到金石文献考经证史的作用,他说:“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11]600也就是说利用金石材料可以证史书之“阙缪”,郑樵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12]总序上述各家所述观点,距郦道元撰述《水经注》已经有500余年,而郦道元在注《水经》的过程中,已经对金石文献的考史、证史价值有所认识,且非常重视,如在卷十五《洛水》“又东北出散关南”条注中对周代悼王、敬王、景王陵墓处所的考释,认为只要“考之碑记,周墓明矣”[7]270。因为陵东石碑录有赧王以上世王名号,通过对其碑记的考释,就可以确定三王陵墓的处所。再如卷二十二《渠(沙水)》“其一者东南过陈县北”条注中对四县馆舍遗址的考证,众人认为其地为孔子庙学的遗址,而郦氏据碑文考释,予以否定,并指出众人之所以会出错,是因为“时人不复寻其碑证”[7]406,也就是说时人不重视碑刻铭文的考史作用。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郦道元非常重视金石资料在考史过程中的运用,对其价值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四、求真求实的金石文献著录理念
金石学是一门非常注重实践的学问,对于碑碣的形制体式、铭文字形及石刻材质等非亲见不能得正确的结论,因而求真求实的思想应是金石学治学思想的应有之义。郦道元在注《水经》的过程中,引用的金石资料大多是其在行旅途中亲身所见。每到一地,他都亲迳碑碣铭文所在之地,勘验碑题,研磨碑文,以证述故老传说、史迹遗闻之真实,如卷十三《漯水》“漯水出雁门阴馆县”条注:“其水又迳宁先宫东,献文帝之为太上皇也,所居故宫矣。宫之东次,下有两石柱,是石虎邺城东门石桥柱也。按柱勒,赵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于此。余为尚书祠部,与宜都王穆罴同拜北郊,亲所经见,柱侧悉镂云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势,信为工巧,去《子丹碑》则远矣。”[7]232在这里,郦氏对宁先宫石桥柱亲所迳见,对其形制规格以及柱勒铭文,述说详细。再如卷十一《滱水》“又东过博陵县南”条注中的《朗山君碑》:“徐水东北屈迳郎山,又屈迳其山南,众岑竞举,若竖鸟翅,立石崭岩,亦如剑杪,极地险之崇峭。汉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蛊出奔,其子远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7]210在此郦文中,由“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语可知,郦道元亲见山南的《郎山君碑》,勘验碑文,证述朗山得名事。郦道元除亲自搜集碑碣石刻,以证述历史古迹、人文掌故之外,还亲历碑碣石刻所在之地,验勘碑文,匡谬正俗,如卷三十二《夏水》“又东过华容县南”条注中《晋西戎令范君墓碑》:“(夏水)历范西戎墓南。王隐《晋书·地道记》曰: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晋《太康地记》、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记》,并言在县之西南,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检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称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观其所述,最为究悉,以亲迳其地,故违众说,从而正之。”[7]556对于范蠡墓的处所位置,郦道元不轻信王隐、盛弘之、刘澄之以及《太康地记》诸家看法,而是亲往其地,检其碑题,勘验碑文,纠正诸家之说。郦道元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堪为后世之楷模。
《水经注》虽是一部私家史地著作,但郦道元在补注《水经》的同时征引存录了丰富的金石资料,为后世学者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源泉。郦道元在著录金石文献时,不仅对碑碣形制、碑石留存、碑主字里籍贯、生平事迹、碑刻刊立缘由、铭刻文字作了介绍和著录,而且也利用金石资料匡谬正俗、补证史实,更重要的是郦道元在搜求金石资料时亲力亲为、远绍旁搜,并且非常重视金石资料的考经证史作用,这些都客观上为后世金石文献的著录、金石学研究方式方法的形成提供了范例,也为后世学者研究金石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注》也是一部金石文献著作,对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作了总结,承上启下,为金石学在宋时形成作了必要地准备。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朱彬撰,绕钦农点校.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佚名撰,郭璞注,王根林点校.穆天子传[M]//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毕沅.关中金石记[M]//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6]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7]陈桥驿.水经注校释[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8]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9]洪适.隶释 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赵明诚.金石录[M]//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11]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