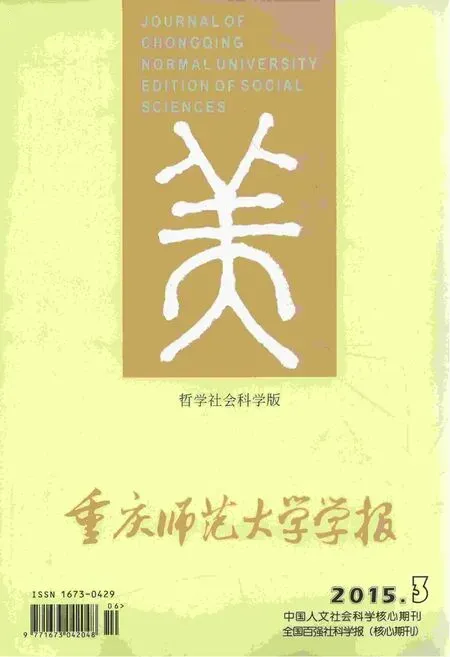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张 瑞 君 孙 健
(1.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0;2.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文莹笔记内容颇丰,或论政治经济、军国大事,或述名公显宦、逸闻轶事,其价值正逐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对文莹笔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献整理、错误订正、版本考证,以及对笔记个别条目的研究等方面,以文学思想为专题研究,尚未有学者涉及。故笔者抛砖引玉,试论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一
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在创作论方面表现为注重诗歌的意境美。《湘山野录》卷上“金陵赏心亭”一条中评论了王琪描写“秦淮绝致”的诗歌:“千里秦淮在玉壶,江山清丽壮吴都。昔人已化辽天鹤,旧画难寻《卧雪图》。冉冉流年去京国,萧萧华发老江湖。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文中说:“此诗与江山相表里,为贸画者之萧斧也。”江山如画的美景,与清绝秀丽的诗歌融为一体,相互映衬。只有做到物境、情境和意境的和谐统一,才能臻得其境,境与情合,创造出优秀的诗歌,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在风格论方面,文莹主张在“唐人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形成宋诗独特的风格。
文莹对唐诗曾进行过深入研究,注意到了宋诗学习唐诗的现象。如《湘山野录》卷上载宼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文莹评价为“深入唐人风格”。《湘山野录》卷下也提到“皇祐间,馆中诗笔石昌言(字杨休)最得唐人风格,余尝携秦访之”。
文莹指出作诗不应专事模仿唐人诗作,而应该在“学唐”的基础上“变唐”,另辟天地,方能自出新意。《湘山野录》卷中记载:
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籍籍喧著。余缁遂寂寥无闻,因忌之,乃厚诬其盗。闽僧文兆以诗嘲之,曰:“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
诗僧慧崇的名句“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1]1464在宋初风靡文坛,连许多士大夫都惊讶于其诗的出色。然而,闽僧文兆后来发现慧崇的这两句诗是袭取了唐代诗人司空曙的“河分岗势”句和刘长卿“春入烧痕”句,于是便写了一首诗嘲讽他:“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偷古人句,古人诗句似师兄。”但是,文莹在这里明确指出,时人是因为嫉妒,才“厚诬其盗”。慧崇的诗句确实对唐人的诗句有所化用,但能自出新意,仍不失为佳句。后人的品评也证明了这一点。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以为“虽取前人二句合成此联,为人所诋,然善诗者能合二人之句为一联,亦可也,但不可全盗二句一联者耳”。《带经堂诗话》卷二十《禅林类》曰:“大抵‘九僧’诗规模大历十子,稍窘边幅,若‘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自是佳句;而轻薄子有司空曙、刘长卿之嘲,非笃论也。”平心而论,变化前人成句入诗未尝不可,这种现象在古人诗集中并不鲜见。吴可《学诗》:“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2]587《陵阳先生诗》卷二·《韩驹赠赵伯鱼诗》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慧崇之诗,是在广泛学习唐人诗句之后的信手拈来之作,字虽同而骨自换。笔者认为,文兆的嘲讽,恐更多的是出于私怨。由此可见文莹评诗眼光之独到,也让我们看到了宋词对唐诗的学习和创新的过程。
文莹注意到了宋初诗人在向唐人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宋初晚唐派枯寂淡薄、清悲怨感的风格,推崇积极向上的文风。文莹作为宋初的诗僧,自然对文坛上一度盛行的晚唐诗派有较多的关注。晚唐诗派宗法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等人,从唐人的诗句中吸取营养,加以创新,形成了特有的清奇雅静的风格。明都穆《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云:“宋初谭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3]387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亦持此说[4]209。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中也提到:“九僧诗乃唐韵”。在《湘山野录》与《玉壶清话》中,有多条关于宋初九僧慧崇、潘阆、魏野、和寇准等人诗歌的记载。如《湘山野录》卷下“潘逍遥阆,有诗名”一条和“处士魏野,志气高尚”等多条,就记载了潘阆和魏野的诸多生活轶事和创作佳句。但是,同为僧人的文莹,却对他们诗中所表现出的枯寂之风和悲凉伤感的情调并不认可,这也正是文莹创作的诗句中没有普遍僧诗的“蔬笋气”和“酸馅气”,而是具有一种至味归于平淡后的本真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的方外之友郑毅夫在《文莹师诗集序》中如此评价:“尽观莹师之诗,得其佳句,则必回复而长吟,窈若么弦,瞥若孤翻,遂与夫溪山之灵气,相扶摇乎云霞缥缈之间,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渊之为行役之劳也。浮屠师之善于诗,自唐以来,其遗篇传于世者班班可见,缚于其法,不能闳肆而演漾,故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予尝评其诗如平山远水,而无豪放飞动之意。若莹师则不然,语雄气逸,而致思深处,往往似杜紫微,绝不类浮屠师之所为者。”[5]1097册246同样,在刘挚的《文莹师集序》中,也有相似的评价:“其辞气象巧,尤不觉其为穷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6]1099册558文莹在笔记中多次表达了对诗坛文人追求清悲怨感风格的不满,其评价寇莱公《江南春》二绝尤可见一斑:
寇莱公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二绝,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殊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莱公富贵时,送人使岭南,云“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以为警绝。晚窜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公问州去海近远?曰:“只可十里。”憔悴奔窜已兆于此矣。予尝爱王沂公曾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后皆尽然。
在此则材料中,文莹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寇准诗作风格过于凄楚愁怨,悲凉感伤,造成了诗歌“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的卑弱格调。其他如《湘山野录》卷中:师鲁也强调“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在文莹看来,这样的诗作“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古人向有“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说法,穷愁之言多了,就会易于伤神,导致气谢。又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王逢原”条:“然所为诗文,多怨抑沉愤,哀伤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寿”。[7]97文莹认为,一方面,晚唐诗歌中那种优柔凄婉的笔调,惆怅感伤的情思,迷离凄艳的景色,悲怨愁苦为主的表现风格,会造成诗歌境界的狭小,气格的卑弱;另一方面,这种风格也与宋初繁荣兴盛的时代格局格格不入。与此种风格相对照,文莹更喜爱吕蒙正的《早梅》“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他认为,好的诗歌应用来表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高远的意志和昂扬向上的气概。正如上文所言:“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气”是贯注在诗词中的血脉,只有血脉畅通,诗词才能有一气呵成,行云流水的意象。
对于养气的重视,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传统。孟子就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十分重视“养气”的作用,除了《养气》一篇专门论述之外,“气”字散落于书中31篇中的81处,如《神思》篇就明确指出:“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8]320文莹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必须用“志高”、“养气”来纠正诗歌中气格卑弱的弊病,他推崇诗文中的“雄豪之气”。在《湘山野录》卷中,记载了“性磊落,豪于诗酒的石延年”的断句,让我们领略到了一股昂扬向上的雄风;记载了慷慨激昂、侠气自任的乖崖公的多条诗文事迹,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大丈夫的豪气。卷上对元厚之诗“九重侍从三明主,四纪乾坤一老臣”,及“过庐都失眼前人”之句更是赞赏有加:“虽向老,而男子雄赡之气殊未衰歇”。可见文莹对豪放之气情有独钟,难怪友人苏舜钦尝称其作曰:“篇篇清雄”。一方面,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气不无关系,宋代实行右文政策,开放了寒门士子进身的通道,士大夫普遍心怀壮志。而庆历时期更是一个士气高昂的时代,义薄云天,气凌霄汉,成为那个时代士人呐喊的最强音。另一方面,随着与一向性格豪放磊落的苏舜钦交往的密切,文莹必然受其诗风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受禅宗平等观念的影响,禅僧自然会生发出自信无求、雄猛奔放的气质。所以,文莹特别钟爱那种“高吟大笑意猖狂,潘阆骑驴出故乡。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1]14267的雄豪之风。
二是反对“西昆体”为代表的典雅华丽的浮艳文风,推崇古文,提倡文风简洁。“西昆体”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是缺乏深厚的内蕴。文莹对宋初文坛流行的这种“雕章丽句”、“徒事藻饰”的文风,多有批判之词,认为是“磔裂雕篆”。《玉壶清话》卷四提到“朱台符所作文字,其雕琢皆类于赋”;卷七也有类似的记载:
文莹至长沙,首访故国马氏天策府,诸学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东野、李宏皋尔。遂得东野诗,浮脆轻艳,皆铅华妩媚,侑一时尊俎尔。其句不过“牡丹宿醉,兰蕙春悲。霞宫日城,剪红铺翠”而已,独《贻汪居士》一篇,庶乎可采,曰:“门在松阴里,山僧几度过。药灵园不大,棋妙子无多。薄雾笼寒径,残风恋绿萝。金乌兼玉兔,年岁奈君何?”又得宏皋杂文十卷,皆胼枝章句,虽龌龊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难也!
文莹评价徐东野的诗为“浮脆轻艳,皆铅华妩媚,侑一时尊俎尔”,“皆胼枝章句,虽龌龊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难也!”可见他对浮艳雕琢、徒事藻绘的文风非常不满。宋初,为反对这种卑弱浮艳的文风,柳开、石介、王禹偁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承传唐代韩愈、柳宗元宗经明道、重散反骈的旨趣,首倡文风复古,开启一代文风。受此影响,文莹亦十分追慕古风,他虽为方外缁流,却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企图用古文来纠正文坛之弊,这在笔记中多有表述:《湘山野录》卷中:“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卷下:“张晦之景,以古学尚气义。”《玉壶清话》卷三:“王昭素,酸枣县人,学古纯直,行高于世。”可以看出,文莹对提倡古文,力振古道的文人是十分歆慕的,好友苏子美亦称他的作品“有古作者气态”。
与“西昆体”雕饰文风相对应,文莹推崇简洁明了的文风,并在笔记写作过程中,实践了这一主张。文莹的语言文字功底很深,评论往往一语中的。在他的笔记中,说明文字简洁明白,议论文字雅洁简朴。对于诗文创作,也是以简为美。《湘山野录》卷中“余顷与凌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一条评价东津寺阁诗:“其语数句,又简而有法”,又如“钱思公镇洛”一条评价师鲁之文:“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体现了文莹对文风的要求,他反对刻意雕琢、繁冗的诗歌,主张诗歌创作简洁明练。在“学僧笺注法音集”条中也有如上记载:“真宗尝以御制《释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诏学僧廿一人于传法院笺注,杨大年充提举注释院事。制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探而笺之,暗碎繁驳将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体本静,动必有变。’其简当若此。”为追求简洁,文莹在笔记著述中多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例如《湘山野录》卷上“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条:
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知润州,治迹无状,浙宪马卿等欲按之,至则陈已先觉。廉按讫,宪车将起,因觞于甘露寺阁,至卒爵,宪目曰:“将注子来郎中处满着。”陈惊起遽拜,宪讶曰:“何谓,何谓!”陈曰:“不敢望满,但得成资保全而去,举族大幸也。”马笑曰:“岂有此事!”既而竟不敢发。
陈中亚凭借一句戏词,使上司最后“竟不敢发”,化解了一场危机。这一条中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惊”、“遽”、“竟”三字,却把陈中亚的机智与上司的惊恐描摹得淋漓尽致。《湘山野录》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崔公谊者,邓州德学生也,累举不第,后竟因舅氏贾魏公荫,补莫州任丘簿。”一个“竟”字,作者的态度便尽显无疑,可以看出文莹对这种不公平待遇是愤愤不平的。
二
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清雅”、“风骨”的审美追求。
首先,他在笔记中多次提到“清雅”、“闲雅”、“风雅”、“博雅”、“和雅”等与“雅”有关的概念,“雅”成为他品评人物诗歌的关键词。《湘山野录》卷上评价陈中亚的药名诗“棋为腊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缩纱裁。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之句,“皆不失风雅”;《湘山野录》卷中:评价安鸿渐的《秋赋》警句“陈王阁上,生几点之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之寒水”为“有才雅”;《玉壶清话》卷一:“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卷三:“折御卿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厖厚,揖让和雅”等等。笔者认为,文莹“尚雅”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这与宋初偃武重文的政策密切相关,文人的地位提高,由“文”而“雅”,实属必然;第二、“雅儒”精神的确立,决定了文学“尚雅”的倾向,宋代雅士大多精神品格求雅,日常生活随俗,品格高雅,自命不凡,达到了诗人精神品格和诗歌艺术品格的圆融统一,使宋诗得以持续发展;第三、这与文莹的生平与交游有密切的关系,他虽然为佛门中人,却“交游尽馆阁名士”,在当时,“忌俗尚雅”是士人的精神倾向,是宋代士大夫的独特的品格。与文莹交游密切的凌叔华,就被称之为“博雅君子”,所以,文莹崇尚风雅,也是不足为奇的。
其次,与“雅”相对应,文莹对于“清”也有独特的爱好。如《湘山野录》卷中:评价王至道之子“器格清粹”;评价时寺阁旧题字“势格清美,无一点俗字。”《湘山野录》卷下“潘阆预谋立秦邸”一条也中提到:
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曰:“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几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渔竿,思入水云寒。”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
《忆余杭》这首词,体现了潘阆诗风自然、平淡的一面,语言通俗,很少雕琢,不同于晚唐五代的柔媚之风。在山水风光的描写中,将士大夫的情怀巧妙地融入其中,给宋初沉寂的词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文莹在笔记中表现出的对于“清诗”的推崇,蕴含着一种对于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的追求。在《玉壶清话》中,这样的记录也有很多。例如:《玉壶清话》卷一评李建中诗“清淡闲暇”,卷七评郑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卷八评郑文宝之诗,“篇篇清绝,不能尽录”。不难理解,文莹作为僧人,对清真的意趣和清新自然的风格有独特的追求。佛经中就往往把清凉世界看作是理想境界,佛教主张清静,要求一尘不染,一念不生。笔者认为,他以清论人,是状其品格清高守志,正直廉洁;以清论诗,则是喜爱至清无隐的清境、旷然天真的意趣、淡泊高雅,不坠浊俗的精神。其实,清美的意识,在当时的士人中十分普遍,他们作诗都追求清新明净的自然意象、清丽雅洁的自然语汇、清新淡泊的自然意境。对他们而言,“清”是一种疏远世事,高雅绝俗、纯净淡白、洒脱旷放、通达旷逸等偏向自由的、个性化的品质。
总而言之,“清”和“雅”向来是不可分割的。“雅”是一种文化追求,“清”则是一种精神形态。清雅的志趣,是自由士人更为实在的生命价值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文莹在笔记中也常常“清雅”并举,如《玉壶清话》卷一评价刘综“敷奏清雅,辞荣秀彻”。其实,文莹追求“清雅”的文学审美倾向,代表了宋初文坛的主流。
再次,文莹笔记中还表现出提倡“风骨”的审美倾向。早在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就指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8]339-340。只有“风清骨峻”之作,才能妩媚动人。同样,文莹认为好的诗歌应该能表现作者的风神远韵。如《玉壶清话》卷五“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一条评张师正武陵赠别之诗“忆昔荆州屡过从,当时心已慕冥鸿。渚宫禅伯唐齐己,淮甸诗豪宋惠崇。老格疏闲松倚涧,清谈萧洒坐生风。史官若觅高僧事,莫把名参伎术中”,及断句“碧嶂孤云冉冉归,解携情绪异常时。余生岁月能多少,此别应难约后期”为“风义见于诗焉”。可见,由诗文作品便可反映作者的风度仪态。又如“杨侍读徽之”一条,对于杨徽之书御屏的十联诗,评价其“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表现了文莹对他的高度赞赏。虽然,杨徽之诗也不脱晚唐窠臼,但却于清俊之中可见峭拔的一面,后来,清代纪昀甚至说在当时诗坛的“一望黄茅白苇之中”,他的诗“如疏花独笑”(《瀛奎律髓刊误》卷四十二)。乾嘉时期诗人谢启昆则以论诗绝句的形式对他的诗表示推崇:“冰瓯雪梳浣清词,学士声名上赤墀。牢落晚年叨宠遇,御屏风写十联诗。”(《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可见文莹评诗之远见卓识。
三
文莹在笔记中,注重考辨搜集前人忽略的作品,考证佚诗,记录残章断句。他的笔记中收录的诗歌大多是文人集中未录的遗诗。这些诗作,正是借助文莹的记载而得以保存流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可见其独到的史家之识。在这类条目中,作者讨论对象或是无名诗人,或是一首无名诗,有些作品也许只有支离破碎的几句,却有很高的价值。例如《湘山野录》卷上所载李白作品“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是除五代《尊前集》所载外,最早记录此诗的著作。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更是将此词推为“百代词典之祖”[9],至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湘山野录》卷中,还考证了“《玉树》歌沉王气终,景阳兵合曙楼空。梧楸远近千家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翻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江山似洛中”之诗是杜牧的《金陵怀古》,为古今学者所重视。另外,记录了少年神童杨亿的断句“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可以增进对杨亿的生平和诗风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类作品的考证,持非常严谨的态度,大多亲历亲闻,多方访求证实,如《湘山野录》卷中:
余顷与凌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谟、吴春卿皆昔师之,素称翰墨之妙。时寺阁有旧题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余,其体类颜而逸,势格清美,无一点俗气。其语数句,又简而有法,云:“杨孜,襄阳人,少以词学名于时,惜哉不归!今死矣,遗其亲于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不忍去。恨不知写者为谁,又不知所题之事。后诘之于襄人,乃杨庶几学士,死数载,弃双亲之殡在香严界佛舍中已廿年。
上述材料说明,文莹是在“诘之于襄人”后,才在笔记中详细记录。又如《续湘山野录》中:“文莹亲于平甫处得花蕊夫人诗词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可见,文莹是怀着实录的精神去记载的,旨在唤起人们对这些被遗忘的作者的重视。由于作者以治史的态度写作笔记,因此书中所记材料的可信度颇高,许多材料还可以补正史之缺。而且,由于其著述的私人性和随意性,决定了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所以,其史学价值颇高。
文莹在严谨考证文学作品的同时,也重视知人论世。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及写作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客观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首先,文莹在笔记作品中,很注意对诗歌人物,背景的介绍,这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欣赏诗歌,对后人考证诗文本意和诗文编年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湘山野录》卷上:“欧阳修顷谪滁州”一条,就详细介绍了欧阳修的传世名作《临江仙》的写作时间和背景:“一同年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曰:‘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孤负曲江花。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霞’”。除此之外,对于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文莹笔记中也有多处体现,如《湘山野录》卷上:
孙集贤冕,天禧中直馆几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节概清直。晚守姑苏,甫及引年,大写一诗于厅壁,诗云:“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寄语姑苏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题毕,拂衣归九华,以清节高操羞百执事之颜。
在这一则材料中,文莹于开头便指出:孙冕是“江南端方之士,节概清直”,接着用他的厅壁诗充分印证了这一论述。最后指出,唯有诗人拥有清高的节操,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可见,文莹评诗是由人品而及诗文。反过来,文莹认为,一个作者的文章风格,也可以反映其性格。《湘山野录》卷中“杨文公由禁林为汝守”条,文莹评价张乖崖文章“其语气劲直,如乖崖之在目”,是由诗品及人品。但是,他也注意到,文品有时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湘山野录》卷中“安鸿渐有滑稽清才”一条就明确的指出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文莹认为安鸿渐有“清才”,有“才雅”,对他的秋赋警句十分的赏识;另一方面也指出:“以凉德尽掩之,然不闻有遗行。”诗歌作品的成就并不能表现一个人的人品,不能“以诗论人”。《续湘山野录》中有一则材料反映了这个问题:
姚嗣宗,关中诗豪,忽绳检,坦然自任。杜祁公帅长安,多裁品人物,谓尹师鲁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姚闻之大喜,曰:“所谓善评我者也。”时天下久撤边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有“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又一绝:“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春昼眠”之句。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既而一庸生张,亦堂堂人,猬髯黑面,顶青巾缁裘,持一诗代刺,摇袖以谒杜公,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扫氛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祁公亦异之,奏补乾佑一尉,而胸中无一物,未几,以赃去任。
身为“关中诗豪”的姚嗣宗,诗风雄豪,诗篇中洋溢着英雄之气,后获得了杜祁公的赏识,得以奏补乾佑一尉,但是,人品却不佳,“胸中无物”,最后“以脏去任”。所以,文莹认为,不能用诗作作为考察人品的标准,同时说明宋代以诗赋取士,存在一定的弊端。
四
作为禅门僧人的文莹自然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特别重视平凡恬淡的平常心,认为真正得道之人的心境,是“闲来石上观流水,欲洗禅衣未有尘”[10]1039,是自然而然的,纯乎天运的自在自为的心境,与这种心境相契合,文莹的诗句亦是超凡脱俗,清新自然,连一向不喜浮屠的欧阳修对文莹都评价甚高,高度赞扬其“平淡之风”可与杜甫相媲美。《湘山野录》卷上载,欧公曾蒙诗见送,有“孤闲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间著书就,应寄日边来”之句。在厉鄂的《宋诗纪事》中,保存了他的一首诗《宝积寺小雨》“老木垂绀发,野花翻曲尘。明霞送孤鹜,僻路少双鳞。天近易得雨,洞深无早春。山祗认来客,曾是洞中真”[11]2180,对于山居生活的描写,富有诗情画意,格调十分清新优美,充满了情思韵致,诗中的物象飘逸空灵,显示了淡泊悠闲的心境。禅宗提倡山水真如,水月相忘,对于自然静谧的自然景物,风月山水的美好意象,文莹可谓情有独钟。在他的笔记中,不论是《湘山野录》卷中记载慧崇的诗歌“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还是《湘山野录》卷下摘录石昌言的赠别诗歌“古意为师复,清风寻我来,幽阴竹轩下,重约月明开”,都表现了一颗纯明无染的素心,一种返于自然、至味淡泊的悟心,一种“但自无事,自然安乐,任运天真,随缘自在”[10]960的情趣。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受到禅宗“因果报应”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的影响,文莹笔记著作中的文学思想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其中记录了一些“诗谶”的例子。所谓“诗谶”,其中有吉兆,有凶兆,但文莹记载的绝大多数诗谶是凶兆,而这类作为凶兆的诗谶主要集中的是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谶死亡,例如《湘山野录》卷中:
潘佑事江南,既获用,恃恩乱政,谮不附己者,颇为时患。以后主好古重农,因请稍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夺田者纷纷于州县。又按《周礼》造民籍,旷土皆使树桑,民间舟车、碓磑、箱箧、环钏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于星火,吏胥为奸,百姓大挠,几聚而为乱。后主寤,急命罢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态。一日晨妆,佑潜窥于鉴台,其面落鉴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恶己,因弃之。佑方丱,未入学,已能文,命笔题于壁曰:“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秪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果当其岁诛之。
此例提到了潘佑少年的一首题壁诗,中间有一句“谪向人间三十六”,后来潘佑果然于三十六岁就去世了。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从理性的角度看,所谓的“诗谶”是牵强附会,故作神秘的,把偶合的诗句当成宿命的解释,为的是追求奇特的说诗效果。还有一种“诗谶”则是谶仕途偃蹇。例如:《湘山野录》卷下:
丁晋公释褐授饶倅,同年白稹为判官。稹一日以片幅假缗于公,云:“为一故人至,欲具飱,举箧无一物堪质,奉假青蚨五环,不宣。稹白谓之同年。”晋公笑曰:“是绐我也。榜下新婚,京国富室,岂无半千质具邪?惧余见挽,固矫之尔。”于简尾立书一阕,戏答曰:“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太乖。五百青蚨两家阙,白洪崖打赤洪崖。”时已兆朱崖之谶。
丁谓曾经在朝中,可谓显赫一时,后因为逞才扬己,卷入政治斗争中,被贬朱崖,终成身累。文莹在此把戏言当成谶语,实属无稽之谈。追根究底,这些谶语都只是无意识的巧合,反映的是古代文人深层的心态,是他们对于生命与偃蹇的关切。只是经过说诗者的撮合,才引起了对此的关注和重视。文莹在笔记中流露出的这些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通过它们却可以让我们窥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民俗风情。
总体而言,文莹笔记的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涉及到了宋初政治经济、军国大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宋代社会文化思潮,进而让我们一览宋初的时代风貌。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学思想,虽不是系统的论述,但不乏自见,思维活跃、议论精辟,对于研究宋代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与意义。笔者在此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希望可以引起广大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5]郑毅夫.郧溪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
[6]刘挚.忠肃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
[7]洪迈.容斋随笔[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8]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1.
[10]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1]厉鄂.宋诗纪事[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