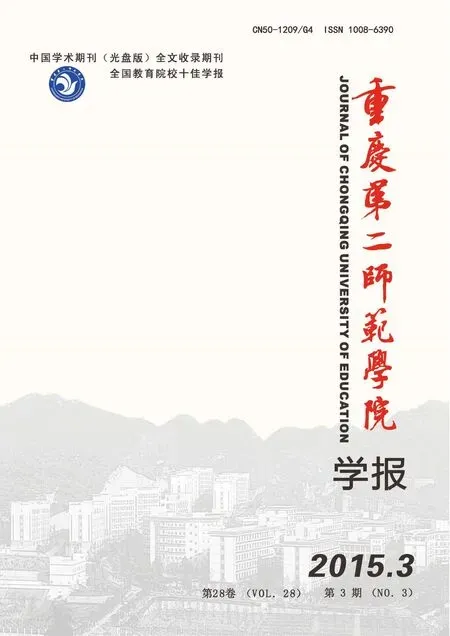虚构、非理性和迷宫世界的探索者——博尔赫斯创作技巧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影响研究
唐 希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虚构、非理性和迷宫世界的探索者
——博尔赫斯创作技巧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影响研究
唐希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博尔赫斯的创作风格和小说表现技巧在对拉美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实验亦发生着示范滋润作用。博尔赫斯在其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想象力、叙事的非逻辑性和迷宫式结构,都成为中国当代的先锋作家和后现代风格追随者们效仿的对象。这些具有后现代创新精神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小说实验中,彻底打破文学思想上的禁锢,用从博尔赫斯等后现代作家那里借鉴的小说创作元素,并以自己对这些文学元素的独特理解,开拓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后现代创作道路。
关键词:博尔赫斯;虚构;非理性;迷宫;影响
作者简介:唐希(1966-),女,四川成都人,硕士,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识码:A
文章编号:编号:1008-6390(2015)03-0057-04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L.Borges 1899-1986)在中国后现代创作中的影响与声望,丝毫不亚于其在拉美。在拉美,人们普遍将他称作西方现代派渗入拉丁美洲的桥梁。他引介并借鉴了卡夫卡和福克纳的创作风格,将西方后现代的复杂技巧与拉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苦难的历史记忆融合在一起,使自己登上拉美后现代文学流派的“先驱”和“鼻祖”的神坛,有人甚至将他称作拉美“后现代小说之父”。在中国,他和卡夫卡、罗伯格里耶等被当代后现代作家特别是先锋作家视为文学创作的实验宗师。中国的先锋作家从他那种有意颠倒作品中的时序,打破空间界限,把潜意识和现实混淆起来的后现代技法中,找到了将中国的现实生活与西方后现代技巧结合起来的最佳途径:他们通过“挪用”从西方后现代技巧和博尔赫斯那里学来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在古老的文明中的丰富感受与记忆。
我们研究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创作技巧对中国后现代创作的影响,从后现代的精神文化逻辑来探索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探讨博尔赫斯从哲人之言、经典故事、历史事件中虚构出的远离社会现实的后现代文本,特别是从其典型的后现代式的虚构性、非逻辑性和迷宫游戏的创作元素中,分析它们如何对中国当代的后现代小说产生积极的影响的。
一、“本质上是实在的虚假事情”
在关于文学创作的虚构性问题上,有人曾认为博尔赫斯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源于作家独特的想象力,他凭借着超越他人的想象力,虚构出堪称后现代文学经典的短篇小说。然而,我们从分析中发现,博尔赫斯的虚构与通常意义上的虚构是有本质区别的。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更看重文学的真实性,即用虚构来构建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真实感;而相对于现代主义,又因现代主义过分看重用虚构来张扬个性,因此依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摒弃。博尔赫斯主张虚构,但是他希望通过漫无边际的想象来揭示世界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他甚至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取名为《虚构集》。在这部文集中,作家收录了虚构文学的代表作《小径分岔的花园》,以及另一部从名字上就能猜出其用意的《杜撰集》。人们从博尔赫斯的虚构、杜撰和交叉小径这种极不确定的后现代思想中,领会和感悟到作家对文学虚假性的认识态度。在博尔赫斯看来,绝对真实和客观的现实内容是不存在的,多样性、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才是真实、客观和现
实的。因此,作家创作中的任何虚构活动,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多样可能性。
从博尔赫斯的小说文本中,人们不难发现,他所谓虚构的真实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虚构已有的文本。这是因为,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大都不是取材于现实,也很少使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它又并非凭空虚构,它是作家借助过人的想象力,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改编、加工和巧妙借用而“创作”出来的新的文本。这种凭借想象力的虚构现象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得到鲜明地体现。小说讲述一战中的间谍故事,但作家却从中引申出间谍余琛家族的中国故事。就这个中国故事本身而言,显然是想象和杜撰出来的。博尔赫斯戏称自己的小说是“抄袭”的结果,是将本质上实在的虚假事情重新组合在一起。二是用虚构进行拼贴。拼贴是博尔赫斯使用最多的后现代技巧。《小径分岔的花园》本身就是拼贴的产物。间谍故事和中国故事的两个片段,通过间谍余琛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生硬粘贴起来的虚构故事,显然只能用博尔赫斯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做出解释。三是借助虚构打乱时序。作家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所表现出来的时序是“正在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时间的网”。在《巴别图书馆》中,博尔赫斯表现出他对知识、世界和人生的另一种认知,世界万物始终都是循环往复的,它们没有既定的顺序,但又互相接近,隔断,交叉;它们互不相干,但是其中却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作家莫言同样是想象力丰富的大师,他在西方和拉美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启发下,激发出自己独有的世界观和领域观。他借助从这种启发中所获得的感悟,彻底解放了“自己的感觉、体验、想象乃至语言的叙述”。从他充斥着后现代探索精神的小说《透明的胡萝卜》《红蝗》《食草家族》等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作家想象力恣意驰骋的宏伟场景。作家在他所构筑的高密东北乡的想象空间里,开掘出“更能体现藏污纳垢、有容乃大、贫穷艰难却生机勃勃的民间本相”[1]。他在最具后现代“怪诞”意味的小说《十三步》中,将奇异的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小说中错乱的时空,显而易见的虚构性,杂糅起来的一个个荒诞的故事,如物理老师方富贵死而复活,殡仪馆整容师李玉婵把人的脂肪拿去喂野兽,方富贵与同事张赤球改换容颜等情节,展示出作者令人瞠目的虚构功力。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虚构的闹鬼故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客观存在的虚假事情,他声称自己就“不下十回亲自看见乡人用桃条抽打附着鬼魂的人身上的簸箕”[2]。作家认为这种虚假的故事内容,并不能表明作家不是写实。王小波力求从虚构走向精神上的真实,以之突破现实原则的羁绊。他秉持好小说都是好神话的信条,用虚构出来的童话故事再现贫困时代的诗意还乡。在小说《三十而立》中,作家把世界虚构成授精的场所,他形容自己走在大街上,汇入滚滚的人流,“我想起三十三年前,我从我爸爸那儿出来,身边也有这么许多人,那一回我急急忙忙奔向前去。在十亿同胞中抢了头名,这才从微生物长成一条大汉”[3],这种大胆的想象和虚构的故事情节,表现出作家对外部力量强加于己的身份而压抑地活在世上的怨愤情绪。
二、“我们的习俗充满了偶然性”
博尔赫斯推崇非理性和偶然性,欣赏卡夫卡等人反逻辑的写作方法,并将这种偶然性与他的时空现象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理解博尔赫斯关于文学反映生活的偶然性主张,必须结合到他的时间观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如他在小说《阿莱夫》中曾经这样解释他对偶然性的认识:阿莱夫在希伯来字母中是第一个字母,是事物中的一个点,一个包罗万象的点,它小到两三个厘米,像个闪烁的小圆球,人们通过它能够看到整个世界,“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了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4]在这里,作家希望说明事物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从一面变为两面,再由两面变为多面,然后变为并非此种事物。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偶然性,它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是任何理性所回答不了的问题。因此,在小说写作中使用这样的非逻辑性推理,正是小说应该表现出来的认识世界的基本形态。博尔赫斯《偶然集》中的作品就对这种偶然性现象进行了讴歌,其中又以《巴比伦彩票》最为典型。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强调巴比伦人“尊重偶然性的决定……我们的习俗充满了偶然性”[5]。作家的经典作品《小径分岔的花园》也处处表现出偶然性的故事内容,如马登发现余琛的间谍活动,阿尔贝的名字与英军炮兵阵地的地名相同,余琛枪杀阿尔贝,德国飞机轰炸英军炮兵阵地等情节与场面,仿佛一切都不具有逻辑性,而这种偶然现象的巧妙堆积,恰恰说明了这一切都是作家的有意安排。《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是博尔赫斯的小说名篇,作家借特隆人之口,表达自己对时空概念独有的理解,如特隆人否定空间的存在,认为“宇宙是一系列思维过程,不在空间展开,而是在时间中延续”,“世界并不是物体在空间的汇集,而是一系列杂七杂八互不相信的行为”[4],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作家对偶然性和虚构性的强化,它使被虚构的事物更加模糊和变形,更加与理性的认识相对立。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对偶然性、非理性和反逻辑的渲染,体现了作家文学创作的认知模式,同时也反映出博尔赫斯在创作中坚守超凡脱俗,视一切皆为虚无和非理性的处世观点。
在中国的后现代作家当中,王小波就有过这样的表述,他在《三十而立》中写道:“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的本身。”在这里,作家保持了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他认为事物相互之间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现象,不能用理性的逻辑思维去解释。因此,这样的描写与博尔赫斯的理论异曲同工,后者描写关于空间中的事物都是杂七杂八存在着的。莫言在建立他自己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时候,也使用了类似博尔赫斯式的想象、改编和白描的艺术手法。人们在他的小说《檀香刑》中所看到的民间传说、巫术、方言、谚语,眉娘的秋千表演,叫花子节上的事件描述,斗须、比脚场面的刻画,孙丙号召乡人喝符水的情节,赵甲行刑前举行的仪式等,都像是随手拈来。然而,这一切却并非符合逻辑的理性行为,它似真似假,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偶然性混杂状态。马原的小说特别是描写西藏高原地区风情的小说,其中的故事情节链条似乎也都是没有联系的事实与事件,如受崇拜的图腾、来自远古的神话、当下盛行的天葬习俗、寺庙中保存下来的壁画、古王朝遗留下来的旧址、人们相互之间的乱伦行为乃至狩猎事件等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形象要素大都充斥着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因素,它不仅如作家所言,这些事实、事件之间的联系是空白的、断裂的,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就像是散片一样,类似杂陈的现象片段。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坚持以梦境为原型,写了一个年代久远的朝代,一个可疑为史官的叙述人,和依次所记录的丞相惠的三个梦境,而三个梦相互指涉又相互缠绕,相互延续又相互撕裂,丞相惠不停地做梦又不停地回忆做过的梦,从而将梦境这种最具偶然性的非理性的现象推向极端。
三、“迷宫是结构小说的理想”
美国后现代学者哈桑认为,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是后现代最重要的创作原则。而迷宫现象又是不确定性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博尔赫斯强调迷宫在后现代小说中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结构小说最为理想的状态。他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借角色之口,宣称写小说和建造迷宫是一回事,其实他是要用迷宫手法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曾这样告诉过喜欢其作品的人,“我不想教导任何人;但是我想讲,讲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故事、神话,讲一首动人的诗,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我的目的是抒发感情”[6]。如果我们结合博尔赫斯的作品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博尔赫斯并不想把自己最真实的感情简单直白地表达出来,他使用迷宫形式来编写故事,为的是用复杂的小说形式来表现他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博尔赫斯建造迷宫,需要把他的迷宫现象与游戏和梦境联系起来理解。就前者而言,作家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将真实的故事与虚拟的故事混杂起来,利用虚构和想象编写出人们永远也无法考证的虚假故事,用表面真实其实虚假的故事来引出另外一个表面虚假,其实在作家看来是真实的故事,它们像圈套一样,使读者偏离故事的真正方向。在这里,我们说作家所构建的迷宫如果还带有游戏的性质,那么他在《圆形废墟》中,则是利用梦境来构建另外一种类型或者是更为虚幻的迷宫。小说中,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和周围的农夫在圆形废墟中做梦,小说的故事也由此在梦境中展开。作家在小说中表白自己自始至终是用神话和梦的形式在进行思考,用“梦”来创造世界和历史。因为,在作家看来,“世界本来就是迷宫,没有必要再建一座”[7]。写小说也是如此,它是还原世界迷宫一样的原貌。“现实是一连串梦的结果”,人类的历史便是这样发展的。作家将其对世界的解释和对梦的解析合并在一起,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所做的一个虚幻的梦,在这个梦中充斥着大量的偶然性因素,世人生活在这个由梦所组成的世界里,就像生活在一个迷宫中一样。大量不可知的、偶然性的和虚幻的因素充斥其中。作家对梦境的理解,确实像迷一样,很难让人把握其创作的真正意图。
对博尔赫斯迷宫式小说的理解,有评论家认为,它是作家刻意在空间场景上的安排。然而,仅此还不够,博尔赫斯亦是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在空间和时间上毫无节度地遨游。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作家对特隆人的时空观做出独特的解读,他们认为宇宙是由一系列的思维过程组成的,宇宙和世界不在空间中展开,而是在时间中的延续;且宇宙和世界本身也不是空间,更不具有物质性。因此,作家在构建空间上的迷宫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时间迷宫的建造过程中。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作家从不提时间,但却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时间的主题。其实,关于时间的概念是博尔赫斯最热衷的话题,他在许多作品中都谈论了时间的存在、时间的永恒、时间的哲学意义,以及人与时间的关系。而这些,作家又大都是以迷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学习和借鉴博尔赫斯迷宫手法的人不少,格非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在小说《迷舟》中直接使用迷宫式的名字,并在其中有意安排出一种谜团式的故事。其中旅长萧被杀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阿伯特的死一样,究竟是为了传送情报还是其他,作品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揣度,使人物的命运更加沾染上一层不确定性的色彩。在《褐色鸟群》中,作家将想象、现实和时间上的思考,与不断循环着的叙事结合起来,释放出一团难解的迷雾。孙甘露在《访问梦境》中以与博尔赫斯相类似的手法描写梦境,用做梦来展开一个个的趣闻轶事,并将梦中的各个偶然性片段串联起来,从而使这种散乱的梦境变得更加不确定。在《请女人猜谜》中,作家采用叙述另外一部遗失了的小说《眺望时间消逝》的方式,使文本的叙事内容发生交叉,造成了所讲述的故事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刻意营造出了一种虚幻的叙事效果。残雪80年代的作品通常使用梦幻与现实相交替的手法,亦真亦幻,表现出晦涩难懂的谜团效应。她的小说《温柔的编织工》取材《伊利亚特》中海伦编织壁毯的故事,以之来表现作家关于对小说迷宫结构的实验。作家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随意转换,给人一种含糊、迷茫和不知所措的阅读感受。而这一类的作品,由于没有明确的主题表达,所指为能指所取代,在接近写实的叙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大都是荒诞的故事内容。而作家借助想象、虚构手法所造成的故事叙事的空缺、错位、中断等,又使故事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充斥着偶然性、非理性和非逻辑性因素。它就像一堆乱麻,理不清头绪,让人感觉莫名其妙。这与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也将想象、虚构、偶然性、非逻辑性和非理性的后现代因素发挥到极致。这一切,正好印证了博尔赫斯在《死亡与罗盘》中所宣称的,“我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
博尔赫斯的艺术技巧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体现在虚构和想象、非逻辑性和偶然性,以及迷宫结构方面。我们在中国作家所进行的后现代小说的创作实验中,亦能轻易地找到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元素。可以说,博尔赫斯帮助中国当代作家找到了将西方后现代的复杂技巧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最佳路径,同时也为中国的小说创作长期以来重内容轻形式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一次新的启蒙,激发了中国作家突破传统文学固有模式的创作欲望,给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刘志荣.从“实感经验”出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68.
[2]莫言,等.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M].邱华栋,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43-44.
[3]廿一行.王小波十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5.
[4]李德恩.拉美文学流派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180.182.
[5]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林之木,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107-108.
[6]徐曙玉,边国恩.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11.
[7]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众议,等,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174.
[责任编辑亦筱]
Explorer of fiction, illogicality and labyrinth world: Jorge Luis Borges writing techniques’ influence on Chinese postmodern novelsby TANG Xi p.57
The writing style and skills of Jorge Luis Borges expressed in his novels not onl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but als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specially for 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Period. In addition, Borges also has been a role model of the vanguard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other followers with postmodernity, for the unique imagination, illogical narration and a labyrinth of structure in his novels. These Chinese writers with postmodernity and innovation completely break the literature thought block in their own novels. They make use of the writing skills referring from Borges and other postmodern writers, combining with their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nd explore a postmodern writing path with Chinese style.
Key words: Jorge Luis Borges; fiction; illogicality; labyrinth;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