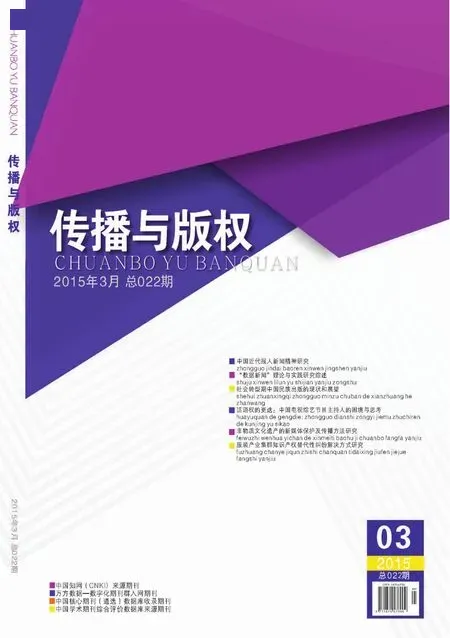特稿与新新闻主义
崔 曜
特稿与新新闻主义
崔 曜
[摘要]新新闻主义以文学手法描写新闻而著称,影响了新闻特稿的写作。但与此同时,新闻必须坚持其真实性,新新闻才能继续体现其对特稿写作的价值。
[关键词]特稿;新闻写作;新新闻主义
[作者]崔曜,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又称新新闻,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以通过文学手法描写新闻而著称。新新闻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新闻界,当时的报业大亨普利策为了迎合读者需求,扩大报纸销量,发起了“黄色新闻”大战,其中某些手法被视为新新闻主义的雏形。如注重细节与场景描写,通过丰富而又生动的细节不遗余力地刻画人物,透过细致变换的场景把故事铺展开来。新新闻主义的集大成者汤姆·沃尔夫在其著作《新新闻主义》一书中说明新新闻具有两大特质,即新闻当事人直接的心理描写和详尽对话记录,以及追求新闻的故事化、娱乐化、戏剧化。研究美国新闻史的学者认为,新新闻主义曾风靡美国新闻界,诞生如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拉里•金(Larry L。King)等一批善于运用新新闻手法的高手,作品大多发表在《纽约客》《乡村之声》以及《老爷》等杂志上。进入20世纪后新新闻主义饱受批评。同时代的记者和编辑指责新新闻主义动摇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让读者难以辨清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新新闻主义至此陷入沉寂,但其风格并未消失,只是以其他形式改头换面而已,如“文学性新闻”“非虚构写作”(相关系列丛书已在国内出版)。90年代新新闻主义呈现复兴之势,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开设“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研究生课程,标志着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20世纪重要的新闻理论流派被学界正式接纳。
一、新新闻主义与特稿关系
特稿(feature)正式被美国新闻界所认可始于1979年,来自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的记者丹尼尔•富兰克林(Jon Daniel Franklin)运用小说手法描述了一场脑部手术。这篇题为《凯利太太的妖怪》(Mrs。Kelly's Monster)得到了普利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赢得了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Pulitzer Prize for Feature Writing)。
美国学者认为“feature 一词对记者而言有多种意义。它是指以人情味为基础的新闻报道——那些不适合硬新闻的严格标准的报道。在我国学术界,更倾向于从写作方式阐释其意义,并将其与新新闻理论联系起来。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一书中提到,“新新闻主义其实为新闻特写与通讯体裁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借鉴范式,甚至可以说提供了变异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关于特稿的定义应该置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美国特稿与美国的媒介环境息息相关,特稿的出现迎合了当时大众化报刊时期的需求,它以人情味为基础,追求趣味性报道。中国特稿的源头在于纪实文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大批优秀记者的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到80年代穆青同志的通讯作品《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和北京青年报的“三色报道”等。
特稿受新新闻主义影响,大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新闻性,特稿是新型的新闻报道体裁,具备新闻所需的基本要素,从新闻性出发它要求稿件具备真实性与时效性。第二是故事性,这一点也是特稿区别于一般稿件最显著的特点。新闻特稿要求拥有深度和广度,细腻的描绘,曲折动人的情节,生动详尽的叙述,从故事性角度讲特稿借鉴了某些文学手法,是具有可读性、主题鲜明、拥有高度的文学价值特点的新闻报道。第三是深度性,新闻特稿之特还在于文本的信息容量大,记者在信息海洋中呈现出对新闻事件的多角度解读,挖掘事实背后的真相。
二、新新闻主义在特稿中的运用
特稿应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与文学性,这句话出自普利策特稿奖的官方诠释“prime consideration to high literary quality and originality”。这样的标准是模糊的,文学性与原创性的外延、内涵、相互的界限在哪里?目前暂无权威的解释,笔者只能从已成文的作品中浅谈自己的理解。文学性要求特稿首先要讲好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必然包含了趣味性和戏剧性两大元素。新华网特稿《带上儿女上十八大》一文讲述了两名十八大
代表一边开会一边照顾襁褓中的孩子。采写特稿时比普通稿件有更高的要求,记者需要在万千素材中找到最能体现人文关怀的足以打动读者的元素。代表蒋敏是当年抗震救灾先进人物,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第一个孩子,陪伴在她身边的是第二个孩子。这个故事没有爆炸性的元素,它平淡的表面下却蕴藏了以人为本的观念,它仍不失为一则好故事。
这篇特稿看似平淡无奇,却不能讲它没有戏剧性。戏剧性也分两种,第一种是显性的戏剧冲突,它指向社会或人生中的直接矛盾,直面生死,如俄狄浦斯弑母,哈姆雷特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发问。显性的戏剧冲突较多出现在西方的特稿中,如开头提到的《凯利太太的妖怪》报道一位医生为一位患脑瘤57年的妇女开刀,却因手术失败不幸逝去的故事。西方读者喜欢显性的戏剧冲突,很大程度来源于他们历史文化中所积淀的悲剧审美心理。他们认为悲剧所包含的戏剧冲突有正面的效果,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有益于人的心理健康,使人在受感动的同时达到伦理教育目的;美国新闻学者也认为媒介有“减压阀”的作用,通过新闻报道受众能分享他人的欢乐或是悲伤,进而缓解内心压力。中国的特稿不是没有戏剧冲突,只是更多时候表现为隐形冲突,涉及新闻人物性格、价值观等认知层面上的冲突。上文中蒋敏既是大会代表,也是一个未满周岁孩子的母亲,作为代表她要尽职尽责,参政议政;作为母亲她又要分身照顾幼子,人物内心的矛盾也就呼之欲出。
特稿应用丰富的细节展现人性的多维度。对细节的精致追求是特稿不同于消息的重要特点,可以讲细节的质量决定特稿的质量。但细节并不是采访中随处可得的无用信息,细节必须是能铺展主题,调动读者情绪,增加文本信息量。在第90届普利策获奖作品《最后的敬礼》(王卓芬译,原载晶报内刊《撇捺》2006年第3期)讲述了一位阵亡的伊战士兵给他的家庭所带来的创伤。原文如下:“他在动。”她说,“过来感觉一下,他在动。”她的两个好朋友从柔软的皮沙发上向前倾了倾身子,把她们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其中一个说。外面飞机引擎的呜呜声越来越响。这段描写发生于刚丧偶的孕妇与她朋友之间的对话。这样的细节描写是需要设定的,记者在采访之前必须有意识需求这样打动人心的细节。孩子还未出生便失去了父亲,对母亲而言孩子是她的精神支柱,胎儿的跳动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再看这段描述的转折也不乏高明之处,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转场,借鉴了电影语言的蒙太奇技巧,将叙事焦点转换到运送丈夫遗体的军机上。“凯瑟琳紧紧捏着美国士兵身份识别牌,更紧地把识别牌攥在手里,一条项链把这些识别牌和她丈夫的结婚戒指串在一起。”动作是叙事的核心,特稿用外在动作描写刻画了新闻人物内在的心理处境。记者笔力稳准,力度逐层加之,且无人为的煽情,对读者情感的拿捏可谓收放自如。美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艾略特在《哈姆莱特及其问题》中提到:“通过艺术形式表现情绪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这样,当获得了与感性经验相应的外界事实时,情绪就立即被唤起了。”大多特稿都直接或间接印证这句名言,细节被融入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之中,对场景有关的人物、事件细致地描绘建立起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桥梁。
三、结语
特稿受新新闻主义影响不假,但无论以往还是当下,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新闻的真实性必须坚持。新新闻主义借鉴某些文学手法,还原新闻发生时的某个情景,使读者更形象更深入地了解事实。不过事实不能虚构,这是特稿与文学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只有走出新新闻理论的误区,才能认识到新新闻对特稿写作的价值,避免重蹈西方黄色新闻的覆辙。
【参考文献】
[1]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建国.新闻英语写作从实例到实践[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3]王冲.新媒体环境下特稿生产理念与技术变革[J].新闻与写作,2013(11).
[4]毛家武.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的悲剧报道与悲剧审美[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0(6).
[5]甘莎.新新闻主义视域下中国特稿的探索实践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