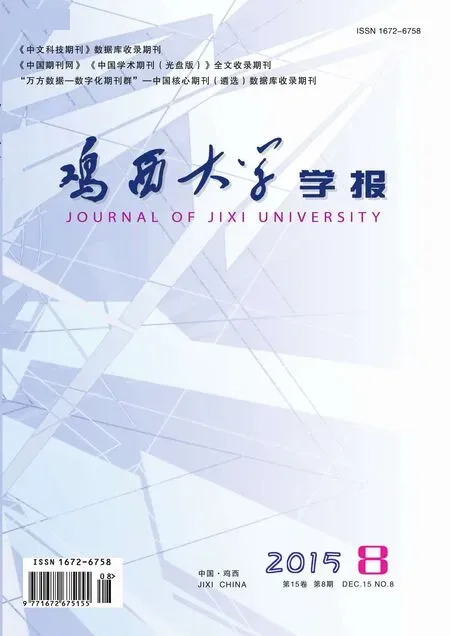原型理论视阈下《我弥留之际》中人物形象解析
周洁,王智音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原型理论视阈下《我弥留之际》中人物形象解析
周洁,王智音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荣格的原型理论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内容,通过运用原型理论对福克纳作品《我弥留之际》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埃斯、朱艾尔和艾迪进行解析,揭示出其人格特征中存在的两种主要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这两种原型在分别诠释了故事中不同人物的狭隘、自抑、扭曲的心路历程的同时,也为本德仑一家在艰难的送葬历程中表现出的种种荒诞行为进行了阐释。
原型理论;《我弥留之际》;阴影;人格面具
一 引言
威廉·福克纳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美国作家,南方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我弥留之际》作为福克纳创作生涯早期的一部实验性作品,被誉为福克纳最好的小说之一,并为他带来了国际性声誉。不同于其“约克纳帕托法世系”系列小说中关注的南方贵族家庭,这部著作描述的是南方一个下层农民家庭——本德仑一家的生活。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讲述的是本德仑家的女主人艾迪去世后,家庭成员依照她的遗愿把她的遗体送回家乡杰弗森安葬的故事。旅程中每位家庭成员都怀揣着自己的秘密,随着时而平静时而狂乱的内心世界自说自话。途中他们不但遭遇了水与火的考验,还经历了情感上的悲痛与失败。福克纳运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如内心独白、无序时空、多样叙述视角等等来展现本德仑一家混乱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折射出现代人精神上的异形与荒诞。而送葬途中本德仑一家表现出的种种人格特征正符合荣格集体潜意识理论中的普遍存在于人类意识里的原型概念。
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心理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荣格在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革命性地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学说。他认为人的心灵由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部分组成。“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了的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1]原型即一种本原的模型,来源于人类的心灵底层,是人类通过遗传从祖先那继承而来的一种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普遍存在,对个体的幻想、情感、思维等种种心理活动起着一种看不见的影响和规范。原型在人的一生中很难被意识到,只有通过后天的途径才有可能为意识所知。原型的种类纷繁复杂,其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是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以及自性。
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刻意在公开场合展现出的希望他人接受的人格特征,目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相对人格面具而言,阴影位于人格的深层,是和社会的价值观所抵触的或未开化的、不发达的人格部分,也是个体心灵中最阴暗、最隐秘的内容。另外,荣格认为不管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都蛰伏着一个异性形象,也就是说人类的心理是双性的。但通常这种双性的心理特征是潜意识的,个体通常只会在睡梦中才会显露出来或投射到生活中其他人身上。荣格把这种男性自我中的女性原型称为阿尼玛,把女性自我中的男性原型称为阿尼姆斯。自性则是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心原型,也是最重要的原型,起着组织、协调心灵中的各个部分以达到人格平衡和统一的作用。下文将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从人格面具和阴影两个角度对《我弥留之际》中人物的人格特征和行为进行解析。
二 以“人格面具”审视埃斯及朱艾尔
人格面具处于原型的表层,协调着个人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个人在外部环境和公开场合中刻意表现出的人格特征。由此而言,人格面具往往并不是个人具体、真实的人格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个体通过“面具”展示出的自我只是希望外界接受的自我的伪装。荣格认为,个体若想与自我保持和谐一致的统一关系,实现心理上的成熟并
达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必须拥有一个灵活多样,富有弹性的人格面具。而《我弥留之际》中,父亲埃斯的人格特质显然没有达到这种个体与自我的和谐一致,他表现出的人格面具虚假而又缺乏弹性。
表面看来,埃斯在妻子艾迪去世后,一直恪守着自己对她的承诺,坚持将她的遗体送回家乡杰弗森安葬。他在周围乡邻面前表现出的人格面具是守诺、重情、自律的好丈夫形象。从艾迪去世那一刻起他便筹划并开始了漫长的送葬历程。途中,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多次拒绝了乡邻的好心帮助,“多谢你,但我明白这会给你添许多麻烦”。[2]当本德仑一家的送葬队伍遭遇了洪水、翻车和受伤等一系列挫折时,埃斯在与别人的对话中亦一再的标榜自己,“这真是一场灾难,但我并未因此责怪她”。[2]“现在她一心企盼这件事,我已经对她做出承诺了”。[2]然而埃斯刻意表现出的这种人格特征是虚假、僵化的,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一直在强调自己做出的牺牲,然而周围的人似乎并未全盘接受他的这一层社会面具。他在整个送葬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将他潜意识里的虚伪和自私表现得淋漓尽致。
埃斯本身就是一个虚伪、吝啬又自私的人,他虽然竭力想表现出恪守妻子遗愿的好丈夫形象,但艾迪病重不舍得花钱请医生的人亦是他。在妻子弥留之际还为了赚三块钱把儿子特尔和朱艾尔打发出去干活,活生生表现出了一副守财奴的嘴脸。送葬途中虽口口声声念叨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可在儿子女儿都拼尽全力搬运棺材过河时,埃斯只是事不关己的立在一旁“行注目礼”。虽然一直对向他伸出援手的乡邻说着“给我的孩子点吃的就好”,可当长子开什因抢救落水的棺材受伤被砸断腿时,为了不花钱请医生,埃斯居然荒唐地买了一毛钱的水泥给他固定伤腿,致使开什整条腿发生病变,无法行走。他表面上振振有词地关心大家,可是他从始至终心中顾念的只有自己。从出发起就一直惦记着回来后给自己换副假牙,“我能装上假牙了,这也算是补偿我了”。[2]埃斯一直在用伪善的措辞来催眠安慰自己不负责任的逃避。所以才会在刚安葬完安迪就迫不及待地装上了假牙,并带回来一位“鸭子样的女人”做下一任本德仑太太,洋洋得意地认为这些是对自己所受“苦难”的补偿。埃斯的人格面具企图表现出一副好父亲的模样,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关心过自己几个孩子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甚至对特尔被抓进精神病院,朱艾尔和杜威·德尔推波助澜的行为亦不发一言,听之任之。自认为在人前表现出的这种伪善面具足以让人折服,殊不知其骨子里的自私、可鄙是这种外在虚假、僵化的人格特征所无法隐藏的。他的送葬“义举”并未在乡邻中留下任何口碑,于人们的印象中仅存一场荒唐的闹剧而已。
与埃斯伪善的人格面具不同,三子朱艾尔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直都是冷漠、疏离而又暴躁的人格特征。顶着艾迪与本地牧师私通的私生子头衔,朱艾尔潜意识里对自己的身份极度自卑,加之在缺乏爱的家庭环境中无法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他每一天都备受煎熬。同埃斯一样,朱艾尔的人格面具并未调节好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所表现出的一直都是自我的孤傲和对外部世界的脱离。对身边的人的行为总是充满了不屑和怨恨,“让我把石子扔下山去,砸他们的脸、牙齿还有其他的地方”。[2]
然而,朱艾尔在送葬旅途中的行为与其冷漠、暴躁的外在人格特征并不一致。送葬途中,虽然他一直坚持不与众人为伍,一个人冷冷清清的骑着马走在一旁。可当横渡大河、马车侧翻、棺材落水的时候,却又奋不顾身地一次又一次跳下河去帮助开什守住母亲的棺材,并坚持不懈地在湍急的水流中为开什打捞他最珍视的工具箱。他的种种行为与他表露在外的冷漠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尽管对家人一直表现出的都是不耐烦和厌倦,甚至还伙同杜威·德尔一起将特尔送进了精神病院,但在危急时刻朱艾尔却仍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本德仑一家在横渡大河的时候失去了拉车的骡子,带着湿漉漉的棺材尴尬地搁浅在了路上无法前行。埃斯提出用朱艾尔千辛万苦打工赚钱买来的爱马换取两头骡子,尽管心中万般不舍,朱艾尔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就是这样一个戴着冷傲面具的朱艾尔,用最真的感情和最真实的自己活在荒诞混乱的世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这个毫无爱意温暖可言的家的爱与恨。
三 以“阴影”诠释艾迪
相对于人格面具而言,阴影位于人格的深层,属于人格中最黑暗的原型,是那些隐藏起来的、被压抑下去的东西,“阴影是与社会的价值观所抵触的或未开化的、不发达的人格部分,是心灵中最阴暗、最深入、最隐秘的内容,它赋予人一种激烈的、挑衅的和暴力的倾向”。[3]阴影是本性中的原始部分。在个体潜意识的众多原型中,阴影原型是最强大、最危险的,也容纳着人的最基本的动物性,是人格中最卑劣的部分。荣格认为人身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存在于阴影之中,所以人若要避免邪恶,就必须压抑和排斥阴影中的兽性一面。然而,阴影不会轻易被征服。人格中被抑制和压抑的阴影只会暂时退隐到无意识之中,并伺机进行反扑。阴影一旦进行反扑或突破意识的限制,就会导致人格的腐化、分裂,甚至激发破坏性的欲望。
阴影可以理解为性格中的阴暗面,内容因人而异。阴影具有在个体的人格上进行投射的特点,每个人身上的阴影基本上是由特有的品质组成,阴影投射的后果则是主体与周围环境日渐疏离只留下一种虚幻的联系。《我弥留之际》中的母亲艾迪人格中阴影的投射是整个荒诞送葬历程的源头。小说中艾迪的独白只有一次,以倒叙的叙述手法回顾了其不幸的一生。从艾迪的独白中可以看出,她一生都在与孤独为伍,并乐在其中。艾迪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人长大,是杰弗森的一名小学教师。她穷其一生一直在与人格深处的阴影作斗争,压抑着内心中的残暴与冷酷,竭力维持表面上的平和。“我很想找个借口用鞭子抽打我的学生”。[2]放学后她经常一个人在山坡后的泉水边呆着,安静
地宣泄自己对世界的恨意。与埃斯结婚后,她虽然表现出一个正常妻子应有的模样,持家,生子。可是婚姻并没有拯救她,艾迪既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宗教的救赎,“无论结果是埃斯与爱还是爱与埃斯,对我来说都无所谓”。[2]内心中的阴影一直在反噬、侵蚀着她的灵魂。她对周遭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恨意。认为生活就是无止境的认罪和赎罪。她痛恨自己的父亲生下了她,痛恨埃斯和孩子打搅了她的孤独。“埃斯也好,爱也好。我的孤独受到了打扰”。[2]艾迪一生共孕育了五个子女,其中三子朱艾尔还是她出于对生活的绝望与本地牧师私通所生。可她对孩子们却是爱意寥寥,认为子女是婚姻给她的报应。除了对朱艾尔稍有偏颇以外,从未对其他孩子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她一直坚信父亲生前对她说过的话,“人之所以生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为永恒的安睡做准备”。[2]在艾迪眼中,死亡才是一切的解脱。然而由于内心深处阴影的作祟,她并不甘于安静的死去。为了远离她不爱的家人,为了报复埃斯对她孤独的打扰和婚后使她遭受的苦难,“终其一生,他都不会发现我在报复他,这就是我对他的报复”。[2]她在去世前提出要求,让家人在其死后一定将她的遗体运回家乡杰弗森安葬。由此开启了本德仑一家充满痛苦和磨难的送葬历程。
四 结语
福克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弥留之际》一书中的本德伦一家在苦熬,在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他们愚昧、自私、暴躁、狭隘,互不理解彼此怨恨,精神和肉体无时无刻不承受着来自现实的重压,彼此伤害相互折磨,终年生活在悲哀之中。而这种精神上的荒原状态正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表露出的是人类身上与生俱来继承着的劣根性。荣格对于原型理论的研究和对人的无意识深层心理的强调,归根结底亦是对人类这种劣根性特质的探讨,并通过具体的原型来揭示人的先天的本能和行为模式,为人类的种种非理性行为找到合理本源,甚至把集体无意识中的典型原型作为人类意识活动中最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因素。原型理论由此为现代作品中人类空虚和荒诞的精神荒原状态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1]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A].荣格文集[C].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39-40.
[2]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富强,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2-172.
[3]裴秀娟.人格面具、阴影及自性[J].信阳师范学院院报,2009(29):135-138.
[4]崔诚亮.荣格的原型思想研究[D].湖南:湘潭大学,2006.
[5]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Analysis of Images in As I Lay D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ng's Archetype Theory
Zhou Jie,Wang Zhiy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ohhot,Inner Mongolia 010051,China)
Jung's archetype theory is the core thesis of psychological analysis.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n analyzing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 Ace,Jewel,and Addie in William Faulkner's As I Lay Dying,two main archetypes can be found in their personalities,i.e.shadow and persona.Each of which serves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rrow,depressed,and distorted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ose absurd behaviors of the Bundrens during their tough funeral procession.
archetype theory;As I Lay Dying;shadow;persona
I712.074
A
1672-6758(2015)08-0133-3
(责任编辑:蔡雪岚)
周洁,在读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智音,硕士,副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Class No.:I106.4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