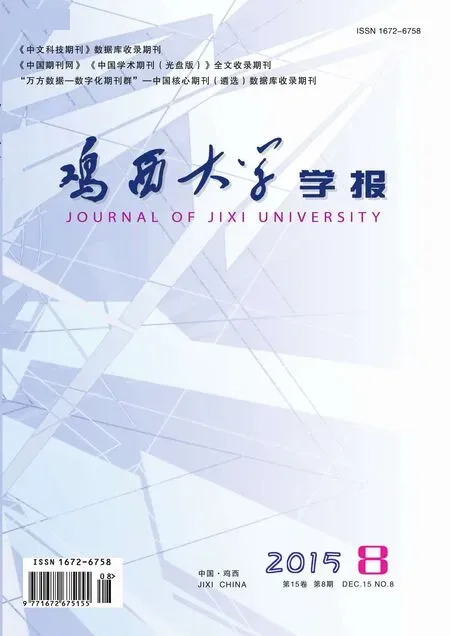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的庄子思想
郭晓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的庄子思想
郭晓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马致远是元代杂剧作家中深受庄子思想影响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中蕴含着厌弃争名逐利,逃避人间是非纷扰,慨叹功名虚幻、人生短暂的庄子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致力于寻找精神归宿,赞颂道家生活的情操。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庄子思想
在元杂剧史上马致远享有颇高地位,有“曲状元”之称的他著有杂剧15种,现存7种。其中,四部神仙道化剧《陈抟高卧》《任风子》《岳阳楼》《黄粱梦》是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元代是非汉族统治中国的时代,草原游牧文明征服了汉族农耕文明,剽悍的蒙古族摧毁了中原几千年的汉族统治,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政权。元废科举,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虽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但却未普遍实行,这给文人们带来一丝幻想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失望。马致远早年,也曾努力追求功名,他在散曲[黄钟尾]中说:“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经过不懈努力,中年时马致远也曾担任江浙省务官。但并不顺心,他无法容忍官场的黑暗和勾心斗角,渐渐心灰意懒,终感到“半世逢场作戏,险些儿误了终焉计。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至此,他看破红尘,远离名利场,退隐山林,过起了隐士生活。《陈抟高卧》《任风子》《岳阳楼》《黄粱梦》这四部剧作正深刻地反映出马致远在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苦闷,继而渴望远离尘世,摆脱功名利禄的纠缠,追求逍遥自在的道教生活。本文中,笔者将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蕴含的庄子思想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渴望出世,厌弃名利
作为道教祖师的庄子崇尚自然,反对追求功名利禄。他在《逍遥游》《秋水》《在宥》等篇中均阐述了“无己”“无功”和“无名”的概念,主张忘掉自我,反对追求功名利禄,对富贵利禄持鄙视态度:
《杂篇·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1]
这里曹商笑庄子之贫,而庄子并不在乎,他则讽刺曹商不择手段猎取财富,表现出他对富贵利禄的唾弃。受庄子思想滋润的文人多淡泊名利,追求超然物外的境界。马致远也不例外,对人间富贵早已看破,《陈抟高卧》中陈抟一上场就说:“吾徒不是贪财客”,正表明了马的心志,他已经看透了俗世的利益纷争,借陈抟之口表明自己的态度。陈抟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剧本一开始,陈抟介绍自己:“贫道陈抟,隐居西华山中,不求人间富贵”,这也是庄子极力推崇的清静无为的理想化生活,马致远更是渴望不已。一般而言,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总会寄托自身的理想,这里我们可以说“陈抟就是马致远”,在元代那种文人毫无地位的社会,马致远经历坎坷,心灰意冷,借陈之口表明自己早已厌弃争名逐利:
【梁州第七】……想他那乱扰扰红尘内争利的愚人,更和那闹攘攘黄阁上为官的贵人,争如这闲摇摇华山中得道的仙人。……坐看蟠桃几度春,岁月常新。[2]
马致远将红尘内争名夺利之人称为愚人,这和庄子对曹商赤裸裸的讽刺相似,二人生活的时代虽相距甚远,但他们对富贵利禄所持的鄙夷态度则相同。
作为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对儒家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持反对态度的,典型代表就是他在《庄子·外篇·胠箧》中所论述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而存焉。”这里庄子以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统治者的真面目。马致远在《陈抟高卧》中也对儒家传统的君臣道德进行了批判,宋太祖做皇帝后多次请陈抟做官,陈则总表现出一种超乎的淡定称自己“本不是贪名利世间人”,他将世间寻求入仕为官者定义为“贪名利世间人”,虽说是“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但在陈抟眼里其结局却是“死无那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可见其对为官入仕的不屑,这正是马致远的心声。
二 逃避人间是非纷扰
庄子曾在《逍遥游》中提出“逍遥”的思想境界,在政治上他也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全部精神世界,对于生活他更是主张顺应自然。庄子看透了人世,他推崇自然之境,并以此来远离和超脱人世的苦难,他力求避世,返璞归真,在《内篇·齐物论》中他用人的影子随人而动的故事形象地说明天地间许多现象是无法弄清楚缘由的,进一步暗示人世间、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是非是纠缠不清的,最好的办法便是远离之。经历了“二十年漂泊生涯”的马致远,饱受坎坷,但他既无力直面抗争,又不愿与世浮沉,失望苦闷之际,清静无为、修真养性的老庄思想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在杂剧中他表露了想逃避人间是非的心理,《岳阳楼》中作者借吕洞宾之口劝世人远离世间纷扰:“我劝你世间人,休争气,及早的归去来兮。”作为文化人,马致远曾受孔孟老庄思想熏陶,本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志。青年时他也曾积极入仕,想要建功立业,但官场的黑暗,使他失望至极无法继续仕途之路。这时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便被他弃之,唯有庄子思想最能给他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陈抟高卧》中,马致远借陈抟之口表达了他想要远离人世烦扰的心情“本居林下绝名利,自不合划下山来惹是非,不如归去来兮”。
《岳阳楼》中吕洞宾的唱词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马致远想逃离世间的烦闷心理:
【叨叨令】则为这泼家私满镜里月髭鬘,熬煎得铁汤瓶一肚皮长吁气。……争如我梦周公高卧在三竿日。[2]
马致远追慕宋初隐士陈抟,劝导世人要“一空人我是非”,典型地表现出了他悲观厌世的态度。但马的思想并非完全消极,在封建社会,对历代文人思想生活影响深远的思想除了儒家,便是道家。一般而言,在政治清明、国富民强时,知识分子多推崇儒家思想,承担社会责任,遵循“修齐治平”的原则;当吏治混乱、社会黑暗,大多文人则以道家思想为精神寄托。因此,文人们厌恶世道并非完全消极,在人生的低谷时期,寻求庄子作为精神依托,调节自身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让自己解脱和释怀的最好方法,也是儒家“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表现。从马致远笔下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出马致远找到了他的精神寄托——道家思想,并以此为乐“石床棉被暖,瓦钵菜羹肥,是山人乐矣”。
三 慨叹功名虚幻、人生短暂
对于生命,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他曾感慨人生短促:“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简单的一句对生命的感叹,即表现出庄子对生命的深沉体验。对于名利,庄子认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近年”。这是他面对险恶的社会而提出的形神兼养的原则,他还曾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命。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马致远当然没有想去修身养神,但他和庄子一样,注重思考生命和人生。在黑暗的社会中马致远经历了宦海浮沉,深知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
【滚绣球】三千贯两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茵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2]
作者借陈抟之口,表明了自己对入仕的看法,任他“一品官二品职”最终还是落得个“纸上两行史记”。他认为人生短暂,纵使博得个一官半职又有何用:
【二煞】鸡虫得失何须计,鹏鷃逍遥各自知。看蚁阵蜂衙,……光阴似过隙白驹,世人似舞瓮醯鸡。便搏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提。[2]
元代知识分子境遇凄惨,往代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使不能入仕,也不会沦落到像元文人那样的境地。元蒙统治者从“马背上得天下”,一向重武功、轻文治,他们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治理封建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因而对汉族知识分子轻视戒备。为防止汉儒参政,元停科举几十年,堵塞了广大读书人的仕进之路。马致远生活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对入仕做官早已不向往,更多的是慨叹功名虚幻。
庄子慨叹人生短暂、功名虚幻是本着复归于人初来世上时的纯真本性,返璞归真,马则是为了抗拒尘世的污浊和不堪,远离世俗纷扰以保持心境的纯真,二人虽出发点不同,但初衷相同。
四 寻找精神归宿,赞颂道家生活
庄子崇尚自由,尤其强调精神上的自在。《逍遥游》中,庄子写大鹏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这是种何等自由壮阔之象,他提出“逍遥游”,主张摆脱世间一切名利束缚,使精神达到一种绝对自由之境。庄子虽更注重精神自由,同时也追求形体自由,在他看来人世间就是一个樊篱,它束缚了人们本该拥有的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精神和身体自由。他希望能返归自然淳朴的“至德之世”,实现对苦难的超越。他向往的理想社会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没有伦理规范约束但民风淳朴;没有统治秩序,人与人平等相处;百姓“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老死而不相往来”的男耕女织的生活。
马致远对宋初隐士陈抟的追慕,对“陶渊明式生活”的艳羡,在《任风子》中任屠户道:“我虽不似张子房休官弃职,我待学陶渊明归去来兮”,寻其源头都在老庄的隐逸思想里。在剧作中作者多次借主人公之口表现对道家隐逸生活的向往:
【三煞】身安静宇蝉初蜕,梦绕南华蝶正飞。卧一榻清风,看一轮明月,盖一片白云,枕一块顽石。直睡的陵迁谷变,斗转星移。长则是抱元守一,穷妙理造玄机。[2]
【双调·新水令】我虽不曾倒骑鹤背上青霄,今日个任风子积功成道。编四围竹寨篱,盖一座草团瓢。近着这野水溪桥,再不听红尘中是非闹。[2]
这两段唱词,字里行间皆流露出作者对道家隐逸生活
的向往。二十多年在社会中飘零,作者想要给自己和灵魂找一个归宿,可在元代社会,知识分子难有出头之日。加之作者厌倦了官场,看透了名利富贵,更无“货与帝王家”之意,便把目光转向世外,并以老庄思想为依托,舒缓自己的苦闷。庄子淡泊生死,他认为人本来就是属于自然,人来到世上是因为遇到了出生的时机;离开人世则是顺应自然,正如他在《内篇·养生主》中说道:“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时也。”马致远在《任风子》中同样流露出这种思想,任风子:“父母生我,是来处来;我若死了,便是去处去。”
老庄哲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尤其当他们飘零、落魄之际。这也是马致远杂剧中蕴含庄子思想的重要原因,孔子也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元代是彪悍的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对汉民族采取与生俱来的歧视态度,对汉族知识分子更是压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马致远这样的知识分子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借自己的如椽大笔排遣内心的愤懑,抒发他们对人生的思考,他们将目光由儒家的修齐治平转向道家的隐逸之趣。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重视个性自由、淡泊名利的个性更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同时,当时全真教的盛行也对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有重要的影响,而全真教与老庄思想更是密不可分,因此,不论从内在原因还是外在条件来看,庄子思想对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都有重要的影响。
[1]张松辉.庄子译注与解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1:654.
[2]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8,15,16,56,179.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On Zhuangzi's Thoughts of Immortal in the Moralistic Drama Written by MaZhiyuan
Guo Xiaof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China)
MaZhiyuan,a famous dramatist lived in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was influenced by Zhuangzi in his liberal ideas His works contain a rejected name for profit,to avoid distractions and human right.At the same time,his works also reflected his desire for spiritual home and the praise of life sought by the Daoists.
MaZhiyuan;immortal;Zhuangzi's thoughts
I207.3
A
1672-6758(2015)08-0123-3
(责任编辑:宋瑞斌)
郭晓芳,在读硕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Class No.:I207.3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