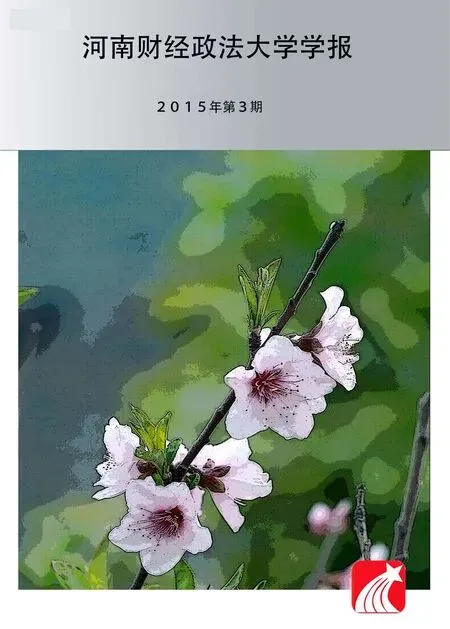土地发展利益的物权法调整模式
姜 楠蔡立东
(1、2.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00312)
土地发展利益的物权法调整模式
姜 楠1蔡立东2
(1、2.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00312)
英美法系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实现对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调整,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对超越不动产法定使用限度所产生的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以及对其他不动价值减损的公平补偿。尽管两大法系法律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土地发展权概念难以直接见融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内。但事实上,通过对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概念的分析,不难发现,土地发展权的功能可以加载于大陆法系物权法中所有权及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囿于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尽管土地发展权不能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但是土地发展利益可以依靠物权法规则加以调整,进而形成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与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两种类型。前者通过不动产相邻关系的修正以及对《物权法》中征收补偿范围的解释得以实现;后者则完全可以纳入地役权制度范畴之中。
土地发展利益;土地发展权;物权法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目前,以《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的我国土地法律制度体系,未将土地增值利益的调整纳入规制范畴,土地增值利益的法律内涵、归属等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由于征收作为变更土地用途的唯一手段,土地增值利益事实上被国家垄断,集体和个人对土地增值利益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构建合理、公平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机制成为我国土地法制建设所要完成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土地增值利益是指不动产权利人或第三人改变不动产使用用途而致该不动产价值增加,这种价值增加值即为土地增值利益,亦被称为土地发展利益。比较法上,英美法系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来对土地发展利益予以调整。多数学者主张,借鉴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建立我国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规制机制。但是,来自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无法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形成有效衔接,整体照搬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并非明智之举。事实上,对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移植不能拘泥于表现形式,更应当注重其实质价值。只有深入了解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内在功能的价值,利用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替代”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实现其功能,将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内化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才是切实可行之策。
一、土地发展利益调整的域外经验: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影响与认知
土地发展权概念起源于英国。英国政府设立土地发展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对土地开发利用形成有效控制的法律制度,进而协调人口增长与城市规划及农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基于上述立法理念,土地发展权设计为一种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并为国家所有的独立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土地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想要变更原有土地用途时,必须向政府购买发展权,私自变更土地用途的行为将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征收等行为变更私人土地用途时要对土地权利享有人予以补偿①有关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演进及含义的详细论述,参见刘国臻:《论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于《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141页、第144页。。美国仿照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土地发展权为土地所有人的一项私人财产权,可以通过市场进行转让(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T D R)。依据政府土地利用功能规划,土地发展权转让区是根据规划需要保护的区域或者是禁止工商业开发的区域,通常是农业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区、需要保存开阔空间地带区、野生动植物栖息区、历史性建筑保护区以及环境保护区等;土地发展权受让区是根据规划可以进行土地开发建设的区域,通常是城市中心地带。当城市商业及住宅密度达到规划上限时,土地开发者必须向使用受限的土地所有权人购买发展权。国家亦可以普通交易者身份购买或出售土地发展权②有关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详细介绍,参见:刘国臻:《论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于《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41-142页;高洁、廖长林:《英、美、法土地发展权制度对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启示》,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第207页。。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的规范客体仍然以土地为中心。但在实践中,土地之上的房屋等建筑物空间亦可以成为土地发展权的客体。例如在法国,当城市个体建筑的面积与占地面积超过法定比例时(被称作法定容积率),建筑开发者要想取得超过规划标准部分建筑物的所有权,必须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否则超标部分归国家所有。尽管法国没有在立法上明确发展权制度,但是法定容积率的设定及政府对土地利用的干预事实上构成了发展权制度③参见高洁、廖长林:《英、美、法土地发展权制度对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启示》,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第208页。。由此可见,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对土地发展利益予以调整。
土地发展权制度之所以产生于英美法系,渊源在于英美法自身固有的特征:没有明确的体系,注重实际应用和经验。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对财产权的规制依靠明确的成文法典,法典中权利的体系与类型相对固定。立法者在对法律做出修改时必然要顾忌到新设权利的必要性以及与既有的权利体系的协调问题。因此,新权利的创设在大陆法系国家受到的阻力较大,而英美法系对财产权利的规制采取判例法与制定法相结合的方式,并不受严格的概念体系的拘束,因而新权利的创设更加容易。此外,英美法系更加注重法律的实际应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土地发展权的创立就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土地利用中的现实问题,并非基于法律概念的推理演绎。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确立开创了以独立的权利模式来调整土地发展利益的先河,对于我国以法定方式规制和保护土地发展利益极具借鉴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制度的移植不是单纯而机械的仿制工程,其实不过是另一种法律发现或创制的理性方式[1]。由于两大法系法律思维模式以及立法体系之间的差异,作为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概念不可能与大陆法系中的某一法定权利概念直接对接。生搬硬套地将土地发展权概念归入我国现行的某一部门法中,不仅不能有效地实现设置土地发展权的目的,而且会对现有法律体系造成难以吸收的撞击,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因此,“拿来主义”的做法难以成为我国土地发展利益调整规范模式的合理选择。构造土地发展利益的中国法律调整模式,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可以当作真的而为现实主义接受的法律概念[2]。
二、土地发展利益调整的本土问题:理论争议及模式选择
随着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与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不断完善,法律对不动产权利人的保护不再仅仅限于使用安全与交易安全的领域,对发展利益的调整应当成为其应有之意。事实上,长期以来,强大的行政权力取代了土地发展利益的权效[3],我国土地发展利益分配极度倾向于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现的公权力主体,进而导致土地发展利益分配不均。以农地征收为例,由于行政征收是非市场化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真实价格被掩盖,农民集体及成员并不能充分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大部分收益由国家独占[4]。多数学者主张通过引进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实现土地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由于土地发展权并非我国本土法律概念,因而理论上对于其性质以及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存在极大的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私权性。同时,作为国家对土地利用关系的干预,又具有公权力性质。因而,土地发展权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权利①参见刘国臻:《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载于《法学杂志》2011年第3期,第4-5页。。第二种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是一种与所有权相独立的财产权[5]。第三种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权,是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②参见杨明洪、刘永湘:《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载于《财经科学》2004年第6期,第24页;王海鸿、杜茎深:《论土地发展权及其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创新》,载于《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第80页。。毫无疑问,三种观点均具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国家对土地利用关系的干预”作为认定土地发展权是一种经济法权利的理由不够充分。国家干预与管制经济法规范之独有现象,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中国家强制处处可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从单纯的经济秩序维护者、仲裁者,演变为结果取向的干预者[6]。单纯地以是否具有国家干预作为划定土地发展权性质的标准欠缺说服力。其次,将土地发展权归入财产权的作法不具有实际操作性。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并无财产法这一部门法,因此,土地发展权的财产权定位并非最终厘清其性质,土地发展权的性质依然模糊。再次,由于我国现行《物权法》并没有将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加之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将土地发展权直接定性为独立的物权亦难谓合理。
事实上,英美法系中的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发展利益的调整是形式结构与实质内容的关系。土地发展权是调整土地发展利益的一种方式,但是并不对土地发展利益调整目标起决定性的指向作用。通过对土地发展权功能的解构,按照功能等值思路,将其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固有的制度资源相结合,便可以有效地建立起本土化的土地发展利益规范机制:
首先,从土地发展权的功能指向来看,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始终以土地利用的自由与限制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为场域,并以土地用途的法定化为存在基础。这与大陆法系物权法中规范物的利用关系的调整范围完全对应。近代以来,随着人口急速膨胀,土地资源的稀缺现象日渐明显。为了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兼顾各方利益,土地权利的绝对化的观念日趋式微,土地权利的社会化思潮为各国所认可③土地权利的绝对化向社会化转变是对个人法益思想向社会法益思想转变的有力回应。这一转变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土地利益划分为的所有利益与资本利益的二分结构,进而形成为所有利益、资本利益与生存利益三足鼎立的局面。法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三种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具体论述参见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1页。。这种法律思想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各国法律对土地使用予以明确限制,土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必须在法定用途范围内利用土地。同时,土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与建筑物权区分所有权亦同样适用此原则[7]。在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作为调整不动产归属及利用关系的基础性法律规范,以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定限制以及用益物权法定化为手段④《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规定:“物的所有人,以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的权利为限,可以随意处分物,并排除他人的任何干涉。动物的所有人在行使其权限时,应遵从关于动物保护的特别规定。”《日本民法典》第206条规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内对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尽管《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了所有权绝对原则,但是该法典第545条还是规定了征收移转所有权的情形。事实上亦承认了所有权受公共利益的限制。《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者外,不得创设。”尽管《德国民法典》对物权法定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该原则为理论及实务界所承认。对于《法国民法典》是否承认了物权法定原则存在争论,不过肯定说更具说服力。有关德国与法国物权法定原则的论述,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同样实现了土地用途法定化的目标。
其次,从土地发展权的功能价值来看,英美法系中的土地发展权实质上是对改变土地用途而产生的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平衡机制。土地权利人变更土地的法定用途,独自享有所获得的土地发展利益,对于其他由此行为遭受损害或未获增值收益的不动产权利人来说有失公允。因此,改变土地的法定利用限度所获得的不动产增加价值的收益不应当归属于该不动产的权利人,而是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将其予以再分配。如何实现这种利益分配,英国与美国采取了不同措施。在英国,国家成为该利益的受偿主体,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手段把土地增价部分吸收回来充当土地减价部分的补偿,这样宏观调控以后,土地利用的控制引起的增价和减价将处于均衡状态[8]。而美国法律规定,超越土地的法定利用限度的不动产权利人必须向其他在合法范围内利用不动产的权利人购买发展权,从而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了补偿与受偿主体的具体化及不动产价值增加和减损利益平衡的目的。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9]。实现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均衡是实现私法适用效果的重要目标。物权法作为私法规制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遵循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引①《物权法》第7条规定了物权的取得和行使过程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权利人在取得和行使物权过程中“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体现了利益平衡的思想。一方面,权利人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具有行使权利的自由,享有物权利益;另一方面,这一权利行使不能对社会和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以此方法明确权利的界限,保障权利主体的法定自由。如果物权人超越自身权利行使的范围,对其他物权人造成损害,其他物权人可以依据《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方法维护合法权益。可以说,物权的保护是实现《物权法》利益平衡理念的具体技术手段。。可以说,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在实现利益平衡的制度理念上与具有私法属性的物权法具有一致性。
再次,从土地发展权的功能效果来看,来自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事实上可以对应于大陆法系不动产所有权与用益物权中使用权能。具体表现为:其一,不动产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人应当按照法定用途利用不动产,超越法定用途使用土地属于权利滥用行为,应当对受损害人予以赔偿。英美国家的土地权利人超越土地法定用途利用土地必须向国家或其他土地权利人购买发展权,对此可以视为该不动产权利人滥用不动产使用权利,对他人不动产造成损害的妨碍而引发的补偿关系。其二,他人强制或者利用其它方式致使不动产所有人或用益物权人超出法定用途利用该不动产,不动产所有人或用益物权人有权请求该第三人予以赔偿或补偿。英美法系国家政府变更私人不动产的法定用途而向不动产权利人购买发展权,法律效果等同于政府对于其妨碍土地权利人正当使用土地权利而进行的损害补偿,该部分规范功能完全可等同于物权使用权能对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范围。基于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而实现的发展权流转,相当于不动产权利人之间以协议约定一方支付给另一方对价,后者容忍前者获取超越土地法定利用限度利益的合意关系,可以归类于一种以意定方式设立的用益物权。
三、土地发展利益调整的基本架构:归属、类型化及实现路径
(一)土地发展利益的归属
关于土地发展利益的归属问题,理论界主要有国家所有、土地所有人所有两种观点。有学者主张应当将土地发展利益确定为国家所有。其主要的理由在于,分配土地发展利益的主要功能在于土地自身价值增加的分配问题。根据土地价值增加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因土体权利人投入资本,土地使用条件得以改良使土地价值增加;二是公共投资(例如修建公路)使土地价值增加。目前我国土地增加值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因而土地增加值应当归国家所有,土地发展利益归属国家较为合理[10]。有学者则反对土地发展利益一律国有化的观点,而认为农村土地发展利益应当归集体所有。其理由在于“土地涨价归公”和“土地发展利益国有”是被征农地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的主要经济依据。但根据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土地涨价归公”实际上只能表明政府有权利“分享”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而不表示被征农地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11]。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存在商榷之处:首先,发展利益单纯的国有化不能解决中国土地利益分配的现实矛盾。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是目前我国土地用途的两大类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对外扩张不断蚕食其周边的农业用地,但是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定途径仅仅限于政府征收。随着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土地价值的利益亦会猛然增加,但是由于法律没有将赎买、价格协商等方式作为征收的前置程序①在西方国家,政府取得私人土地并非依靠单一的征收途径,而是往往将自愿性的协商作为征收土地的前置程序。例如,2004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征地守则第24段做出了以下建议,在申请征地授权以及整个申请过程中,征收机构应当在任何可行的情况下争取通过协议获得土地。强制收购或征地应当被视作无法达成协议时才需要诉诸的最后手段。参见张千帆主编:《土地管理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与用益物权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实际损失数额的补偿,根本没有参与分配土地发展利益的机会,最终的土地增值价值实际上由政府所垄断。可以说,在国家管制权的作用下,我国法律虽未言明土地发展权,却近乎采取了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12]。这种垄断事实上剥夺了农地所有权人及用益物权人对土地应当享有的合法利益,违反了《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②所谓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是指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对所有民事主体的一体保护。但以单一且具有强制性的征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唯一法定途径,本身就意味着两种所有权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有关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具体论述,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8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192页。相同观点的论述,参见田春雷:《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中土地发展权的配置》,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149页。,同时也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其次,由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只有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两种形态,因此,发展利益究竟是归国家所有还是归土地所有人所有的区别意义仅仅在于,是否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土地发展利益,而国有土地发展利益引发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在我国取消农业税后,村集体的行政职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但村集体作为私权利之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功能依然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甚至因集体财产的来源基本上已经枯竭,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补贴也一般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致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错位的情形并未得到根本的转变[13]。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存在模糊性与虚位化的状况下,由于该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意思形成与决策机制,如果将土地发展利益赋予其所有,很难保障利益惠及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土地发展利益归属于土地所有权人的观点,在当下中国土地所有制背景下亦存在不妥之处。
从土地发展利益的物权规范模式出发,其内容可以加载于土地物权的使用权能。不动产的使用权能是土地发展利益产生与存在的基础载体,土地发展利益归属于用益物权人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同时,土地发展利益归属用益物权人具有一定的实效上的合理性,具体表现为:其一,能够使土地发展利益真正为个体权利人所享有,打破土地征收过程中国家垄断发展利益的局面。国家和集体组织虽然是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人,依据物权法的一般理论,所有权具有使用权能,但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农业用地之上几乎全部存在相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假定用益物权存在的场合,所有权人将用益权能让渡于用益物权人。因此,土地发展利益事实上归属于用益物权人,征收过程中农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土地增值利益必然归属于承包经营权人,而并非属于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如此以来,缺乏利益驱使的政府的征地行为将更加慎重与理性,土地利益的分配将更加公平与均衡。土地发展利益归属于用益物权人,并不等于彻底排除国家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权利。因公共投入致使土地价值增加的部分,国家可以通过行使税收权力获得补偿③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颁布了《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这是政府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税法依据。但是该税种征收的对象仅仅限于国有土地,未将集体土地纳入规制范围,没有明确政府获得集体土地增值利益的法定范围,进而导致政府垄断集体土地增值利益权力的异化。因此,有学者主张修订现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集体土地,设计合理税率,才能彻底划清政府参与集体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权力边界。具体论述参见:汪辉、陶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6页、第81页。。其二,使土地发展利益落实到用益权人个体,有利于防止权利主体不明确问题的发生。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制权利主体不明确的问题一直为人所垢病。“人人所有亦为人人没有。”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个体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个体所有权长期受到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长期压制甚至被完全取消,“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高于个人所有权”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公有制下人们对个体财产所有权毫无归属感。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财产权是属于每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它也可以呈现一种集体的形态,从而赋予公共警察力量以正当性[14]。个体与集体是一组相对概念,个体所有权是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不承认个体所有权存在的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必然只是形式化与空洞化的所有权。从我国目前土地权利体系的框架来看,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主要的表现形式与实现方式便是,以法律个体所有为基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与行使①参见张千帆、党国英、高新军、曲相霏、杨世建、田飞龙:《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利保障》,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主体与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争论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可以说,确定土地发展利益归属于用益物权人更加符合现实制度理念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土地以外,不动产另一种重要的类型为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由于我国《物权法》中用益物权的类型只限于土地上的用益物权,依据物权法定原则,房屋不可能成为用益物权的客体。空间性的土地发展利益不可能归属于用益物权人,而只能归所有权人所有。因此,单纯的以土地为客体的土地发展利益应当归属于用益物权人,而以房屋为客体的空间性土地发展利益只能归属于房屋所有权人。
(二)土地发展利益的类型与实现路径
土地发展利益基于土地用途变更的事实而产生。广义的土地用途变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土地利用功能的彻底变更,如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另一种是土地利用功能的非彻底变更,如农业养殖用地变更为耕地。两种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土地发展利益应当对应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利用功能的彻底变更主要表现为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实现这一变更过程的唯一的法律途径为行政征收。因此,土地发展利益表现为一部分征收补偿费用。由于物权法恒涉及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与社会公益有重大关系,故物权法中通常有不少关于公益之规定[15]。《物权法》第42条、第121条有关征收的规定体现了物权法的公益性特征。土地用途彻底变更而产生的土地发展利益依据上述规范加以调整。与之相反,土地利用功能的非彻底变更而产生的土地发展利益的平衡不具有公共性,可以依据纯粹私法规范加以调整。利益是法律命令的原因,立法对需要调整的生活关系和利益冲突所进行规范化的、具有约束力的利益评价[16]。私法的调整方式可分为意定主义与法定主义两类[17]。这种利益调整机制反映到物权类型中便形成了法定物权与意定物权。法定物权是指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经由法律规定而发生。意定物权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成立的物权。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物权成立的要件和适用的法律不同[18]。因此,土地用途非彻底变更而产生的土地发展利益,借助于物权法的调整模式,亦再次划分为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与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的调整可以加载于不动产相邻权关系。约定发展利益的调整则加载于地役权机制。
土地权利人改变土地用途获得不动产增值利的情况下,相邻不动产权利人可以依据不动产相邻关系主张自身享有的土地发展利益。按照《物权法》第48条的规定,相邻关系规范“利用不动产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不动产的使用权能的存在为前提。在规范基础的形成方面,土地发展利益的分配与相邻关系存在一致性。此外,《物权法》第48条中的“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亦包括用益物权人,土地发展利益的归属者为用益物权人,两者在法律关系主体范围方面又形成包含关系。相邻关系的规范功能在于调和不动产相邻权利人的利益冲突,以谋共同之利益[19]。由于不动产所有人和用益物权人在利用不动产过程中对其享有直接的支配权利和使用自由,因此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之间不免产生纠纷。为了排除此类纠纷的产生,提高不动产的利用效率,法律为相邻关系双方配置一定的权利义务从而使双方的利益得以平衡。概括起来,相邻关系的权利内容主要是指合理使用不动产,在必要限度内使用邻地的权利以及对于相邻关系对方造成其不动产损害的求偿权。相邻关系的义务内容主要包括合理使用不动产并对邻地权利人在合法限度内使用其不动产的容忍义务以及造成邻地损害的赔偿或补偿义务。依据《物权法》第86条至92条的规定,我国相邻关系主要分为五种类型:(1)用水与排水的相邻关系;(2)通行的相邻关系;(3)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管线的相邻关系;(4)采光、通风以及日照的相邻关系;(5)不动产妨害的相邻关系,其中包括不可量物侵入以及不动产安全维护及合理使用他人不动产避免损害的相邻关系。按照法定的利用限度使用土地虽然并不属于上述相邻关系之法定具体类型,但是基于权利行使必须符合公益原则之相邻关系建构理念[20],按照法定使用限度利用不动产必然属于土地相邻关系的应有之意。对于超越不动产使用限度所产生的土地发展利益的分配与调整可以通过维护不动产相邻关系的救济方式加以实现。可以说,从规范主体、内容及功能角度分析,相邻关系完全可以将法定土地发展利益纳入其规范范围。
不动产使用人擅自超越法定限度使用该不动产,给相邻关系人造成损害的,可以行使排除妨害、妨害预防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相邻关系人可以要求违法使用不动产的权利人恢复不动产的法定使用限度;在不动产违法使用过程中请求使用权人停止违法变更行为。不动产使用人违反法律规定限度利用不动产,由此而获得的土地市场价值增值收益即属于违法所得,无论该行为是否对于邻地造成实际损失,此项增值收益视为对相邻关系人造成的损失,当属赔偿范围。如果该行为客观上致使邻地价值增加,则增加部分应当在赔偿范围内予以扣除,适用损益相抵原则。如果土地使用权人擅自超越法定的土地使用限度致相邻土地价值下降,非法利用土地的使用权人应当对减损的价值予以赔偿。如此以来,以土地相邻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发展利益规范机制得以建立。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现行《物权法》对于相邻关系的规范仅仅围绕不动产使用价值的利用与限制而展开,而忽略了对于相邻关系中不动产动态交换价值关系的规制与调整。未来《物权法》修订过程中,将土地发展利益列入相邻关系的规制范围实属必要。具体措施内容包括:其一,将《物权法》第90条“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修改为“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不动产权利人擅自变更土地用途不当获利或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向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增加“不动产权利人擅自变更土地用途不当获利或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向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的内容,实现以相邻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发展利益保护的法定化。其二,将《物权法》92条中“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中的“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内容删除,从而为土地发展利益的实现预留出规范解释空间。
基于行政征收行为而产生的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配置,则需要以《物权法》中规定的征收补偿关系为基础。征收是政府依据公共利益需要,以行政职权强制变更土地所有权的行为,被征收的土地绝大多变更了使用用途。因此,在土地变更用途的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市场价值的增值与土地市场价值的下降便属于土地发展利益的内容范畴。从法律关系的主体角度分析,公共利益的需要成为政府征收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但是其行为毕竟突破了法律关于土地用途的限制性规定,损害了被征收人的利益,因而征收人需要对其进行补偿。在征收过程中,征收人作为土地发展利益的补偿主体当无疑问,而《物权法》第121条的规定,用益物权人可以成为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的求偿主体。因此,《物权法》第121条成为用益物权人作为享有发展利益主体的法律依据,但是发展利益的最终实现需要对《物权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的征收补偿范围进行进一步解释。
从立法状况来看,目前我国征收补偿标准的规则体系过于复杂,标准不一,且内部结构不合理,对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保护处于空白状态。具体表现为:首先,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补偿标准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规定,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为“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农业耕地的补偿标准依据《土地管理法》执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这是一种凝固的、停滞的、毫无前瞻性的静态标准。其既不考虑土地生产能力的动态发展性,又不考虑土地用途的发展变化性,一刀切地将收益价值的基点确立为“征收前”“原用途”“产值的”“固定倍数”[21]。显然,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补偿标准高于耕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其显失公平的负效影响甚为明显。对于土地发展利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以及《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亦未予以明确承认。其次,对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居民的房屋所有权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统一的法律及行政法规加以规定,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保护更是无从谈起。
制定新的法律,实现对行政征收中土地发展利益的保护固然具有必要性和长远性,但是这一过程必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难以满足实现土地发展利益保护的迫切性需求。与此相反,对《物权法》征收补偿的范围作目的扩张性解释,将以征收补偿为基础的土地发展利益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不仅能够维护现有法律体系稳定,而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主要表现为:其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位阶低于《物权法》。如果《物权法》第42条的补偿范围包括以征收补偿为基础的土地发展利益,那么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土地发展利益的保护应当优先适用《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其二,与《土地管理法》相比较,《物权法》属于后制定的法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于耕地发展利益的保护同样优先适用《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排除《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适用。其三,因政府的征收行为而消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农村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权利人获得补偿的请求权基础为《物权法》第121条和《物权法》第42条第3款。上述用益物权及所有权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单行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加以规定,因此其征收补偿标准应当直接适用《物权法》第42条第3款的规定,补偿范围当然包括土地发展利益。此外,虽然征收补偿范围是否包括土地发展利益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实践中被征收人的部分土地发展利益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得到补偿①例如,实践中“城中村改造”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政府将村组建制撤销后的剩余集体土地直接收归国有,并依照城市房屋拆迁程序实施拆迁和补偿,实际上是将宅基地从集体土地性质变更为国有性质的土地发展利益归于被拆迁人,并在拆迁时将村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作为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以此方式向其分配土地发展权益。此外,还有广州市政府采取的旧城改造中被拆迁房屋市场评估价外的“溢价补偿”模式;北京市政府采取的农村房屋拆迁中产权置换的“双控模式”及农村房屋拆迁时的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模式;厦门市政府采取的“金包银”模式;重庆市政府采取的“地票”交易模式。具体论述参见顾大松:《论我国房屋征收土地发展权益补偿制度的构建》,载于《法学评论》2012年第6期,第21-24页。。可以说,《物权法》第42条第3款的征收补偿范围包括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解释方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除了以法定物权调整土地发展利益,不动产利用人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获得土地发展利益。与法定的发展利益不同的是,意定的土地发展利益基于的土地限制利用的强度高于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义务相对人不仅不能超越土地的法定使用限度,而且其对土地的利用不能超过与权利人约定的范围。首先,从法律关系的主体角度来看,地役权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人,亦包括土地用益物权人②对于用益物权人是否能够成为地役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地役权是以调整土地利用关系为目的,用益物权人在利用土地过程中肯定具有参与到这一关系中的可能性,如果否认其成为地役权主体的可能性,必然对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利用产生损害。否定说认为,地役权的客体在于供役地本身,而非建立在用益物权之上。因此,用益物权人并不当然享有设定地役权的权利。用益物权人设定地役权必须得到土地所有人的许可或授权。笔者赞成肯定说,理由在于否定说固然有道理,但是在实践中难以具有操作性。例如,国有建设有地使用权人为将自己享有用益权的建设用地为他人设定地役权,依据否定说需要政府部门的同意,此时原本属于私法性质的约定行为转变为行政审批行为,此时的地役权的设定不在属于物权法调整范畴,违背了地役权的私法本质属性,不具合理性。肯定说的观点参见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版)》,陆庆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否定说的观点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6页。。用益物权人即可以成为享有地役权的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说,土地发展利益关系主体与地役权的法律关系主体存在重合之处。其次,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产生的原因是他人为其不动产合法利益之实现而利用他人之不动产。土地发展利益享有人的主要的行为模式是消极地限制义务人对于土地的利用,利益相对人应当在双方约定的范围内利用其不动产①物权法中的地役权其实质在于为自己土地便利使用而用他人土地的权利。这种便利使用的范围要超过相邻关系中对他人土地的利用程度,而且地役权的设立亦不为供役地与需役地相邻为必要。参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作为不作为的对价,利益享有人应当对相对人予以一定的补偿。再次,地役权与约定土地发展利益均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产生。因此,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完全可以通过设定地役权的方式加以实现。例如,对于私人所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的保护,文物保护部门可以与建筑物所有人约定以设定地役权的形式限制建筑物所有人改变建筑物原貌及变更用途。同时,文物保护部门应当对所有人因此所受损失和所失利益予以补偿。这里地役权约定的补偿针对的就是建筑物所有人的发展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对土地发展利益加以调整的地役权与传统的地役权类型有所不同。该类地役权并不完全以需役地的存在以及从属性为必要条件。近代以来地役权的涵射范围不断扩张,增加了人役权的相关内容。可以说,需役地与从属性不再构成地役权的绝对必要条件②具体论述参见蔡立东、杨晔、刘国栋:《历史建筑保护的物权法进路》,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67、69页。。例如,为了维护公共通行之目的,在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明确承认公用地役权。“公用地役权关系之对象,系不特定之公众,且亦不以有供役与需役地之存在为必要。”[22]从属性更是无从谈起。
四、结论
英美法系的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可以归类于大陆法系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能的内容。虽然土地发展权不属于现行《物权法》中独立的权利类型,但是土地发展利益依然可以借助《物权法》的规范体系予以合理分配。具体措施包括:其一,将土地发展利益类型化,划分为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与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其二,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通过对不动产相邻关系的修正以及不动产征收补偿的解释从而融入《物权法》规制范畴;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则可以通过地役权制度的机制得以完全实现。《物权法》规制下的土地发展利益调整机制是以不动产利用过程中发展利益的确认归属为核心,包括增值利益的分配及损害利益的补偿。这种规范模式不仅仅限于法律强制的分配机制,还可以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来完成。
[1]米健.比较法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吴郁玲、曲福田、冯忠垒.论我国农地发展权定位与农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J].农村经济,2006,(7).
[4]蔡立东、刘国栋.农地权利财产属性的强化[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4,(1).
[5]于华江、杨飞.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农民土地发展权保护[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6]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7][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M].吴越、李大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刘国臻.论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评论,2008,(4).
[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0]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J].河北法学,2002,(2).
[11]张期陈、胡志平.论被征农地增值收益的归属[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6).
[12]陈柏峰.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J].法学研究,2012,(4).
[13]高飞.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民法构造[J].法商研究,2009,(4).
[14][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M].秋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5]陈华彬.物权法原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16][德]魏德士.法理学[M].丁晓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7]易军.“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私法精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4,(4)
[18]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9]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0]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21]王洪平、房绍坤.论公益征收补偿的标准[J].山东社会科学,2010,(11).
[22]王泽鉴.民法物权—用益物权·占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The Adjustment Mode of L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of the Property Law
Jiang Nan1Cai Lidong2
(Law School Jin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nlin 100312)
Common law countries realize the legal adjust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system,and its core function is to realize the real legal use limit of valueadded benefits generated by r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fair burden on the other value loss.Referring to the idea,this system will help to accelerate the legalized and normalized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land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But becaus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big law legal systems,land development rights concept is difficult to directly acknowledged under China’s current legal system.In f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of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the function of 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 can be loaded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law under continental law system and the access to usufructuary right. Constrained by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real right limits,although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cannot become an independent property rights,but l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can rely on the rules of law to adjust,the two types of l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interests and agreed by the land developments.The former can be realized by real estate neighboring relations correction and compensation scope on the property law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the latter can be built into the category of easement system.
l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The property law
D923.9
A
2095-3275(2015)03-0096-10
2015-01-25
1.姜楠(1983—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法;2.蔡立东(1969— ),男,吉林长春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合同法、公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