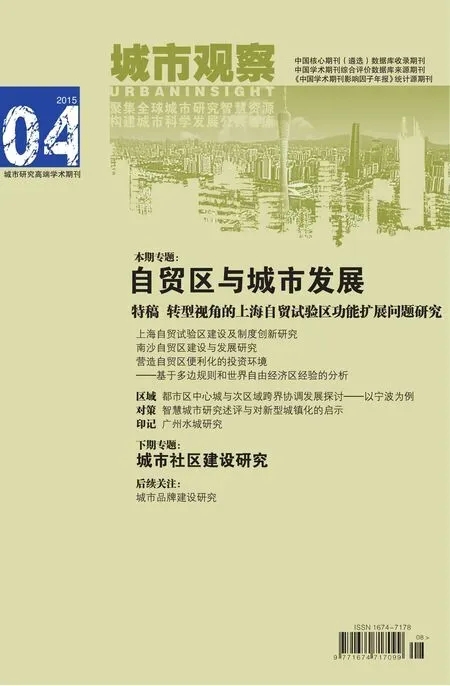符号消费逻辑下城市空间意义的转化——空间视域下的田子坊解读
◎蒋立业
符号消费逻辑下城市空间意义的转化——空间视域下的田子坊解读
◎蒋立业
摘 要:田子坊作为一个城市空间,它的再生与开发实际上不过是空间的意义再建构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创造出的文化意义,符合了当前文化消费的符号逻辑。因而,在经历了空间意义转化为符号消费对象之后它完成了商品化的过程。
关键词:符号消费 田子坊 空间意义
城市空间在当下的城市规划语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众多城市将其改造与升级同城市本身文化产业发展相联系起来。包括北京798以及上海田子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内的众多城市空间改造都颇具各自的特色。然而城市空间的转化与再生其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律、是否能发现其本身所共有的一种城市发展的本质性的特征?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田子坊作为上海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本身便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目前,该园区仍旧保持着一部分居住的空间功能,而并未像其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一样,以商业消费与旅游等功能完全挤占原有的空间功能。虽然对一部分居住功能的保留仍然引发了许多矛盾,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该园区的空间文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但事实上这样的居住空间在旅游体验的消费之下也日渐成为一种被观赏的符号化存在了(即对于旧有上海民居以及市井生活的观赏)。
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决策者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空间的转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该空间本身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资本参与对城市空间的改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在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的保留与资本对城市的改造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张力与平衡。
一、田子坊空间意义的产生与转化
田子坊位于原卢湾区(现为黄浦区)泰康路上,原名志成坊,始建于1930年。“田子坊”是1999年画家黄永玉为其取的
新名,以史记中记载的一位画家田子方的谐音为名。如今田子坊早已是一派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拥挤的街道中,来自全球的各色人种、不同年龄段的游客,被裹挟在熙攘的人群中,在这弄堂中游荡。弄堂两侧吸引他们的与其说是古老的具有各式风格的建筑,不如说是各式的店铺的招牌以及临街开放的酒吧与小店橱窗前摆放的五颜六色的商品和废旧的酒瓶。这就是田子坊如今给人的直观感受,各式的消费空间所展现出的色彩风格与老旧的房屋颜色作为背景所衬托出的琳琅满目甚至有些致人目眩的风格是它最大的特色。然而,作为游客的人们也许不会去想田子坊作为一个空间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
何谓空间的意义(这里指城市空间)?现代城市中的空间大多是以其功能划分的,无论是居住空间还是商业空间,然而在当代都市中这类空间也并非具有较为明显的区隔。空间意义指的是空间作为功能性场所的定位所传达出的一种观念。假如将空间看作城市当中的一种符号,那么由建筑所构成的物理外形,必然是它的能指,而它的功能却恰恰是它的所指。这里的“功能” 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一方面是空间的实际功能,而另一方面则是空间功能所传达出的意义,这种意义受到空间实际功能的影响关乎空间给人们的感受。通俗来说就是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列斐伏尔在提出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之后具体探讨了作为想象的空间和物理的实际的空间两者相结合后所产生的第三种空间批判的视角。而这里我们所探讨的空间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归为一种对于空间的想象。
早在租界时期,田子坊所属泰康路一带是法租界的南端与边缘,在这附近建有许多作坊式的小工厂,至1930年小工厂已经有30多家,基本上处于华洋混居的状态,同时空间功能的复杂化也使得该区域内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空间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区的石库门建筑被收归国有,进而被分配给各单位的职工,同时导致原本一户人家居住的房子住进了五六户的人家。①而20世纪90年代产业功能调整之后,里弄工厂效益逐渐下滑,导致整个空间原有功能的衰落,空间内基础设施老化。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田子坊空间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保持空间运作发展的产业结构的衰退便是空间当中生产方式变革所需要面临的悲惨处境。而实现空间的再生所需要做的应当是为空间重新确立意义的过程,即重新表征空间存在的过程。陈逸飞、尔冬强等艺术家在1998年开始进驻田子坊,重新将老旧的厂房加以利用,从而将其变为工作室进行艺术创作与实践。
当初陈逸飞选择田子坊的时候,是看中了它独具特色的建筑结构和极具生活气息的老上海市井氛围。然而在进驻之后他所要做的事情则是主动参与到了对于空间的改造过程中。在租下了第一个厂房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工作室空间不断扩展。
“陈逸飞选中的老厂房面积大约有800平方米左右,在开设了自己第一个工作室后,陈逸飞又把楼上难以为继的公共浴室也租了下来,经过装修,变阁楼为展示室,下面则安置了瓷窑。”②
不仅如此,陈逸飞还同时参与到街道具体的改造空间内部环境与居住设施的工作中,当然这其中的过程不仅包括饶有趣
味地为了弄堂里的垃圾去居委会的投诉,同时也有颇具商业头脑地租下更多厂房进行经营的决策。事实上最为重要的是陈逸飞等人作为艺术家参与到空间的再建构过程中去了。他们自身的艺术家身份,以及独特的审美眼光与气质为空间的再建构提供了更基础的再建构方向。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空间意义重建的过程。
城市中最讲求的是集聚效应,现代城市本身也是人口集聚的产物。在田子坊空间内部由于陈逸飞、尔冬强等著名艺术家的进驻,越来越多的画家群体开始关注并进驻到这个空间之内,而陈逸飞本人也为这些画家的到来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在陈逸飞之后,最早来到田子坊的画家是王劼音先生。2001年,王劼音将自己的画室搬进了田子坊。”“田子坊画家楼的规模并不大,五层老厂房里,其实只有下面的三层每天开启着画家工作室的大门……虽然同时只能容纳不到百位画家,但十年中在画家楼里进进出出的画家,却有三百位画家之多。许多画家来过,走了,过段时间又来了。来了不走,便成为田子坊里的主人。走了的,还想回来,是希望最终仍然可以成为田子坊的主人”。③
除了画家之外,更多的艺术家与创意工作室开始在田子坊中集聚。画家艺术家工作方式的独特性,以及陈逸飞本人对该空间有意地进行塑造的过程,使得田子坊逐渐变为了一个都市中颇具艺术风格的“飞地”,而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不仅有艺术家的创作,同时还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在考察画家选择田子坊作为其创作基地或者说驻扎点的原因时,我们能够发现其中有不少的画家对它的都市地理位置、内部生活气息、空间建筑特色情有独钟。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包括刘伟光、杨兴雅、明丽华、雷振华等人,均是从浦东的画家村迁入到田子坊之中的,如上文所述,一方面的原因是田子坊本身的空间气息(这其中自然包含着独特的历史建筑风格同时也包括一种生活气息在内)对艺术家们的吸引,关于画家们为何选择田子坊,沈纯道先生在《田子坊的画家群落》一书中,有一段精确的总结:“陈逸飞崇尚唯美艺术,把视觉艺术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现时的画家,之所以选择田子坊,正是认同了这样的定位,他们没有去莫干山50号,因为那里的艺术太当代;他们没有去文定路,因为那里的绘画太装饰;他们没有去大东方,因为那里的风格还没有形成,谁去都可以。唯有田子坊,给每一个到达此处的人们一种现实的感觉、唯美的享受。”④
另一方面,则是与陈逸飞对这个空间的改造付出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些画家既需要上海这个具有开放窗口的都市,同样也需要在都市之中找到自身的容身之地。他们所希望的是在被迫离开浦东画家村的同时将田子坊看作了一个新的艺术家乌托邦。
杨兴雅曾经面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表述他来上海的理由,“上海市是走向世界的窗口,我需要这样的窗口”⑤。
早期进驻田子坊的画家们用自身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身份挽救了田子坊这个即将衰弱的空间。而田子坊作为空间的意义也开始发生了转化,从一个濒临破败的后工业时代空间景观的遗产与具有地方特色的
市井文化的混合物到一个艺术家聚集其中并且不断地被美化的颇具理想特色的乌托邦空间。在这一个阶段之内,空间的新意义被逐渐树立了起来。这个意义或者说此时,空间的所指就变为了一种不断变化的乌托邦范畴,而作为一种乌托邦的范畴其最重要的特点即是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即列斐伏尔所说的第二空间之中)。田子坊空间的乌托邦范畴则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
1.带有互助性的有明显的身份标示的群体与都市冷漠人际关系的对立。
2.艺术创作与世俗生活的对立。
3.现代化都市文化与内部市井邻里文化的遗存的对立。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规划者们如何强调,对于空间的物理改造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假如这个空间不具备它自身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改造终究不能挽回空间衰败的局面。
当代城市空间的开发不同于以往,开发这个词本身就是资本运作的方式,以当代我国城市最普遍的现象为例,城市空间被开发商购买之后,那么这个空间必然已经被当作原料买进了,而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被当作商品进行分割出售,无论是楼盘还是商铺,概莫能外。然而消费主义的逻辑关心的是对于商品在出售前符号化的表征过程,我们必须用广告的方式对其进行推销,而无论楼盘还是商铺的开发,抑或是小型的消费空间例如咖啡店以及剧场,空间商品化之后它自身的功能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商品进行包装,即对其进行符号化的过程。鲍德里亚指出:“越来越多的需求、需要欲望被带进了意义王国,个体丢失了控制权,屈从于代码符号潜在的重要性使社会变得井然有序,同时使个体产生一种自由和自我决策的幻觉。”⑥
我们消费商品已经不是消费商品本身而是商品被表征成为的那种符号,因而对田子坊的开发必然也具备一种商品符号化的过程,因为这是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的基本逻辑。这样的一个过程随后在田子坊也上演了。
二、符号消费逻辑对空间意义的利用
在经历艺术家群体自身对于空间自觉以及不自觉的改造过程之后,田子坊作为一个空间的新意义逐渐生成了,而这个新的空间意义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根据符号消费的逻辑被资本介入并重新包装了起来,成为了一个被消费的对象。
在李挚的《自下而上的旧城更新模式研究——以上海田子坊为例》中,作者将田子坊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总体上,田子坊的自主更新在空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 1998 年至 2004 年工厂区内艺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酝酿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之后“田子坊”概念扩展,居民区全面开放,商业蓬勃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从入驻的产业形态变迁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8年至2004年底左右的第一阶段,以艺术圈内人士为主;2005年至2007 年第二阶段,以小圈层游客进入为标志;2007年之后的第三阶段,大众知名,成为旅游之地”。⑦
从时间上来看,田子坊真正开始被推广,同时进驻的商业开发主要是在第二阶
段,由于第一阶段艺术家的进驻与活动本身为空间带来了新的意义,一种城市乌托邦气息使得空间本身极具包装与推广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完成了它的第一步的转化,空间成为了商品,而空间的新意义成为了商品符号化的对象,具备消费的价值。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空间内部房租的急剧上涨。城市开发的资本逻辑被表现了出来。
在集聚效益的催生之下,城市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和现象就是房租的持续上涨,由于田子坊的商业区位优势。加之其本身的由于艺术家集聚所创造的文化价值,自然比城市之中其他的空间具备了更多可被消费的可能性。然而,随着空间的集聚导致的房租价格的不断上涨,居民对于利润的追求更加浓厚,使得一部分不具有市场潜力的画家群体不得不逃离这个空间。艺术家所追求的那种超然的创作空间,以及蛰伏以期待融入市场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多元化的产业模式已经将田子坊完全变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商业开发的空间,随后带来的就是不少艺术家工作室逐步的退场,将位置让位于资本。2012年《上海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尔冬强艺术中心难以承受租金 无奈告别田子坊》的报道。而在2012年3月20日的《常州日报》上刊登的名为《异彩夺目:田子坊的画家群》一文中也写到了一名叫姜昱的画家因租金问题而无奈离开田子坊的事实。作为一种空间意义被符号化消费的结果,以上的事实给出了最直接的表达。
城市开发过程中的空间生产,开创了一种新的资本介入方式,不同于普通城市那种硬开发模式即对物理空间的改造,资本的软介入所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当一个空间具备经营价值时,这个价值事实上就是空间意义本身是否具备市场化的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化过程中的品牌效应。资本开发的重点就是将这个空间意义编码后投入符号消费的市场之中。2006年5月3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题为《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进入品牌竞争 “田子坊”品牌效应日趋显现》的报道。田子坊本身的品牌符号消费价值开始具体呈现出来。
随着空间意义进一步被包装入一个品牌之下,那么这个品牌便成为了一个可被消费的符号。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集聚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不仅仅是创意产品的生产与经营,更多的还有高端的设计公司,以及不断增加的餐饮与服务行业,共同构成了当前田子坊本身空间运作的产业基础与支柱。原有的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仅剩下的是被消费的意义,同时也包括一部分能够融入市场化运作的某种程度上成功的艺术家个体。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餐饮与服务业的兴起事实上是针对日益增多的以体验为目的的游客群体。如此田子坊完成了它的商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空间的生产。
三、符号消费逻辑下的历史空间建构的本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工业社会文化消费的浪潮之下,空间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生产方式以及活动的存在场所,而逐渐变为了一种加以购买和占有的商品,消费空间这样一种行为一方面包含着对于空间意义的感知与体验,另一方面同样也包含着借助空间进行自我表征的过程。在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生产首先成为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行为,而消费则是以购买的方式对空间实施占有的过程,然而人们在对空间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本身也是参与空间建构与意义传播的过程。从田子坊的意义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画家群体、艺术家群体参与对其的改造过程来说,本身是一个较为良性的并且是具有极高审美天赋与能力的人们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创作活动,这个活动本身甚至比创作巨幅的壁画教堂装饰的天顶更为伟大,因为他们利用自身独特的审美能力作为在场者,参与到了对社会本身的建构以及空间的重构过程中。而这样的一种改造正如前文所述是田子坊意义变化以及其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特殊空间而区别于周围街区的第一次尝试,在这之后,在城市土地开发的浪潮中,田子坊借助被艺术家群体所构筑起来的独特文化意义,而获得了新的开发模式,政府通过整合多方力量将田子坊打造成为创意园区。
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城市对于老城区的再生开发没有更好地把握第一阶段的实质,而往往是从类似田子坊开发的第二阶段直接做起,当代城市空间的开发重要的是如何为空间寻找一个确定的意义。无论是对物理空间的硬重构还是资本的软介入最终都离不开对于空间意义的营销。当代对于空间的消费首先是文化消费,而文化消费的实质是商品拜物教中所传达出的那种对于商品符号的消费与占有。而符号的表征自然也离不开对于其所指范围的确定性。城市作为一个空间,它的推广同样也应当遵循这样的逻辑。因为我们当下的世界是依靠传媒所构筑起来的。而活跃在传媒网络之中的恰恰是观念,符号作为观念的表征形式自然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回顾田子坊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想在城市之中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已经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因为在理性的理想国中,根本没有前者的容身之地了。但画家也必然要参与到市场的浪潮中去,要获得认可,如何在空间开发的过程中既利用类似画家群体所创造的独特空间意义,创造商业价值从而复活一个历史性的街区,又能够在商业气息与文化气质之间保持良性的张力互动,我们仍然有很多路要走。就在不久前,《北京晚报》有一则消息,说的是南锣鼓巷因商业气息太过浓厚而落选历史文化街区,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注释:
①同上。
②沈纯道.田子坊的画家群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
③沈纯道.田子坊的画家群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3.
④沈纯道.田子坊的画家群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3.
⑤沈纯道.田子坊的画家群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2.
⑥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44.
⑦李挚.自下而上的旧城更新模式研究——以上海田子坊为例,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卢小文)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Significance under Symbolic Consumption Logic: An Interpretation of Tianzif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Vision
Jiang Liye
Abstract:As an urban space, Tianzifang’s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virtually a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cess to creat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s in line with the symbolic logic of current cultural consumption. Therefore, Tianzifang has accomplished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spatial significance to the object of symbolic consumption.
Keywords:Symbolic Consumption; Tianzifang; Spatial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蒋立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 24 doi: 0.3969/j.issn. 674-7 78.20 5.04.0 8
——以上海田子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