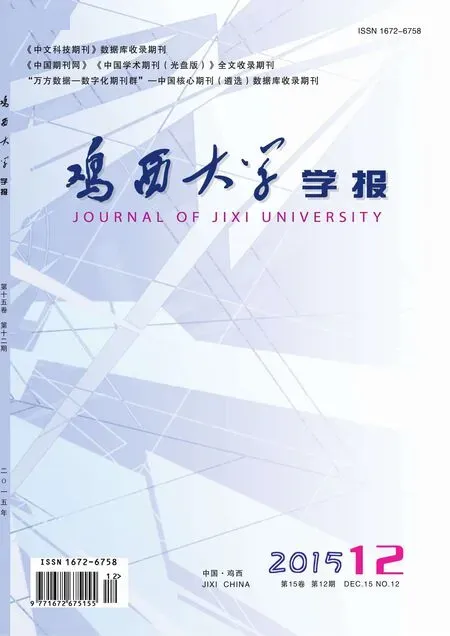论北宋初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
王 通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宋初三朝,上承五代,下接庆历时期,是宋代文学风格形成的过度时期,在古文运动这一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无疑十分重要。纵观这一时期的散文,我们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作者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以求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乃至整个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有更细致深入的把握。
一 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现象
翻阅宋初三朝的散(骈)文,虽然作家风格各异,有一个现象却相对统一,即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上重儒家思想与创作上重词采的矛盾。
北宋初年相当一部分作家在理论上反对五代以来片面重文而不顾思想内容的文风,标榜儒道,强调文章的道德教化作用,有些作家甚至因此提倡韩柳散文,然而在实际创作中依然以骈体文为主,主要将精力集中于文章的声律、文采上,与他们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北宋初年文坛普遍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作家们在理论上强调儒道在文章中的核心地位,提倡文章应具有政教意义。宋太祖在建国之初就要求臣子的进策“情绝虚浮”“不得乱引闲词”,务必做到“事关利害”“易国便民”,[1]册1,94着重强调文章的政教作用。徐铉认为:“苟泽及于民,教被于物,则百里之广,千室之富,斯可矣。与夫杨、孟之徒,坎轲闾巷,垂空文于后世者,不犹愈乎。”[1]册2,174-175在他看来,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要远比文采重要,而杨雄、班固那种劝百讽一、重文轻道的文风是不可取的。凡此种种,都证明了重视儒道、反对片面重文的主张在北宋初年是相当普遍的。
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多数作家则依然将精力集中于声律、文采,于五代片面尚文的风格并无明显不同。对柳开的古文大加赞扬的王祜,他的文章被徐铉评论为“音韵调畅,华采繁缛……观其丽而有气,福而体要……如四子复生矣”,[1]册2,196初唐四杰总体上也是继承了南朝以来的繁缛风格,可见王祜实际的创作还是以声律辞采为主。稍后的西昆体诸作家,更是将华丽文风发展到了极致,正如元人刘壎所言“我宋盛时,首以文章著者杨亿、刘筠,学者宗之……然其承袭晚唐五代之染习,以雕镌偶俪为工,又号曰‘西昆体’”,[2]并且这种文风成为了一时文坛竞相仿效的主流。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创作风格,大多还是承接晚唐五代,作家们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声律文采上。
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重视儒道,标榜文章的政教价值,反对片面的重视辞采华美,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却还是在延续五代以来骈俪繁缛的风格,对文章的思想性有所忽视,理论与创作无疑存在着矛盾。
2.理论上要求符合中庸之道与创作上偏激风格的矛盾。
北宋初年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还体现在作家理论上要求文风和思想内容都要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却往往呈现出极端、偏激的风格。
宋北初的作家在文学理论上大多讲求中庸之道。王禹偁在评论黄宗旦的《正汉臣对策》时说:“文义诚为高古,其间责晁错不言王道,而谓汉文几与王道;以史传较之,责晁错太重,褒文稍过耳”,[1]册7,391作文不应该立论偏激,而应该取中庸之道,做到情感的诚,内容的信。为了追求中庸之道,北宋初年的作家进一步主张温柔敦厚的雅正文风,宋初名作家张咏不但认同作文在思想内容上符合纯儒,在行文风格上更是要求“参古之正辞”,若“好古以戾”,则“非文也”,若“好今似荡”,亦“非文也”,[1]册6,120追求一种非“戾”非“荡”文质彬彬的“正辞”,其对雅正文风的主张可见一斑。以上材料均证明了北宋初年文人散文理论上理论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
然而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些主张中庸之道的文人却大多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柳开的创作多浮夸偏激之处。柳开将杨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一事曲解为杨雄对王莽的讽刺,为赞美辩护自己所建立的道统,不惜歪曲事实,在另一些篇章之中,毫无愧色地直言自己是孔孟的传人、当代的圣贤,这种种现象都和他雅正文风的理论追求相去甚远。穆修也是如此,他在《毫州魏武帝帐庙记》中热烈赞扬曹操“挟持汉室”的行为,这与儒家“君为臣纲”的忠义的观念背道而驰,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于名教……显然以乱贼导天下,尤为悖理”。[3]卷152,94柳开与穆修,作为北宋初年古文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行文所具有的这种偏激的风格,无疑代表了这一流派当时的一些创作共性。
因此,散文理论上重视纯儒的中庸之道,而创作中却流于浮夸偏激,这种矛盾在北宋初年的文坛上也是普遍存在的。
3.理论上要求语言平易与创作上语言艰涩的矛盾。
北宋初年散文理论与创作上的矛盾还体现在,许多作家,尤其是古文家理论上要求作文须平易晓畅,反对辞涩言苦,然而在实际创作中语言一味模拟古代经典,造成文章晦涩难懂。
纵观北宋初年的散文创作,追求平易、反对艰涩是十分普遍的。柳开在《应责》一文中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长短,应变作制,同古人之形式,是谓古文也”,[1]册6,367他认为,其要求只是清楚地表达“意”而已,因此应文从字顺,长短多变,灵活自由。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如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1]册6,396既要求文章要通顺,又要求所表达的思想要清晰准确。
然而实际创作之时,许多作家跟其提出的理论产生了矛盾,文章往往写的文脉不畅、晦涩难懂。柳开作为道统派古文家的领袖,就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其文章对经典的语言机械地模仿,造成文章文脉不畅,词句生僻古拙,一些篇章往往省略不当,指代不清,真正走到了其理论的反面。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见闻:“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适见有奔句马践死一犬……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景曰:‘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4]这一见闻不但说明了穆修、张景等古文家作文的晦涩难懂,还说明了这种文风“当时已谓之工”,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坛的整体风尚,诚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言:“柳开、穆修、张景,当时号能古文……可见当时以偶丽工巧为尚,而我以断散拙鄙为高……彼怪迂钝拙,用功不深,才得其腐败粗涩而已。”[5]
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文坛,理论上理论上要求语言平易与创作上语言艰涩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
二 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形成原因
由以上论述可知,北宋初期散文理论与创作之间存在矛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应该与北宋初年特殊的文化环境、文人心态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试论之。
1.对晚唐五代文风的因袭。
由纷乱的五代入宋,文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环境自然会产生对文章新的要求,然而创作总是滞后于理论的,在晚唐五代早已形成惯性的文风在北宋初年被因袭,这是造成北宋初年散文理论和创作矛盾的原因之一。
晚唐文人身处末世,无心如韩愈般高举道统大旗,文人环境和心态的变化使唐代的古文运动也走向了低潮,很多晚唐文人重新将道与文割裂开来,文坛出现了重文轻道的现象,李其中李商隐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6]肯定六朝文学成就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重文轻道、尚骈文的倾向,在五代时期更是变本加厉,科举“中场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7]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虽然骈文重新占领了晚唐五代的文坛,古文创作却从未曾停止,少数好古尚道的文人仍然在坚持。然而失去了政治、学术环境的古文创作,也走向了歧途。正如李肇所言:“元和以后 ,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8]樊宗师、皇甫湜的尚奇、尚古的倾向,被晚唐五代的文人自觉地继承下来,并变本加厉地发展为奇奇怪怪、泥古不化的文风,在文章的思想内容上,晚唐五代的古文家也往往流于空洞,多是对道口号式的呼喊。
北宋初年的散文家,大多由五代入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因袭着上述风气。四库馆臣就在评价徐铉的散文创作的时候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徐铉)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3]卷152,94阮元将也北宋初年的文坛概括为:“骈俪之文,斯称极致,赵宋初造,鼎臣(徐铉)大年(杨亿),犹沿唐旧”,[9]这些都可以证明以徐铉、杨亿为代表的大部分北宋作家对晚唐五代文风地因袭是十分严重的。另一方面,如柳开、张景、穆修等少数坚持古文创作的散文家,他们在创作上奇奇怪怪、文辞艰涩的风格,也明显地继承了晚唐五代古文的文风。因此无论骈文还是古文,北宋初年的作家整体的散文创作都对晚唐五代的文风有着明显的因袭,虽然北宋初年的文人在散文理论中也反映了时代的变革要求,然而创作的惯性,并不完全受到理论的约束,造成了理论与创作的矛盾,因此对晚唐五代文风的因袭,是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之一。
2.作家思想杂驳。
众所周知,一个作家的文学理论或是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个作家的思想构成。北宋初期许多散文家的思想构成比较驳杂,除了纯粹的儒家思想之外,往往参杂了其他思想,这种思想的驳杂反应在散文理论和创作上,成为了造成理论创作矛盾的又一个成因。
北宋初年紧承五代,文人的思想上往往带有乱世的印记。乱世对儒家思想道德的破坏是十分巨大的。五代时权利多为武力强大、心狠手辣之人所篡夺,整个时代对于儒家思想和文化艺术都持一种轻视的态度,后汉大臣史弘肇的一句“安朝廷,定祸乱,直需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就是最好的例子。[10]
在这种环境下,知识分子不再去讲求坚守名节,呈现出避祸全身、朝秦暮楚的特点。这种思想倾向一直延续到了北宋初年,数朝宰相冯道就例证,他“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11]而在北宋初年,冯道的人生却被士人看做典范,北宋初对五代士风的承袭可见一斑。而这与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背道而驰了。因此在北宋初年,许多作家的思想中既有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同时也掺杂着避祸全身、游戏人生的消极思想。
与此相联系的是,追求避祸全身的文人,自觉地亲近宣扬出世理想的佛道两教。道教方面,正如学者卿希泰所言:“自晚唐五代入北宋以来,道教内丹术渐次兴起,丹家辈出,如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皆为著名代表”,[12]当朝的文人大多亲近道教。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宋初名臣张咏,曾经“欲学道术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无仕志”,[13]出倾心于学道之外,他与许多当时著名的道士都有着密切的交往。佛教的情况也与道教相类似,自隋唐以来逐渐兴盛的禅宗对北宋初年的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王禹偁曾说“坐禅为政一般心”[14]“夫禅者,儒之旷达也”,[1]册6,72晁迥更是自觉地将儒释道三者与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先驱。在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文人思想的构成早已不再是纯正的儒家思想,因此他们标榜的道也多在儒道的基础上渗入了佛家与道家之道。
另一方面,许多北宋初年的作家,尤其是北方文人,继承了五代时期崇尚暴力与权势的流弊,染上了粗豪野蛮的习气。以柳开为例,虽一向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却做出了“生脍人肝”的残忍行径。同样主张尊儒复古的张咏,也是一例,他被陈抟评价为“性度明躁”,[13]无论是他好击剑并手刃数人的史实,还是在蜀中吃馄饨的趣闻,都足以证明他粗豪急躁的个性。无论是柳开还是张咏,他们的行为相比于儒家“文质彬彬”的追求,可谓“谬之千里”。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一部分散文家的思想之中,既有温柔敦厚的儒家思想,也掺杂着五代崇尚暴力,野蛮粗鄙的一面。
总而言之,正是这种思想的杂驳,造成了散文家在提出散文主张时,理性地或者惯性地标榜纯儒精神,而到了实际创作时,却不经意地流露出其思想中的异质成分,实为造成北宋初年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原因之一。
3.行道意识的缺乏。
散文的发展,还与学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正如陈植锷先生所言:“在北宋文化史的各个层面中,与儒家学派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代散文……古文是宋学传播与传承的主要工具,北宋古文运动是儒学最重要位置上的学者……站在儒学最重要位置上的学者,往往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15]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北宋初年的散文,我们会发现,宋初知识分子行道意识相对缺乏,也是造成北宋初年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重要原因。
北宋初年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即官方学术和私人学术。官方学术代表着当时学术的主流。北宋初年编修的学术著作多是注疏、正义类著作,依然以汉唐以来重视文字训诂的治学风格为主要特色。以邢昺、杜镐所著《论语正义》为例,此书“依循孔颖达《五经正义》的精神,以何晏《论语集解》作为底本,删削皇侃的《论语义疏》,加上邢氏的发明”而成的,[16]因袭色彩失分浓重。延续上百年的治学之风,已然流于死板,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儒生们多囿于章句制度的考证,极少能突破注疏去追寻经典的义理,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无疑将经典与读书人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
私人学术方面,一些学者已经敢于突破官方学术的局限,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风气。学者们开始怀疑传注,以己意阐发经典的义理,然而这种新的学术风气尚处在萌芽阶段,当时私人学术的代表人物,大多破大于立、流于片面和武断,种种问题也局限了当时文人对道的弘扬与践履。当时私人学术的代表人物柳开和王禹偁在对经典的解释上都存在武断的问题,又如王禹偁在《五福先后论》中,没有根据地不满《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五福”的排列顺序,并把事先确立的尚德的观点强加在可能并无意义的“五福”的排列顺序上。柳开在《达臧丙第三书》中说:“夫圣人之道……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得之不能备耳”,[1]册6,298直接否定了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进而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圣人是命中注定的,这无疑间接地否定了学习修身的必要性,进而割裂了儒家经典与士人现实生活的联系。这种对学习、修身、成圣粗浅的理解无疑对当时知识分子行道意识的弘扬起了反作用。
保守的官方学术与尚不成熟的私人学术,都没有很好地将儒道与社会现实、个人修养联系起来,这无疑造成了知识分子行道意识的缺乏。正如上文所言,学术与散文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北宋知识分子行道意识的缺乏体现在了散文的创作中,也就造成了散文理论践行意识的缺乏,作家无法很好地将散文理论实现在其创作之中,自然造成了理论与创作的不同步。因此,行道意识的缺乏无疑是北宋初年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认识价值
北宋初年作为宋代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现象无疑有许多意义与影响可以发明,以下试论之。
1.限制了北宋初年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北宋初年,各派散文家为革除五代流弊、振兴文学做了可贵的尝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代的创作从贯穿唐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的进程来看已然处于低潮期,作家们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无疑限制了他们的成就。
一方面,理论本身的漏洞局限了实践,北宋初年作家对儒道认识的漏洞限制了他们的革新,以创作骈文为主的作家,虽然也高举儒道的旗帜,但是他们将道理解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柳开张景等人,则往往流于空洞的鼓噪。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是柳开主张圣人是天生的,非学能致,还是骈文家标榜歌颂王德,对儒道的标榜,更像是争名夺利的一种手段。因此,无论从对儒道认识的深刻程度上,还是从对儒道的态度上,北宋初年的文人都有着诸多缺憾,这种不足无疑无法赋予当时浅俗的文风以深刻的思想和严肃的文学观,因此也就限制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另一方面,实践没有成功地贯彻理论。以创作骈文为主的作家在创作上仍然延续五代风格,自然不会在创作上对古文运动做什么贡献,而主张文风改革的古文家如柳开石介等人虽然表示过,作文要文从字顺,不能文辞艰涩,然而在实际创作当中,片面重道,轻视文章的词采,造成文章难以卒读,抹杀了散文作的艺术性,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没有文采的散文创作自然不会取得什么成就,而且也会对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也就限制了古文运动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总结起来,理论和实践、对文和道的理解以及二者关系的处理,种种问题,在北宋初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无疑限制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2.为庆历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树立了目标。
北宋初期的散文创作在矫正五代文风士风、重振儒学道等方面的可贵探索为庆历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指明了方向,而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存在的诸多不足与局限又为庆历时期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训,这一反一正两方面无疑庆历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初年柳开王禹偁等人对儒道的重视以及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为庆历文人指引了方向,庆历文人沿着这些宋初前辈的道路继续前进,对北宋初年文人提出的诸多儒学命题与观点进行了更加细致精深的探索。北宋初年文人,激烈批判当世无人行道,强烈地呼唤行道精神,庆历文人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更加细致深入地探讨如何行道,使道德践履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对于知识分子个人修养也更加具有指导意义,孙复在其著作《春秋尊王发微》紧密地结合了当时的现实,提炼出了“尊王”“华夷之辨”等思想作为春秋大义的核心,张载、周敦颐等人将儒家道德于个人心性、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提出了性理之学。行道意识的自觉、儒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对散文的创作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它使得散文理论中的所崇尚的道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指导创作的意义,而这种杰出的探索正是以北宋初年文人开辟的方向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北宋初年文人对于文道关系的不恰当处理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引起了庆历时期文人的反思,欧阳修对北宋初年文人“溺于道”和“溺于文”的现象都提出了批评,[1]册33,58并从经典中找到了肯定文采的依据,如“《诗》《书》《易》《乐》《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1]册33,79他崇尚一种文道并重、文质彬彬的散文风格,并且在庆历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使古文运动走向了高峰,而成就的取得与北宋初年散文家的勇敢尝试是分不开的。
3.宋型人格的初步形成。
陈植锷先生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曾将宋代知识分子与汉、唐知识分子相比较,指出宋代知识分子有“兼擅经术、文章与吏事”[15]的特点,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与历代不同的宋型人格。而北宋初散文家骈文家的理论与创作,正体现了集“经术、文章与吏事”初次尝试,对后来稳定的宋型人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代重视儒生,唐代重视文士,三者的身份泾渭分明。北宋初年这种“经术、文章与吏事”相分离的状况还多有体现,赵普作为宋初两朝重要官员就被评论为“少习吏事,寡学术”,[17]这与三者兼备的宋代典型知识分子人格无疑有着很大的差距。
而北宋初年的散文家与前代相比,不再将儒者所弘扬的儒道与文士所追求的文采割裂视之,而是试图在散文中融合文章之学与经术之学。同时,这些散文家又多是官员,他们也通过自己官员的身份极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提拔后进,并将此视为其官员身份应承担的责任,王禹偁就通过自己的官员身份和文坛地位,指导和奖拔过许多后进,并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个提倡古文与古道的群体。从北宋初期散文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人格的新变,他们努力改变着五代不顾礼义廉耻不顾百姓疾苦的官僚作风,改变着视文学为游戏和争名夺利的手段的文学观,他们试图统一儒生、文士、官员三者,追求一种文质彬彬的新人格,虽然在他们身上还存留着过度时期的痕迹,表现出种种矛盾,但是没有这种可贵的尝试,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北宋初年的散文呈现出一种由五代散文向宋代散文过度的风貌,而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则是这种风貌的具体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前代的影响,又与当时的政治学术背景息息相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Z].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刘埙.隐居通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商务印书馆,1935.
[4]张富祥,译注.梦溪笔谈[M].中华书局,2009:162.
[5]叶适.学习记言序目[M].中华书局,1977:733.
[6]李商隐.樊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41.
[7]曾枣庄.二十四史全译旧五代史[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184.
[8]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7.
[9]王水照.历代文话[Z].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221.
[10]欧阳修.新五代史[M].中华书局,1974:552.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1956:9512.
[12]卿希泰.中国道教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35.
[13]释文萤.唐宋时聊笔记丛刊.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M].中华书局,1984.
[14]傅璇琮,等.全宋诗[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94.
[15]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6]唐明贵.邢昺《论语注疏》的注释特色[J].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09(1).
[1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8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