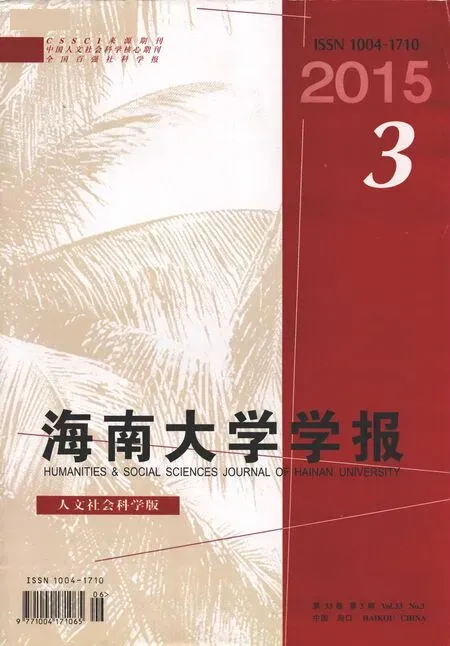从有机叙事到非有机叙事——吉尔·德勒兹美学视域下艺术叙事新探
李 坤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
一、超越有机叙事
任何一种艺术表达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时刻渗透着创作者自身对于世界的理解。不同的哲学观念、美学追求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表达,因此,当人们欣赏一部叙事作品时,绝不能忽略这种潜在的动力对于作品形成的深刻影响。对于西方的艺术叙事而言,长期以来隐蔽在其背后的是一种有机整体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强调任何一种叙事都要力图成为一个首尾相应、具有起承转合的有机整体。
艺术中有机整体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说道:“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1]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更是全面阐发了自己的关于艺术叙事的有机整体论。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个行动和一定长度保证了叙事的合法性,那么,“完整”又意味着什么呢?他解释道:“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起始指不必继承它者,但要接受其他存在或后来者的处于自然之承继的部分。与之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承继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继的部分,它的承继或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因为符合多数情况。中段指自然地承上启下的部分。因此,组合精良的情节不应随便地起始和结尾,它的构合应该符合上述要求。”[2]74此外,他还提出了“情节整一律”。其言:“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它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2]78可以说,这两段论述道出了整个《诗学》叙事的核心观念,其所围绕的中心是情节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强调其有机性和整一性。在此,不能不承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对有机整体的强调道出了艺术作品本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即叙事艺术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强调的联系是有机体内部的联系,并没有涉及到开放性问题。换言之,这是一种“向内”的联系。从哲学上来说,这种“向内”的联系之特征在于对主体性的确证,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对审美所力图实现的超越主体性的一面表现不足。当人只将焦点聚焦在自己身上,艺术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便会随之而来。在《诗学》之后,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了“合式”的有机整体论,文艺复兴时期卡斯特尔维屈罗提出了“时间整一”、“地点整一”与“情节整一”的三整一律,新古典主义的布瓦洛继承了卡斯特尔维屈罗的观点,用“理性”刺眼的光芒一度抹杀了艺术的自由精灵。
时至今日,这种有机整体论的思想依旧统治着叙事界。例如,对于故事的事件组合而言,“在开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在中间则成为了或然的,而到了结尾处一切都已经变成必然”[3]。这就是用一种人为的因果性过分强调内部联系的结果,于是便导致许多叙事作品看起来很过瘾,但看完之后却没有太多东西值得回味,因为它用“人工”代替了“天然”。又如,整一的有机叙事还造成了人物塑造的功能化倾向,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所体现,而在当代电影叙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认为的,结构即人物,人物即结构,“如果你改变了一个,就便改变了另一个。如果你改变了事件设计,那么你也改变了人物;如果你改变了人物的深层性格,你就必须重新发明结构来表达人物被改变了的本性”[4]。试想,如果不削平一个人物活生生的棱角,又如何将其置身于整一性的叙事结构之中呢?
然而,日常经历的事件并不是按照某种单一、必然的逻辑依次排列的,鲜活的人物也绝对不能被简化为功能性的符号。这种简化的行为之所以发生,从哲学根源上说是因为我们只将视线局限于有机体及其内部,而未能从一种更为宏观的大生命观来理解生命与艺术。对此,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让人们有了超越这一局限的可能。
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器官身体”呢?从字面上看,它似乎意味着一个没有任何器官的身体,但这显然属于望文生义,因为如果身体没有器官,那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就没有任何生命性可言了。德勒兹认为,“无器官身体”不是器官的对立面,它的真正敌人不是器官,而是对器官的组织,它“不与器官相对立,而是与那种被称作有机体的器官的组织相对立”[5]220。德勒兹援引威廉·巴斯勒《裸餐》表达了对有机组织的愤慨:“人类的有机体就是一个可恶的无效之物;为什么人们有一张嘴和一个肛门——它们都具有失调的危险,而不是只拥有唯一一个多用途的孔洞,它可以用来吃饭和排泄?我们可以将嘴和鼻子封死,将胃填满,并直接在肺上穿个通气的洞——从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干。”[5]208事实上,“无器官身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不确定性的方面来说,“没有器官的身体并不缺器官,它只是缺有机的组织,也就是说缺对器官的组织”;从确定性的方面来说,“没有器官的身体的定义并非是器官的缺乏,它并不仅仅因为器官不能确定而得到定义,说到底,他是通过确定的器官的暂时的、临时的在场而得到定义的。”[6]50-51由此,“无器官身体”:首先,它不是没有器官的身体,而只是器官不发挥日常功能的身体;其次,“无器官身体”不是组织好了的身体,即不是很好的有机化了的身体,但同时,它也不是完全脱离有机的身体,因为它还需要器官临时的在场。质言之,“无器官身体”既是“变动的身体”,又是“临时的身体”,始终在“组织化”和“去组织化”、“有”和“无”、确定与不确定之间进行永恒的摇摆,其蕴含着生成性、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比如,在《感觉的逻辑》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德勒兹就阐述了作为器官的“手”在与外界复杂多变的交流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方面。同样作为对身体状态的一种“整合”,有机的身体把器官之间的界限和功能都当作是人所固有的、先在的、理性的本质;而“无器官身体”则将器官放回到身体“原始”的生成状态来理解,其联系是临时的然而却是更为本质的。
如果说有机体的视角强调的是一种“人类视角”,那“无器官身体”则可以称之为一种“宇宙视角”,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用人类中心的眼光衡量万物,另一个则呈现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展现德勒兹所说的“非有机生命”(nonorganic life)[7]。马克·伯恩塔等指出,“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更加确切的解释其实就是“非有机组织论的身体”[8]。如果将这种“非有机的生命”观引入到对于叙事的理解,就会发现一种“非有机叙事”(nonorganic narrative)。相对于有机叙事中的“故事线”,从非有机叙事中抽取出的是一条“逃逸线”(a line of escape)。逃逸,是为了远离一个或几个固定的中心,对现有的、既定的疆域进行“解辖域化”,释放边缘的力量,让“虚假”成为真实。所以,德勒兹特别推崇一些所谓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叙事。文学领域中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伍尔夫、梅尔维尔、惠特曼,电影领域中的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阿伦·雷乃等人都是他所青睐的艺术家。需要指出的是,非有机叙事并不与有机叙事对立,它与有机叙事其实是一种互补关系,因为“人类视角”总是包含于“宇宙视角”之中,非有机的生命既是有机生命的开始,也是其完结,并时刻伴随着有机生命的生成过程。也正因如此,对于艺术而言非有机叙事就显得更加的神秘与迷人。
二、非有机叙事的艺术特色
从逻辑上说,艺术作品可以被划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对应在叙事中就体现为故事和话语。然而,在实际中内容与形式、故事与话语始终是融合在一起的。用不同的艺术媒介讲述所谓的“同一个故事”是不可能的,正所谓“媒介即讯息”,当人们改变了表达的外在形式,其呈现的信息和内容必然也会跟着变化。由此观之,只具有非有机的形式或只表现非有机的内容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对非有机故事内容的表达注定要通过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的叙述话语加以呈现;另一方面,新的叙述形式也会自然而然地表达着全新的故事世界。质言之,二者是一个相互交叠、不分你我的“皱褶”,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共同造就了非有机叙事的艺术魅力。因此,笔者在此并不准备采取一种故事、话语二分的叙述策略,而是试图以时空观、事件观、人物观三方面为例来一窥非有机叙事的艺术特色。
叙事是时间的艺术,但是叙事中的时间却可以有不同的面貌。对于传统叙述来说,不管是平铺直叙,还是通过倒叙、预叙等方式,最后几乎都能被还原成一条线性时间线,即先有过去,再有现在,再有未来,三者就像是三个不同的点被依次排列在同一条线上。表达这种时间观的叙事艺术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对于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时间观,德勒兹予以了深刻的质疑。德勒兹站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尤其是依于法国另一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相关研究,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时间就是一道永不停息的绵延之流。德勒兹认为,“现在”或者“当刻”是一个正在流逝着的“当刻”,换言之,“当刻”在它还是当刻的时候就必须已经“流逝”,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言说“当刻”或“现在”时,“过去”已经在场[9]。同理,“未来”也已经到来。申言之,任何“当刻”或“现在”,都是包括着“过去”和“未来”的。换言之,先有过去、再有现在、再有未来的线性时间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日常时间观,而这种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非线性时间观才是宇宙时间生生不息的原貌。如果前一种时间观是一种日常时间,那后一种时间观则可称之为“纯粹时间”。不难看出,这种“纯粹时间”就是非有机的生命,或者说,非有机的生命呈现出的就是这种“纯粹时间”。因为它们都要破除暂时的确定性,而要呈现永恒的“生成”与变化,“正是生成的同时性逃避了当下的在场”[10]。由是,非有机叙事就是要呈现这样一种本然的时间观。塔可夫斯基的《镜子》便是一个经典范例。本片从形式上来说由以下元素构成:新闻片、泛黄的影像、彩色影像、叙述者的讲述以及诗歌独白。这些元素从逻辑上讲可能意味着:新闻片和泛黄的影像呈现过去的事情,彩色影像倾向于现在,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塔可夫斯基的化身,而诗歌独白则代表着作为诗人的塔可夫斯基的父亲。然而,在影片的进程中,各个元素相互交叉、生成,原有的清晰划分开始变得模糊,过去的事情开始呈现出色彩,现在的事情也出现在泛黄的记忆之中,时间成为了多元维度的综合。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有一场母亲洗头的戏,塔可夫斯基通过精湛的视听手法让自己年轻的母亲和年迈的母亲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当中,此时已经无法抽离出线性时间的脉络。
在这种非有机时间观的影响下,叙事的空间组合典型地体现为“脱节空间”(disconnected)和“空的空间”(emptied)[11]。在阿伦·雷乃的《天命》中,克劳德前去看望情人,但当他从情人所在旅馆的阳台推门而入时,却进入了自己的家,并和家人吵了起来。而当他走出自己家时,却又转到了旅馆的阳台上……此时,空间的衔接失去了日常逻辑的支撑。如果说空间的常规连接是为了让整个叙事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那么,“脱节空间”就是为了打破这个整体,释放出一个更为广袤的非有机的全体。逻辑空间衔接出的整体指向的是线性时间,而“脱节空间”形成的全体则指向“纯粹时间”。“空的空间”涉及一个空间自身的时间生成的能力。“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是一出戏所需要的一切。”[12]当彼得·布鲁克将一个“空的空间”认为是戏剧所具有的的一切元素之时,当然也包含了戏剧叙事。只是这里的空已经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容器之空,毋宁说,它就是满。例如,在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中,关于花瓶的空镜头静静地展示了父亲和女儿之间复杂、多义而暧昧的亲情之爱。“空的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纯粹时间”的异质之“场”。它的“场”的连续性保证其最小叙事性,而对时间的不断异质生成则成就了它最大叙事性。质言之,非有机叙事的空间呈现是一种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异质性生成的空间”。“同一性”意味着“脱节空间”不是任意两个空间的胡乱拼接,而是建立在时间造化这一本体之“流”上,对于具体的叙事而言就体现为其所表达的最为本质的一些“场”,如“存在”、“虚无”、“道”等;而“异质性”使得表达开放性的观念成为可能,从而使得“空的空间”成为一个由实入虚、妙境叠生的生成空间。总之,非有机叙事的时空观的最终目的是超越日常的对于时空的固有见解,以释放生命最为纯粹的力量。
人们对农药众多负面的认识和印象,大多是因为对农药不了解。因此,不要嫁祸和妖魔化农药,积极为农药行业正名,让农药企业发声,全面系统地介绍农药及其生产和管理情况,使社会和百姓对农药有全面、科学和客观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叙述的空间呈现一样,非有机叙事的事件观也深深打上了“纯粹时间”的烙印。传统叙事中的事件往往被看作是封闭的原子,讲述一个故事就是让这些封闭的原子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确定的故事序列。形象地说,传统事件组合之间存在着“停顿”,正是一个个的“停顿”让事件彼此分割,依次排列。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事件观。相反,非有机的事件观将事件放置在“纯粹时间”之中,因此每一个事件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总处于一种“持续”之中。申言之,“停顿就不是在两个事件之间,而是在事件本身之中,停顿令事件具有深度”[13]。在安东尼奥尼的《奇遇》中,女主角在故事的一半突然失踪,在常规事件的发展脉络中男主角应该立刻去寻找女主角,然而,《奇遇》却将焦点聚焦到了女主角失踪后的这一“停顿”之中,男主角似乎忘了失踪的事,反而与其他女人开始调情。“停顿”此时成为了主角,从而让事件的序列产生断裂,而意义就产生于在那无尽的深渊之中。
深入地讲,传统叙事模式的叙事链条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事件原子之间有着明确的因果逻辑。对于古典或现实主义叙事作品来说,因果联系构成了这类故事情节的关键性因素。为打破这种因果逻辑,德勒兹提出了“虚因”的概念。对这一概念而言,一切原因和结果都不是孤立的事实,而是必须放在动态生成的事件中才能理解。换言之,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因”或“结果”,有的只是“事件”与“事件”之间在时空中的交流与互动。这类似于互联网中的“超链接”,可以通过一个链接指向另外一个,以至无穷,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作为开始的0,也没有一个链接作为最终的1,一切链接都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巨大网络之中。加缪的《局外人》可谓是对因果逻辑进行反思的标准模本。这部小说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主人公马尔索遇到的一系列事件:参加母亲的葬礼,看了一部费尔南德的电影,到海边去,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等。这些事件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联系,他杀死阿拉伯人是没有任何前兆的,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杀人短片》一样,杀人不需要理由,荒诞感才油然而生。然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当马尔索被法官们控告时,他的一系列没有联系的事件却被一条人为的因果链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在这个后来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马尔索杀死阿拉伯人的事件成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在此,加缪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世界的丰富性被逐渐窄化的过程。“生产情节就是削弱或窄化可能性的过程。选择变得越来越有限,而最终选择看上去完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必然。”[14]13正是通过对这种“窄化”的反叛,非有机的事件通过对因果逻辑的破除,将事件放置在“纯粹时间”之中,从而成为了一种“纯粹事件”。
在“纯粹时间”与“纯粹事件”之中,非有机的人物塑造也一定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统叙事学将人物与功能联系起来,而现代叙事的发展已经让古典的人物功能观的价值大打折扣。试问,如果以功能观的角度视之,《到灯塔去》的拉姆齐夫人、《等待戈多》中的弗拉基米尔、《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马塞尔等究竟执行什么样的功能呢?此时,叙事对人物的理解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人物的特性不再是固定的了,而是处于一种本体的生成状态之中,即从有机人物过度到了非有机人物,从现代的“圆形”人物转变成了“生成—人物”。因为,此时“真实”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的物理性存在,“真实”此时存在于伍尔夫般飘忽不定的“普通生活的瞬间”[15],故而主体性或类型化的人物已经不再适合这个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可谓塑造这种新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部经典的电影中,人物不因自己而得到定义,相反,人物通过“他者”而确认自己的存在。片中一共存在两个维罗妮卡,一个在法国,一个在波兰,二人只有一次出现在同一时空中,她们彼此并不认识对方,但一个人的死亡却可以被另一个人感觉到。影片在叙事上刻意强调二人感应的意象性画面,比如法国维罗妮卡会梦见波兰维罗妮卡的父亲所画的风景画,关于水晶球的意象也同时出现在两个维罗妮卡的生命中。理解这种新人物,必须从有机的生命过度到非有机的生命,从主体过度到非主体。德勒兹认为,要想摆脱这种主体性的困难,就是要“处于……之间,就是穿越……之间”[5]391。当言说主体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自我的经验层面,却忽略了自我在本体层面那生成变化的一维。对此,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提出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厉与西施,诙诡谲怪,道通为一”[16]等齐物思想,也是要破除人顽固的主体性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了世界本源的生成状态当中,凸显出生命非有机的一面。
可见,对非有机叙事的艺术表现来说,“时间”是起本体作用的贯通之流。不管是“脱节空间”、“空的空间”,还是“纯粹事件”和“生成—人物”,都是为了传达出“纯粹时间”的本然面貌,彰显非有机的生命。而对于这种“纯粹时间”的表达,也使得非有机叙事成为了一种具有一定本体或哲学意味的“纯粹叙事”。
三、非有机叙事的审美特征
有机叙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在明确的分工之下协调运作,使得相关功能得以确认:对时空变迁来说是时间的线性发展与空间的逻辑连接;对情节发展来说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依次序列;对人物塑造来说是“典型”人物或“扁平”、“圆形”人物。可以说,有机叙事中的一个隐含原则就是确定性,其中包括叙事元素功能的类型化与各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明晰性。所以,宏观来说,有机叙事凸显了一种认知逻辑的倾向。
有机叙事的认知逻辑在讲述故事之前就先对世界进行了一次人为的预先编码(线性的和理性的)。当一切都被预先编码后,叙事所传达的只是对这个编码世界的一次图解。比如,在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豺狗、斑马、猩猩、老虎分别对应着厨子、华裔水手、少年派的母亲和少年派内心的动物性,而少年派在海上的奇幻漂流映射着他在动物性、人性和神性之间对抗的自我救赎之旅。虽然李安拒绝任何一种可能的诠释,但片中的一切都遵循着类比的逻辑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所以也就不能怪观众得出确定性的理解。查特曼举过一个例子:当我们在一个句子中被告知约翰穿上衣服,而在下一个句子中他冲向机场的检票口,在其中我们可以设想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他抓起行李箱,乘坐巴士或出租车等[14]14。虽然在穿上衣服和冲向检票口之间的可能是无限的,但是这一头一尾的限定已经让可能性变成了可数的。总之,有机叙事中存在着鲜明的认知逻辑,它首先对世界进行编码,再对其进行图解,从而呈现出的只是世界的表象,与真实世界隔了三层,是“影子的影子”。它让生成中的事件下落为了确定性的事实,是一种诉诸脑的叙事逻辑。
但是,非有机叙事却力求诉诸心,试图呈现一种“感觉的逻辑”。说感觉具有逻辑性从日常角度来说是矛盾的。对康德来说,逻辑是属于知性层次上的法则,它所要排除的就是感觉。但是,这里所说的逻辑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的先验逻辑,而是感觉自身生成、变化的运动轨迹,是“纯粹事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生成之中的共振,是“无器官身体”在“有”、“无”之间的永恒摆荡。事实上,“感觉的逻辑”是一种“变易”的逻辑,它让理性试图确定的任何事物都变得不再确定,让逃逸者成为革命的英雄。申言之,“感觉的逻辑”就是时间本身的逻辑。德勒兹的时间是绵延的时间、纯粹的时间,是感觉的时间,它与机械时间或线性时间不同,其中无法理出清晰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绵延的感觉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理性拆分的综合体。因而,笔者可以认为非有机叙事呈现出的是一种“时间—意象”。
在这种“时间—意象”中,不存在任何预先的编码和图解,因此其所呈现的艺术形象不是从某个已有的现实中的形象“拷贝”过来,换言之,其所显现的类比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相似性造成的类比,而是一种感觉的类比或真正的“美学的类比”[6]117,它总是通过“不相似性”来进行类比。以人物塑造为例,在有机叙事以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中,通过认知的逻辑抽取出人物的特征,并以“圆形”、“扁形”或“典型”等来对之进行划分,从而得出一个“像”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或概念中的坏人的形象。以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包含着认知关系。由于人的存在具有“纯粹时间”性,但是相似性的类比总是倾向于确定性(a 与b 相似,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些确定的性质),所以真正“美学的类比”才总会以不相似性来呈现。如此看来,荒诞派的人物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其以不相似的“人”来类比现实生活中的人,呈现出的都是非有机的人物。如果把他们理解为某种类型化的类比的人物就会误读荒诞派人物的内涵,因为其中没有任何需要类比的确定原型,所以不能从中抽取出任何的确定的类型。
需要指出,认知的逻辑和感觉的逻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机叙事和非有机叙事亦是如此),它们只是相对地呈现出的不同的倾向,且相互“皱褶”在一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机叙事依然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而不至于沦落为纯粹的说教。应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叙事,感觉始终是最为根本的层面,它不是理性认知的初始阶段,即不是作为低级认识论。毋宁说,艺术中的感觉是在理性之上对理性认知的超越,是一种“超理性”,这点从“纯粹事件”和日常原子事件的对比中可见一斑,前者是叙事谓语的极动状态,而后者只是谓语的一种确定状态。有机叙事因其认知倾向遮蔽了感觉,非有机叙事却极力让感觉呈现出来,展现了一个在逻辑上类似于道家“自然”的本然世界,“只有在‘道’的辅助与呵护下,‘万物’之‘相对自然’才可能产生和谐、完美的结果,整个世间万物才会真正有序而自由地存在”[17]。
综上所述,德勒兹美学下的“非有机”观念为人们理解艺术叙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一方面,非有机叙事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和后现代叙事。大家知道,与传统叙事相比,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叙事因其形式的怪异、多变,内容的晦涩难懂而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在叙事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也多停留在技巧或形式的分析上,而鲜有哲学、美学方面的探讨。试问,如果缺少了这一更为本体的维度,又怎能理解现代与后现代叙事背后的深意呢?另一方面,“非有机”的美学观念还启迪人们超越传统的叙事或剧作模式,探索新的叙事艺术语言。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传统的叙事和剧作模式已经越来越类型化,新的叙事探索势在必行。非有机的美学观念可以让人们超越狭隘的原子事件与类型化、功能性的人物塑造,在时间哲学与“感觉的逻辑”中进行全新的时空探索与叙事试验。更为重要的是,非有机叙事凸出着艺术超越主体性的一维,彰显着非有机的生命,努力实现着人类生命的超越与精神的自由。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非有机叙事并不是一种叙事类型,相反,它反对任何类型化的思想。非有机叙事是一种叙事理想,它用在路上,用在生成。
[1]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3.
[2]亚里士多德. 诗学[M]. 陈中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Paul Goodman. Th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14.
[4]罗伯特·麦基. 故事[M]. 周铁东,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24-125.
[5]德勒兹,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M]. 姜宇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6]吉尔·德勒兹. 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M]. 董强,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Giles Deleuze. Francis Bacon:The Logic of Sensation[M]. London:Continuum,2004:45.
[8]Mark Bonta ,John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M]. 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62-64.
[9]徐辉. 有生命的影像——吉尔·德勒兹电影影像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9.
[10]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M].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0:1.
[11]Giles Deleuze. Cinema2 The Time-Imag[M]. London:The Athlone Press,2000:5.
[12]布鲁克. 空的空间[M]. 邢历,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1.
[13]吉尔·德勒兹. 哲学与权利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 刘汉全,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2-183.
[14]西摩·查特曼. 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5]张友燕.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希腊文学传统的寻绎与回归[J]. 求索,2015(1):156.
[16]郭象,成玄英. 庄子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7-38.
[17]宋洪兵. 老子、韩非子的“自然”的自然观念及其政治蕴含[J]. 江淮论坛,201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