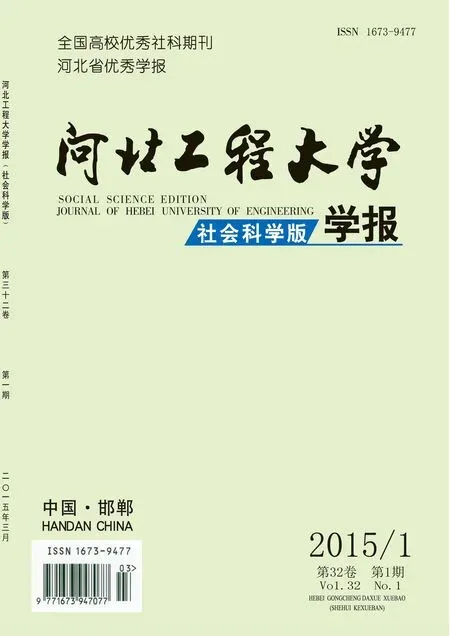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刘政
(1.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长办公室,北京 100006)
一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唐代以前的道教,各家各派皆相信仙界是实有的,成仙是可能的。而这一观念五代以后开始发生了逐渐的变化,神仙实有和神仙可成的思想发生动摇,随之而来的是道教金丹思想向内丹学说转化。唐代以前道士以外丹为仙道之极,而至北宋张伯端《悟真篇》出现以后,道教修仙理论开始专主内丹,斥外丹黄白为旁门左道[1]。
道教在唐宋之际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士人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于文人的创作也有着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本文拟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李白与苏轼皆成长在有好道传统的蜀地。蜀地自汉代以来就风行道教,唐宋时期更是达到顶峰。宋真宗时,有“先是,道教之行,时函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重”[2]的记载。李白和苏轼自幼耳濡目染,深受道教文化的熏陶,熟读道经,两人的坎坷经历,又促使他们更主动地接触道学,结交道士。这是两人的相同之处。具体到道教观念,两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又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
李白和苏轼道教观念的不同,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唐宋之际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的转变。
首先,两人的神仙观念不同。李白相信神仙真实存在,并亲自寻访神仙。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其时,道教受到唐玄宗的扶持,发展到鼎盛。在盛唐的崇道热潮中,各种神仙精怪之说层出不穷,真伪难辨。受这种社会风习的熏染,李白期望成仙并漫游寻仙是不难理解的。他游遍天下名山,相信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访道求仙的愿望。李白自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可惜他的寻仙之旅皆以失败告终。李白在《赠嵩山焦炼师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传说嵩山有神人焦炼师,生于齐梁时,而年貌可称五六十,胎息绝谷,居少室庐,游行若飞,倏忽万里,入东海,登蓬莱,莫能测其往。李白对此深信不疑,并与李颀访之不遇,作诗寄赠,遗憾之余,深愿睹仙容。可见李白的寻仙意识有多么强烈。
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苏轼,对于神仙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苏轼有一次经过安乐山麓,听说这山上有一种树,树上有叶,叶上有纹,乃道教的符图。传说这是因为张道陵曾住过此山,所以才有这等异树奇叶。苏轼对此传说作诗讥讽道:“天师化去知何在,玉印相传共世珍;故国子孙今尚死,满山秋叶岂能神?”[3]可见,苏轼不相信张道陵的神话和长生不死的传说。苏辙也明确指出苏轼是不祈求成仙的:“君颂黄庭内外篇,本欲说心不求仙”(《次韵子瞻书黄庭内景卷后赠道士拱辰》)。可见苏轼阅读道教经典《黄庭经》只是为了静心而不是为了成仙。道教发展到宋代,宋人大部分不再相信轻举飞升、炼丹成仙,坚信“我命在我”、“我命不由天”,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我生命。苏轼的神仙观念是符合这一历史趋势的。
其次,两人的道教炼养方式不同。我们先来看道教经典《抱朴子·神仙传》中的一段话:“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去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得仙。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能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其次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但不能使人不死,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葛洪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想成仙,或长生不老,就需要服“还丹、金液”和“云母雄黄之属”,普通的“草木诸药”只能使人健康长寿而已。
李白相信神仙实有并羡慕神仙幸福潇洒的生活,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自己得道成仙。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实现呢?那就是服食“还丹、金液”和“云母雄黄之属”,即外丹。李白是相信外丹的,并且亲自修炼过外丹。李白关于炼丹的诗句有很多,如“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早秋赠裴十七仲堪》);“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荥阳别元丹之怀丘);“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一直期盼服药成仙的热切心情。晚年李白在避地安徽安庆司空原时,甚至希望“倾家事金鼎。”
苏轼既然不相信神仙实有,不追求成仙,那么对于道教中所谓能助人成仙的外丹之道必然也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虽然苏轼也服用丹砂和炼丹,但他主要是为了养生而不是成仙,并且他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苏轼用历史的经验知道丹药有时会致人死地,所以告诫他人不可乱用。“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然只可自内养丹,且不可服外物也……戒之戒之。”[4]苏轼服食较多的只是寻常药物所炼的药丸,即葛洪所说的“草木诸药”。除此之外,苏轼更重视内丹的修炼。有学者对苏轼的炼养之术进行了分析,其中内丹修养占了绝大部分[5]。 “兴起于唐末的内丹炼养热潮流入两宋,愈益波澜壮阔。尤从北宋神宗朝起,内丹空前盛行,其学说趋于成熟,呈取代内丹以外一切道教传统炼养之术。”[6]受此风气濡染,苏轼提倡并践行道教内丹之道。苏轼说,“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唯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数为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运行体中,痒痛安能近人也。”[7]苏轼的这番话颇符合张伯端“虚静”之说[8]。
由此可见,李白和苏轼的道教观念是很不相同的。李白相信神仙实有,漫游求仙,期待成仙并积极炼丹;而苏轼却不相信神仙的真实存在,对道教的金石丹药持怀疑态度,更重视内丹修养。于此相表里,两人在文学创作上也呈现出微妙的区别。李白和苏轼的文风都以豪放、浪漫,想象恢弘而著称,然而在两人看似相似的风格中,因两人的道教观念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三
李白的诗歌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多的作家作品都以想象丰富而闻名,但李白的想象却因他与道教的结缘而具有其特殊的特点。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中认为,李白诗歌之所以具有超迈飘逸、不可捉摸的艺术风格,与其天生的仙姿妙质以及后天的求仙学道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赵翼的评论很有见地。当代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受李白的道教信仰影响,李白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想象力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想象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幻觉特征了。由于李白强烈渴望成仙,“产生对神仙世界的幻觉,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谪仙’意识,由此形成了他在主观意识上的自我仙化倾向;在思维方式上,则常常将人间和仙境合二为一,实现了人间和仙境的自由往来。因此,李白在诗歌创作时,思维往往能够随时随地打破现实世界的界限飞入仙境,使其想象的空间获得极大的突破与扩张,使一些原本容易写得比较拘泥呆板的作品,也极具飞动飘逸之态。我们不妨把李白的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幻觉思维’”[9]。
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有道理的。我们在读李白诗歌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诗歌里恣意汪洋的想象某种程度上真的带有幻觉的色彩。天宝元年四月,李白漫游到泰山,作《登泰山》六首。在这六首诗里,李白详细描写了自己与仙人的相逢。“山际逢仙人,方瞳好容颜”,“缅彼鹤上仙,去无云中迹”;“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仙人激碧峰,处处笙歌发”;“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在这些诗句中,李白不但看到了仙人的容貌,骑坐的坐骑,在云端中离去的飘忽姿态,还看到了仙人向自己招手,并送给自己礼物,甚至还听到了仙宫中的笙歌声,这明显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想象而带有幻觉特征了。李白类似的诗句有很多,如《登太白峰》中,诗人感觉到自己向仙境飞去,天上的太白金星仿佛在跟自己说话,并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天界的大门。
李白诗歌里带有幻觉色彩,自然也与他好饮酒有关。唐朝嗜酒的诗人有很多,不过,饮酒最出名的应该还是诗仙李白。他自己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通过饮酒,李白宣泄、消解了现实之悲,并在醉的幻觉中物我两忘,诗兴大发。李白服食丹药,有可能会产生幻觉,其功效似乎与饮酒相类。
李白的诗歌创作,奇思涌溢,天马行空,纵横恣肆,其想象自由驰骋,不受任何事物约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甚至带有一定的幻觉和迷狂色彩,我们不能说这全来自道教的影响,但是李白的神仙观念和其服食丹药的炼养方式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李白的想象,有助于形成其飘然而来,忽然而去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
苏轼的作品中,想象不可谓不丰富。苏轼的二十五篇赋充分显示了他这一才情。苏轼的想象形式多样,层次分明,尤其擅长由物及理,快速捕捉物理间的关系。如《酒子赋》中对酒理的比喻。他用君子的刚柔相济的品格比喻酒的甘而小苦的清醇,用婴儿的拙朴比喻酒的生涩,用少女的青春比喻酒的甘香等等。作者独取各种人内在的神韵,给出酒味的真意,从而使读者由审美之门进入悟理之境[10]。
我们不难看出,苏轼作品中的想象有别于李白的想象,更多地带有一种理性的节制,富于理趣。苏轼是一代思想家,他的诗文追求理趣,自然跟他思想家的身份有关,但这一突出特点也跟苏轼的道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葛兆光先生指出,初、盛唐之后,士大夫们把向老庄复归的一派思潮作为道教的“正宗”而加以追求[11]。苏轼的道教信仰及炼养之道正是这一复归的例证。苏轼在道教信仰上濡染道教借用的老庄思想,文学技巧和风格也深受老庄影响,富于理趣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点。老庄文字以谈玄说理为旨归,又都善于借曲譬、隐喻、寓言来发人妙悟,其突出特点就是借物明理。苏轼创作也多借物明理。如《前赤壁赋》借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来说明宇宙万物有变有不变的道理。又如《超然台记》紧扣楼台的兴建来阐发游于物外则无往而不乐的道家哲学,都是著名的例子[12]。
我们来看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老庄思想给中国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心灵化了的纯净、和谐、安静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13];而道教“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14]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李白和苏轼在文学风格上的区别。由于唐宋时期道教自身的重大变化以及李白和苏轼道教观念的不同,道教带给李白的更多的是一种热烈与迷狂的情绪,故而李白的诗作中具有一种“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苏轼受道教影响更多的是道教借用的老庄思想,故而苏轼的诗文中体现出一种恬淡的情感和富含哲理的色彩。
四
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15]。这句话的内涵很丰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也从道教中汲取着营养。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跟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和苏轼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但是他们对于道教的态度和所承受的影响,却是不尽相同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葛兆光先生曾说,“道教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人们涉足较少的领域”[16],如今近30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进来,也取得了很丰厚的成果,然而这片领域仍是一所富矿,值得我们继续挖掘。
[1]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40-447.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七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03—304.
[4]苏轼文集 卷五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贾喜鹏,王建弼.从道教炼养方式看苏轼的道教信仰———兼及在道教传播史上的地位[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27(9):6-8.
[6]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89.
[7]苏轼文集 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张伯端.悟真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鲁华峰.茅山宗道教方术与李白的幻觉思维[J].周口师范学院院报,2006,23(6):16.
[10]孙艳平.体察苏轼赋作中的想象信息[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院报,2007,25(增刊):203.
[11]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05.
[12]李豫川.苏轼与道教[J].中国道教,1996(2):21.
[13]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70.
[14]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71.
[15]鲁迅全集 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5.
[16]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