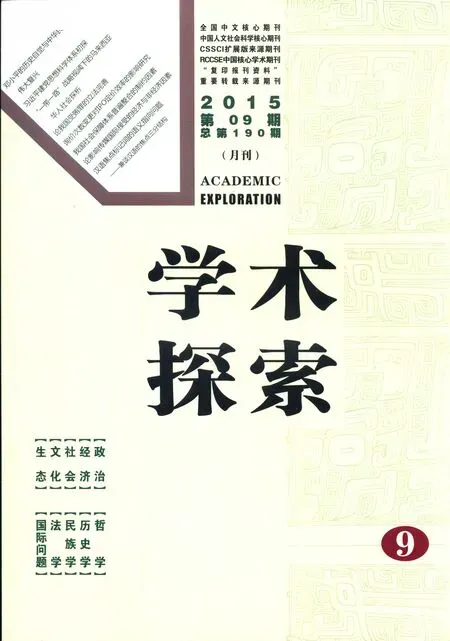汉字的稳固性与民族认同心理
王 迈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汉字的稳固性与民族认同心理
王 迈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稳固结构,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也折射到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甚至对民族结构、国家政治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字的熵值是印欧系音素文字的两倍以上,承载的意义达到了概念级别,可以直接作用于人脑的意义感知区域,使读写交流达到极高的效率。语言的共性源于语言背后的思维和概念体系,语言的本位不是词或字,而是语言所要表达的思维对象——概念。
汉字;稳固性;字本位;联结主义;思维概念
一、汉字的三个维度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仍在使用且没有断层的词符词素文字,大量历史文献和古代文物展现了汉字演变发展的大致脉络。19世纪末出土的殷墟甲骨文把汉字的历史前推至距今3300年的殷商时期;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出土的陶文进一步把汉字的历史前推至距今五千年以上(虽然陶文的文字地位还有争议,但其与汉字有历史渊源关系,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如果说汉字发展过程在甲骨文之前还不甚清晰,那么甲骨文之后,随着史料的日趋丰富及解读难度的逐渐降低,其演变脉络基本是可考的,汉字经历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一直发展到今天通用的草书、行书、楷书。
我们可以从音、形、义三个方面考察一个汉字,这正对应传统小学的三个部门——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而现代语言学有了更科学细致的分析手段。
现代汉语中,一个汉字基本对应一个音节。音节由声、韵、调三部分构成(表1)现代汉字的基本笔画包括横、竖、撇、点、折、勾、挑、捺八类,若干笔画按一定笔顺组成汉字的基本构件——偏旁,若干偏旁再按一定空间结构组成汉字。汉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类,独体字由单个偏旁构成,合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偏旁构成。“永字八法”是书法用笔法则的归纳,它同时也展示了汉字的八种基本笔画。

表1 汉语的音节结构
汉字产生之初,以字形直接表达字义是一般采用的造字方法;之后则更多是在原有汉字形音义稳定的基础上采用构件组合的方式创制,构件或与字音相关,或与字义相关;也有近音借用或近义借用的现象,经约定俗成后,字的义项便增加了,这是在用字过程中创制新字的方法。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六书”的概念,这是汉字构字规则的学说,同时也是对汉字字形与字义相互关系的总结:“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字义研究可以采用按义分类的方法,例如,我国最早的训诂学著作《尔雅》共录2091个条目,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19篇。
汉字造字的理据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观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理据性和自由性并非是完全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文字单位上。以象形字为例,“焉”的字形像一匹马,有四条腿一个脑袋,有鬃毛,这是它的理据性;但是到底像正面的马还是侧面的马,线条是这样布局还是那样布局,就是它的自由性。再说形声字,字音随声符,字义随义符,是它的理据性;但是具体采用哪个声符哪个义符,就是自由的。理据性和自由性反映了一个汉字的不同层次,都是汉字具有的属性。
二、汉字的稳固性与民族凝聚力
音、形、义是汉字的三个维度,它就像三脚架的三个支点起到稳定的支撑作用,使得三位一体的汉字具有极强的稳固性。虽然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读音,但这些差异往往有着成体系的对应规律,字音的稳固性甚至体现在不同国度的汉字系统中,例如汉语、日语、朝鲜语中的汉字读音就有着相对严格的对应规律,甚至很多在现代汉语标准语中不复存在的中古汉语语音面貌,在日语和朝鲜语中还成体系地保留着(王迈,2011)。字形的地域和历史差异相对字音要小些,这一方面缘于字形具有可视性,其时空传递性较字音更加可靠;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历史上历届政府对字形开展的规范化工作。字义是最为稳定的,不同方言区的人虽然无法听懂对方的话语,但见字知义的“笔谈”往往是有效的沟通手段;字义的变化大都是派生出新的义项,而基本义很少发生变化,基本义的稳定是字义稳定的根基。
汉字的稳固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也折射到汉民族的文化、风俗、社会心理等方面。书法艺术、诗词格律、灯谜字叶等与汉字密切相关的文化财产是中华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重要基石;汉语中,“认字”有时是“有文化”的代名词,同为对个人知识层次的描述;而“字如其人”、“见字如见人”则说明在汉民族的社会心理层面,从字迹即可判断一个人的修养、品格、性情、心绪。
汉字的稳固性甚至对民族结构、国家政治的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汉语区地域辽阔,内部分化情况复杂,各方言间语音、词汇、语法的差异明显。通常情况下,语言的分化会引起民族文化及国家认同心理的弱化,进而形成一种与民族、国家统一反向的分散力。例如,有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分裂,语言文化是重要的因素,其靠武力维系的巨大版图存在显著的语言文化差异,先是希腊区和拉丁区的分裂,继而是拉丁区的进一步分裂,今天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都源于古拉丁语,它们的差异甚至没有汉语八种方言间的差异显著,但都成为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具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而汉语,内部分化要显著得多,但汉民族始终保有强大的凝聚力,维持着地域辽阔的统一国家,虽然历史上也有分裂期,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是大趋势。这与汉字的稳固性有密切关系:虽然汉语地域间方音各异,汉字却极少变化,“音相异而文相同”,统括着汉语的各种方言,使汉民族保有共同的根基,促进了民族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反观印欧系诸语言,由于音素文字更直接反映实际读音,方音的分化很快引起拼写的分化,进而形成“音文皆相异”的状况,使共同的根基逐渐失去,形成了心理认同上的分散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音素、音节文字表示语音单位,只能通过语音中介同语义发生联系;汉字则通过形体直接与语义发生联系,或称“表意文字”。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汉字的音、形、义三位一体,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字音并非直接属于汉字,它其实是汉字所代表的语素的发音,或可称“语素音”;字义也不是直接属于汉字,而是汉字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或可称“语素义”;只有字形是真正属于汉字的,是汉字的本质属性,即便在文字画过渡到图画字之前,也即汉字的前身阶段,形状就已经作为必需的要素而存在了,这完全不同于通过语素间接联系起来的字音和字义。
探究汉字与音素音节文字的差异,不应只关注形、音、义等外在表象,而应透过表象看本质。汉字区别于音节、音素文字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具有更高的熵值、更丰富的信息量。冯志伟(1984)对容量12370字的语料库进行统计,测出汉字的平均熵值为9.65bit,而印欧系音素文字的平均熵值仅有4bit左右,两者的信息承载能力的差异达到了2(9-4)=32倍之多。
汉字承载的意义达到了概念级别,如“山”、“水”、“天”、“地”、“人”,而概念正是人脑存储信息、进行思维的基本单位。因此,汉字可以直接作用于人脑的意义感知区域,使借助汉字进行交流可以达到极高的效率,所谓“一目十行”,正是对汉字读写效率的文学性描述;而联合国文件的各个语种的翻译本中,中文版总是最薄的。
三、语言本位观之种种
自《马氏文通》引入西学文法,洋为中用成为汉语研究的主流,受西方不同语法流派的影响,演进出多种汉语“本位”观:①词本位(或词类本位)(马建忠,1898);②句本位(黎锦熙,1924)(史存直,1986)等;③语素本位(程雨民,1991)等;④词组本位(郭绍虞,1978)(朱德熙,1982)等;⑤小句本位(邢福义,1996)等;⑥字本位(徐通锵,1994)(潘文国,1996)等。
“如果说词本位是欧洲传统语法在汉语中的折射,句本位是斯威特语法革新派在汉语中的折射,语素本位和词组本位是美国结构主义及早期乔姆斯基理论在汉语中的折射的话,则小句本位就是从布拉格学派到伦敦学派,特别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的折射了(潘文国,2002)。”简短的总结反映出这样的事实:西方语言学对当代汉语研究的影响力之深远,已使得中国传统语言学以字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显得小众而过时,被束之高阁的命运似乎难以避免。
句本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它是对汉学界长期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反拨,也是对西方语言学理论下无法解释的汉语问题的一种新的探索,是对汉语独特性的强调和再思考。
作为一种破旧立新的理论,句本位获得广泛关注,可谓毁誉参半。一种主要的反对观点认为:汉字是文字单位,是符号的符号,是第二性的,既然不是语言单位,如何能够成为语言系统的本位?句本位的支持者一般通过汉语的特殊性应对上述质疑,认为汉字是表意、自源文字,而其他语言多是表音、它源文字,“功能性”的分类与“发生学”的分类在汉语与世界多数语言的对比上重合了,这种区别对于汉语研究有重大的意义(潘文国,2002)。
我们认为,上述对字本位理论的质疑没有切中要害,文字和语言是否需要截然分开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就如同一只蝴蝶,幼年期是没有翅膀、也不会飞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定翅膀不属于蝴蝶,或者充其量只是表示其具有飞行能力的一个标志;同理,我们也不该仅凭语言产生之初没有文字,就断定文字不属于语言,或许文字就是语言成年后长出的翅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语言只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文字,我们不该忽视语言文字间的这种必然性而强行将两者分立。至此,我们认为以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来质疑字本位,本身就是立足不稳的,针对它的辩护显得不必要。
陆俭明(2011)的质疑更值得关注,他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口吃者说话时,音节重复、停滞、拖延之处,一定不会在一般认可的词之后。如:
我我我本本本来打打打算多多多查查查阅两两两本本本书。
这说明,在口吃者的心理中,汉语语法结构单位是词而不是字,从而反驳了字本位理论关于“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的论断。我们暂且不论汉语语法结构单位到底是词还是字,只把注意力放到徐通锵先生想证明以及陆俭明先生想质疑的方向上来,即“心理”或者“心理现实性”。
需要强调,本位不应该只是某种具体语言的本位,它应该具有普通语言学价值,体现出语言的共性。如果我们同时论证了英语本位是词,汉语本位是字,那只能说明这种本位观(或判定标准)只反映了语言的个性特征,仅具有较低层次的具体语言学价值。我们不否认具体语言学的研究价值,但我们同时可以就语言本位的判定标准做更高程度的抽象,使其涵盖两种语言的共性,进而达到所有语言的共性,使其成为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本位判定标准。而上述“心理现实性”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两位先生之所以同时关注到它,并产生分歧,足以证明其作为本位判定标准的重要性,因为“心理现实性”具有跨语言的性质,具有普通语言学价值。只可惜两位先生都没有继续深究、抽象、继续找寻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位。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是概念的推演。虽然语言之间的差异千姿百态,语言所承载的思维以及思维背后的概念结构,却总是具有人类的共性,这是由我们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决定的。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观察语言的眼光越具体,语言就展现出越多的个性;越抽象,就展现出越多的共性。以词汇体系为例,在幼童的眼光下,词代表一个个具体的事物,苹果和牛奶互不相干;入托前后的孩子开始有了类的概念,知道苹果和牛奶是吃的,杯子和碗是盛东西的,共性意识开始启蒙;小学生开始有了词类的概念,知道苹果和杯子是名词,唱歌和跳绳是动词,对共性的认识达到了更高的抽象度;再大一些的学生开始意识到实词和虚词的差异,逐渐掌握虚词所表达的种种关系。
因此,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是一对互补的概念,它是有梯度的,关键在于我们观察语言的眼光,换言之,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梯度由判定标准的抽象程度决定。我们想获得哪一级梯度的共性与个性,只需相应地调整判定标准的抽象度即可,如上例,若提高标准抽象度,名词和动词就具有了实词的共性;若降低标准抽象度,名词内部就有了食物和餐具的个性差异。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工具,只要使用得当,总能获取所需梯度的语言共性与个性。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我们已经将判定标准抽象到最高层级,却仍然找不到语言间的共性所在,本节讨论的语言本位观即是如此。假设“英语是词本位语言、汉语是字本位语言”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继续提高判定标准的抽象度,就应该找到属于英语和汉语的共同的本位主体,然而事与愿违,我们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无论标准怎样设定,英语和汉语的本位主体似乎都无法统一起来。
语言间无法找到共性的情况具有普遍性,本位观只是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是研究的终点,越过语言的樊篱,我们发现,语言的共性,很多都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思维和概念体系结构中,这是寻找语言共性的一片新天地。
四、思维概念与语言本位
语言的词汇体系,归根结底是用来表达意义的,与意义对应的,就是思维中的概念体系结构。概念体系结构具有跨民族跨语言的人类普遍性,虽然对某些具体的概念认知,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有些许差异(例如中国人认为彩虹有七种颜色,美国人认为有六种,欧洲某些地方的人认为是五种),但那通常是认知自由度较高的综合概念,而底层概念的认知自由度相对较低,民族间差异极少(例如对彩虹和色彩的基本感知及心理映像,因物种共同的生理基础而不会有质的差异)。正因为如此,语言间的差异,通常都能从概念体系中找到共通之处,语言本位也是如此。
人脑中的概念以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网络的形式存在,其中,局部网络(Localist Network)中每个观念都由一个单元来表征,分布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中每个观念的表征分布于一组单元(葛鲁嘉,1994)。语言结构网络类同于思维结构网络:语言体系的自然节点是词,词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词素,因此词的网络是一种分布网络,每一个节点都可以看成是包含它的一组节点的全息影像。思维结构的网络节点由概念单位充当,概念虽然大都以词的形式作为表征,但两者并不总能画等号。例如:“山”、“水”、“吃”、“睡”、“多”、“好”作为一个概念问题不大,但“谢幕”、“退婚”、“混纺”就要复杂一些,至少在理解上要涉及多个概念,另一些构词能力很强的黏着词素如“者”、“化”、“反”、“族”等,也可以表征一个概念,只是相对抽象一些。这说明,大脑中的概念表征与语言单位的词并不严格对应,而是有交叉的,网络节点除了包括作为概念表征主体的词,还应该包含一部分词素。包含词素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词素是构词理据的承担者,虽然它体现的只是所表征概念的显著特征而非本质特征(例如“机器人”的构词理据“人”表示机器人具有“人”的显著特征“人形”,但并不表示它具有“人”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根本不是人,甚至连生物也不是)。
概念与不同语言文字单位(小句、词组、词、词素、字)的对应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做出如下归纳:
一个小句对应多个概念:常态(例略)。
一个小句对应一个概念:单句形式的熟语,如:艳阳高照、叶公好龙。(熟语化后,多个概念融合成一个复杂概念。)
多个小句对应一个概念:复句类型的熟语,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虽然比较复杂,仍可以看成一个概念。)
一个词组对应多个概念:常态(例略)。
一个词组对应一个概念:词组形式的熟语或专有名词,如:天之骄子、北京大学。
多个词组对应一个概念:多个词组构成的熟语,如:拆东墙,补西墙。吃一堑,长一智。
一个词对应多个概念:大都为并义类型的词语,如:花草树木、东西南北。(通常可分解成词素,每个词素对应一个概念。)
一个词对应一个概念:常态(例略)。
多个词对应一个概念:可归入一个词组对应一个概念。
一个词素对应多个概念:可能不存在,但若以义素分析法加以分解,也可认为存在,如:妪=女性+高龄。
一个词素对应一个概念:常态(例略)。
多个词素对应一个概念:可以归入一个词对应一个概念。
汉字与概念的对应:按照“字本位”的思想,若把汉字也看成语言单位的一种,那么古代汉字大多与词对应;现代汉字大多与词素和词对应,则可以将其归入上例,不再另立。
上面的分析想说明:虽然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思维概念结构基本相同,但在各民族语言内的表征方式却千差万别,具有极高的自由度。古代汉语一个词对应一个概念,同时对应一个汉字,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概念系统日趋丰富,而汉字受到易用性的限制其数量不可能增加过多过快,迫使汉语必须使用多个汉字来表征一个概念,然而汉字具有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稳固性,多个汉字表达一个概念并没有引起汉字原义的消失,字音、字形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只是在对应方式上做出妥协,使得现代汉语中一个概念既可以对应多个汉字(多音节词),也可以对应一个汉字(单音节词或词素),甚至对应更大的字组(词组或小句)。
印欧系语言的发展则走了另一条道路,西文字母未达到意义级别而只与发音绑定,与概念对应的声音串(以及记录声音串的字串)就不像汉字那样稳固,随着概念数量的增加,西文可以在原有声音串的基础上自由地改变发音,以产生新的声音串来表征新的概念,记录它的字串也随之变化,于是新词产生了。由于印欧系诸语言的演进没有像汉语那样受到汉字这种大颗粒稳固体的限制,概念与词的对应关系相对稳定单一,新词的产生途径主要是以旧词为基础的音位曲折变化,而汉语则只能在汉字之外做文章,用汉字的不同排列组合来产生新词。
我们的结论是,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位不是词,也不是字或其他,它代表了语言的共性,应该在语言背后的思维概念结构中寻找。人的思维概念结构同语流的线性结构不同,是由节点(概念)和关系组成的联结主义的多维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一个节点的存在都可以由与其相关的节点做出解释,或者说,一个概念的身份可以由它的上位概念、下位概念以及同位概念加以说明。语言单位的网络却不尽然,词的意义并不是词素义的简单相加,小句的意义也不是词义的简单相加,并且,为了在语言的线性序列中表达概念网络中的复杂的多维关系,语言进化出语法系统,通过屈折、附加成分、语序、辅助词、重音等手段来表达概念节点的多维关系(语法意义)。因此,语言的本位不该受到语法特点或语流结构的左右,它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归结成一句话,语言的本位不是其他,正是语言所要表达的思维对象——概念。
把概念作为语言的本位,汉语的词性不定论也就容易解释了:在联结主义的概念网络中,汉语的词对应的是一个概念节点及其周围所有的联结关系,每一类联结关系表达这个概念的一个方面,例如“翻译英语”和“英语翻译”中“翻译”的区别,只是同一个节点与不同联结关系相组合的结果(其本身就已包含联结关系);与此相对,英语的词仅仅对应一个概念节点,其周围的联结关系须由不同的词形来决定,例如translate与行为相联,translater与行为者相联。在这方面,汉语与英语的差异没有体现在表层的语言结构本身,而是落在了深层的概念网络结构中。
The Sta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Psychology of National Identity
WANG Mai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xchang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Chinese character has stable structure with trinity of form,sound and meaning.It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language,but also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psychology,and eve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tability of national structure and state politics.Besides,the entrop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more than twice that of the Indo-European phonemic languages,and themeaning they bear reaches the conceptual level,which can directly act on the sensory area of human brain and result in high efficiency of reading and writing.The common features of language comes from the thinking and concept system it represents,the source of which is concept—the object of thinking,rather than words or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stability;character standard;coupling principle;thinking concept
H12
:A
:1006-723X(2015)09-0138-05
〔责任编辑:黎 玫〕
王 迈,男,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语音学、语言形式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