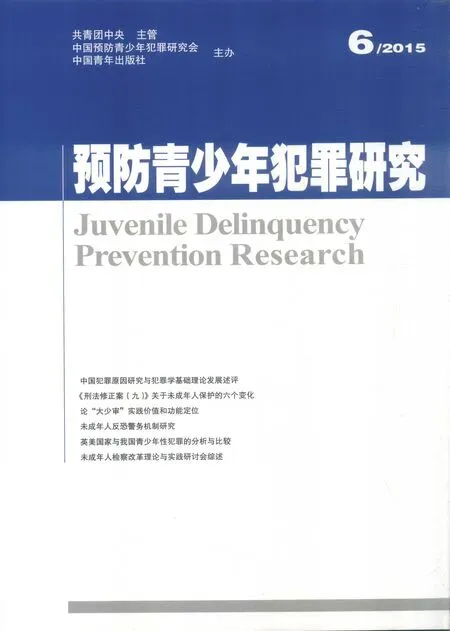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彭 燕 史 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2200)
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彭 燕 史 焱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2200)
史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数量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置措施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起诉到法院。在新刑事诉讼法新增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仍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应扩大适用,但与此同时,针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存在的诸多风险,如不起诉标准未予明确、品行调查的不确定、再犯罪的可能性、对被害人造成进一步伤害等,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从明确适用条件、限定主观及客观条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加强对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风险评估机制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自行作出处理的方式包括公安机关撤案、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等。相对不起诉作为挽救和教育涉罪未成年人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最能体现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及对未成年人的法律关怀,有必要扩大适用。但实践当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存在若干风险,需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处置的现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突出,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2009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有135件227人,占当年全部案件数1333件的10.13%;2010年有85件133人,占当年1409件的6.03%;2011年有118件167人,占当年1424件的8.29%;2012年78件113人,占当年1571件的4.96%。从中可以看出,除2011年比2010年案件数及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外,未成年人犯罪数不仅其绝对数量处于逐年递减态势,而且其在全年犯罪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置情况,仍以笔者所在的昌平区检察院为例进行分析:2009年至2012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共计640人,其中,由检察院自行作出处理的仅有26人(包括公安机关撤回移送审查起诉8人,法定不起诉1人,存疑不起诉4人,相对不起诉13人),其余614人则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进入审判程序,并最终由法院作出判决予以定罪量刑。而法院对未成年人多处以短期自由刑或非监禁刑,占全部判决人数的59.29%,其中,短期自由刑中拘役61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53人,占18.57%;非监禁刑中拘役缓刑63人,有期徒刑缓刑149人,占34.53%;同时,另有8人被免于刑事处罚,30人被单处罚金,占6.19%。

表1 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置情况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在案件处置时的适用率很低,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数量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置措施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案件被起诉到法院,但法院的判决情况又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处理趋势。
二、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相对不起诉,又称为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时,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制度。
(一)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必要性分析
1.现有刑罚处置情况的必然趋势
如上所述,未成年人不起诉适用率较低,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院最后还是提起了公诉,法院对未成年人进行了判决。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法院判决一半以上是短期自由刑或非监禁刑,究其原因,主要是防止监禁刑导致的交叉感染。未成年人的可塑性比成年人强,未成年人初次犯罪时可能主观恶性不太深,但在服刑期间,有可能受到主观恶性强的罪犯的感染。特别是在我国羁押场所环境没有彻底改善的前提下,由于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比较弱,因此羁押场所很有可能成为二次犯罪的传播场所。由此看出,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对待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
2.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和刑罚人性化价值目标的诉求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障刑罚目的得以实现,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通过惩罚犯罪,预防已经犯罪的人重新犯罪,预防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实施犯罪,更好地保护人民。对于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案件,如果作出起诉,交付审判, 未必就能得到教化,甚至对其将来重返社会造成阻碍。通过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使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下接受教化和监督,实现刑罚人性化,更能体现对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尊重和各项权利的保障。因此,刑事诉讼目的和追求刑罚人性化也是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得以适用的深层次原因。
3.适用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启动司法程序的同时意味着将要耗费相当大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如果每一个轻罪轻刑的刑事案件都经历由立案到执行等诉讼阶段,就会耗费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诉讼效率。1张羽.论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J].犯罪研究.2009(02).此时,如果适用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就会大大地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中的经济投入,提高各方面的效率。
(二)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可行性分析
1.我国适用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已见成效
现阶段的青少年犯罪,虽然有暴力化、团伙化的趋势,但有相当一部分处于轻微犯罪的幅度内,对于这些轻微犯罪的青少年,由于他们较强的可塑性,教育、感化这些青少年罪犯比判罪处刑更为可行。笔者所在的检察院的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2年,共对13名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这项制度不仅挽救了13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开始新生活,而且,迄今为止,13名被不起诉人均未再次出现不良行为。由此可见,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能更好地挽救未成年犯,挖掘其身上的闪光点,通过专家和检察官的帮助教育,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今后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不仅免于犯罪前科,而且更易回归社会,具有切实可行性。
2.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具有可操作性
在法院审理的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判处缓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本身量刑不重,可以合理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而不对未成年人冠以罪犯的恶名,同样起到惩戒、教育的作用。在我院办理2009年到2012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从判决结果来看,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有8人,单处罚金有30人,拘役缓刑有63人,有期徒刑缓刑有149人。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罪犯最后被判处了较轻的刑罚,对于这些判刑不重的未成年犯,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决定相对不起诉,而使其免于进入审判阶段显然更能维护未成年犯和被害人的权利,可以有效避免未成年犯被贴上罪犯标签的同时为被害人讨回公道。因为在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时,要对行为人进行一定期间的考察,在该考察期间内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去除其思想里的腐朽、不良因素,注入先进思想,使其在重归社会后能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在避免监禁刑交叉感染同时达到教化的目标。考察期的教化过程,同时也是对未成年犯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惩罚过程,被害人在得知未成年犯在思想层面上受到惩罚,亦能消除其心中的愤恨。由此,检察院实行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3.国际社会实践成效的有效借鉴
结合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在法治发达的国家,都纷纷建立起与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相类似制度,并取得有效的成果。例如,有学者统计了日本暂缓起诉和刑满释放的人再重新犯罪的对比,同样是在三年时间里,暂缓起诉的人再犯罪的比例是11.5%,而刑满释放的人回到社会重新犯罪的比例是57%。2孙力.关注暂缓起诉的理论与实务[J].京师刑事法治网.通过这些成功的例子,可以知道,国际社会上适用暂缓起诉、相对不起诉等相似的制度可以起到改造未成年犯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我国也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改善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使其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三、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存在的风险
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存在若干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明确的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标准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犯罪情节轻微”的内涵和构成要素不明确,难以把握,实践中通常将相对不起诉局限于轻微罪之内,而一些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如抢劫等未成年人涉案的常见罪名,即使该未成年人在案件中系从犯、胁从犯、被教唆犯罪的或有自首、立功等情节,也因为涉及重罪名的缘故而基本不被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1李玲.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J].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法学论坛.2009(09).此外,由于缺乏明确的相对不起诉标准,检察官拥有了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这虽然有助于检察官根据案情做出最符合实际的决定,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这项权力被滥用,犯罪者就可能利用这一漏洞来逃避其本应受到的刑事处罚,这增加了社会所面临的风险。
(二)未成年人本身的可改造性存在不确定因素
现行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未成年人的品行表现如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成长经历、平时表现、性格特点等进行评定是决定是否对其起诉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品行表现的评定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成年人可能会故意在此阶段表现良好以避免被起诉,而过后却又重新犯罪。首先,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性,当面对可能面临的刑罚时,即使他们在本质上并未真正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后果,但出于逃避刑罚的目的,也会以认罪来争取获得不起诉处理;其次,在实践中也根本无法准确的判断犯罪人的真实想法,因此,就难免会发生对仍存在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人进行不起诉处理的情形,进而使其重新危害社会,而这也是相对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三)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存在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诚然,任何一项制度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相对不起诉制度既有着保护未成年人的一面,同时又有着增加犯罪的可能,这也是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又一风险所在。对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来说,在对一个未成年犯罪者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其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受刑事处罚,因而继续犯罪。同时,对该未成年人周围的其他未成年人来说,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未受处罚,其他人就可能会怀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也不会被处罚,进而开始进行一些犯罪活动,这不仅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也与建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因而,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可能会给未成年人以错误的引导,使其认为犯小错误就可能不会受到刑罚,进而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提高。
(四)存在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的风险
被害人作为犯罪活动的直接受害者,其所受损害不仅包括身体的损害或财产的损失,同时还包括心理上的挫伤。对犯罪人进行处罚,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对被害人心理上的扶慰。在实践中,如果对犯罪人作出不起诉处理,则可能会使被害人认为犯罪人逃脱了本应受到的惩罚,这不仅会使其心理受到进一步摧残,同时也会使其对我国的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会导致其选择以私力救济的方法对犯罪人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报复。
四、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风险评估机制
司法实践中,扩大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就应使该制度符合惩罚犯罪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因而,针对该制度在适用上可能存在的风险,可以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风险评估机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定,以使该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一)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标准评估机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标准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前提条件也应当参照此标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标准,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在实践中“犯罪情节轻微”并不仅仅局限于轻微型犯罪之内,在重罪中也可能存在着“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一般来说,未成年人犯罪者都会被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即使未成年人犯了重罪,如果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犯罪情节轻微”量刑情节的,也可能被认为是犯罪情节轻微。1叶莹.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M].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04).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虽说其犯罪情节往往与他的年龄大小、对社会的认识程度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紧密相连,但不可忽略的是,十四周岁以上的人的世界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有了一定的区分善恶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犯重罪的未成年人一般都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对其适用相对不起诉,则很难保证其不会重新危害社会,因此,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范围必须局限在轻微型犯罪之内,对于犯重罪的未成年人,即使其具有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也不能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此外,在实践中,如果能够适用缓刑,即说明其犯罪情节轻微,故而可以参照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对于这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才可以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这也是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最基础条件。
(二)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主观条件评估机制
具体来说,应当建立全面调查机制,不仅审查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事实经过、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而且注意调查其犯罪动机、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品行表现、社会评价等,从而对其主观可改造性作出评估,并决定是否适用相对不起诉。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明确拟作出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悔罪作为一种主观心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未成年人痛改前非、改过自新的决心。这一点主要可以通过其犯罪后主动坦白、如实交待罪行或进行检举揭发等表现出来,对于这类未成年人如果其真正有痛改前非的决心,且在犯罪后该未成年人或其家长能积极主动的采取行动以挽回损失的,则可认为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可以对其作不起诉处理。1叶莹.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M].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04).其次,应考察未成年人是否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否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是否会重新犯罪。而自控能力的强弱可以根据该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来进行判断,如果其在犯罪前一贯表现较好或者无劣迹,且能够接受老师家长的教育,对于这类未成年人即使在犯罪后也容易被教育改正,不至于重新犯罪,可以对其进行不起诉处理;而如果其犯罪前一贯表现恶劣,劣迹累累,应认为自控能力弱,不具备适用不起诉的条件。最后,应考察未成年人是否属于主观恶性较小的情形。判断主观恶性的大小,可以从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动机入手,犯罪的原因和动机又主要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犯罪人的主观意识形态,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
(三)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客观条件评估机制
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时,必须考量其是否具备一定的监护条件和社会管理教育条件,使其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有必要对拟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的客观条件进行评估。首先,良好的家庭监护条件能够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物质基础,并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和保护,使他们得以健康成长。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成长中容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健康成长不能离开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故而,如果没有没有良好的家庭监护条件,就不应对其适用不起诉。其次,社会管理教育条件能够使犯罪的未成年人在被适用相对不起诉后,其回归社会时依然能够就学就业,或虽不能就学就业,但生活有保障,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能对其进行监管教育,如此才能使其不再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被害人谅解评估机制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也意味着该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已被降至最低,因此有必要建立评估机制决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取得受其犯罪行为伤害的被害人的谅解。实践中,在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中,特别是盗窃、轻伤害等案件,被害人往往更为关注的是其经济损失能否得到尽快的补偿、赔偿,此时如果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能够主动向被害人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则被害人在经济、心理等方面的补偿要求就会基本被满足,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该未成年人。此时,在对该未成年人做出不起诉处理的话,其也更能接受,不至于造成其他不必要的后果。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不起诉适用率较低,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被起诉至法院。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应该也能够完善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同时,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时,应对该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风险进行考量,建立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风险评估机制,从而使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此外,还应当注意相对不起诉制度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衔接。
作者简介:彭燕,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兼未成年人检察处处长。
收稿日期:201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