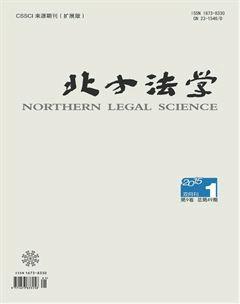环境侵权证明责任的司法实践现状与评析
罗发兴
摘要:在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对环境侵权案件在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问题,已经形成了值得肯定的做法。但对酌定确定损害赔偿额的,法院应当通过释明保障当事人知晓和辩论的程序利益。对污染导致身体疾病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疫学因果关系证明、合比例认定原则等降低受害人证明责任。
关键词: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
中图分类号:DF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1-0105-08
一、研究目的和样本情况
有媒体指出: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纠纷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但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不足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发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举证难、审判难等。①但无论是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还是更早之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订)、《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表明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立法者对受害者设计了最轻的证明责任,特别是对因果关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受害方只需要证明加害方存在污染行为和自己受到损害即可。法律对证明责任的这种分配若仅从理论上观察,受害者胜诉应当相当高,而若受害者胜诉率高,则加害者环境污染的成本将加大,环境污染将会较少。但上述媒体的观点以及关于我国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现状,②提醒我们应当对这种“书本上的法律”在现实中的运作状况(即“社会生活中的法律”)进行探究。
在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下,诉讼作为其他机制失灵下的救济和补充方式,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小觑。鉴于事实认定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重要地位,探讨环境侵权中证明责任的司法运作现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污染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的障碍和问题,并通过完善相关机制以发挥诉讼治理环境污染的应有作用。
基于此,笔者随机收集了60个涉及环境侵权的案件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数量越丰富越有利于提高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③但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本文所选的作为分析对象的环境侵权案件在数量上只有60件。但这些案件所发生的地区具有分散性和广泛性,克服了单一地区案件来源的片面性,从而增强了本文分析基础的可靠性和分析结论的可接受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60个环境侵权民事案件中,46个案件(均以民事判决书形式出现)来自于北大法宝数据库,另外14个案件来自中国知网(包括报纸和期刊)、中国审判法律应用系统(V3.0版)和互联网。这60个案件均已排除同一被告同一污染行为所致的纠纷,即如果有2个或2个以上的原告针对同一被告的同一污染行为提起不同诉讼,则只选择其中1件作为样本。从案件所涉及污染源来看,涉及空气污染的有22件,涉及水污染的有31件,涉及磁场污染的有6件,涉及噪音污染的有1件。从损害后果来看,因财产遭受损失提起诉讼的案件有52件,因健康遭受损失提起诉讼的有8件。
二、环境侵权证明责任的司法实践现状
环境侵权案件主要涉及三要件的证明,即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尽管在个别案件中可能还会涉及对免责事由的证明,但其出现的几率非常小,本文所收集的样本也未涉及此类案例。
(一)侵权行为的证明
环境侵权案件中被告的侵权行为主要是环境污染行为,因此,原告首先需要证明被告存在污染行为。从收集到的案例样本来看,
关于是否存在污染行为,在多数案件中是不存在争议的。有70%的案件被告对其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并不否认。这些案件往往存在一些情形:污染行为比较明显,并且也持续存在,原告及时的证据保全,被告因污染行为已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经过事先的协商处理。
有30%的案件被告否认存在侵权行为(污染行为)。但对于一些无法通过肉眼观察,或者非持续性的污染以及造成污染的主体非单一时,被告往往会对其污染行为予以否认。特别是像噪音污染,由于其对环境的影响不累积,一旦声源停止发声,噪声也就消失,造成原告取证难。此外,在某些案件中,被告不否认其对污染物的排放,但被告通过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污染物排放量未超过国家标准或者装置合格达到国家标准或者其系无“三废”企业称呼获得者,从而否认侵权行为的存在,故而损害后果与其污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例如在张某某诉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某某分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中,被告某某公司提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的批复意见复印件,证明烯烃厂的装置合格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④在苏联芝与陈家才等鱼塘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被上诉人南宁市农富复合肥料厂提出其属无“三废”企业称号,因而否认存在污染行为;⑤在隋平等十人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被告之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抗辩称,其外排废水均实现达标排放,其中一些排放指标还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⑥
从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对于以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为由进行的抗辩,除电磁辐射污染案件外,法院均未予采纳。法院所持的理由,大多如在隋平等十人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所引用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91]环法函字第104号)中指出的,“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污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因此,即使被告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也不能推翻其行为构成环境侵权行为。但在电磁辐射案件中,法院对此问题则持相反观点。例如在原告张德新、吴小健与被告福建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南靖分公司因电磁波辐射引发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告提出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经检测,均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后来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这一抗辩,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⑦在其他涉及电磁辐射的案件中,法院均采取这种思路,即只要经检测辐射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则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或者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是导致原告损害后果的原因。⑧
(二)损害后果的证明
1.通过鉴定确定损失额。在60个案件中,共有36个案件是通过鉴定确定损失。在有些案件中,通过鉴定确定损失的前提是需要先确定相关养殖物的数量,但有时在鉴定时因养殖场腐烂等原因无法确定,法院通常会适当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例如,在邬良永等诉邬宗军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虽然原告养殖的水产品实际损失数额无法准确统计,但法院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认为七原告向宁海县海洋环境监测站所陈述的塘内养殖的各种水产品的数量都在合理的养殖密度之内,对其主张可予采信。根据宁波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认定七原告养殖的水产品直接经济损失为137140元。
2.法官酌定损害额。在减轻原告对损害后果证明责任上,对于损失难以计算的,法院有时直接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确定损害额。例如,在九江市庐山区虞家河乡东光村村民委员会诉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九江发电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在认为“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请即要求被告赔偿恢复水源治理费、解决饮用水供应所需费用及经济损失费、人身伤害治疗及康复等费用50万元,原告未提供具体计算依据和有关证据”的同时,“考虑到损害事实存在,故可酌情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0万元”。⑨在笔者收集的60个案件中,法官酌定损害额的案件有4件。
3.法官估算损害额。对于损害额较少、启动鉴定程序不经济的案件,法院有时会直接根据市场价格对损害额作出判断。在笔者收集的60个案件中,只有1个案件法院采取估算确定损害额,即刘伟南与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该案中,法院在确定污染以及受害人自身未开增氧机都可能造成死鱼的情况下,认为“鉴定报告,确认上诉人鱼死亡是由于缺氧造成,与被上诉人排放到河涌的污水的有机物消耗河涌水的氧气有一定关系。但因缺氧有多种原因,如上诉人未开增氧机也存在一定关系,在不能具体确定谁的责任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鱼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故根据上诉人鱼死亡的数量及当时的市场价格以及上诉人起诉主张死鱼损失为5251.6元等情况,被上诉人以赔偿4000元较为适宜”。⑩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
1.对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环境侵权案件中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污染者就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应当先行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例如,广东泺雅灯饰制造有限公司与谢赞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盖然性的证明上诉人实施的排污行为导致其鱼类死亡”,继而认为“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排污行为与被上诉人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对于原告先行提供的初步证据,则只需达到很低的证明标准即可,例如上述案件中,“被上诉人经营的本案所涉三口鱼塘分别于2003年11月、12月、2004年3月发生非正常死鱼现象,均在上诉人投产经营、开始超标排放污水之后”,法院即据此判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盖然性地证明上诉人实施的排污行为导致其鱼类死亡”。
有的案件还以因果关系推定为由,认为受害方需要证明一般情况下污染环境行为能够造成这种损害,浙江平湖“蝌蚪”索赔案即为其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写道:“根据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受损人需举证证明被告污染(特定物质)排放的事实及自身因该物质遭受损害的事实,且在一般情况下这类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够造成这种损害。本案原审原告所举证据虽然可以证实原审被告的污染环境行为及可能引起渔业损害两个事实,但由于原审原告所养殖青蛙蝌蚪的死因不明,故不能证明系被何特定物质所致,故原审原告所举证据未能达到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由于原审原告据以推定的损害原因不明、证据有限,其所主张的因果关系推定不能成立,其遭受的损害无法认定为系原审被告引起,故要求原审被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
在刘芳钰诉钦州国星油气有限公司等滩涂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未完全适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而是按照心证比例分担。该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原告(上诉人)的文蛤死亡是否是被告(被上诉人)的抽沙行为造成的,对此,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广西区防疫站的检验报告仅说明文蛤带有病毒,但没有明确病毒的起因,即可能是文蛤自身携带,也可能是水域污染、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原因所致。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未能举出有关抽沙与文蛤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其所举的证据也不能证实抽沙与文蛤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因为钦州市环保科研所作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大纲》以及广西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作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只表明合法的抽沙不会对文蛤养殖造成影响,但两被上诉人的抽沙船有时越界抽沙、并靠老人沙养殖场较近,以上几份证据均不能排除这些因素会对生态环境及附近的养殖业造成影响。因此,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因其他因素如天气、病毒、养殖技术等造成的损失由上诉人自行承担。”
2.污染导致身体伤害(疾病)案件法院认定因果关系的现状。在收集的案件中有8件涉及因污染导致疾病而提起诉讼的情形,但原告胜诉的只有1件。原告败诉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法院以疾病(如癌症)的发病原因复杂为由,认为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缺乏事实依据。例如,在刘德胜诉湖南吉首市农机局喷漆污染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第二次再审的抗诉机关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主张,认为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市农机局不能证明其喷漆行为与刘德胜患癌症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对刘德胜进行赔偿。事实上,市农机局也曾经对此做过许多努力试图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均告失败。但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书中认为:“市农机局在生活区进行喷漆作业, 对刘德胜等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但刘德胜主张患上癌病是市农机局喷漆行为所致,由于目前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病的起因,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市农机局举证不能为由推定本案所涉市农机局环境污染行为与刘德胜患癌病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
第二种情况是法院采用流行病学方法说明因果关系不成立。例如,在吕某等与姚某等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中原告吕某、王某的大儿子被市儿童医院诊断为患有结节性硬化症,二儿子王博乐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后医治无效死亡,吕某、王某认为其孩子病因与废品回收站环境污染有关,遂起诉废品回收站的业主和出租经营场所的村委会,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废品回收站的污染行为与原告孩子病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废品回收站自2009年2月开始擅自从事废塑料粉碎和清洗加工,对厂区内的水和厂区附近的水井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但没有证据显示在2009年2月之后废品回收站对南门村的饮用水造成了污染,而王博乐因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患了白血病,并且在南门村还有其他孩子与王博乐一样患有同样的白血病。而根据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南门村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该“废旧回收站”落户前10年和后6年都处于车墩镇乃至松江区的低水平,虽然后6年该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明显低于松江区全区水平,也低于对照的联庄村。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王博乐患病、死亡与废品回收站没有因果关系。二审法院判决认为,王博乐患病死亡固然值得同情,但其病情证明中并无院方对其病因的判断,亦无对病源作出明确诊断,因此从举证责任上看,吕某、王某尚未完成王博乐致死疾病源于环境污染之盖然性的举证责任,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
第三种情况是法院以原告的污染排放量达标为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这种案件主要集中在电磁辐射案件,在原告以电磁辐射造成其身体疾病为由提起的诉讼中,法院均以辐射量未超过国家标准为由,进而否定原告的疾病与被告设备的电磁辐射存在因果关系。例如,在杨某诉某电业局一案中,杨某主张电业局的高压铁塔的电磁辐射导致其身体产生疾病,但鉴定表明高压铁塔周围电磁辐射的各项指标低于相关国家标准允许的限制或强度。法院因此认为该行为不具备违法性,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驳回杨某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在众多污染导致疾病的案件中,笔者仅收集到一件原告诉求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件,而且该案系发生在中国立法贫瘠的1978年。该案原告王娟为被告员工,1978年7月1日,雷击导致被告工厂出现大范围氯气泄漏,附近10多名居民中毒,被送往医院医治。原告因吸入氯气中毒症状较为严重,住院治疗1年多时间。被告支付了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赔偿了她的收入损失。原告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过敏性支气管哮喘,需要继续治疗。原告再次要求被告支付其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被告以过敏性支气管哮喘与污染事件不存在因果联系为由拒绝。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受理了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一,原告在此次患病以前从未患过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并且其本人无此类疾病之家族病史;第二,医学实验证明氯气中毒可致人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疾病;第三,原告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疾病的时间正是在青岛市化工厂发生氯气外溢污染事故以后。法院据此判定,原告的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系青岛市化工厂氯气外溢污染事故所致,故被告应对原告负赔偿责任。最后,双方当事人接受了法院调解,达成了赔偿协议。
三、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司法实践的评析与完善
(一)排放标准未超过国家标准与侵权行为的认定
从前文对现状的总结来看,对于电磁波辐射以外的污染行为,即使其排放量未超过国家标准,法院一般也不会据此认定不存在侵权行为。但是对于电磁波辐射案件,法院则采取相反的态度。那么,电磁波辐射是否具有不同于水污染、空气污染的其他特殊性,而使其需要做出与水污染、空气污染不同的处理思路?
在电磁波辐射的控制上,一方面国家需要满足公众通讯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维护人体的健康,为此,相关法律围绕对二者的协调和平衡设定相应的规范。具体体现在:电信设施的辐射不能高于国家规定的辐射标准,同时必须严格按照1997年环保总局发布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进行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后电磁辐射验收,已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的电磁辐射设备,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功率,对于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防治电磁辐射污染环境的保护设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
上述规则为我们界定电磁辐射构成侵权行为提供了外在标准。首先,电信设施的辐射标准不能超过国家标准,一旦超过国家标准,即构成侵权行为。此外,考虑到电磁辐射的测量具有专业性,普通民众难以自行测量,而且由于存在时间差,不排除电信部门通过调整功率等手段规避测量,测量的时间点未超过国家标准不必然代表此前的辐射标准未超过国家标准。因此,需要结合其他外在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其中,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审查一个外在的标准来确定电磁污染。根据上述《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应当认定构成侵权:未于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后未进行电磁辐射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擅自改变经批准的功率;对于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防治电磁辐射污染环境的保护设施,未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对于作为受害人的原告提出被告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规定,即当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例如,原告主张被告未于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于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否则被告应当承担该事实认定的不利后果。
(二)损害后果证明中的酌定
根据前述对司法运行中对环境污染案件损害后果的认定来看,采用鉴定确定损害的方法固然应当作为首选,但面对许多案件中损害额的难以确定,绝对采用鉴定并非合理之举。因此,采用酌定或估算不失为可选择的方法。但需要分析的是酌定、估算,特别是酌定这种认定方法的依据。
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赋予法院或法官直接确定(酌定)损害额的,只出现知识产权法领域,最早出现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2款中,此后修改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也明确了法官酌定赔偿额的权利,这种制度也被称为法定赔偿制度,还有学者称其为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或损害数额酌定,它指的是在损害赔偿诉讼中,如果损害事实确实已经发生,但权利主张者难以证明或无法证明具体损失大小的时候,从诉讼公平角度出发,赋予法官根据言词辩论情况和证据材料对该损害赔偿数额作出裁量的制度。
司法运行中损害赔偿额的酌定给我们的启发是,该项制度需要及时在立法上予以确定,因为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尚未有规定。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损害赔偿额酌定的适用前提必须是鉴定困难或者鉴定成本高于当事人的请求金额或者与当事人的请求数额明显不相称。但当法官有意采用损害赔偿数额酌定时,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即应由法官对当事人进行释明,让当事人有机会对是否具备损害额酌定条件以及损害额酌定范围进行辩论和发表意见,防止因法官的未释明造成突袭裁判。
(三)因果关系认定中原告是否负担部分证明责任
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规定下,仍有部分判决书认为原告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此前提下才由被告对污染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负担证明责任。对部分判决书的这种观点如何看待?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在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中,主要有三种模式:
1.原告负担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被告否认的,必须提出反证。例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规定,原告只要提出表面证据,证明行为人已经或很可能导致环境污染,诉求即可成立,若被告否认,则必须提出反证。
2.因果关系推定。根据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公害犯罪处罚法》,如某人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且其单独排放量足以危害公众健康,而排污后公众健康事实上受到或正在受到危害,便可以推定该危害是由该排污者引起的。德国《水利法》和《环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作出了较详细规定。法院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具体化,受害人只要提出证据证明已发生的损害,且证明该损害是某废弃物造成的,就可以推定该废弃物的排放企业是加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其证明因时间或空间等原因,该废弃物不会与环境发生反应而导致损害,或者即使发生反应也不会导致该损害。
3.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在我国,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实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即受害方只需要证明加害方存在污染行为和自己受到损害即可,而关于免责事由和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则由加害方负担。与因果关系推定相比,受害方无需证明损害是污染造成的,因此其更有利于受害人。
由于我国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的原则,那种认为原告需要负担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我国立法规定。这实际上是法官主观上认为在个案中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过小,为了避免直接适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所带来的不公平,通过要求原告提供初步证据,以求得法律与现实的适当平衡。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个案的特殊性,如果在这些个案中这种做法是妥当的,则说明我们的立法对所有环境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存在不合理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环境侵权造成受害人健康损害的情形,对于这个问题,在下文笔者还将继续论述。
(四)污染导致疾病的因果关系证明
在笔者收集到的60个案件中,污染导致疾病的案件只有8件。依据后果具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污染导致急性疾病的发生;一类是污染导致大规模同类疾病的发生;还有一类是污染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甚至演变为癌症。这三类案件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类案件原告比较容易胜诉。该类案件导致疾病的发生比较迅速,因果关系往往较为明显,法院一般会适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认定因果关系存在。例如前述的1978年氯气中毒案件。
第二类案件往往具有群体性特点,笔者目前尚未收集到该类案件,可能是由于这类案件往往涉及维稳问题,政府会通过行政手段或其他方式予以解决,导致司法中这类案件几乎找不到。在日本曾经发生过两起这种大规模的案件,一起是因食用受镉污染大米而导致的疼痛病,另一起是新泻水俣病案。
第三类案件原告通常难以胜诉。这类案件由于疾病的发生往往距离污染开始的时间较长,而且往往只是原告一人提出其受害,相邻的其他人未有相似的疾病发生。从目前医学角度来看,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难以判断污染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不会适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来认定因果关系存在。例如电磁辐射案件即属此种情况。
对于第一类案件,实践中发生的较少,一般都是由生产事故造成,污染的气体或污染物毒性较强,致害后果较为迅速和严重,因此,因果关系往往比较明显。
对于第二类案件,在国外往往采用疫学因果关系证明法(或称流行病学因果关系证明法),例如,在日本富山地方法院于1971年6月6日日本四日市哮喘诉讼判决中以及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地方法院支部于1972年8月7日所作出的判决中,对因居民因长期食用受镉污染的稻米而导致全身性骨折的“呼疼病”,采用了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即从地域、季节、患者等因素出发,考察该疾病的特点及规律,以确定疾病发生的病因。根据判例,疫学因果关系的证明必须满足四个要件:第一,该因子在发病的一定时期以前就有作用;第二,该因子的作用程度显著时,该疾病的发病率就增高;第三,减少或除去该因子时,该疾病的患病率会降低,并且在不具有该因子的集团内其患病率也非常低;第四,该因子作为疾病的病因、机制能得到所有生物学上的合理说明。
目前最值得研究的是第三类案件,由于疾病本身的产生具有多种因素,现有科学技术难以确定其中的具体缘由。因此,即使法律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实行倒置,在原告主张污染导致身体疾病案件中,当因果关系真伪不明时,法官要么通过认定污染物排放未超标否定因果关系,要么要求原告证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司法行为已经实际上改变了法律对因果关系倒置的规定。这类案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才能既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不会无辜追究污染者的责任。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由谁来承担风险更合理,不仅是实体法问题,也是程序法问题。
在美国,对环境污染导致疾病发生的案件,未采取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做法,但法院采取其他方法来减轻原告的负担。例如,法院解释联邦证据规则允许统计证据和医学证据,从而为采用疫学方法奠定基础。再如,有的法院采用实质因素标准(substantial factor test),按照该标准,如果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有很大的影响,即使是没有被告的行为原告的疾病也可能发生,被告也应当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即使证据只是表明被告实质性增加原告损害(疾病)的风险,被告也应当承担责任。
对比来说,我国立法在对受害者采取最优的法律机制(即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司法却在提高受害者的举证责任;而美国立法对受害者采取的并不是最优的法律机制,但司法通过其他方法在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二者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因果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情况下,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未必可取。既然上述第二类案件中环境污染与疾病的产生具有极大的科学不确定性,法律应当对这种不确定性进行合理分配。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方法是采取合比例的认定原则,即由法官综合案件的各种因素,包括受污染时间长短、污染量、与原告相邻其他人的受害情况等综合进行心证。该方法最早由日本的仓田卓次法官提出,针对的是法官心证未达到证明度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在该情形下法官内心一般也会存在着四六分或三七分的心证比例,据此在实体判决中对相应比例的请求予以支持。例如在仓田卓次判决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中就采用了该认定原则,在交通事故与后遗症因果关系的认定中,法官对肯定因果关系证据与否定因果关系证据形成的心证分别为七成与三成,由于肯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度为70%,因此,法院对原告请求中的70%损害额予以支持。在环境污染案件中,采取按心证比例确定民事责任的,除了在污染导致疾病这类不易确定因果关系的案件外,在污染导致财产损害的案件中,如果涉及到可能是多因一果或者难以排除其他因果关系情况的,也可采用这一原则。例如,前文提及的刘芳钰诉钦州国星油气有限公司等滩涂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即采用此种方法。
综上,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中立法者对污染受害者在证明责任上的有利规定,在实践中既有合理的创新,但同时也产生了异化,导致了受害者在维权中遭受挫折。科学的不确定性风险在立法上需要重新进行斟酌分配,完全的“一边倒”之立法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适用困境,采用合比例认定原则将会更公平。
Review on Judicial Practice of Burden of Proof in Environmental Torts Ca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60 Cases
LUO Fa-xing
Abstract:In light of the rather general regulations by law, judicial practic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positive and feasible rules on burden of proof pertinent to tortious conducts, damages and causation in environmental torts cases. In case that the amount of damage is determined by discretion, judges should inform the parties concerned their procedural interests to know and to debate. With regard to claims for pollution-related diseases, different rules should be appli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uch as shifting burden of proof, causation of epidemiology and proportionate determin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tortscausation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