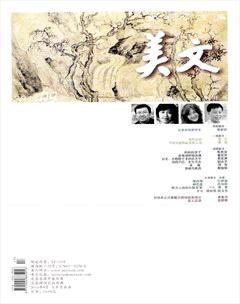鸣禽
微风物
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有时间有兴趣去听别人的唠叨?脑袋紧随着屁股,身体服从于脚跟,这时代的道路是用不着刻意选择的,正确与否,只欠一个评价,而评价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标准,有人说好就好,有一些人说好就更好,现在的人们需要的是在自己的脚印后边点一个精短至极的“赞”,而不需要在脚印前方指手画脚。
二来,我的文章多为郁结的“心气”所凝成,因为对现实及人生看得太冷静、太清楚了,只要照实发出“音”来,就总是有些不中听。
惊蛰一到,消隐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乌鸦,便从平原的另一端飞来,开始了一声声的鸣叫。
于是,那些略显沙哑似被久久压抑了的声音,像领了春天之命的野草,终于挣脱寒冷的禁锢和冬的咒语,以不可阻挡之势,从乌鸦的歌喉里汹涌而出。
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微风和煦,阳光明媚,翻涌的白云高高挂在天边。
白云下有一条横贯南北的林带,清一色高大的白杨,叶片丰厚繁茂,暗绿鹅黄地堆拥成绿色的浪涛,远远望去,俨然一条奔腾的大河。而三三两两傍林而翔的乌鸦,却如绿潮上匆匆掠过的点点黑帆。
“啊,啊,啊啊——”乌鸦们边飞边大声呼喊,声音粗粝而富有激情,长长的尾音在林间草地上回荡。这是个有一点儿孤注一掷的春天,一口气把全部力量和意念都押在绿上,除一览无余而主题鲜明的绿,其他颜色竟都被忽略或忘记了。乌鸦们正是这种狂热情绪的推动者,它们沉浸在亢奋的抒情之中,除了飞翔和叫喊,似乎并没有心情再做别的了。
那么,就“大声歌唱吧”!
上个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个无知少年,虽然凭着单薄的身体和力量尚且无所作为,但却已经传染了那个时代的狂热。所以,那时我也会时不时地清一清嗓子,准备着像春天里的乌鸦一样,为“火热的生活”引吭高歌。
那时,田野一片宁静,除了农人赶牛的吆喝声和耕牛们偶尔发出的愉悦或郁闷的叫声,其他声音似乎还没有完全从寒冷中苏醒过来。乌鸦的叫声就这样成为春天的第一份宣言。
接下来出场的是戴胜鸟。
一只很大的花鸟,在“惊蛰”与“小满”之间,张开印满花纹的翅膀,从村头飞掠而过,将“布谷谷、布谷谷”的鸣叫,撒向麦苗儿泛青的田野。那鸟儿的鸣叫,自带着悠扬、旷远的回声,不经意间,就将春天的疆域和含义豁然拓展开来。
早听说有一种能够为人类促播的鸟儿叫布谷鸟,看它的样子,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它不但能用声音提醒人们去播谷,还会以飞翔的姿态去示意。它们的飞翔,看起来并不是飞翔,倒像是在空间或时间的急流里游泳,一起一伏,一次次沉落又一次次奋力向上,在湛蓝的天空里划出一道透明的波浪状轨迹。它们身体的每一次下沉都让人联想起农民的一次弯腰播种;而每一次奋力向上,又让人想到对某种淹没或沉落的抗拒。
记得小学时的一次语文课上,我们正被老师絮叨得昏昏欲睡,突然传来了“布谷谷、布谷谷”的鸟叫声,仿佛一阵清凉的雨,唤醒了午后萎靡的树叶,我们纷纷打起精神寻声把头转向窗外。少顷,便有一只漂亮的鸟儿落在了教室外的泥墙上。只见它披一身精美的羽毛,灿烂的冠羽下,一双明亮的圆眼睛活脱有神,就像一个老朋友似的,不惊不慌地侧过头,与我们对望。语文老师不失时机地指着那鸟儿借题发挥:“布谷是一种灵鸟,它总是准确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催促农民及时播谷,而现在它就是来提醒我们,要好好读书,别辜负了大好时光……”从此,那鸟儿在我的心里更加神奇得如精灵一般。
直到多年之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一场误会,乡间俗称为“臭咕咕”的戴胜鸟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布谷鸟,真正的布谷鸟儿是指生活在山地林间的大杜鹃或中杜鹃。
不过那之后,我却当真按照“布谷”的寓意,好好学习,致力于纸上耕耘,并成功地泅出了那个时代、那片土地和那些往事。渐行渐远矣。匆忙的行进之中,已无法判断自己到底在岁月里走了多远多深,正在走进的是哪一个夏天。
“小满”一近,北方就迈进了夏的门槛。农谚有“小满鸟来全”的说法,意思是节气到了小满,各种各样的鸟,包括常驻的留鸟和迁徙途中“打间过站”的候鸟,该露面和该发声的,都将在季节的舞台上登场亮相。
一时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一派繁荣景象。草原上、树林里、水塘边、田垄间、房前、屋后……到处是鸟的身影和鸣叫。有整天叫个不停的小柳莺,也有体形稍大却不轻易张口“言语”的伯劳、黄胸鹀和灰头鹀。我知道红喉歌鸲和蓝歌鸲都能够发出清脆而复杂的鸣啭,但它们生性羞怯,很少在人前大摇大摆地飞过或大胆鸣唱,它们多藏身于远离村庄的林子里,专门在清晨或正午时分,以歌声打破原野的宁静。黄鹡鸰一边轻轻细细地啼鸣,一边匆匆赶往湿地水洼,停落时长尾巴不停地上下摆动,倒影映在浅水之中,仿佛地上和水中各有一只黄鹡鸰在比足对望。
记忆中最常见也最令人难忘的鸟儿,当属被乡邻称为“俄乐儿”的短趾百灵。它们灰白色的羽毛具有高度的伪装性。如果它们不动也不叫地站在枯草中或发白的碱土丘上,很容易被当成一个从地上凸出来的土块儿。它们只有悬停于蓝天白云之下忘情歌唱时,才彻底摆脱了土色的遮蔽,人们也才发现那其貌不扬的小东西竟然是个巧舌如簧的歌手。但从此,它们也违背了生命基因中暗含的天意,将自己赫然暴露于敌手的视野之中。
这勇敢而又莽撞的小鸟,有时真让我那颗脆弱的心为之震颤。怎么能因为逞一时的意念之强,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不顾及自身安危甚至身家性命呢?用一句东北的土话讲,那叫“显摆”或“得瑟”。要知道,那个时代中国大地正处于极左阴云的笼罩之中,我虽少不更事,却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和其现实的危险与恐怖。
我有一个叔伯舅舅,我称老舅,曾上过学,受过系统的教育,回乡后在小学里当语文教师。乡里人常说“好人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老舅是天生的辩才,能说会道,又深明事理,所以深得村民的推崇和折服。他本人也就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止不住言说的冲动和欲望,大说而特说,以至于忘乎所以。老舅对着人群口若悬河大讲道理的样子,总是让我联想起短趾百灵煽动着翅膀悬在半空中大叫特叫的情形。
针对老舅这类人,父亲在世时给出的评语就是“叫唤雀儿没肉吃”。他可不信“好人出在嘴上”那种“奇谈怪论”,他认为一个男人的力量主要应该表现在行动上,事情是做出来的,并不是说出来的:“穷叫唤,有什么好?祸从口出,早晚要惹大祸。”果然,不出一年,老舅这个人类中的“叫唤鸟”就不幸“中枪”,被打成右派。就在他遭受批斗、拷打期间,仍然人“倒”嘴不“倒”,没有一天停止过与批斗他的那些不讲理的人“讲理”。让那些批斗者最愤怒,让亲友们最担忧的始终是他那张爱“叫唤”的嘴。为什么他宁死也不肯把那惹祸的嘴闭上?他们这类人的生命里到底潜藏着怎样怪异的激情与动力呢?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鸟类的书籍,了解了禽类特别是有关鸣禽的一些常识,才知道鸟儿在春天里啼鸣原来也是一件很功利的事情。它们美丽的鸣啭下潜藏着极大的野心,往往直指交配权,只要谁叫得好听,叫得动情,谁就能够得到雌鸟的青睐,为它产一窝能够将生命基因传往后世的卵。很显然,说个不停的老舅并不是为了爱情或传宗接代而“叫唤”,我们看不出他真正的目的,感觉他只是为了抒发和表达,满足于嘴上的痛快。但后来细想,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他潜意识里也有一种将自己生命信息传向永远的激情,不幸的是,他是人类政治漩涡中的弱者,他隐蔽的传世欲望注定会被明晃晃的暴力所摧毁。
就这样,一个月后,一窝小短趾百灵出飞,两只鸟儿变成了七只鸟儿,而老舅依然还是那个老舅,知道和崇敬他的人并未见多,只是脸上更多了些悲壮,身上徒增了几处残疾。
据说,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有一种很奇特的鸟叫做琴鸟,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雄琴鸟不仅能模仿出20多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而且还能模仿出许多它们听到过的其他声音,如照相机的咔嚓声、汽车的喇叭声、斧头的伐木声等等。由于模仿得惟妙惟肖,人们或其他鸟类根本就无法分辨真假。说起来,这鸟儿倒有一些像人类中的舞文弄墨者,虽泰然而坐,不动声色,却已将鸟语花香或万钧雷霆运诸笔端,可能感人肺腑,也可能摄人于十步、百步甚至于百里、千里之外,好不令人心驰神往或胆战心寒。
这奇特的鸟类,到底还是让我从内心里生出了一些担忧。将来,会不会有那样一个春天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了很多很多的琴鸟,却没有一个能够或敢于发出本真的鸣叫,出于某些原因,只是一味吱吱扭扭或丁丁当当地模仿其他声音……若是模仿其他鸟类倒也很好,那样的春天大概也会显得丰富热闹、妙趣横生;但若一群鸟儿全都疯狂地模仿起鹰啸或枪声,那时,恐怕不仅是鸟儿,就连人类也将被恐怖氛围所笼罩。那样的春天,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春天呢?
事实上,鸟类的世界不可能如我想象的那样阴森,毕竟它们的行为一向透明简单,不会像人类一样心、口及言、行严重相悖,动不动就能将一种看似平常的活动演化成某种可怕的“运动”。如果以阳光、乐观的心态去观察,很多鸟类随着春风而来,不过是借我们的屋檐、树枝、地面歇歇脚,寻一口水,讨一口饭。由于环境优美,气氛祥和,它们可以暂时放纵一下享乐之情,把内心的爱慕表达给钟情的异性,或者,把一路走来积聚于心的种种感触与同伴们分享;当然,这一切我们也都可以理解成对季节或对生活的歌唱和赞美。反正,那些没有定价,不讲销售策略的甜美声音如同清新的空气一样,总可让我们随意取用,尽情享受。
“小满”过后,大地里的庄稼开始疯长,不消几天,树上的叶子就大过了很多小鸟的身形。一支恢宏的乐曲进行到高潮之后,便注定要渐渐滑向低谷。鸟儿们借助一天天浓密起来的绿色屏障,开始向新的迁徙地进发。
窗外的鸟儿已日渐稀少,连续几个清晨,我都情不自禁地停下手中的写作,趴在窗口聆听此起彼伏的鸟鸣。虽然心里很惦记自己还没写完的文章,却不想回来伏案,索性由着性子尽情地听个够吧。这比朝露更加新鲜也更加容易流失的鸟鸣,在我的心里,远比我的文章美妙、珍贵。一来,我的文章总是显得太长,对于步履匆匆的人们本来就是一种障碍或压迫。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有时间有兴趣去听别人的唠叨?脑袋紧随着屁股,身体服从于脚跟,这时代的道路是用不着刻意选择的,正确与否,只欠一个评价,而评价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标准,有人说好就好,有一些人说好就更好,现在的人们需要的是在自己的脚印后边点一个精短至极的“赞”,而不需要在脚印前方指手画脚。二来,我的文章多为郁结的“心气”所凝成,因为对现实及人生看得太冷静、太清楚了,只要照实发出“音”来,就总是有些不中听。尽管我一直注意语言的优美、语音的清脆和语调的委婉,但其清脆嘹亮也还是不及过路山鸟的一声啾啾。对此,我自己也曾在私下里做过比较和反思,其悦耳程度大约只略强于乌鸦,但至多也不会超越麻雀,或者仅接近于麻雀。
麻雀的音调和音质我是很熟悉的,虽不具莺声燕语的娇媚、清丽,却也别有一番平实和晓畅,但是听起来就是感觉不那么动听,甚至有一些喧闹和令人不快。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麻雀的鸣叫细品起来确实有一点粗硬,直戳戳如一截木桩,虽掷地有声,却显然欠了些回旋和委婉;至于另外的原因,怕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麻雀自身,要怪也只能怪麻雀离人的距离太近。身边无风景,任何两种事物靠得太近都会有审美疲劳,更何况麻雀和人类已经近得如同一家,以至于一直被人们称作“家雀儿”或者“老家贼”。
对于同一屋檐下的鸟儿,称其为家里的“雀儿”倒是很好理解,可反过来又称为“贼”就有一点儿匪夷所思。大约还是因为平日里麻雀们进进出出之间,误以为自己也是“主人翁”,可以与真正的拥有者共同分享这个家和参与家中的事务了,所以就大大咧咧地随意起来,今天不打招呼吃了几粒谷,明天隔窗发现了室中一些正当或不正当的隐私,并明目张胆地议论几句。人心无常,久而久之,人们心里很自然就生出些反感和敌意来,认为那些贼头贼脑的家伙们天天在监视或觊觎着自己的生活。
古往今来,大凡那些多受误解之人,认真总结,其性情里一定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毛病和缺陷。比如传统的文人或文士,天性里就有一段难以更改的幼稚和愚痴。自以为“此心可鉴”,可真的谁都有兴致去“鉴”吗?说是“忠言逆耳”,但现实中深晓此理并能够按理行事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他们就像不受待见的“叫唤鸟”一样,横跨历史地一叫几千年,自然,也连续不断地被收拾、打压了几千年。这样想来,那些“老家贼”应该都是历代文字狱中冤死文士的灵魂所化吧?它们就那么无穷无尽、挤挤挨挨,自以为是并不可回避地排布或翻飞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野鸟散尽之后,能够传到耳边的鸟鸣也不光是燕子、乌鸦、“老家贼”等几种司空见惯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啼啭零星来自于巷尾或街头。寻声望去,总是能够望见某户人家的阳台或小区的树桠上悬挂着鸟笼。远远地,就会望见一只或几只辨不清种类的小鸟儿,在笼子里蹿上跳下,奋力地叫着,却总是让人猜不出那绵密的声音里蕴含的到底是一种激情还是一种怨愤。
那日,清早散步,恰路过一处鸟市,一眼望不到头的一个大市场,店铺、街面到处是鸟笼,到处是鸟鸣,一片翻滚沸腾。这边黄鹂唱罢,那边娇莺又啼……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很多叫不上名字,平生少见的鸟儿都在那里争鸣,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热闹的大戏台,仿佛集中了天下所有的鸣禽。
就那么走着走着,竟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所缠绕,于是便转身离开了那个市场。很久,仍有尖利的鸟鸣从身后隐约传来,但毕竟已是渐行渐远了,最后终于完全消失。
是啊,一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声音,又怎么追得上移动的脚步呢!可就在这时,又有一团困惑的乌云从我心底里倏然升起:人类的思维真是奇怪,为什么极其痛恨的或者极其喜爱的,最后,都要用笼子关起来呢?
任林举
吉林乾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青年理论评论家班学员。先后在《散文海外版》《作家》《散文选刊》等四十多种刊物上发表各类文字近百万。曾获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全国电力系统优秀著作奖等,代表作《玉米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