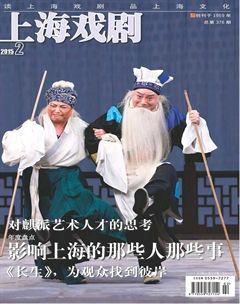何为现实?为何诗意?
翟月琴
若读过林语堂的《论幽默》,定记得起始处麦蒂列斯的“含蓄思想的笑”。作为真正的喜剧的标准,“笑”看似容易,然,试问多少前仰后合付诸一笑、言之无物,更何谈含蓄蕴藉?又有多少抚掌大笑流于粗鄙,以媚俗迎合观众,视思想于不顾?如此看来,笑亦非易事。但自1976年始,编剧陆伦章却跨越这屏障,不遗余力地向滑稽戏发起挑战,以独到的艺术感悟力,诠释出“含蓄思想的笑”。
《探亲公寓》,自2013年11月在中国戏剧节亮相,直至2014年10月20日江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的压轴演出,已经上演了六十余场次,不单为陆伦章赢得第三次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荣誉,还为滑稽戏奉上了又一部难得的扛鼎之作。全剧牢牢扣紧“含蓄”和“思想”,不仅令观众含泪而笑,还巧妙地回答了何为现实,为何诗意。一对在拆迁房过夜的农民工夫妻,遭遇联防队的审讯。此情此景,令阳澄湖畔春来客栈的老板娘阿德嫂思绪万千。回想起四十年前插队时玉米地里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阿德嫂仍痛心疾首、苦不堪言。当即决定为打工青年提供探亲方便,将“春来客栈”改为“探亲公寓”。所谓的现实,不言自明。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生活在底层,既缺乏经济保障,又备受人格歧视。选择如此棘手的社会问题作为题材,以石头的硬度撞击现实,却并非编剧的用意。相反,在他看来,面对体制的疏漏、生活的残酷,与其鱼死网破、头破血流,倒不如以柔软的诗意,关怀、超越进而鞭笞现实。
诗的线索清晰可辨,形成一套完整的抒情表达,为全剧引航导路。其中,以诗开场,揭示出集体所遭遇的社会压力;以诗束腰,流露出款款沁入的温暖;又以诗收尾,进一步燃起生活的希望。且不谈农民工弹唱的诗,在全剧里的鱼贯、点睛之妙,单是探亲公寓的空间设置,便凝练而含蓄地传达出编剧的诗意情怀。探亲公寓如同空间符号,它承载着社会现实的压力,还饱受人情冷暖的丈量。第三幕,上、下阁楼,隔离出两个空间,折射出两代人的共同理想;三个分区,灯亮灯灭,闪动着三家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选择。阁楼下的一代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两对年轻夫妻。A区,束兰花迫于经济压力坚持堕胎,与丈夫丁建设争执不休;B区,娟子身体虚弱,不论丈夫燕舞如何奉劝,她却力求保胎又坚持工作挣钱。两个分区已然流露出窘迫的生活现状,尽管如此,为何阿德嫂愿意不计得失,倾囊相助?燕舞的诗句“我们是蜷宿在天堂一隅的寻梦人”,点出了几家人的情感共鸣。C区,阁楼上的一代是返乡回城四十余年的夫妇阿德、阿德嫂,四十年前在苏北插队,经历过“文革”岁月摧残,返乡后经营客栈。轻率而应的一句话,如同儿戏,众人纷云:“给他们一张床,真正欠思量”。挂牌三个月,95.3%的外来务工客源,六折的房价,经济收入堪忧。附近居民怨其扰民,工作人员阿菊、阿桂执意辞职,老板阿德也心生不快。虽是这般艰难,为何阿德嫂反而不由分说、坚持己见?阿德嫂的一句“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贫下中农给了我们朴素善良的关爱和帮助”,道出了缘由。探亲公寓浓缩了不同的生活情境,上下阁楼是压抑的政治环境与穷困的经济生活的对照,然而,勾连起三个分区的轴心却在于“寻梦”。这种为梦而活的生命追求,这种全然不顾现实的压力却选择进城打工、蜗居受苦的人生理想,又何尝不是编剧一笔一笔描绘的诗意?
“寻梦”不仅是拥抱现实的一抹温情,更是登临塔顶俯瞰现实的一种深远。一个是安逸的农村生活,一个是蝼蚁般的城市生活,阿德、阿德嫂实在不能理解,农民工为何偏偏选择后者。透过探亲公寓里两家农民工的比对,便能探出究竟来。全剧最大的苦难,集中体现于娟子与燕舞夫妇的不幸遭遇中。在水天堂足疗中心工作的妻子娟子与拆迁公司打工的丈夫燕舞,结婚五年“想要个宝宝”,却因为出租房条件太差,做贼一般在即将拆迁的化工房过夫妻生活,反被联防队抓个正着;探亲公寓克服重重阻碍,好不容易为他们提供了一张床,刚刚怀孕的娟子又因为工作辛苦濒临流产的危险;阿德嫂帮助娟子住在公寓保胎,不料还是不幸流产,更糟糕的是,意外又降临到丈夫燕舞身上。18层砸落的花盆,令燕舞成为植物人,住院、手术、疗养,处处需要钱。一笔巨额费用,使娟子痛哭流涕、喘不过气来。束兰花与丁建设夫妇,则映衬出农民工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CEO家做保姆的束兰花和沙家浜旅游区的保安丁建设,经济条件显然比娟子夫妇优越。束兰花对城市生活耳濡目染,一心想脱离乡村的影子,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已经怀孕的她,不愿意跟未婚夫丁建设领证结婚,甚至不惜堕胎维护她头脑中建立起来的高质量生活。不能达到目的的束兰花,还将个人的不满足迁怒于阿德嫂,甚至将阿德嫂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针对两对夫妻的差异,编剧并没有植入高高在上的道德评价,反而将人性的复杂丢给观众去思索。前者选择为希望而继续留在城市生活,后者则最终绝望地逃离城市;前者的冲突集中于现实生活与个人追求之间,后者的矛盾在于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内心不平衡感;前者不顾外在的城乡矛盾而坚守人生理想,后者则由内在的不满转化为思考回到乡村生活。但归根结底,从这种自内而外,又自外而内的差异与转化中能够看出,陆伦章是寄望于超越现实生活的不幸,而寻求至高的生活理想。
温情的现实关怀,超越的生活理想固然是诗意的重要层面。但这是否就将诗意推向温柔敦厚、绵软无力?恰恰相反,透过诗意,也能够嘲讽、鞭笞现实的残忍,以柔克刚,更彰显含蓄所蕴藉的思想之光。阿德困惑于阿德嫂为何频频伸出援手,追问:“我一直不理解,你对农民工感情、热情、激情从何而来?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更无法接受阿德嫂一次次自掏腰包帮助娟子调养身体、为植物人燕舞垫付18万元,抱怨道:“我们开小旅馆是小本经营,你当我是保险公司银行啊?我真弄不懂,农民工和你有啥关系?”同样经历过“文革”,但夫妻二人却有着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判断。这不同,自然是现实常态,是人性多元,但同时也挑起全剧人物关系中最大的冲突和悬念。编剧添出一笔阿德被网住的场景,这种意象化的处理方式,明晰地显露出编剧的诗意表达。一张“网”,勾连起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同时也怒斥着贫瘠压抑的政治遭遇。阿德嫂不断召回阿德四十年前的记忆,让他从现在控诉、到感恩过去,又从理解过去、到回报现在。阿德嫂一句“忘不了啊!”好似叩开阿德的记忆之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突然晕倒在开河工地上送到县医院抢救。又是老余头卖掉了家里的一口大肥猪,替我交了医药费,救了我一条命。后来才知道, 这笔钱,是他准备儿子结婚给女方的彩礼。”回忆是为了回到现实,政治苦难已过去,经济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为何当初的往事却忘得一干二净?其根本是以历史鞭笞现实,这才是诗意背后的力量。因为疼痛,才以诗语疗救创伤,寻得希望。关于这点,不妨从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笔端“细小的针孔”里看去,大抵被痛刺穿,“我遇见的辽阔的悲伤,犹如大海般灿烂/在细小的针孔停伫,闪烁着明亮的疼痛”(《碇子》),才会烙上记忆的印痕,“她们充满活力的躯体,跟灼热的庞大的机台/被抽走,剩下无声的荒凉,潮湿的记忆”(《停工的车间》)。
全剧连环设问,带领观众在笑声中一同思考,处处留有编剧以诗意处理现实题材的痕迹。尽管这也是陆伦章所期待的更高的艺术追求,但反向而言,也是对编剧的考验。其中,无论是第一幕娟子、燕舞被联防队误会时的一句句反问,第二幕阿德假装心脏病发作来回翻牌的场景,还是第三幕阿德嫂一句俏皮的“一个女人的品位,在于她身边站着一个怎样品位的男人”,还是第四幕阿德为唤醒植物人燕舞俏皮地吻了他一下等等,可谓处理得节奏适中、张弛有度。但就细节方面,阿菊、阿桂的态度转变,植物人燕舞突然起身说出银行密码的行为,则显得浪漫有余,现实铺垫不足。笔者以为,若能回旋几笔,对人物性格的丰满、情节发展的流畅,都不无益处。
行文至此,值得一提的是,对照2014年1月刊登的《探亲公寓》,不难发现,在不断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强化了编剧陆伦章叩问现实又寻访诗意的愿景。如他所云:“我始终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在社会底层,默默地行走在感恩与负重之间,低头觅食,抬头仰望。”饱受苦难的编剧,试图以仰望的方式观照现实生活的苦难,犹如他总是以未来的眼光打量滑稽剧的现状一般。路漫漫兮而坎坷,这不仅需要更多年轻一辈参与到滑稽剧的创作团队中,为其持续注入新鲜的血液。更要紧的是,寻找贴切的路径,以“含蓄思想的笑”消除包裹着滑稽剧的层层屏障,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