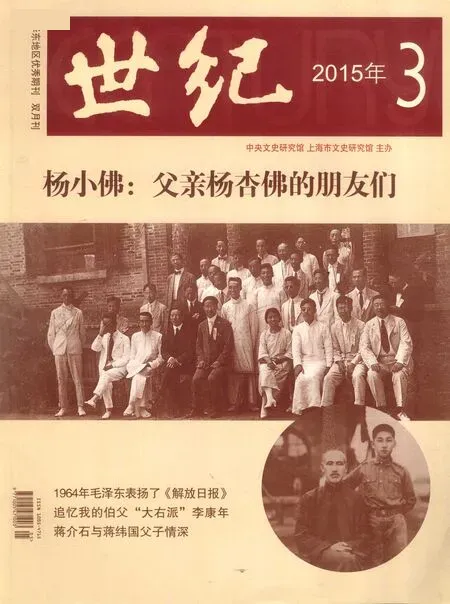私立复旦大学女生宿舍“东宫”
周桂发
私立复旦大学女生宿舍“东宫”
周桂发
今天的人们对于女生上学、男女学生同校读书司空见惯,却不知100年前,这简直就是一种梦想。因为在当时传统观点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没有读书的权利。辛亥革命之后,西式学校出现,才使得女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而男女同校则出现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
到1922年,除北大之外,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及附属学校女生已有250人。大学男女同校的禁令被冲破之后,中学男女同校也开始实行。当时女学生的成分复杂,有留学归国者,也有不甘家中寂寞的少奶奶进学堂读书消遣时间。
今年适逢复旦大学建校110周年。在复旦校园里,子彬院与燕园之间隔着一片萋萋芳草。当年,这里却是神秘而旖旎的女生寝室——“东宫”。
“东宫”建于1928年,由一位名叫陈性初的爱国华侨捐资二万两白银建造。这座西式二层砖墙楼屋占地465平方米,共计43间,可容纳148名女生(笔树《复旦最早的女生宿舍》,1986年复旦大学校刊)。一间间窗明几净,布置高雅大方,门前一圈绿篱,围着一大片如茵的草地。
由于该寝室地处当时校园之东,外观又为“宫殿之式”,精美气派,因而被称为“东宫”。1928年6月,第七期《复旦旬刊》上最早出现了“东宫”一词:“宫殿之式建筑甚精,绿窗与红壁齐辉,足为江湾道上增色。未来中国女文学家、女科学家均养成于斯灿烂宏伟之‘东宫’中,即记者所望也。”有人曾在校刊上这样描述东宫:“虽无飞檐斗拱,但是它那硬山正脊,分峙两翼,八道垂脊,鸱吻高耸,也着实壮观!”(《女宿舍新秋落成之预闻》,作者不详,《复旦旬刊》第二卷第七期,1928年6月25日)

1928年建成的复旦大学女生宿舍“东宫”
男女同校时代得来不易
就在兴建“东宫”的前一年,一群女生袅袅婷婷步入秋日的校园,正式拉开了复旦“男女同校”时代的帷幕。
这一步对于复旦而言,来之不易。1927年的中国,除了几所只招女生的教会学校外,鲜有大学开“女禁”,即使是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也是如此。老校长李登辉担心男女同校会牵扯男生心思,败坏学风,曾放出话来:“复旦要想男女同校,须等我死了以后!”(张计红《复旦女生,优雅作别封建的过去》,《新闻晨报》2005年9月22日)

1930年代复旦女生在上普通体育课(柔软操)
当时正值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校长的四个门徒百般努力加以劝说——“学校也需迁就时代,目前女子大学太少,富有革命精神及领导学生运动的复旦大学不招女生,似乎有违男女平等之原则,一般有志升学的女子也得不到求学机会。可否在暑期补习班兼招女生作为试办?”终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老校长在深思过后,同意一试。之后,学校通过层层面试,精心挑选出十余名女生参加暑期补习班。
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一位校友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平常一般顽皮而天真的男同学骤然间见到了这些女同学,好似人力车夫见了交通警察一样,深恐触犯规章,人人谨言慎行、内务整洁。而功课方面也比往昔更加用功,生怕成绩落在裙钗之后。”这样的场景让李登辉校长放下心来。1927年9月,第一批女生正式进入复旦学习,这些女生有的进入大学一年级或预科班学习,有的则自其他学校转来,从二年级或三年级念起。女生们所进入的专业,既有像大学社会科、中国文学科这样的文科类专业,也有大学理工科、生物学科这样“被视为高难度”的理科专业。女生们成绩优异,在当时全市性的外语比赛中包揽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二名获得者因未能夺冠,当场哭了鼻子。
“卓尔不群、不让须眉,大概就是从女生进校那刻留下并延续至今的传统。”复旦大学已故校史研究专家许有成曾经说过。这份传统,也不断鞭策着复旦的男生们,使其倍受激励,唯恐落于女生之后。
1928年,更多女生进入复旦,“南宿舍顿时无插足地矣”,“东宫”便应时而生。

1920年代复旦大学女生宿舍内景
男宾止步 门禁森严
几十载光阴从摇摆的裙裾间滑过,“东宫”的佳人们留下了众多逸闻趣事,也留下了自己青春年华里的喜嗔喟叹。很久以后,当她们各自漂泊世间、随命运的波澜而起伏时,“东宫”里的那些回忆,或许仍能化为一点星火,温暖漫长的岁月。复旦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几位年逾八旬的老校友回忆起了“东宫”轶事。
“‘东宫’门口有‘男宾止步’的禁牌,一位调皮鬼在‘止’字上加了一横,纠集一群人喊着一、二、一‘正步走’直奔宫内,吓得‘公主’们个个雨打梨花深闭门。”
“只有校庆节日,‘东宫’才欢迎男生参观,房间布置得十分雅洁,‘公主’们都逃之夭夭,留下一二位能言善辩的担任发言人,答复男士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那些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绅士们,却暗中干着顺手牵羊的勾当。出宫后,有的袖笼里抖出糖果,有的口袋里摸出胭脂、口红、香水、手帕……他们开了庆祝向“东宫”进军的‘战利品展览会’,然后来一个‘失物招领’。”
“有一位女生案头摆了一个一寸多长赛璐珞做的小棺材被摸走了。她气得不得了,狠狠地骂道:‘哪个小瘪三偷走了我的小棺材,一定不得好死。’旁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东宫”门禁之严离不开里头三位颇具特色的人物。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邵梦兰校友曾撰文回忆他们:“第一位是门神爷老头子,我始终不知道,也不曾问过他姓甚名谁,只跟着别人喊他老头子就是了。这是把门的。他热心负责,从来不曾放进一个男生过。老头矮矮胖胖,冬天一身黑直贡呢长袍,夏天穿一身米色纺绸褂裤,稳稳重重,有三分威严,整天到晚坐在门口一张小写字桌上,里面有两位,一个叫徐妈,另外一个叫凤仪,梳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她是管楼上的。徐妈和凤仪,都穿短褂裤,凤仪经常喜欢罩一件黑布背心。要是有人会客,先在老头子那里登记,然后老头子站在二门边向里面直着脖子一喊:‘徐妈(或凤仪),几号房间X小姐有人会客,那来宾在会客室等’,被请的也就应声而出了。凤仪是一位姑娘,黑黑的,长一脸的青春痘。做事干净利落,蛮凶的。我有一次看她跟子彬院的男工友讲话,大声大气,像一只母老虎……”
邵梦兰从复旦政治系毕业后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温州中学教授谷超豪国文课,执教杏坛逾一甲子,成就斐然。退休后,她还在台湾东吴大学等校兼课。八十岁以后,她多次出席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
“东宫”佳人的传奇人生
1927年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中,有一位名叫严幼韵的闺秀,长得十分漂亮。在“东宫”建造前,她总是坐自家的轿车从位于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八十四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的“爱的花”。严幼韵的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她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令人眼花缭乱。“爱的花”这一外号于是越来越响亮,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只知道“爱的花”,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名。
严幼韵当时在整个上海都十分有名。她常常在各种舞会上出现,以其风姿倾倒众人。后来,她嫁给了外交官杨光泩。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攻占马尼拉,时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面对命运骤变,严幼韵这位几乎没有吃过苦的上海滩名媛却镇定地承受着一切,含辛茹苦地带领外交官家属的大家庭顽强地生活下来——她不仅带领她们在马尼拉的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还学会自己做酱油、肥皂。抗战胜利后,她到联合国担任礼宾司官员,后来嫁给著名外交官顾维钧。现年110周岁与复旦同龄的严幼韵,仍然健康快乐地在纽约生活着。
与严幼韵一同进入复旦的女生中,还有一位名叫陈瑛的中文系学生,也许很多人对她的笔名“沉樱”更为熟悉。陈瑛1927年从上海大学中文系转入复旦中文系,1928年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回家》,受到茅盾称许,从此步入文坛。

复旦首届女生陈瑛年轻时的照片

1931年,陈瑛与当时任教于北大的梁宗岱结识,两人相爱,几年后结为伉俪。1944年,身在重庆的陈瑛听闻丈夫移情别恋的消息,带着与梁宗岱所生的三个孩子黯然离去。其后,陈瑛到了台湾,在斗焕坪,她教书、翻译,仍一直以“梁太太”自居,署名仍写“梁陈瑛”。两人在上世纪50年代时恢复通信联系。此后沉樱筹划着将梁宗岱的书稿出版,其中甚至包括梁写给新欢甘少苏的词集《芦笛风》。但1982年,重病卧床的梁宗岱希望能见陈瑛最后一面时,犹豫过后的陈却决定坚守曾经许下的“永生不再相见”的诺言,未与梁见面。两人几十年的爱恨纠葛成为了一个难以为外人参透的谜。
我国著名的话剧艺术家、戏剧理论家凤子也是从“东宫”中走出的女士。凤子原名封季壬,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她在大学时就表现出了很高的表演天分。中文系出身的她文学功底深,英文功底好,常常担负翻译剧本工作。复旦剧社的创始人洪深教授觉得她有当演员的天才,便引导她参加话剧演出。她成为国内第一位演《雷雨》中四凤一角的演员。凤子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在戏剧《日出》中扮演女主角,公演后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和妻子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赪。”凤子后来回上海主编纯文艺杂志《人世间》,得到了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胡风等许多作家的支持。
凤子的丈夫沙博理是个中国籍美国专家。他定居中国五十年,入了中国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江青,凤子曾有四年时间受到审查。沙博理始终对她不离不弃。(《凤子,从杨贵妃故乡走出来的明星》,载于2007年6月5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
另一位学者毛彦文女士,曾经担任“东宫”的女生指导,与复旦女生“相处融洽,亦师亦友,几年下来,相安无事”(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毛彦文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是出演了一场轰动江山的逃婚事件。这件事让她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性”(张昌华《民国风景》第57节“毛彦文的往事”,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毛彦文最真诚、最热烈、最持久、最痴迷的追求者是吴宓。他为毛彦文代取了“海伦”的名字,为“海伦”写了大量的情诗。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吴宓还请人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像悬于壁上自赏。这份单恋最终无果——毛彦文下嫁给父执辈的熊希龄,两人的忘年恋缔造了一段传奇。
在自传《往事》中,毛彦文回忆了熊希龄追求自己的经过。那时,毛彦文受聘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余时在复旦”。熊希龄内侄女朱曦本是毛彦文就读湖郡女校时的同学、知己。毛彦文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常随朱家姐妹到熊府玩耍。熊希龄一直对其关怀备至。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侄女朱曦家。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紧接着,朱曦持续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坚拒。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同时,熊氏加大攻势,几乎每天给毛写信或填词寄赠。之后,熊希龄的长女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1935年2月9日,33岁的毛彦文与66岁的熊希龄举行了婚礼。

熊希龄生平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去世后,毛彦文继承乃夫遗志,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长年在桂林、柳州、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业,造福良多。1961年毛彦文赴台后自动放弃美国绿卡,在台重执教鞭,生活低调。1999年10月3日,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年的“东宫”早已毁于日寇的炮火,而“东宫”中那些年轻的身影也逐渐没入历史的尘埃。但,见证这一切的复旦依然存在,带着那个时代的情怀与记忆,并将继续留存下去。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