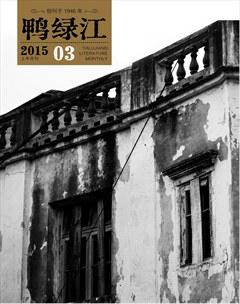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日头》(节选)
闺女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儿。
我最喜欢二闺女火苗儿了。这个小棉袄儿烈性,暖和,贴心。要是哪个男人想抢我的小棉袄儿,那就好比从我心头挖肉。火苗儿漂亮,日头村的男人,瞅她的时候眼神发直,眼珠子发绿。我这闺女也爱瞅帅小伙,盯着小伙子时眼珠也有绿光。老婆偷偷跟我说:“你说咱闺女是不是得了花痴?”我没鼻子没脸地呵斥老婆一顿:“胡说个啥!”老婆不再吱声了。不是我吹牛,火苗儿这孩子,长相的确出众,鹅蛋脸,大眼睛,长睫毛,面皮白嫩。大辫子被她自己剪掉了,留个新式运动头,像个假小子,走路一蹦一蹦,说话干净利索,宛如一阵清风。那眼媚的,那皮嫩的,她不用咋打扮,就亮一条街。村人都夸奖说:“老轸头那闺女少见,真是少见。”媒婆婶子说:“火苗儿这孩子,长大一准儿就是迷死男人不偿命的小妖精。”听到这话,火苗儿不气不恼,只是嘻嘻地笑。
可是,这个雪天,竟然有人挖我的心头肉来了。
仰了脸瞅,雪纷纷扬扬。雪没在地上印出一个脚印,却将古钟糊住了。古钟挂在状元槐半腰,槐枝嘎地响了一声。状元槐树枯着,竟然没折,家雀儿呼啦啦飞了。灰巴巴的槐树枝,一律快活地动着,弹出雪粉。槐树下麦秸垛也气吹似的涨起来,隐隐有些抖动。
常日里出来溜达的老人和孩子,一个也不见。
雪越下越疯,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歇不住。雪和泥搅成一团,踩在脚下,揉搓出干燥的摩擦声,哧啦哧啦的。路很滑,我走得不紧不慢,却跌跌撞撞,只一个孤独的影子。
我佝偻着身子走着,村里响起年轻人叽叽喳喳的声音。槐树、麦秸垛、猪圈、鸡窝都被雪盖上了。扭头瞅见金家门楣上,挂上了一串串的红辣椒。金家媳妇小米微笑着探出墙头,喊:“轸叔,跟你说个秘密!”我一愣:“啥秘密?”小米神秘地说:“说了您别生气呀!”我揩了脸上的雪,说:“不生气。”小米咯咯一笑说:“有人偷你的小棉袄儿啦!”我糊糊涂涂:“啥?我穿着棉袄哪!”小米大声地吼:“装啥糊涂?告诉你吧,你家火苗儿跟个男人在麦秸垛那儿亲嘴哩!”说着,她抬手指了指北边。
我一听,脑袋轰的一响。追我家闺女,哪个浑小子有这么大胆啊?
我急了,赶紧掉头去找。
北风浸骨,瞬间起了雪雾,远远近近一片模糊,近了,要喊一嗓子,才知道对方是谁。我愣了愣,一跐一滑,走不大稳,这树、这钟、这街巷、这平原、这山峦,晃晃得虚成一个梦了。嗖一声,一条黑狗蹿来,短腿在雪地上踏动,踏了一阵,一跳一跳地跑开了。
我踏雪寻找火苗儿来了。
到处是白雪,哪里有人影!我在槐树下站了好久,风骤然狂猛了,掀得雪粉飞扬,雪粉从枝杈上掉下来,掉进脖子里,叫人觉出几分寒凉。我暗暗骂:“这丫头野成啥样了!多冷的天,跟谁亲嘴啊?”
雪住了,日头没露头。天是白的,地也是白的。两股白搅成一团,是铜钟的青光。风冷冷地涌来,真是无风不起浪,有浪高三丈。当真见鬼了,我看见金沐灶和我家火苗儿在一起呢!
村街的麦秸垛旁,我瞅见金沐灶把一枚毛主席像章给了火苗儿。金沐灶戴着一顶军帽,胸口别了三枚毛主席像章,威风凛凛的样子。火苗儿仰着运动头,含情的眼睛闪了闪,火辣辣地烧着。金沐灶那身影,那感觉,是悠悠晃晃的迷醉。我躲在暗处屏住呼吸仔细听着。
金沐灶说:“火苗儿,我想看看你。”
火苗儿说:“沐灶哥,看我,你晚上做梦了吧?”
金沐灶说:“做啦!”
火苗儿问:“做的啥梦?”
金沐灶抓着脑袋说:“跟人说梦伤运气。”
火苗儿笑了:“还不好意思呢,梦见美女了吧?说,梦见谁了?”
金沐灶说:“梦见你啦!”
火苗儿说:“梦见我干啥?”
金沐灶笑了笑:“井里打水一根绳,哥就爱妹一个人。”
我眼前一黑,差点儿背过气去。金沐灶瞄上我家火苗儿是啥时候的事啊?
金沐灶掐着嗓子,唱起了冀东驴皮影:
日头一出照四方,
毛泽东思想闪金光……
火苗儿大睁着眼睛,鼓了鼓气,说:“不对,这是电影《地道战》的插曲,太阳一出照四方,不是日头。”
金沐灶耍赖说:“我们冀东平原,日头就是太阳,太阳就是日头。亏你还是日头村的人呢!”
火苗儿说:“你这是偷换概念哩!”
金沐灶仰脸笑了,说:“你说偷换就偷换吧。火苗儿,你记住,以后的日子,我来保护你!”
火苗儿生气地说:“沐灶哥,我们是同学,如果掺杂别的就是对革命的亵渎。请金司令铭记。”如今金沐灶是造反派的司令,他带着同学们一回村,三下五除二就把权桑麻支书的权夺了。
金沐灶拽了拽她的胳膊,火苗儿挣脱了:“我说得还不明白吗,你到底想干啥?”
金沐灶说:“火苗儿,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吗?”
火苗儿说:“喜欢啊!”
金沐灶说:“我们结婚吧。”
火苗儿咧嘴说:“忒着急了吧?先定亲不中吗?”
金沐灶说:“定亲也中啊!”说着就将火苗儿满怀抱住了,吧吧地亲个没完。
这个突然动作,吓了我一跳。
我粗声喊道:“兔崽子,作恶,作恶,真是作恶呀!”吼着,我手中的轸木就朝金沐灶扔了过去。
金沐灶和火苗儿吓得连跑带颠,四处奔逃。
我追了几步喊:“火苗儿,火苗儿!”
火苗儿拽着金沐灶飞跑,没搭理我。
我猜想,她准是玩火绳去了。这丫头从她娘肚子里生出来,是屁股先露头,坐着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叫“倒座莲花”。那时正是冬天,有一天屋子里生着火盆,我老婆手忙脚乱奶孩子,把她掉进了火盆里。我娘见状浑身抖成一团,想说啥,却说不出来。我急忙把孩子从火盆里抱了起来,只见她嘴里喷火,全身没有一点儿烫伤,喷着火居然还能笑出声来。打那以后我就让人们叫她火苗儿。火苗儿自幼就喜欢划火柴,爱闻那硫磺味。她还经常带着火绳玩耍,拿火柴点火绳。
我不追了,收住双脚,气得浑身颤抖。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可我为啥不同意金沐灶娶女儿呢?因为金沐灶这小子性格让人抓拿不住,胆子大得能捅天。他娘张慧敏威震八方,愣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金沐灶的命有点儿邪性,他是他娘绊门槛跌了一跤,把他跌到人间的。他一落地,双眼瞪得溜圆,却不哭。赤脚医生抓着他的小腿提溜起来,朝小屁股一巴掌,没哭;两巴掌,还是没哭;三巴掌,他的小脸憋紫了,嘴巴吐出一点儿黏液,一直不哭。大夫说,这孩子邪门了,长大了怕不是常人。金沐灶自幼淘气,被娘一怒之下系了个拴贼扣,拴在院里的菩提树下。他还有一个爱好是用驴皮雕刻皮影人,唱皮影戏。
我哽了哽气,开始用轸木敲钟了。
咣!咣!钟声跳着,滚着,响远了。
噢,还忘了说我自己呢。我叫汪长轸,我种过庄稼、守过大车店、当过饲养员,杀过猪、宰过羊、卖过鸡蛋,是村里最后一个敲钟人。
我祖上都是种田的,也是敲钟的。我爷爷穷得没饭吃,喝刷锅水长大,因为没裤子穿,只好披个麻袋片敲钟。那一年大旱,日头一天比一天毒,熬干了燕子河,熬干了庄稼人的血。我爷爷敲钟求雨,敲了两天两夜,最后一口血喷在古钟上,累死了。接着,雨就噼里啪啦下来了。
日头村人管这敲钟的木棍叫轸木。这是雷击过的木头,棒硬,铁疙瘩一样。祖宗把轸木传给了我。我跟古钟一样,心怀慈悲之心。轸木敲在钟上,满街的慈悲之音。村人都知道,敲钟给我带来异相。记得有一年,我一敲钟,头发、胡子和眉毛都白了。霎时,我满脸皱纹,苍老起来。我回家对着镜子一瞅,吓得瘫软在地。后来家人慢慢适应了我的模样。此前,村里的人常对我说:“你这老轸头,人总不老,我穿开裆裤时就这样儿,如今还是这样儿。看来你是定在那儿不变了,敢情是个仙人吧?”我骂道:“我算啥仙人?人家杜伯儒道士才是真正的仙人哩!”
说到杜伯儒道士,必说他的祖先杜康。
日头村主要有四大姓,被称作四大家族。金家、权家、汪家和杜家。起初立村,杜家祖先主持布局。传说杜康这位老人白发如雪,脸呈桃容。老人手扶白须,嘴巴念叨:“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按杜康的指点,四个家族,所居住地按五行分布:金、木、水、火、土。金家住西头;权家住东头;汪家住北头;杜家有木,青色,也住东头。而南头属火,是血燕和栗树的天地,围成一个圆圆的气场,拢着状元槐和古钟。在日头村有很多事说不清来龙去脉,人们只知道状元槐、古钟和魁星阁。日头村人造房子就像血燕垒窝,一嘴草,一口泥。房子一住,杜家先人就预言说:“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家生着汪家,汪家生着权家,权家生着血燕,血燕生着杜家。”
天色幽暗一些,远处有踏雪声。
孩子们在雪地里撒欢,打雪仗,踢腾得雪粉像雾一样。钟声合我的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
钟声一响,村街就流淌起活气了。
孤单的老槐树热闹起来。槐树底下飘来一片红。这钟声,竟然招来了游街的红卫兵队伍。
卡车卷着冷风过来,车顶上戳着大喇叭,呼喊着他们的“革命宣言”。
我赶紧回家给红卫兵烧水。火苗儿凑到我身边,我刚要为她和金沐灶的事发怒,火苗儿用话遮掩过去了。她说造反的红卫兵到日头村来的,除了金沐灶这一拨儿,还有刚来的另一派别。
红卫兵说来就来了。人真多,满街里咔嚓嚓鞋底子响。
一个矬胖子脚步放慢,走到我跟前说:“老乡,这白水我不喝,我要喝茶水,还要吃炖肉。”我愣了愣,吸了口凉气。有人说:“这是我们的黑五司令!大名叫辛俊武,是邻村辛家庄人。”
我抬头打量他,矮、胖,熊猫似的大眼睛,白白净净的,只是外号叫黑五。我为难地说:“红卫兵小将,你胃口太大了吧,难道还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黑五嘿嘿一笑:“哪能呢,老乡,我们是干革命来的。”他仰脸喝了我的茶水,“老乡,好茶!年轻人血热,喝完水又蹦又叫的,有好戏看哪!”我劝他们到别的村去闹,黑五却不走,非要开个批斗会再撤。
黑五仰着脸嚷嚷:“嘿!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娘的蛋!”一群红卫兵噼里啪啦地奔过来。
以后事情的变化,恐怕连黑五都没有料到。姜还是老的辣。权桑麻虽被红卫兵看守起来,却让他儿子权大树给黑五递纸条。黑五看了纸条,嘿嘿地笑了。
后来听说,权大树几次偷偷找来了黑五,终于促成权桑麻跟黑五谈了一整天。黑五比金沐灶还邪乎,夜间好不容易睡着,街上突然响起鼓声,他又赶紧起来游行。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风云变幻。在诡秘的命运面前,占星法往往也无能为力。这一事件将长久地影响到这个村庄的历史。我心中有了一个很深的疑问:他们为什么彼此仇恨?
责任编辑 晓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