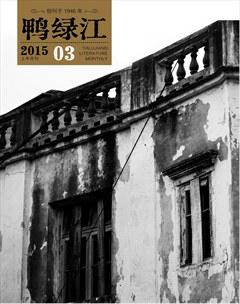强挽时光
张大威,曾用笔名秋水、河姬,1954年生,女,汉族,辽宁辽中人,现居沈阳。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曾任《辽宁日报》文学新闻部主任、高级编辑。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作品以散文为主。曾在《随笔》《散文》《中华散文》《文学自由谈》《鸭绿江》《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散文多篇。作品四十多次被收入花城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编辑出版的年度选本及其他重要选本。作品集《时光之水》获第三届辽宁文学奖——辽河散文奖,散文《我的美丽乡野》获第六届辽宁文学奖——辽河散文奖,代表作品《消逝的村庄》获中国作协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
皱纹
谁也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第一道皱纹是什么时候生出来的,反正它已经如刺目的沟壑顽横地在脸上凹陷。而且它就像被春日里的惊雷震醒的第一只在地上爬行的虫子,具有强大的引导与表率作用。继它之后,更多的皱纹会蜂拥而至,使整张脸彻底沦陷。岁月的刻刀一般会按遗传的形态——你父亲脸上的皱纹、你母亲脸上的皱纹——以及你个人的沧桑史来刻画你脸上的纵横交错。皱纹属于一种生命密码,一种断裂的生命密码,一种消逝的生命密码,一种以破坏的形式来遗传的生命密码。
皱纹,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隐藏在你生命的某个角落中,就像一朵鲜嫩的黄玫瑰的结局必然是一朵枯萎的黄玫瑰一样,一张圆月似的鼓脸,经过时光揉搓与刮擦,必然会变成一张核桃似的瘪脸。生命就是如此不可逆转。
你出生的时候,多么像一尾没有记忆的鱼,清白,光滑,没有一丝皱纹。你睁着圆圆的眼皮很短的眼睛——面孔上镶嵌着两个圆圆的黑色小纽扣——无邪地看着这个世界。鱼也在看着这个世界。不同的是鱼是在水里看,你是躺在摇篮里看。后来,鱼一直没有离开水,那是鱼的幸运。虽然如此,鱼也长满了皱纹。你离开了摇篮,皱纹也随着你一起上路。一把无形的剑在时光深处时时把你刺伤。“生活中,死亡有时会登门丈量人体。拜访被遗忘。生活仍在继续。但尸衣在无声中做成。”(特朗斯特罗姆)世上万物谁都逃脱不了衰老的结局,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与鱼。
个人的沧桑史是另一把刻刀,它由你在人生中的各种经历与时光共同完成。它的来源不是遗传基因,它是即时性的(一个人的脸,按最长的寿命计算,也就八十年或九十年的光阴,在时间的长河中它还是属于即时性的)。这种“即时性”对脸的破坏作用,如毒火舔过纸窗,白白的窗纸已经化成灰烬,只剩下丑陋的窗棂——那些使人厌恶自己也厌恶镜子的皱纹。
那就祈求没有皱纹,祈求原地不动吧。可是衰老与消逝并不是因为人的意志薄弱,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够虔诚,而是因为时间。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或发明能够抗衰老的任何物质,科学家仍然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在一个个漫长而枯燥的化学试验中,猎狗嗅闻猎物般地寻找能够逆转生命的那个“核”,“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科学家在寻找抗衰老的道路上尽皆衰老,尽皆死去。天已是黄昏,一道道皱纹又爬上了人们的脸颊。
有无数化妆品宣称它们能够抗衰老,我们只有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好的心理暗示或美好的愿望。抗衰老?挺着一张衰老的脸的人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抗衰老,这事值得商榷。你仔细分析一下化妆品的原料构成,答案清晰而又令人沮丧,因为这些原料无论是提炼于动物,还是提炼于植物,或者本身是矿物质,总而言之,它们自身统统没有因为对衰老的恐惧而产生的抗衰老基因,除了人其他动植物并不理解衰老与死亡意味着什么,更何况人那么恐惧衰老与死亡都没有产生抗衰老基因呢!化妆品只有遮盖(或许还有保养?)的作用,化妆品涂抹的厚度与遮盖的强度成正比。一个出镜时浓妆的女明星与女主播的脸,与卸妆后同样是她们的脸相比,你可以看出化妆品在人脸上的作用,其实是一个短暂的逃避时间的安慰性快乐游戏。一掬清水,洗尽铅华,脸上的皱纹与斑点原形毕露,四处扑腾。人可不能就这样败下阵来,人还得与时间对抗,于是,美容手术出场,某把刀子划过脸庞吱吱叫声,拉紧了发皱的脸皮,弥平了一条又一条显而易见的皱纹。某针肉毒杆菌的缓缓流淌,正在以绝望和亢奋的速度,向已逝的青春逆流而上。人到中年甚至是已近暮年,心底的沧桑衰飒与肉体的老迈沉重,刀子与针剂都无法祛除,但脸却可被摆弄得像一枚刚刚洗过澡的鸡蛋那样光滑有趣。于是,在我们的身边常常会出现一些年龄不明的老人,不可辨认的熟人,以及其他一些形象与原先大相径庭的什么人。
他们的身上还在顽强地发出美丽和青春的信号,可我们又常常怀疑那到底是不是一种伪信号。伪信号?这又有什么要紧。反正我的嘴唇、我的脸庞已经享用了这种美丽。当年龄使人的相貌陷入了不可遏止的下滑趋势,我们的脸像被疯狂的飞鸟啄过一般、千疮百孔,阻挡是必须的,即便是钟表的分针与时针在我们的身旁一刻不停地走动,我们仍然要力不从心地去强挽时光。
旧物
旧物是我们的身体与生命老化和褪去的部分。是的,只是老化和褪去,并未毁灭。它们如一张张蜕掉的皮,带着我们的人形、体温,还有思想,充满爱怜地——我们对它的爱怜,它对我们的爱怜——躲在储物间、阁楼里、床底下,整日窃窃私语,柔情似水,散发着牵绊、迷恋与一步三回头的气息,在有用和无用之间不停地摇摆,使我们与它们的纠葛日益加深,在取与舍之间进退两难,举步维艰。
旧物是我们生命的轨迹,人如果没有与物的相依相帮,人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房子的人,在万家灯火的晚上,在城市某个僻静的街角忧伤地徘徊,即使你能像一只乌鸦那样融入夜的黑暗,你也会感到如身处无人沙漠般的荒凉和寂寞。一个没有外套的人,在严酷的冬天,寒风以魔鬼般的力量,汹涌着从四面八方钻进你的皮肤、你的骨髓、你的心脏——请想一想果戈理小说《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吧,没有外套,生命不仅感受到了严冬的磨损与腐蚀,甚至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与焦虑。
物,其实是我们生命的另一半。如果有这样一件又厚又软的外套,帮我们度过几个漫长的冬天,给了我们无数的温暖与安慰后,它变旧了,它该退役了。可它哪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退役呢?此时,无论是外套还是我们都在同遗忘和抛弃做着搏斗。它样式过时了,显得老旧与可笑。它质地变薄了,不再具有优秀的抗寒能力,它的身上已经堆积了几个冬天的时光,它已经被严寒压得气喘吁吁了。总之,它已经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旧物了,它应该被抛掉了。
扔掉旧物与扔掉旧思维一样艰难。舍弃就是一种切割。又一个冬天到了,你买了一件新外套,你终于从旧外套中钻了出来,钻进了新外套。怎样处理这件旧外套呢?扔掉,这怎么可能?因为你,抑或是你的一个同貌人,看似从旧外套中钻了出来,其实,你的旧我还是百般不舍地留在旧外套中,依恋地睡在那里。今天的你在新外套中,过往时空中的你在旧外套中。如果不是你的躯体,至少也是你的影子还在旧外套中徜徉。当然,谁也不知道这种徜徉的确实意义,可是我们就是徜徉。
如此,我们的旧鞋子——那里有我们的脚。我们的旧手套——那里有我们的手。我们的旧眼镜——那里有我们的眼睛,也许不是眼睛,只是几缕狐疑的目光。管它是什么,都被旧物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如此,旧物占领我们,我们占领旧物。最终是我们成了旧物的囚徒,旧物也成了我们的囚徒。
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房子越来越逼仄,逼仄到使你感到局促、茫然、窒息。夜晚,无数旧物的暗影蝙蝠般翩翩起舞,将你重重围困。你展眼望去,一件件旧衣服成了螨虫的乐园,有着陈年旧物特有的怪异。一双双旧鞋子,除了保留你当年汗脚的臭味,又加上了蟑螂、蜘蛛网等等的味道,一堆堆过时的报纸杂志,纸页早已发黄变脆,报道的消息与写作的文本也早已老掉牙了,一张张商家打折活动的宣传单,活动早已完成多年……你像一只蝜蝂一样背着这些旧物,不知爬向何处。你感到沉重、混乱、纠缠、碍手碍脚,如陷入一个巨大的泥潭之中。
终于,你的目光变得坚毅起来,这事该做一个了断了。某个午后,你打开了储物间,从灰尘中抽出一件衣服,抖掉上面的螨虫与碎末,拿到阳光下仔细评估与辨认,它该不该扔掉呢?左眼右看,呀!这件衣服还不算太旧,质地也好,当年买它时,着实花了不少钱呢,这种款式过几年能不能又兴回来?这件……暂时……最好不扔。这双鞋子,也许……下雨天还能穿,不扔。这堆报纸杂志,将来写点什么,可能用得着上面的一些资料,不扔……
你在储物间整整消磨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浩浩荡荡的旧物队伍被你检阅了一番,但什么都原封未动,旧物依旧缠绕如初,只有暮色爬渐渐爬上了窗子。日复一日,我们与旧物就是这样难舍难分,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旧物”。
逝者
死去的亲人,只能与我们在梦中相见,让人伤感的是梦没有道路,谁都不能把梦中人从梦里领出梦外。梦中的人,在梦里有血有肉,并在我们的目光中,清清楚楚地印满了生活的轨迹,他们行走、谈笑、吃东西、读书、升官发财、婚丧嫁娶,在梦里过着与尘世一般无二的日子。可这些景象都是无根的花,缥缈的雾,他们在梦里呼吸,离开了梦,便是一种完全的空荒,不能被凝聚成具体形象的虚无。只是虚无,连空白都不是。因为空白还可能是曾经在场的离去,抑或即将在场的等待。
梦是一个独立体,不与谁认真交往,也不完全听命于它的主人,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是计划中的梦。但人往往做的是计划外的梦。弗洛伊德解析了梦的原因,可那又有何意义?我们逝去的亲人,都已被囚禁在梦中了,我们知道了做梦的原因,梦还是不会找到它的突破口,梦还是一个不能溢出的封闭的圈儿。它不断地徘徊在我们的睡眠之中,它并未寻找任何人,它缺乏明晰的主动性。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主动地寻找它们,而这种寻找又常常是徒劳。
比如,我很思念我那早已去世的母亲,在某一个夜晚,我祈祷在梦里与她相见。但那样的夜晚,母亲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即便我做着很大的努力,艰难跋涉,赤脚(我在梦中总是赤脚)走回我的老家。老家的茅屋仍在,屋子里灯火通明,通明的灯火却被某种穿不透的东西所覆盖,它类似于寒冷清亮的阴影,这阴影隔开了生与死,这阴影就是消逝。你纵有千般不舍,也不能挽住这消逝。时间给我们最痛楚的感觉就是消逝,还有对这消逝的无能为力。无论我怎样在茅屋四周徘徊,我都走不进那座茅屋了。因为它与死亡位于同一纬度,而我却在生的一边。
我们被梦抛弃后,便寄望于逝者留下的老照片,与其他逝者的手泽。这些老照片上印有亲人的容颜,印有当年的那个微风轻拂的芳晨丽景。我的手头就应该有这样的一张老照片,我那年轻的母亲,站在一株白杨树下,清晨的阳光像金黄色的柔软绸缎一样从高天往下流泻,我母亲的整个身体就裹在那绸缎漾起的涟漪中。
可我的手头并没有这样的一张照片,母亲生我时,已年过四十,多子,劳累,贫寒,疾病,使她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老上十岁。她没有留下年轻时的照片,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描绘她年轻时的样子。她真实的样子永远都是一身青衣青裤,脑后挽着一个发髻的农村老太太。这简直是一个奶奶的年龄了,对于一个孩子,这是多么大的缺憾啊!我们儿时的母亲都应该是端庄美丽的少妇,都应该过着春风没有吹尽的日子。母亲有没有其他的遗物呢?戒指,卖了。镜子,碎了。衣服,烧了。
逝者的轨迹如此瘦骨嶙峋,他们完全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灯火通明的茅屋我又走不进它。生者滴滴泪水。
如果有老照片,有遗物,它也只能在我这一代被看重被珍惜。由于血缘关系在一代一代淡薄下去,我的儿子,我儿子的儿子,谁还会对一个平凡如大地上的一棵草一样的老妇人的照片与遗物感兴趣呢?细细想来,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这样,时光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又会把我们湮没得无影无踪。
也许生命的真谛根本不是记忆而是遗忘。死亡则是最彻底的遗忘。不是这个世界抛弃了逝者,而是逝者抛弃了这个世界。
如此,我们多少会松开一些强挽时光的手指吧!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