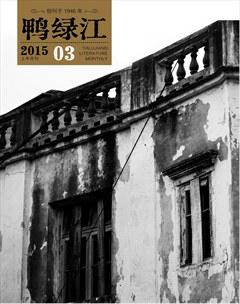读城笺
维 摩,或名维摩诘,本名王小朋,70年代末生人。生于晋,长于洛。斫文为业,字米疗饥;文学人,喜好足球、艺术和酒。《牡丹》杂志主编,洛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他的创作感言:设若文学是一片土壤,作家便是耕作之农夫,要想比别人多收三五斗,除了付出极大的辛劳之外,还得祈求上天垂赐灵光一现。
这是我的城。三十岁时,我才接纳她,而她已经养育我二十二年。
我的枝干在这里生长,时而繁茂,时而瘦削,时而盘根错节,时而笔直参天。那些默默的轮回把一株株嫁接于异乡水土之上的幼苗催发成硬朗的大树,其中就包括我这粒从黄土高原刮来的种子。或许过路的雨水会偶尔把故乡的气息带过来,但那只是片刻的陶醉。脚下,才是坚实的存在。
于是我决定为她写点什么。
将城市诉诸文字,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对于文字来说,城市难以描摹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体系结构和人际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千人一面的楼房与街道,很难给人以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感受。
但是不能因为难,就放弃。城市是一封信笺,写起来困难重重无法落笔,读起来却真情处处不忍释卷。
食事
接受一座城市,先要从接受饮食习惯开始。
我来自盛产粟米的北方,那里干旱少雨,只有这种外形如同狗尾草般的坚韧作物,才能扎根于那样贫瘠的土壤。粟米得到了土地的垂青,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在那片土地上,每天的早餐,必是从粟米开始的。黏稠的小米粥里,搅拌着我的童年岁月。那种温和甜润的记忆淌过舌尖、滑过喉头、落入胃囊的过程,用七八年的光阴反复强化,存储入脑海,极难修改。
这座城市,早晨却是从一锅冒着葱花味儿的热汤里醒来的。汤是咸汤、鲜汤、肉汤。
熬汤的工序,从头天晚上就开始了。过程非常讲究,需购买新鲜牛骨牛肉,将牛骨砸断铺在锅底,牛肉洗净切成大块,铺在骨上,加水过肉,旺火烧沸,撇净浮沫,将汤滗出不用。加上适量清水,煮沸后再撇去浮沫,随后放少许牛油稍煮片刻,再撇去一次浮沫。将大料花椒等用纱布包起,与姜片、葱段、精盐一起放入锅内煮沸,炖成奶白色即可。头天下午六七点开始备料熬汤,熬完封火,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起来再熬滚了方能出售。起锅之时,按食客口味加上肉片、杂碎、血块,再佐以各种调料提味。一锅汤卖完,就从后院的另一锅里取汤兑来,少加清水再炖。
爱喝汤,是这座城市血脉里的积习。有句老话,说即便全城的生意人都破产了,也饿不死卖汤的。在这里,缺了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缺了汤馆。这里的人一天不喝汤,心里惦得慌,三天不喝汤,浑身挠痒痒,就连外地来走亲访友的人,也要好奇地尝个鲜,看看这传说中的牛肉汤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味道。民风如此,自然少不了卖汤的生意人。这里汤馆遍地,不下百家,谁家汤好,都是百姓口口相传,胜过电视广告。常有老饕起五更从城西跑到城东,就为喝口跟自己对脾气的头锅汤。
头锅汤就是每天开门做生意的第一锅汤,常常是熬了一晚上,味浓好喝。每天清晨,汤馆门口,或立或坐或在墙角阳光下一蹲,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多撒些葱花芫荽佐味,就一块烙馍火烧,呼呼啦啦一口气灌进肚里,全身的汗毛孔都涨了三涨,上下通泰、大汗淋漓,一天都有使不尽的力气。
北方人做汤如做人,粗犷惯了,毕竟不如南方精致,这座城市也不例外,但单论起喝汤这一习俗来,这里与广东不遑多让。这里居民的食谱里,常见的汤有二三十种——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杂肝汤、胡辣汤、豆腐汤、小碗汤、凉粉汤、粉丝汤、不翻汤、丸子汤等等,甚至连鸡汤也如法炮制,将十余只整鸡扔入大锅熬煮,卖时用粗瓷大碗盛了,撒上葱花芫荽,泡馍当早餐吃。
添汤是不另收钱的,倘若你有那个决心和肚量,大可以把一整锅汤喝完。这似乎是这座城市独有的传统,很多老饕都是热汤端上来,先呼呼啦啦喝一半,然后抹一把汗,把手里的锅盔火烧掰碎泡进碗中,站起身去添一碗,再慢条斯理地看着街道渐渐繁忙起来,一口一口踏踏实实地把碗里的汤喝下肚子里去。少年时,我们都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作为饭量大消耗快的穷学生,学校门口的汤馆是窘迫时理想的去处。先凑钱派一个人去打汤,另外几个少年趁跑堂伙计不注意,各自取只空碗出来,等汤打来,每人碗底分上些,便可堂而皇之地去添汤,余下的钱,买几只烧饼,便能把肚子填饱。其实这样的小聪明,根本逃不过汤馆老板的眼睛,但善良的他们看在眼里却并不说破,一碗热乎乎的牛肉汤,温暖的不仅是肚子,还有年轻脆弱的自尊心。
时间给予我们的大多不是澎湃,而是聚沙成塔的点滴改变。小米粥的味道总是难忘的,赶早去喝头锅汤也渐渐成了不错的选择。
习惯了喝汤,便看惯了喝汤人形形色色的习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便是喝汤就酒了。在汤馆里,我见过不少白发的老人以汤佐酒,慢慢消耗一上午光阴,然后酒足饭饱地离去。羡慕之余,总叹息自己没有那样的悠闲与洒脱。那一年,我也喝了一次就酒的羊肉汤,与我对饮的,是一位诗人。
诗人
一个城市,如若没有诗人,就会无趣很多。
诗人就应该像他这样:深夜,在熟睡中被吵醒,有陌生人敲开他的门,说:“我也写诗,想跟你聊聊。”他立刻邀请对方进去,然后点亮自己的屋子,擦拭桌椅,切一碟咸菜,取两瓶烈酒,边喝边聊,边聊边喝,待到东方发白,阳光敲窗,两人已醉倒在地板上,昏昏睡去,只留下叮咚作响的句子,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这样的故事,未结识他之前,就已多次听说。
他洒脱。认识那年,他五十岁,可无论面对七十多岁的白发诗人,还是不满三十的我,一律称兄道弟。
他真诚。每当遇到青年才俊,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推荐,而对于泛泛之辈,也从不会吝于批评。某一次去舞钢采风的路上,有作家递了一组诗给梅主编。梅老师略略读过,随手递给他,问他意见,他看罢笑着说:勉强及格吧。
要知道虽然这话没有当着作者面说,但也与此不差多少,小小车厢,他那么高的声音能逃过谁的耳朵?
在舞钢,我俩成了酒阵中的主力,各自独当一面,一塌糊涂后,终于会师在同一张桌上,其间说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是觉得再见面时,亲近了不少。第二天一早醒来,洗漱完就去寻他,想看看他怎样了。谁知刚到门口,就见门户洞开,他床头柜前一溜摆开六只小酒杯,进门者须先与他同饮一盏——那架势,颇有一夫当关的感觉。
后来就熟了,常常一起喝酒、聊诗、谈文学。有一次和他在老城丽景门喝羊肉汤,先拿了瓶二锅头,就着汤喝了,不尽兴,又拿了一瓶,继续喝。高谈阔论之间,时不时蹦出几句诗来,引得食客们纷纷侧目。我俩不以为意,继续舞之蹈之,吟之诵之。人渐渐多了,有两位顾客没有座位,就来我俩旁边凑台子。喝得兴起,跟人家也连干带碰,喝作一处,饮完之后,各自散去。
“酒怕少壮。”何况他酒量一般,总是喝不过我。每每朋友们酒酣而散,他就要送我,我看他一摇三晃,反倒送他回去,到了楼下,又非得让我上去坐坐。客厅坐定,说不上几句,他就鬼鬼祟祟地拿出珍藏的衡水老白干来——我最喝不惯的就是这酒,太冲,六十七度,几杯下肚,我就醉倒在他沙发上了。
“诗人”这个词,有着太多的悲剧色彩。
几次劝他,少喝点酒,少参加些活动,在五十岁这个黄金年龄,多写些东西。他听了,频频点头,私下也和几个好朋友说,要收收心。正好农历新年临近,他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兴高采烈地通知我,说要休养生息,年前不见面了,年后再聚。我应了,谁知当晚七点多家里便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走了。
他洒脱了一辈子,连走的时候都极其洒脱。
据说是下午喝了一点酒,犯困,就在床上睡了,谁知这一睡,再没有醒来。
他曾经跟我说过,不经历痛苦、不拖累人的死法,是最理想的。真是一语成谶。
受他家里的委托,我为他整理出版一部作品集。当拿到他厚厚的几个笔记本时,我才发现,他写了很多好诗,可是他宁愿把它们锁在幽暗的抽屉里,也从没有让我帮他发表,哪怕让我帮助推荐一下都没有。突然觉得,我其实根本没有了解他。
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自己的诗:
山鸣水啸——
我们曾经活过
行色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沿途有着无数动人的风景,可惜我们总是行色匆匆,甘于错过。
例如我的父亲,他戎马半生,飘荡了半个中国,似乎只要有军营,他便可以随遇而安。只是那种“安”,仍然避免不了匆匆行色。无法把根扎下来的日子,在岁月的洪流里,显得无处安放。这座城市,终于可以让人卸下行装,安然生活。
因为这里有佛。
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卢舍那。传说佛有三身,即法身佛毗卢遮那、报身佛卢舍那、应身佛释迦牟尼。按照佛家的观点,报身佛,是表示征得了绝对真理,获得佛果而显示佛智的佛身。因而佛之三身中,只有报身佛卢舍那,才宣称“现世现报”,我即是佛,佛就是我,人人皆可为佛。
这恰与武则天的心思暗合。据《大卢舍那像龛记》载,当时身为皇后的她捐出两万贯脂粉钱,在龙门西山修建了气势恢宏、雕工精美的卢舍那大佛。这尊卢舍那大佛面容饱满,秀丽端庄,嘴角似有笑意,被誉为“世上最美丽的佛陀”。不少学者认为,这尊佛的蓝本,就是时年四十四岁的武则天。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传说释迦牟尼在世时,带领众弟子托钵行乞,路遇一群孩子在沙堆边玩耍。其中一位调皮的小姑娘,眼见佛陀渐渐走来,便捧起一把流沙,笑吟吟走到佛陀面前,将沙子倾倒在佛陀的钵盂里。佛陀面带微笑地接受了这个特殊的流沙供养,领着弟子们远去了。
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心中纳闷,说这个女孩如此无礼,用流沙戏弄世尊,而世尊竟然不以为意,是何道理?佛陀说道,一千五百年以后,那个女孩将投生东土为王,我受此流沙供养,使其种下善根因缘,从此光大佛法,岂不是一桩好事?
果然,武则天一生笃信佛教,尤其是后来借助《大云经》登上帝位以后,更是对佛教推崇备至。
其实,佛教与这座城市结缘,早在汉代就开始了。
相传,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梦遇金人,白光环绕,自西而来,梦醒有感,遂遣使西行求法。三年后,使者偕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归国,并以白马驮经相随。明帝闻之,命人在雍门外建白马寺供养,此为中国政府官方认可佛教之始。摄、竺二僧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并使佛法流布于东土。一千九百多年的滚滚烟尘,湮没了曾经繁华的汉魏故城,倒是这座伽蓝历经风雨,几毁几建,香火绵延到了今天。
佛学在中国流传后,越来越多的僧侣对于这些仅从西域、中亚或是海上丝路辗转而来的散乱经文感到疑惑和不满,于是自魏晋开始至晚唐时期,东土掀起了旷日持久的西出阳关的求学运动。五百年间,先后有百余名僧侣,或组团,或独行,前往佛教诞生地印度深造。
梁任公认为,世界上其他古国的文化,无不是互相影响,互相传播,而导致伟大思想产生的;而中国东南皆海,西有雪山大漠,北有胡骑环视,思想和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完成的,出现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高峰以后,一直处于低谷之中;此时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有机会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到养分,同时,佛教中的哲学观念与中国文化极其投契,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自然对其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一方面是宗教力量的感召,一方面是文化探索的求知欲,导致了一批批僧人不惧艰险,不远万里,踏上西行之路。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玄奘法师了。
内子的家,便在玄奘法师诞生之地。流经这里的造纸河,相传为东汉蔡侯造纸旧址,因而这里的民风极重文化。幼年的玄奘法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着优秀的品格。八岁时,他听父亲讲《孝经》,讲到“曾子避席”时,他立刻站起身恭立一旁。父问其故,他对答说,古贤人见到老师就立刻起身聆听教诲,今天父亲给我讲经,我怎么能坐着呢。
十三岁时,玄奘在净土寺出家,自此献毕生心力于佛法。经过游历各地、遍访名师,年轻的玄奘很快成长为一个受人景仰的僧人,但他却不满足于此。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各地各宗的论点颇有不同,有些甚至相悖,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法的念头。
有一位同乡,已经走到了他的前头。两百年前,诞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道整和尚曾经跟随法显禅师,从西安出发,出敦煌,渡流沙,经鄯善,越葱岭,到达印度。这位同乡后来并未随法显回国,而是终老于佛国的土地上。
但玄奘这次,注定是历史上最艰苦最伟大的西行。由于没有获得朝廷的许可,玄奘只能孤身一人“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在边塞,由于没有出关手续,他冒着杀头的风险,混在灾民中闯关而出;在高昌,由于高昌王的刻意挽留,他“水浆不涉于口三日”,以生命博得继续西行的机会;在莫贺延碛,“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伏无水草,顾影唯一。四夜五日口腹干焦,几将殒绝。四顾茫然,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若时雨。”由于向西的通路为突厥人所控制,他不得不绕道阿富汗、乌兹别克和巴基斯坦,辗转到达印度那烂陀寺,路途之险远,在西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玄奘一生都在匆匆行色中度过,身体或者心灵,总有一者在路上。西行游学十九年后,当他再次迈入大唐的国土,立刻受到了太宗李世民的礼遇。又一个十九年开始了,在这个十九年里,玄奘共翻译佛经一千三百五十卷,平均每年译经七十卷。在他生命最后的四年里,这个数字达到了年均一百七十卷之多。译经占据了他的大多数时间,但他所做的还不仅仅是译经而已。据他的弟子记载,每天译经完毕,玄奘还要礼佛行道,三更暂眠,五更又起,读诵梵本,拟定次日的翻译内容。黄昏时分,他还要为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僧侣们开坛讲经。夜晚掌灯后,更要不厌其烦地为本寺内的百余名弟子答疑解惑,“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这样的治学精神,真可称是古学者中的典范。
玄奘归国后,曾两次上书要求回故乡,或是在故乡附近的少林寺修行,最后一次“乞骸骨”已是晚年,但都被皇帝拒绝了,这或许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麟德元年正月,玄奘在玉华宫翻译《大宝积经》,仅仅翻译了开篇的几行,便将梵文经书合上,对众僧说道:“我大限将至,恐怕是无法翻译完这部经书了,现在只想去兰芝谷拜拜佛,看看我亲手栽种的那棵娑罗树。”众僧相顾,莫不潸然。从兰芝谷回来后,玄奘开始专心礼佛,不再翻译经文。
停笔一个月后,不知疲倦的玄奘法师终于在疲倦中功德圆满地涅槃了。
佛教讲求解脱,大乘讲求度人。玄奘用他的匆匆行色,为世人卸下沉重的行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数千年以来,最为壮观的行色了。
风物
如果要以一件物什代表这座城市,那必是牡丹无疑。
少年时,曾是羞于谈起牡丹的。似乎这种花因为象征富贵而流于庸俗,一旦沾上,就再难“高雅”起来。白衣胜雪的年纪,总是有着神经质般可笑的精神洁癖。容易被别人的观点左右,说出自己都不懂的,或是违心的话。
关于牡丹,多数人跟我一样,是受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影响。“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仅仅一个“众”字,就让敏感的少年萌生了万千抵触。象征“隐逸”的菊花,象征“高洁”的莲花,自然是人中龙凤,选择这些花朵,会显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选择牡丹,就意味着泯然众人,是绝难接受的。
那就折中一下,选择梅花吧。这是开在漫天飞雪中的花朵,天生具备“为有暗香来”的低调,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不二之选。事实上,梅花也确实是很多中国人喜爱的花卉,尤其是她遒劲的枝干,料峭的香味,细碎的花朵,犹如清癯的高士,让人生发出很多瘦弱的联想。
既然瘦弱是美,丰腴又何尝不是?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梅花与牡丹,似乎是两个审美的极端,一种是极致的简约,一种是极致的雍容;一种是极致的单纯,一种是极致的浓烈;一种是极致的内敛,一种是极致的开放。因为极致,所以动人;因为动人,所以都“宜乎众矣”。
置身于四月,置身于这座城,才能深切感受到“宜乎众矣”这四个简简单单的字,蕴含着怎样一幅壮阔的风情画卷。“姚黄流金三千顷,魏紫铺玉十万家。”看花的人潮涌动在大街小巷,空气里充盈着缤纷的色彩和醉人的花香。所有关于灿烂或者繁华的注脚,都可以在这里轻松找到。这座古老的历史之城、传说之城、诗歌之城,此刻终于变成了牡丹之城、繁花之城。寂静一年,突然喧闹,就像是已经迷失很久的青春,一夜之间重回了这个铅华洗尽、从容依旧的地方。
一千多年前的今天,花的艳潮也许正在盛世大唐的桥边陌上、宫内坊间肆意流淌。整个城市都在为它疯狂,市民们簪花而行,狂歌痛饮,醉卧丛下。诗人们酒气萦身,呼朋喝友,肥马轻裘,踏花归去,一路马蹄馨香,写下荡气回肠的句子。还有不远百里从各地赶到中原的王侯商贾,他们为求珍品,争相竞价,一掷千金,珠玉如土。甚至还有胡姬,那些容貌妍丽、装束奇异的外邦美人,三五一群,嬉笑而来,性感的嘴唇操着浓重的域外口音,火辣的腰肢撩着香艳的异国风情,故意挑逗着京都少年们炽烈如火的目光。那徜徉花海的人群里,或许还混迹着怀才不遇的青年李白,或许还夹杂着情窦初开的太平公主,或许还散落着你前世心仪的翩翩少年、纤纤少女……
或许,这才是“国民之花”的动人之处。
最早的牡丹,或许代表了爱情。三千多年前,在《诗经》的暮春里,青年男女们互赠牡丹和芍药来表达心中的爱慕。与今天热恋中的情人们热衷于消费玫瑰这种昂贵的舶来品相比,古人显得多么朴素雅致。或许是因为这种花朵艳丽饱满、光彩夺目,与热烈的爱情有着气质上的契合,用她来形容情人,胜过一切语言文字,因而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爱情之花”。
很难想象,这样雍容华贵的花朵出身贫寒,长在乡野,历尽磨难。欧阳修曾写道:“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换句话说,牡丹早先算不上什么名贵花木,仅仅是普通百姓灶膛里的柴火而已。
谚语云“牡丹长一尺缩八寸”。牡丹当年新枝的上半部分到冬天自行枯死,仅剩下少量木质化成枝,这样的生长规律,恰与“厚积薄发”的传统生活哲学一致。俗话说“牡丹舍命不舍花”。当牡丹在不适当的季节移栽或营养不足、环境骤变而难以生存时,她会积聚全身之力,让花朵盛开,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然后心甘情愿地死亡。这虽然是植物适应环境变化、进化和繁衍后代的本能,但这种行为与人的美德何其相似?
孰非过客,花是主人。在这里,城市的浮华与历史的光芒可以渐渐剥落,唯有牡丹依旧盛开。
我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军装整洁、英气勃发。那时,他还没结束漂泊,但已经对这个城市心仪许久。那是他第一次带我们一家四口来看花时的留影,留影的地点,就在最负盛名的天香亭前。彼时的我,还是坐在他臂弯里、吮吸冰棍的小孩子,对于眼前的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的概念,更不知道,几年以后会被她接纳、养育。
我的儿子,跟那时的我年龄相仿,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外婆家的村子里,有一片种牡丹的大田,所以他早早就见识到了这种花的绚丽夺目。与那些生长在田野里努力开放的细碎小花相比,在他的眼里,只有牡丹那样灿烂的植物,才配得上“花”这个名字。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