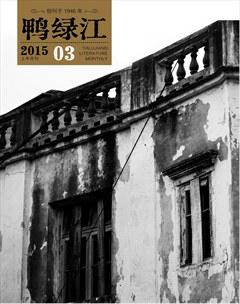故里三题
寇洵
寇 洵,河南卢氏人。有近百万字的作品见于多种文学期刊。获河南省五四文艺奖金奖等三十余项。著有诗集《我曾到过那片树林》,散文集《风过龙门》,小说集《悬铃木的夏天》等。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他的文学感言是:我希望我的文字是一株植物,它扎根在泥土里。我希望它破土而出的时候,能够带着泥土的芳香。
炊烟
炊烟在村庄的上空弥漫,上面是瓦蓝瓦蓝的天,炊烟在下面翻滚着,越升越高,越高越淡,到最后变得无影无踪,仿佛它们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我不知道炊烟的故乡在哪里,我曾经想过,它在云上面。当我看到一块云飘过村庄的上空时,我总觉得炊烟就站在上面。只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我想象不出,它们为什么要站在云上面。
我有时候又想,也许它们是被风带走了。村庄里多的是风,谁也不知道它藏在哪里,它总是想来的时候就来,想走的时候就走。它有时候从田野里来,也有时候从树林里来。从田野里来的时候,它带着青草的、小麦的气息,从树林里来的时候,它带着潮湿的、腐烂的气息。在村庄里待久了,我总是能熟练地嗅到它的气息。很多次,我看见风窜上了烟囱。我看见它在烟囱周围徘徊着,迟迟不肯离去。我看见它与炊烟纠缠着,我就知道,它可能想带走它。但我同时也看到了炊烟的不情愿,炊烟挣扎着,翻滚着,有几次,它甚至又回到了烟囱。但最终它还是又出来了,它被风吹到了高处,它本来应该是直的,但现在它弯曲,它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但它顽强地往上走。我抬头看了一下,上面有一块云,我想,它可能想追上那块云。
我不知道炊烟最终有没有追上那块云。我再也没有看到它,风停的时候也没有。它总是一到高处就散了。谁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后来有一次,我在玩耍时,看到烟囱外面的一堵墙,我才知道炊烟也是有影子的。炊烟是走了,但它却把影子留在了墙上。影子是黑的,埋在黄土夯成的墙上非常醒目。我不知道它埋得有多深,我只知道只要墙不倒,炊烟的影子就一直会在那里。
村里几乎每家每户的墙上都留有炊烟的影子,谁也说不清,这些影子是留给谁看的。很少有人会去注意这些,就像很少有人会去注意炊烟。就连我,一开始注意它,也并非是喜欢它,而是要靠它来判断吃饭的时间。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村庄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无论一个村庄如何变换,不变的永远是人家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
有一次,我看着炊烟,忽然想起了母亲。我想起母亲弯下腰往灶里填柴禾的情景,她一只手按着灶台,另一只手拿着柴禾往灶里塞,火光把她的脸映得通红。我想起浓烟滚出来,呛了母亲一下,她剧烈地咳嗽,她微颤的身体,我想起她熏红的双眼里,忽然滚落的泪水。我想起那漫长而又艰辛的岁月,我想起母亲额头上日渐增多的皱纹,我想起……
我的心像被什么狠狠刺了一下。我想起这么多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母亲是这炊烟的制造者。母亲制造了炊烟,可她却很少有机会看到炊烟。她总是在灶台间忙碌,从案板到锅台,她来回不停地走着,一遍又一遍,这么多年了,谁也不知道母亲走了多少遍。我只知道,当母亲走出灶台的时候,也就是炊烟散尽的时候。母亲一次次错过了她亲手制造的炊烟。
村路
村路上走过很多人,这中间,有些人已经死去,死在这条路上,或者更远的一个日子。有些活着的人,依然每天在这条路上走。他们来来往往地走,不知疲倦地走,直到有一天,他们也离开这条路,去得远远的。
早些年,我在这条路上碰到的人,有些我现在还能遇到,有些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谁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呀,他们好像商量好似的,过些年就会有一个人离开。这条路上的人本来就不多,到后来就更少了。
很多年了,我在这条路上遇到的差不多都是老面孔。这些老面孔,我到老也忘不掉。我差不多记得他们每个人的特征。谁脸上哪儿有颗黑痣,谁经常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偶尔也会有新面孔出现在这条路上,那是外面的来人,他们或是路过,或是来走亲戚,或是干别的什么,我与他们打个照面,有时候互相点一下头,问一声好,有时候一句话不说就过去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很快就会忘掉他们。
我一直忘不掉的是我祖父,到现在为止,他是我们家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最长的人。祖父是一个庄稼汉,他总是扛着锄头出现在这条路上。他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永远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我曾经以为他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后来有一次,我就那样看着他,我看着他慢慢地走远了。他从此没有再回到这条路上,但是每个阳光明亮的午后,我都会看见祖父扛着锄头走在这条路上,我总觉得他还没有走远。
我父亲后来也在这条路上走,和祖父不同的是,父亲没怎么扛过锄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骑着摩托车在这条路上飞奔的情形。父亲端坐在摩托车上,两手紧握着车把,眼睛目视着前方,一踩油门,摩托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起来。我有时候会觉得父亲的样子很神气。父亲的摩托车是村里的第一辆。他在村路上跑的时候,村里有些人就站在自家门前,他们看父亲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多年以后,我还记得他们当时的表情。
再有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后来一次次走在这条路上接我和送我。我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就在这条路上接我、送我,直到我工作以后,母亲依然在这条路上接我、送我。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母亲在这条路上接我、送我了多少次,我只知道母亲头上的白发在增多,一年比一年多。我曾经想,没有人比母亲走这条路的心情更复杂。年复一年,母亲一次次看着他的儿子从这条路走出去,又走回来,她的心情一定比任何人都复杂。多少个早晨和黄昏,母亲站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村路,她希望在那里看到她的儿子。知道儿子要回来,母亲总是提前忙完手里的活计,做好饭,过一会儿就到院门口望一望。在一次次的眺望中,母亲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母亲愣了一愣,然后飞快地走到村路上。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下车后故意站在村路边,因为知道我要回来,母亲早早地就站在院门口。我看见母亲伸长脖子朝村路上张望。那时候是夏天,我的周围有一小片槐树林,它们茂密的枝叶遮挡了母亲的视线,母亲没有看到我。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就回屋里去了。就在我往村路上走的时候,母亲忽然又一次出现在院门口。这次,母亲一眼就看到了我。她已经朝我走过来了,我看着母亲,有那么一会儿,泪水忽然就下来了。
村里的牲畜也都在这条路上走。那时候村里很多人家都还喂着牛,我就常看见村里人赶着牛在村路上来来往往。牛总是一副散漫的样子,一边走一边低头啃两口路边的青草。也有刚卸犁的牛,走起路来有气无力,主人就割一把青草掖在身上,这是要回来犒劳牛的。牛不会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它连路边的青草看也不看一眼。
有些年的夏天发洪水,村路被冲毁过几次。洪水过后,村里很快就会召集人去修路。遇到这时候,几乎没有人推辞。我曾在一场洪水过后,看到父亲和村里人在满目疮痍的村路上修路,他们卷起裤腿跳进河里,把簸箕大的石头往路上推,每个人都使出吃奶的力气,身体弯得像一张弓。那时候,我就觉得,村路是村里人的命根子。
村里的树
在村庄里待久了,我开始注意那些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树。村里有那么多的树,我从来就没注意过它们。再出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村里的树。
我家院子里最早有一棵苹果树,我记事的时候起,苹果树一直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树身上有不少虫眼,有时候还流出一种胶状物,用手一摸,黏乎乎的。那棵苹果树不久就死了。
院子边还有一棵樱桃树,樱桃熟的时候,我站在地上,一伸手就能扯下一枝来。那些年,因为这颗樱桃树,给我增添了不少欢乐。院子东边是一块麦地,地边原有一棵杏树,每年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地里忙活,我就拿棍子站在杏树下往下敲。敲下来的杏子金黄金黄的,我总要在手上多拿一会儿,才会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口。杏子吃完了,杏核还舍不得扔,我就悄悄找个地方把它埋了,盼望着能再长出一棵树来,结更多的果子。只是我很少看到杏树长出来,好像是有那么一两回,杏树倒是长出来了,但没过多久就旱死了。西边房后,父亲栽了一溜桐树,挤在中间的两棵稍小点,其他的则高大粗壮,我曾经试着去抱过,但那时候我还抱不过来。有一年,父亲找了几个邻居,将桐树锯下来,拉到村里的锯木场冲成木板打了家具。
我家河对面原有两棵核桃树,只是我从来也没见过。听村里的老人说,那是两棵老树,谁也说不清有多少年,他们记事的时候,那两棵树已经老得快不行了。后来发了一场大水,两棵老树被连根冲了去。邻居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核桃树,也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年龄。祖父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祖父告诉我,我家河对面那两棵核桃树比这棵不知道要粗多少,这棵树跟那两棵一比,简直就是小树了。祖父的话让我有点不敢相信。要知道,邻居院子里这棵树至少也有一抱多粗,那两棵更不知道有多粗了。我更是很少见过那么粗的树。我就觉得,那两棵树可能是村里最老的。
我大些的时候,有一次到离村不远的西洼去放牛。顺着河沟往沟里走的时候,坡边有一棵老树吸引了我。那也是一棵核桃树,只不过它太出乎我的意料。它实在太粗了,我估计几个大人也抱不过来。它长得也很高,把周围许多树都比了下去。老树周围是一大堆石垄,我搞不明白,它周围怎么会有那么多石头,它的根几乎被石头给包围了。我的目光沿着它黝黑的树干往上爬,一直爬到它遒劲的枝丫上。虽然说这棵树已经很老了,但它的叶子依然很茂盛,多得数不清的枝丫上缀满了绿叶,有种密不透风的感觉。站在它面前,我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以后,我又从它身边过了很多次,但我没有一次走近它。我时常会觉得,和它相比,我实在是太渺小了,渺小得我连走进它的勇气都没有。
村口的井台边有一棵大槐树,差不多有十几丈高,在村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注意它的人似乎并不多。谁会去注意一棵树?村里没有人会去关心它的荣枯,我估计它有一天死了,也没有人会去注意。村里的很多树都有主家,我不知道这棵树属于谁家。它虽说长得很高,但并不粗,枝条也不多,只在树顶分了几个杈,斜出来了几枝。枝上的叶子也不多,零零星星的,叶子本来就小,再加上少,所以,我总觉得它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但它并没有死,很多年前它是那样,现在它依然是那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喜鹊在树上垒了一个窝。开始的时候,那窝很小,喜鹊不断地叼来树枝,那窝就越垒越大。我在村里的时候,经常看见一只喜鹊站在窝上。那是一只很漂亮的喜鹊,羽毛有黑白两色,翅膀和脊背为黑色,腹部为白色,搭配完美得无可挑剔。它站在窝上,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它一会儿望着村庄,一会儿又低下头,用长长的喙在身体两侧捣着什么。等忙活够了,它又会忽然飞起,有时候它会飞得很远,也有时它就绕着村庄的上空,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村前的公路边有一小片槐树林。那些槐树都不是很大,但却枝繁叶茂,开的花也多。开花的时候,整个小村都能闻到浓郁的花香。有些年的春天,我经常看见放蜂人在槐树林边放蜂,成群蜜蜂嗡嗡着扑向路边的槐树林。
村周围的山上是很茂密的树林,树林里大多是桦栎树和青冈树。这些树大都长势良好,除非它被人砍下来,很少会有枯死或老死的。早年,村里允许砍树的时候,村民们每年都会砍大量的桦栎树和青冈树来种植木耳和香菇。桦栎树出产的木耳不仅薄,而且黑,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比。故乡特产中有一样黑木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指桦栎树木耳。桦栎树出产的香菇也很不错。森林被禁伐以后,有几年,村民们开始大量种植袋料香菇,这时候的香菇已经不如从前。
我在村里生活了十多年,很多树就陪了我十多年。有些树,我至今还叫不上它们的名字。也许,我永远都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但我不会忘记,那些曾在我生命中生长的树,那些曾在我少时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树,那些我摸过、爬过、砍过,甚至是烧过的树,我总觉得,它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脚下站的是同一片土地。我们都在向土地索取,直到有一天,我们再完整地把自己交给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会记得那些慢慢老去、慢慢枯死的树,它们说不定也会记得我,在我小的时候,当我老的时候,有一棵树一直默默地陪着我。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