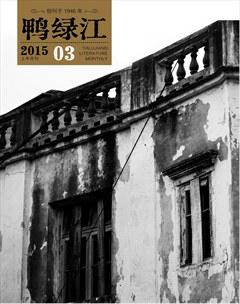深掘现实与精神飞扬
关仁山是当年河北“三驾马车”之一,多年来,他成为了国内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联系的著名作家,成为了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变迁的作家,成为了一位满含深情和充满挑战精神的作家。他的长篇新作《日头》(作者的长篇小说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的收官之作),发表和出版以来,获得国内文坛很大影响,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小说描写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波诡云谲的巨变,通过金家、权家、汪家、杜家几代人错综复杂、缠绵纠结的关系图谱,鲜活地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北方农村斑斓多彩、震撼心魄的生活画卷。
主人公金沐灶的父亲为护钟而亡的不祥序曲,预示着故事的诡秘与神奇。金、权、汪、杜等几个家族的三代子孙,在利益角逐、灵魂博弈中,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活剧。金沐灶为农民的新生活一生求索,与心爱的女人火苗儿分手,火苗儿赌气嫁给了仇家权桑麻的儿子权国金,三个人演绎的爱恨情仇,贯穿了半个世纪现实的探索和精神的漫游,显示了文化的断裂和延续。日头村,这个充满了历史与传说、纠葛着现代与过去血脉传承、有着说不清几千年历史的村落,生活着相生相克的权、金、杜、汪四大姓氏……这片土地与这些人,注定日头村与日头村的农民,在现代化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道路上变革与顺应的艰难,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变革过程中剥离传统生活方式与思维惯性时伤口撕裂般的疼痛。
作者厚积而薄发,作品生活气息浓郁,细节真实丰沛,笔触扎实灵动,鲜明的现场感与空灵的超越感相结合,在处理历史、现实与个人的关系方面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从文化的角度,深刻反思了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剖析了农民的劣根性,对权力、资本致使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做了果敢的批判,并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困境和探求做了深度刻画。
小说以古钟作为主线,用十二律结构全篇,并与二十八星宿相衔接,成为全书最大的象征性意象,筑成了小说宏大高妙、新颖独特的时空结构。小说风格饱满尖锐、沉郁浑厚、雅正恢宏,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可以说,《日头》是对中国乡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次完整的艺术呈现。在艺术上,作者将现实的探寻与精神的漫游、物质的批判与文化的想象、正史的端庄与野史的奇异有机结合,使小说焕发出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为乡土中国文学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我们郑重向读者推荐该部作品。
关仁山,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白纸门》《唐山大地震》,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执政基石》,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落魂天》,短篇小说《苦雪》《醉鼓》《镜子里的打碗花》等。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香港《亚洲周刊》华人小说比赛冠军等。部分作品译成英、法、韩、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台剧上映。《日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对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我们首先要有面对现实写作的勇气。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直面这样的现实,其实难度很大。难点在对时代生活的认知上。如何深刻认知当今变动的现实与复杂的乡土,是横亘在作家面前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难题,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要有强大的爱心,要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因此,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这其实是精神层面上的双向互动。作家所需要的这些精神力量,要经常补充,不断更新,办法就是要到时代的热流、基层的民间和普通的大众中吸取精神力量。这个时代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向前行进,是主流,是大势,作家应与自己所处时代肝胆相照。
就文本仔细一想,宏大叙事带来厚重,同时也是笨拙的,如果作品艺术手法单一,全能全知的视角较为固定、重复,人物类型也相对单调,没有从文化角度深挖其行为根源。只写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改革的进程解决了,小说还有读的必要吗?没有必要读的小说还有必要写吗?创作中,我常常怀疑自己的艺术能力,同时也怀疑小说。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农业现代化、土地所有权、农产品价格、农村剩余劳力出路、贫富分化、城镇化拆迁、农村社会保障、怎样融入城镇生活等等。农村走进了时代的旋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农村问题急迫而严峻。乡土叙事还处在摸索阶段,怎样才能找到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让我们困惑,我无法面对这样巨大的农村变化。一个小村庄,有几十亿富翁,有中产,有一般贫困户,还有很穷的农民。怎样概括它?这是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仇视城市吗?廉价讴歌乡土吗?展示贫苦困境吗?整合破碎的记忆吗?每一个单项都是片面的,应该理性看待今天乡土的复杂性。土地流转也好,城镇化也罢,都需要时间来印证。这些流动的、新鲜的、不确定的因素,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以我们对农民和土地的深爱和忧思,描述这一历史进程中艰难、奇妙和复杂的时代生活。
话题回到《日头》这部小说上来,这部小说创作源起,要说到“天启大钟”,这篇小说是由天启大钟而起的。我的故乡稻地镇有这样一口大钟,与北京怀柔红螺寺的天启大钟是一对儿。由大钟联想到这部小说的十二律结构。我这人有个习惯,总是在小说开笔之前,把自己的构思讲给朋友听,在朋友那里获得验证,然后我才有写作的信心。有一次,我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回避今天残酷的现实,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过去歌颂土地多了一些,这一篇再也不能与农民的苦难擦肩而过了,要加强批判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这部作品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写农民的书,怎样才能做得好?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日头》跳出了农民种地的传统模式,抛弃了原来用过的精神资源,带着忧患意识去写一种新的形态。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苦难和眼泪,小说必然是沉重的。这类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现实,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提纲阶段,不断对自己说:前面有《天高地厚》和《麦河》,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书,一定要面对良心说真话。所以,在风格上就尖锐一些,大胆地探索一些问题,写出时代的旋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以此看来,我想借助金沐灶这个人物在思想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不知读者会不会满意?
回想创作期间,我多次到农村搜集素材。写作过程很痛苦,其间,确实出现过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人搅着事,事推着人,农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写实,这是不够的,作家要超越现实。显然,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将现实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应该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层传奇色彩,让他们部分地异于常人,异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诡秘和神奇中回归常人,回归常理。另外,我在这部小说中格外在乎故事,故事性、传奇性、情感性的渲染会使小说有效地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现实的弊端。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
有的小说是读味道,有的小说是读故事。《日头》故事性较强,讲述了文革红卫兵砸钟伤人、焚烧魁星阁,以及后来大钟埋入墓地被盗、城镇化拆迁挖湖挪钟事件、强拆中的自焚事件等等一些传奇事件。我想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故事的传奇性会给小说增加野逸风格,会淡化政治色彩,所以热闹的背后我还是想让读者读故事背后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思想和文化含量。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殖民,这一惨烈的过程,用孟繁华先生的话说,那是乡村文明的崩溃。我们目睹了崩溃,还是要呼唤新的文明形态的建立。比如说,按佛家的因果关系来说,文革压抑人性是因,改革开放人性的解放就是果。人性大解放人性在金钱面前的疯狂,造成人格裂变的果。人格分裂的因,又造成如今国人精神困境的果。这些东西都与乡村文明的崩溃相关。
必须埋下问题,浮起追问。我塑造的农民金沐灶是个民间思想者,借助他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这样方能带领读者思考。一幕幕活生生的事件促使金沐灶对“文革”后的日头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真切的顿悟与认识。面对着自己心爱的火苗儿,金沐灶痛心疾首地说:“火苗儿,我对不起你。我不配提爱情。烧掉魁星阁、砸毁天启大钟的时候,日头村人的心里是不是黑暗一片?是不是到处充满仇恨?可是谁来化解仇恨?谁来拯救苦难?流血的悲剧还会在日头村重演吗?我以为没有‘文革,悲剧就不会重演了。然而,我错了。事实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资本时代里,你姐姐大妞留下的那只脚、披霞山铁矿流血惨案、披霞山大火、汪老七的死、大拆迁中的强暴、失地农民的血泪,这都是悲剧啊……”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强调,金沐灶的这段话语,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善于思考的人心中的呐喊。《日头》没有对城镇化引起的弊端过分情绪化的诅咒,而是通过金沐灶试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中,从“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镇化的正确方向。从体制上看,我们目前的城镇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野蛮性。错误的政绩观与恶意资本的联手,会伤害农民的,资本与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和变异是触目惊心的。这时候我想成为乡村文明的审视者,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属性上的追问和审视。比《麦河》讴歌土地更进一步,土地属于谁?这是个重要问题,我想在故事的背后探微农民的精神困境与迷失的文化根源。
由此,我想起乡愁话题。因为我的童年、壮年和青年都是在冀东平原一个小村庄和小县城度过的。小时候,在大槐树下,听盲人唱大鼓、算命,下雨了,下雪了,我们到外面看雨,看飘舞的雪花,那是怎样惬意的事情?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暖而闲适。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走出乡村游子的精神慰藉。恶意资本和极权对这个氛围的冲击和破坏,使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裂变后的乡村和农民,怀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走向了历史的新形态。
我走进开始新生活的农民中间就想,他们是新人还是旧人?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人,看见农民、土地和庄稼,还能感动吗?还能感动,说明我还能写乡村小说。《日头》小说中的毛嘎子在天上的云顶议论抒情,其实是在痴人说梦,他还会围绕二十八星宿解梦,他在天空中见证了一个村庄由兴盛到消亡的过程,但是,他是超脱的,因为超脱才是乐观的,他离太阳最近,身体是温暖的,作家应该以温暖写冷酷,唤起的不是仇恨,而是对同情、怜悯、善良和博爱的憧憬。实际上,我是借毛嘎子的嘴说出我心中最温暖、最隐秘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乡愁和恋乡情感。
二十八星宿照亮了我小说里人物的内心,太阳照亮了大地。我赞成一个说法,小说要照亮生活。也就是说,小说最重要的是要点燃或者“照亮”人性中最柔软的东西。这柔软的东西是珍贵的,那就是大地乡情带来的悲悯和爱。守住这样的东西,那样我想,就会达到深掘现实的目的而让精神飞扬起来。
反响
《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6期选载
荣登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第二名
荣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4年11月“大众好书榜”
荣列《人民日报》年度推介“五佳”长篇小说
荣获2014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作家贡献奖”
读关仁山的长篇新作《日头》,一面感受到他仍在延续着《天高地厚》《麦河》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一面明显感到他的笔墨变化了:如果《麦河》的重心是“写土地”,那么《日头》的重心则可谓“写文化”。小说文化气息浓厚。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宗教文化相交织,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伦理、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我们对此当然不可作绝对化理解。但不管怎样,作者偏执于对农民文化性格乃至文化基因的探寻,追溯文化断裂的惨痛历史,寻觅今天文化重建的路径,即所谓“续文脉”,则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与现代化转型中,发现并培育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无疑是新的富于时代审美价值的命题。
——著名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雷达
长篇小说需要对时代的概括。关仁山在《日头》里的概括是有颇有深度的。他细微地写出了村庄里那些隐蔽、缓慢而影响久远的变化,写出正统民间文化形态消亡后带来的颠覆性后果……今天的时代,几近疯狂的物欲,生活成本的负累,社会道德的滑坡,使今天的不少人们,与传统人格渐行渐远,基本的特征,便是崇奉实利而无精神信仰。关仁山借助宗教力量,透过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撕开了生活表象,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令人担忧的乡村状况,这里埋藏着各种乱象的根源,特别是人性和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作家的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且根深叶茂。作品中的金沐灶,正是作者的化身,金沐灶力图重建魁星阁,作者则建构了一部厚重的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品。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胡平
《日头》是关仁山突破自己创作的一次重要的挑战,一个作家突破自己是最困难的。关仁山韬光养晦多年,他用自己坚实的生活积累和敏锐观察,书写了日头村传统文明崩溃的前世今生,实现自己多年的期许。他对乡村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和文学想象,也应和了我曾提出的一个观点:乡村文明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对乡村中国书写的终结,这一领域仍然是那些有抱负的作家一展身手前途无限的巨大空间。
——著名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孟繁华
关仁山的《日头》在具备艺术审美价值的同时,其认识价值的突出也的确不容忽视。从根本上说,一部作品认识价值的突出,须依赖于作家深刻思想能力的具备。所谓思想能力,就是强调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对自己的表现对象有深切独到的理解与发现。很多时候,文学作品的不尽如人意,关键原因首先在于作家 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所欲表现的对象客体想明白。如此一种境况,乃所谓思想贫弱症者是也。相比较而言,关仁山显然应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中国作家中思想能力相对突出的一位。他一方面在自己所特别钟爱的小说创作上从来也不固步自封,总是以一副海纳百川的姿态广泛地吸纳各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长期关注思考乡村大地上农民兄弟的命运变迁,其中尤以对现代化思潮强劲冲击下乡土中国未来发展可能的关切而引人注目。
——著名评论家、山西大学教授 王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