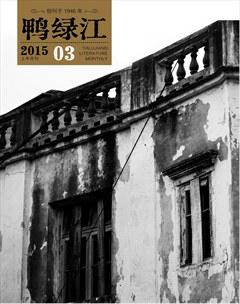梅娘:一脉文心,续写传奇
邱丹
邱 丹,辽宁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沈阳城市学院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美学,并积极探讨实践化教学教法,公开发表《论史铁生作品对宿命意识的穿越》《无名氏小说的存在主义思考》等多篇学术论文。
在东北这片神奇的“冻土”上,不仅孕育着倚仗着肥沃黑土而赖以生存的人民,也在时代递嬗中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时代的动荡、生存的苦难、沦陷的痛苦、人性的纠葛、政治的斗转星移……最终化为延留的记忆,在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回声。当我们翻阅梅娘的作品时,这种回声依然在清晰地叩响,虽然她纤细的笔触、温暖的文字、自由恣放的情欲、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得我们面对文学流派的历史追认时,总是将其置于东北作家群的边缘,更愿意在探寻“东北女作家群”“沦陷区女作家群”时,将其置于前列,但不可否认的是,共有的东北大地上的历史遭际,更似精神纽带,链接着散落的个体,她的存在不仅丰赡了“东北女作家群”的存在,而且她们以女性独有的敏感与细腻共同完成了东北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确证。可以说早在40年代就享有“南张北梅”桂冠的梅娘,她的人生足以演绎一段过往的“历史”,她的作品足以诠释一代人的“印记”。
一、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燃尽微光,送走生命”是梅娘在《我是一只草萤》中的自述,“草萤”的自拟或许带有自谦的意味,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个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时,想到那黑暗中灼亮的一角时,想到那个被历史搁置快要忘掉曾经的过往时,也连同想到了70年代末,重拾写作之笔,继续与文学续缘的梅娘,流逝的伤痕并没有使其消沉,她负重的飞翔,终于以生命与创作的延续方式,重新获得了声音,因此“燃尽微光,送走生命”,是对这位跨世纪老人一生创作最恰的表述。从1936年《小姐集》问世,到2013年刊载在《芳草地》的随笔《企盼、渴望》,梅娘的写作生涯延绵近八十载;2013年5月7日病故于北京时,民间藏书家田钢的挽联恰是对梅娘文学经典的最佳描绘——
上联:小姐集鱼蚌蟹奉读者精神食粮
下联:黄昏献梅芷茵通书简一脉文心
横批:长夜萤火
梅娘(1920一2013),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1920年生于清政府割让给沙皇俄国的割据地海参崴。
幼年丧母,养母的冷漠与尖刻,慈父的才智与胸怀,使得梅娘养成了一颗敏感、独立、早慧的心。梅娘成长于吉林长春(当时为日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留学于日本东京,曾与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沦陷区三剑客”,并在中国文坛上享有“南玲北梅”的盛誉。1931年春,梅娘插班考入吉林省立中学,11岁的她已才华初绽,入学作文《论振兴女权的好处》的思想深度与超前性,令主考教师震惊。16岁高中刚毕业,集结习作,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小姐集》,作品掷地有声,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目前虽已散失,但其“难得的真诚,难得的清丽”,不失为沦陷区文坛中的一泓活水。20岁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第二代》,视野开阔,题材不拘泥于女性,情韵细腻,思想犀利。1942年学成归国,定居北平,在北平《妇女杂志》任职,小说集《鱼》和《蟹》也相继结集出版。1943 年,梅娘凭其作品《蚌》,获得“大东亚文学奖的选外佳作”。1944 年,梅娘凭借小说《蟹》摘得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奖”。
然而人事代谢,时代急转,曾经的盛誉,却在历史的重负下幻化为境遇的坎坷,使梅娘在艰难中游弋。曾经自喻为“高空中不沾尘埃的百灵”,在肃反、反右、文革一系列运动的裹挟下,一如“喑哑的夜莺”,“谈鱼色变”的梅娘自此消声,隐姓埋名。直至80年代,《鱼》的原版才得以重印,1987年刊发在《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五辑上的长文《写在<鱼>原版重印之时》,梅娘的名字才重见天日。此后,梅娘40年代的小说创作才重新结集重印,如《长夜萤火》《梅娘文集》《黄昏之献》《梅娘——学生阅读经典》《鱼》等。
梅娘曾说:“我的蔷薇只开了一天便凋谢了。”的确,虽然写作生涯延续近八十载,但属于她的小说创作只有短暂的几年,这确实太短了。但是她之于中国文坛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漫长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的命运与演变,更因为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这枝“曾经怒放过的蔷薇”时,重读这些作品,你仍然会为之感动,你仍然能够体会到其文字的热度。 纵观梅娘的作品,无论是对细小生活的探微挖掘,还是对女性主体情感的自我辩驳;无论是潜隐于笔端对殖民主义的回应与纠结,还是在时代投射下对人存在状态的描摹与忧患,其温暖的文字、孤傲的身影、微弱的呐喊,在沦陷区文坛相对荒凉的状态下,都似寒夜中的一缕微光,温暖着被铁蹄践踏的大地。这也许是对梅娘的最合乎心愿的嘉赏,点点金光,并不耀眼,却温情无限。一如她所愿:让“最后的一点芳香流向人间”。
二、波澜不惊,愈见峥嵘
文苑岁月悠悠,无论历史下的梅娘,还是梅娘诉诸笔端下的历史,都足以成就一段传奇。梅娘以近百年的人生历程记录着中国百年历史的风雨征程,她的创作折射着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及心境,也隐含着日伪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盛誉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冷落,转眼已经成为陈迹,她存在的本身不仅是历史的印痕,亦是文化的积淀。作为沦陷区历史的见证者,梅娘的存在是沦陷区文学热潮的剪影;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梅娘的存在,亦是对一个时代代表作家谢幕的致敬。
动荡的时代,波澜不惊是对这位跨世纪老人最恰当的书写。梅娘这一代从30年代跨过来的知识女性,正值历史的动荡时期,新旧矛盾、民族矛盾交锋,梅娘坎坷的命运也是一代人的命运,在时光的流转中,她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偶,而曲折的政治经历,更是震得她肝胆欲裂,我们无法想象梅娘在劳改期间,作为一个母亲是怎样担心着毫无生活来源的三个孩子,命运造化的恶谑,使得其先后失去了爱女与爱子。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历经苦难的梅娘,将苦痛化为一种岁月沉淀之下的沉稳与坚韧,人间万象在梅娘的笔触下老练苍劲而又洒脱,这是梅娘的人格魅力与文人风骨,它使得梅娘能够在数不尽的冷酷与屈辱中,依然可以拂去尘埃恣意奔放,这是梅娘在历史清醒之后,在文学场域中重新获得盛誉、展现风华的重要原因,也是她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所在。她犹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此时的梅娘是幸运的,生命的延续,是对她苦难人生以及文学生涯的馈赠。
物换星移,“南玲北梅”已经跨过了半个世纪之余的淘洗,南“玲”的热度似乎从未消减,于此相比,北“梅”的热度确显不足。当新时期梅娘的名字重新浮出历史地表,面对这位风华已过、华发盖顶的老人,人们似乎更想探寻那个云遮雾障之下的历史,甚至有人质疑是梅娘自编自演了“南玲北梅”的出台,其作品的自我删改,引发的“沦陷区文学”真实性也颇受争议。但是作为一个时代代表作家的世纪转化,其存在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与文化符号的表征。“南玲北梅”反映的不仅仅是对其文学史地位的褒奖,它折射的更是“南北”不同沦陷区之下的价值思考,它蕴含的更是不同地域女性创作不同特质及审美追求。当人们反观梅娘时,更应该跳出“南玲北梅”的审美框架,你会发现其翰墨书香留下的手泽,也似空谷绝音。
不难发现梅娘的小说,是与“五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其创作总是饱含着青春的激情,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会构成一种不自觉的张力,在她的文字中,我们也会发现沦陷区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以及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污垢,也因此其内在神韵构成的文学风格、其一脉文心凝聚的人格魅力足以在文学场域中叩起回响。
三、《第二代》及“水族三部曲”
与梅娘漫长的人生历程相比,梅娘创作的黄金期却相当短暂,纵观梅娘的一生,其优秀作品大都写于1945年前,动荡的时代过早了地剥夺了其写作的权利,也造成了其生存的困窘,但是那个曾经属于梅娘的辉煌瞬间,却值得我们驻足品读。
《第二代》是继处女作《小姐集》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于1940年10月由长春文丛刊行会出版。主要收集了《第二代》《花柳病患者》《在雨的冲激中》《六月的夜风》《蓓蓓》《最后的求诊者》《帘卷西风》《一个女职员》《迷茫》《时代姑娘》《应该受罪的人》《追》《落雁》十三篇短篇小说。梁山丁为之作序:“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意识。《小姐集》描写着作者的小儿女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渗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它体现了梅娘审美视域的拓展,也为她赢得了文坛上的好评,作者将艺术的笔触探向生活真实,是“以热情和哀怜的情绪作文学的骨骼,多方面的捕捉人生的动静”。也因此奠定了梅娘在东北沦陷区文坛的重要地位。
《第二代》是梅娘创作由闺阁到社会人生转向的标志。梅娘“泼辣地描写着一群游户似的男女和一群浮浪的孩子”[ 山丁.关干梅娘的创作.华文大阪每日(日本)5卷10期,1940年11月15日】。
譬如《花柳病患者》讲述了一个瓦匠在“塘子胡同”不幸染上了花柳病,在男子羞怯的言语间,梅娘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底层人的正常生存欲求与无奈。而在《在雨的冲激中》,本应是一群童言无忌的孩童,但言语间叩击在童贞孩子心中的却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差异,引人深思,一群被倾盆而泄的雨滴冲激的瘦削身影,在读者心中形成深深的感印。总体来说《第二代》中的小说,题材新颖大胆,结构精巧,内蕴深刻,质感厚重,梅娘在纤小细腻的笔触中嵌入了刚劲的笔致,也因此《第二代》这部短篇小说集绝非前尘旧影,它体现了梅娘对于人生与人性的思考,至今读来,依旧余味延留。
在梅娘的小说创作中,关注程度最高的当属“水族三部曲”,即《一个蚌》《鱼》《蟹》,这也是梅娘著作中最能突显女性意识的经典文本,三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上并没有接续性,但很多散在的共性却自成一体。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启蒙,她们一方面渴望爱情与自由、自立要强;一方面又是没有自由的活囚,孤独且感受不到家庭温暖,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家族的命运。《一个蚌》描写了面对强势的家族权威,梅丽的爱情遭遇阻隔,只能在束手无策中一点点耗尽生命的热望,一如软体动物的“蚌”,“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 梅娘.一个蚌.鱼[M].华夏出版社 2011:85)
与《蚌》不同,《鱼》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诉求,更为鲜明泼辣,“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落在地上都好”(梅娘.鱼[M].华夏出版社 2011:17),与梅丽相比,芬的情感更炙热,她毅然决然地钻出了家族掌控,面对林省民的出轨、琳的敷衍,芬依然发出了女性内心关于爱欲的呼唤:“爱的时候不容选择,留给我走的只有这一条路,我走了,‘诽笑是他们的权利。”( 梅娘.鱼[M].华夏出版社 2011:32)芬的路也是这个时代女人的路,“女人的路是窄的”,这是这个时代女性的悲剧。
《蟹》是“水族三部曲”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蟹》的题材由婚姻爱情拓展到家族兴衰,使得文本更具张力感与饱满感,同时《蟹》也更多地融入了梅娘自身的生命体验。《蟹》非常精妙地呈现了沦陷区大家族的破败以及破败之后的兄弟妯娌之间的明争暗斗及相互倾轧,人性的丑恶、世俗的嘴脸在这个趋于崩溃的大家族面前一览无余。男性世界中的大伯贪色无能;三叔嗜钱如命、急功近利;张贵狡黠市侩;女性世界中的祖母陈旧懦弱;继母冷漠无能;三婶强势贪财;长孙媳侍宠傲娇……没有沾染俗气的秀秀最终却陷入了父亲亲手编织的圈套之中,所有的格格不入,玲玲只能选择出走。《蟹》体现了梅娘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也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不凡点缀。
“水族三部曲”中,与被“强化的女性”相比,是被“矮化的男性”,这凸显了梅娘鲜明的女性叙述立场,她的文字细腻平滑,形象却生动无瑕,当我们面对逸出婚姻的男性个体、当我们走近情感丰益的女性个体,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境遇,感受到她们面临幻灭的肉体及精神追求时所体现的源自生命深处的焦灼和呐喊,这种声音足以让我们震撼、停留、凝思。
四、未曾忘记,世纪回响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当我们重新瞭望那位恬静、安闲,负重、坚韧的世纪老人时,既是对她百年风雨人生的回望与尊重,更是对历史苏醒之后梅娘重现的庆幸,我们经常会想如果梅娘在创作的黄金时期没有遭遇一切,将会怎样?事实证明,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终将重现,梅娘曲折复杂的生命历程,反而增添了其研究的魅力,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不断追逐梅娘的足迹,90年代后期,梅娘被列入中国现代作家百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梅娘的书籍不停再版,关于梅娘的研究也纷至沓来,可以说,梅娘已然是中国文学历史叙述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每个人都仿佛在付诸流水的细沙中行走,在时间的延展中贴近生命的脉动,在静静的时光流逝中,整个世界仿佛都可以遗忘。但是感谢在时光的隧道中,我们能够重新与梅娘相遇。在20世纪70年代,梅娘仿佛随着时代的更迭,忘却了自己,年轻一代甚至闻所未闻,包括写作与生命同构的史铁生先生。史铁生在《孙姨和梅娘》中谈到:“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没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张泉.待序一.怀人与纪事[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4:2)直到后来史铁生才知道孙姨就是梅娘,史铁生初见梅娘时,她痛失爱子不久,而梅娘依旧温暖如故,命运多舛的一生最后练就了泰山崩于前的坦然,她对生活的直接面对和积极态度以及对生命的尊重,也为当代人确立了一种正向的精神标举,其坚强及富有传奇的一生,也释放着一位老者对人生的豁然与光华,她才是生命真正的实录者。也因此陈放在《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中评论道:“梅娘以往全部的作品总合起来,也逊色于她的生活,逊色于她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梅娘.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学生阅读经典[M].文汇出版社 2002:309)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作为一位作家,其才华造诣依旧不可掩盖。
梅娘真正的创作始于沦陷区,也恰恰止于沦陷区,最终也因此重现,这仿佛是生命的轮回,其实也恰巧说明梅娘对于沦陷区殖民化下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作,是弥足珍贵的精神书写。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选集《长夜萤火》,梅娘作为东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其小说收录于此。陈放评说道:“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样的吻和冰一样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送来了歌声。”(梅娘.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学生阅读经典[M].文汇出版社 2002:309)梅娘关注女性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但是人文关怀的向度绝非仅仅停留于此,她呼唤和向往的更是人自身,这是对新文学思潮的回应,更以东北女作家的地域身份,共同构成了新文学的整体向度。梅娘的作品关于对人性普遍关注,让我们体会的不仅仅是时代的波动,女性破碎的命运、挣扎的灵魂、旧家族负重式的背负,又重又痛,更是对女性内心声音近距离地聆听。松花江的哺育、黑土地的孕养,使得梅娘有着独立思考、勇于抗争的人文品格,她是“北方之强”的真正歌者,也因此梅娘其人其文,总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温暖去化解这沉重的个体,去平抚这破碎的世界,给人以生命的温度与感动。
梅娘将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散文创作,与其创作力衰竭的解释相比,我更愿相信这是梅娘的自由选择以及选择的权利。梅娘在《为什么写散文》中提到:“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渴望坦诚的心灵、渴望向善的物事、渴望深邃的爱情,等等等等。”(梅娘.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学生阅读经典[M].文汇出版社 2002:217)
至今,我们能够翻阅梅娘的怀人、旧事,展示了一位世纪老人对于人生、历史和现实的感悟,更觉这是饱经沧桑之后凝结的苍劲与反思,梅娘作为过往的亲历者,为文注入的饱满情感,就似沉淀于沙底的珠贝,具备着为文为史的双重价值。时至今日,当我们触摸梅娘“绚丽而不忘平淡,求非膄不忘简约”的文字时,仍然能够聆听到其一脉文心的世纪回响。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