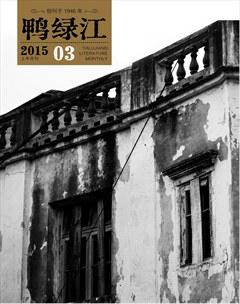五车间
朱日亮
五车间是462路汽车的终点站。这地方位于老城的郊区,除了五车间找不到一个醒目的标志物。五车间厂房高大,差不多有三四层楼高,所以462路汽车站名就把五车间用上了。
客车厂在城里,因为地方狭窄,又因要扩大规模,就在郊区建起了五车间。原打算全厂都搬到这边来,后来下来个文件,不搬了,所以五车间和总厂不在一起。虽不在一起,五车间却是厂子的龙头老大。五车间是客车厂总装车间,是客车厂最重要的车间。一辆车有上千上万个零部件,进入五车间之前,它们都是散着的,是一个一个铁疙瘩铁片子。进了五车间,它们就合到一起了,变成一辆漂亮的大客车。当年客车厂生产的大客车,全国各地马路上都见得到,有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东边的镇江徐州,南边的广州海南,西边的成都乌鲁木齐,北边的佳木斯满洲里,都跑着客车厂的大客车。那时,提起客车厂,没有谁不知道。如果你说是五车间的,听到的人会眼珠子发蓝,恨不得立马把闺女嫁给你。全国有名的国营大厂,哪个人不羡慕?只要说到五车间,就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说的人精神,听的人也精神。
客车厂全称叫黎明客车厂。客车厂生产客车,这是一定的。如果你认定客车厂只能生产客车就大错特错了,老客车的人都知道,厂子还能生产军车,就是那种军用卡车。只要上面红头文件发下来,就会有一辆接一辆绿色的军用卡车从五车间开出去,据说,连越南和朝鲜的大山里也跑着客车厂的军用卡车呢。
现在,五车间已经不是一个车间了,它是一座巨大的空房子。不光五车间空掉了,墙外的家属房也渐渐空掉了,只剩下王进山一个人。这一天,王进山坐在一根工字钢上,像一条老狗一样看着空旷的五车间。在王进山的眼中,车间里除了一部老掉牙的车床和埋在地面上的钢轨之外什么也没有。车间的窗子早就没有玻璃,看着就像一个老妪的眼睛;水泥地面斑斑驳驳,就像一幅一幅破碎的地图。风从窗子刮进来,刮进几片黄了边的树叶子。王进山拣起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咬着,这哪里还是五车间?分明就是一片废墟。五车间没了,说不定哪天,连这座空房子也没了。现在,五车间属于显达房地产公司,十年前显达公司就把五车间买下来了,不光买下了五车间,车间里的设备也一起买下来了。十多年了,显达公司并没在这儿盖房子,就这么把五车间空着,空得周遭长满了荒草,车间的屋顶上也长了草。
当年,五车间可是好大一片地方,车间里的设备顶呱呱。除了这座车间,外面还有一个篮球场,那是区里唯一的灯光球场,国家青年队还在这里打过比赛呢,厂区还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现在,那个游泳池成了一个烂泥塘。
王进山进厂就在五车间当学徒。他当的是维修钳工,那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种。钳工们屁股蛋子上吊着工具袋,袋子里面插着钳子扳子螺丝刀,走起路来晃晃当当,那真是要多威风有多威风。王进山十五岁进厂,二十一岁就带了徒弟。那天,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两个女的说,大王,新分来两个徒工,你带着她俩。这两个徒工一个是高云,一个就是他的前妻春刚,那时当然还没有前妻那一说,那时她俩还不到十六岁,两个人都是顶花带刺的黄花闺女。
女的?王进山没正眼看那两个女的,心里骂道,娘的,老子命不好。满心不乐意地把两个丫头片子领进维修班。没想到高云和春刚在维修班一干就是几十年。
两个小女子第二天上班时穿上了工作服,怪去了,那工作服就像为她俩定做的一样。进了车间,几百号人都看傻眼了,这不就是车间墙上的宣传画?宣传画上就有那么两个女一男,雄赳赳气昂昂的,她俩和画上的女子一模一样!
王进山也傻眼了,长到二十一岁,他就没见过这么打眼的女孩子。客车厂二十六个车间,一万八千多号人,女职工占了小一半,他就没见过这等人才。不过王进山心里有小九九,好看不是真本事,好看多半是样子货,就像墙上的宣传画,谁也不能把画揭下来当饭吃。
没想到这两个丫头片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那个叫春刚的,本来已经考上市里的机械学校,可她硬生生没去。她老爹是客车厂的,她早就想进厂子了,上了机械学校也未必能分到客车厂,有这样的好机会她当然不能放过。另一个叫高云的,也是人托人才分过来的。高云在中学就是响当当的人物,是全市学生的头,听说小学时还给邓小平献过花呢。
两个女子万没想到,刚进厂就分到五车间,那可是五车间啊。在五车间当钳工,走到哪儿都是尖子,五车间的钳工组,在全国技术比赛中拿过第一呢。她们认定老的就是好的,满心跟定一个老师傅,学得一手钳工的好武艺。都说车钳铆电焊,给块金子也不换。五大工种里钳工是一顶一的全能,五大工种里没有钳工干不了的,钳工好比体操里面的全能,春刚和高云不知道,师父王进山虽然年轻,但他就是那个全能冠军李小双,不过这是后话。
有一次车间书记对王进山说,你这名字和一个将军一样,他也叫王近山。王进山说,少给我灌米汤,我哪里比得上人家,人家是将军,我就一钳工。话是这么说的,王进山可是狠狠自豪了一把,心里自傲着呢。跟将军他是没法比,但在五车间,在维修班,没有谁他不敢比,客车厂里面访一访,有谁不知道五车间王进山?王进山是五车间的王,车间里那些铁块子铁片子螺钉螺母钳子扳子车床冲床铣床就是他的兵。
王进山是大个子,也不是太高,他是显个那种人,车间里人都喊他大王。现在五车间的老人不叫他大王了,叫他老王,年轻的,叫他老王头,更年轻的,干脆就不认识他。现在,王进山很少能看到五车间的人了,只要有红白喜事他都去,只要见得到,火葬场他也要赶过去。
怕自己迷糊过去,王进山站起来,吐掉嘴里的树叶,围着五车间转起来。往上看,五车间头上是钢灰色的天空,一大片云彩被风撕扯得支离破碎。往下看,蒿子又长高了,蒿草甚至伸进了窗子,蝈蝈在草丛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那叫声本来挺好听的,王进山却听得心烦,他把眼睛掠过那些蒿草。五车间的墙体是耐火砖砌的,上面有很长很长的标语,字体已经看不清了,但王进山还能念出来,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念出来。
职工们一起洗澡,一起打篮球,一起去食堂,一起会战加夜班,一起打架。大客车一辆一辆从五车间开出去,几十年的事情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打转。那时加班不加工资,顶好的是补几斤粮票,工人们也不怎么计较。没想到在一次会战加班的夜里,王进山和一个女子擦出了火花。
夜里的五车间像一座辉煌的宫殿。
有一天,骚猴子来了,还拿来一瓶酒。骚猴子在五车间当了三十年车工,当年这家伙因为偷看女工洗澡,差点被厂子开除。那天喝着酒,骚猴子说,大王,你说我看见谁了?王进山说,谁啊?骚猴子说,你猜。王进山说,你都六十了,经见过的人成百上千,谁知道你说的是谁?骚猴子说,我看见高云了。王进山一阵心跳,拿杯子遮住脸说,她呀,她不是在沈阳么?骚猴子说,回来了,跟儿子过不到一块儿,一个人回来了。王进山轻描淡写地说,找个老头不就得了,干吗回来?骚猴子说,我也这么说呢,她要找好找,哎,你没看见,高云现在还她娘的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奶子还是翘的,说四十也有人信呢。王进山说,你个老猴子,又犯骚劲了。嘴上说骚猴子,心里却是一阵骚动。骚猴子说,我倒是想犯,骚心有,骚劲没有了,我问你,当年你是不是和她有一腿?王进山说,说实话?骚猴子说,当然说实话,我跟你就说实话。我偷看女工洗澡,差点被厂子开除。王进山说,你活该。骚猴子说,我不是看女工洗澡,我是看高云,看看还不行吗?许你绕山放火,不许我屋子点灯?王进山说,还有脸说,你把灯点到人家女澡堂了。骚猴子说,说实话我恨死你了,我恨不得你让大客车撞死,好事都让他妈你霸着,五车间两个大美人都他妈的喜欢你。现在我也恨你,恨你是恨你,我他娘的恨你还喜欢你。你技术好,我是车工,你车件比我车得还地道,不过你小子别得意,除了你,我骚猴子谁也不服。王进山说,老皇历,别提了,喝酒。骚猴子说,老皇历?我就乐意翻老皇历,五车间那时多热闹,比现在电影明星还火,还热闹,操,那肉皮子,白,紧实,说,你和她有没有一腿?
骚猴子总是说话跑题,跑题是跑题,最后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个宗就是女人。王进山明白骚猴子又犯骚劲了,也明白那“白”和“紧实”说的是谁,说就说吧,骚猴子也就是过过嘴瘾,酒喝到这份上,王进山也憋不住了,他说,差一点。
真就差那么一点。那天,王进山把高云送到卫生所,医生给高云打点滴。医生说,车间里那么热,女孩子又不能像你们男人那样光膀子,小高是中暑了。
高云真中暑了,不过一瓶子点滴打进去,高云就醒了。见到王进山,她问,谁送我来的?王进山说,我。高云坐起来说,我要回家,你送我。大黑夜的,一个女孩子,中了暑又是他徒弟,王进山只好送高云回家。高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门刚关上,高云一下抱住王进山。
骚猴子问,上床了么?王进山说,没上。骚猴子酸酸地说,到嘴的肉你没吃?说死我也不信。王进山说,不信就不信。
还是那句话,就差那么一点了,让高云紧紧抱住的王进山已经晕了头了。一个女孩子这么样抱住你,你还有什么不明白,还有什么可说的?高云身子热得烫人,王进山也热起来,身体上的所有零部件全都嗷嗷地鼓噪,他也紧紧地抱住高云,情势已然势不可挡了。就在那一刻,王进山看到了高云工作服上的工牌,15号,他想起,有一个人的工牌是16号,想起那个人,王进山放开了高云。
高云狠狠剜了一眼王进山,捂着脸跑进屋里。几十年了,王进山总忘不了高云那一眼。
隔不几天,王进山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一拿起来他就知道是谁了。他说,你是高云。高云说,我还没说话,你咋知道是我?王进山说,听喘气就听出来了。高云说,你出来吧。
高云在一家小馆子里等着王进山。高云一点没显老,骚猴子眼睛花了,看女人却是一点不花,王进山想起骚猴子那句话,眼前的女子果然腰是腰屁股是屁股,两只奶子果然是翘着的。看着王进山坐下来,高云说,你没刮胡子。王进山说,忘了刮。高云说,我才不信你忘了呢,早先会战加夜班,你还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呢。王进山说,又不是会战加夜班。高云说,下次来把胡子刮干净,你就当是加夜班。
王进山说,去哪儿加班,做梦吧,你多久没去五车间了?高云说,两年了。王进山说,两年没去?你可真狠。高云说,不想去。王进山说,再不看你就看不着了。高云说,不想看。王进山说,沈阳可是大城市,在那儿过得咋样?听说你儿子在那儿有买卖?高云淡淡地说,开个网店,房子买了,车也有了,还是嚷嚷没意思,你说,他们年轻轻的都没意思,我有什么意思?
酒一沾,高云的脸红了,眼睛也亮了,从那眼睛中,王进山又看到了他熟悉的浪劲儿,还有寂寞。他想,喝酒有坏处,也有好处,酒不做假人就不做假,比方现在,几杯下去高云又成了以前的高云。他看着她说,跟儿子过不到一块儿吧?高云说,也不是,我在沈阳一个熟人也没有,闷死了。王进山说,闷?扭秧歌,跳舞,扭起来跳起来就不闷了,现在时兴跳舞。高云说,我才不跳呢,让那些骚老头子搂着抱着,恶心死了。酒进肚,王进山说话也放肆起来,说,老牛吃嫩草,不让老头抱,让小伙抱啊?高云在桌子下面踢他,瞪着一对桃眼说,烦人,又说,有脸说别人,你还抱过我呢。高云那一脚把他的情绪踢起来了,王进山也被高云带入了港,有些神往地说,是抱过,那天会战加夜班你晕倒了,我抱你去的卫生所。高云说,你还记得卫生所么?王进山说,那还能忘?咱厂子卫生所是全市最好的卫生所。高云说,现在我也不相信你抱过我,我觉得那像做梦。忘没忘,春刚怀你儿子就是在卫生所查出来的,全市第一台B超呢。王进山说,别提B超,也别提他。高云说,为什么不提?你说他傻?傻也是儿子,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回来呢。王进山说,屁,回来?十多年了,五车间卖给显达十多年了。高云说,显达是炒地呢,要不是卖给显达,黎明不会犯病,不犯病他就不会走。王进山说,和那有屁关系?高云说,有关系,我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黎明是在五车间长大的。看王进山拢起眉头,高云突然笑起来,笑得满脸飞红。王进山问她,你笑什么?高云说,听说有个女人五十岁还生了孩子。王进山说,怎么扯到生孩子了,你信那鬼话?高云说,鬼话?电视都播了,那女人五十一了。王进山说,电视也说鬼话。高云突然生气了,站起来说,这鬼话那鬼话,我看你就是个鬼话。
王进山看着高云,明白她用的是激将法,但他还是绕山绕水地说,真忘了,你也奔五十了。
把话说到这份上,这家伙还在绕,高云忽闪着一双桃子眼,对王进山说,大王,我不跟你讲废话,你要是不烦我,我今晚就跟你去五车间。王进山被高云逼得发慌,岔开话题说,显达公司说在五车间盖楼,十多年也不盖,一大片地就那么空着。高云白他一眼,说,你盼它拆掉啊?王进山闷闷地说,有一个单口相声,说的是夜里楼上把一只鞋扔在地板上,楼下的人等啊等,等他扔另一只,楼上就是不扔。高云说,你就是楼下那个人,我知道你,你不是盼他扔,你是怕他扔。王进山说,也不是,鞋扔了,也就死心了。
高云说,别啰嗦你的五车间,说句痛快话,你烦我不?王进山脸红到脖子上,闷声闷气地说,我没说烦你。
他怎么会烦她呢,他从来就没烦过她,要不是春刚,他说不定会娶她。不到三年,高云和春刚脚跟脚出了徒,那当然是名师出高徒,她们也像他一样屁股上挂着钳子扳子螺丝刀,像他那样晃晃当当走路,像他那样解决车间和厂里的疑难杂症。高云本来有机会去长春一汽,不知道为什么她没去,结婚不到两年她就离了,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婚,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带着孩子自己过。这么多年,五车间流传很多涉及她的花花事,但是谁也没见过那花花事里的男人。
高云放下酒杯,说,走,跟我去打车。
夜晚的五车间不再灯火辉煌,看着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黑洞洞的窗子就像野兽的眼睛。两人一脚高一脚低地围着车间绕了两圈,高云问他,总装设备和机加设备怎么都没了?王进山说,让他们卖了。高云说,不看了,难受。王进山说,告诉你,地上的五车间是没了,地下还有一个五车间,五车间地下的管道能绕全城十圈。高云说,一百圈也得卖掉。王进山索然地说,不想看你就回去。高云由悲转喜地说,你的意思是不让我回去?王进山盯着她不吭声,高云看到了一口白牙。
在床上,高云拥着王进山说,我是不是做梦?王进山说,做梦?人要总是在梦里就好了。高云说,你真不嫌我老啊?我五十了。王进山说,要说老,我比你还老。高云说,你是男人。两人再不说话,话都用行动替代了。
高云把一条光腿搭在王进山身上,意犹未尽地说,大王,我城里有楼,两小室,你若是同意就搬过来。王进山想也不想地说,不去,想搬你搬过来。高云说,烂草丛,烂泥坑,我搬过来,你让我喂蚊子啊?王进山说,怕蚊子有驱蚊香,车间院子里艾蒿比人高,那东西熏蚊子最好用了,比驱蚊香还顶用。高云说,蚊子咬也罢了,这里不能上网。王进山说,上网干什么,找老头啊?五车间传你不少花花事,你有没有他们说的花花事啊?高云说,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我倒宁愿有,死了也不冤枉。姓王的,我过年就五十了,走到这一步你还拿捏我。王进山说,我真不是拿捏你,我还要看着这房子呢。高云腾地站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蹦着说,王进山,你就死在五车间吧。
又过了一年,五车间还是没拆,王进山还在这里看着这座空房子。拆是没拆,显达公司在这里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工地。看样子五车间还是要拆。一个雨天,骚猴子又来了,带了一瓶白酒两只猪脚。喝酒时,骚猴子说,娘的,一看那狗牌子老子一点胃口没有。王进山明白他说的是显达那牌子,说,没胃口你喝酒。骚猴子说,五车间要是拆了,462路站点还叫五车间么?王进山说,不叫五车间叫什么?骚猴子说,保不定就不叫五车间了。王进山说,只定叫五车间,叫别的,谁能找得到啊?骚猴子说,你又犟,犟一辈子了还犟。王进山闷头喝酒,再不说话。骚猴子说,想起以前的五车间,血都往上涌,你说怪不,我现在总想以前的事,越往前的事,越他娘的记得清楚,眼前的事却一点不记得。你说,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没过好?厂子黄了,白米饭也吃腻了,楼高了,人也懒了,我他娘的也越来越迷糊了。
骚猴子比王进山晚几年进厂,年纪却比他大几岁。王进山看着骚猴子,人没回忆就成傻子了,不光骚猴子,人都活在记忆里,他王进山也一样。就这么一年,骚猴子老了,骚猴子成了真正的老头子了,原来那股骚劲剩得差不多了。
高云再没来找他,把手机也关掉了。骚猴子说,高云又去沈阳了,儿子在沈阳给她找了个老伴,那老头六十五,比高云大十五岁,是金杯集团的高工,退休还开五千多呢。这女人找来找去,还是找个造汽车的。高云生了个鬼精儿子,给老妈找老伴,轻松把老妈蹬了。王进山说,精个屁,老妈老妈,老妈就是老妈子,我看他不精,他傻。
那天夜黑,五车间突然来了两个人,他们是开着一部带挂卡车来的。开车那人给王进山递了一支烟,说,老哥,我是骚猴子的表侄,有个事和你老商量。王进山说,你说你说。那人说,显达公司就要扒房子了,明年就要在五车间起楼。王进山听出那人话里还有话,说,有话你就说吧。那人说,这房子里的破烂显达肯定不要,地里埋着的破铁轨,还有那烂车床,你老合几个钱小侄我拉走。王进山说,合几个钱?那人说,凭你说。王进山说,一分钱不要。那人惊喜地说,那我拉走了。王进山说,那可不行,这地方一块砖你也不能动。那人说,这里早就不是五车间了,显达不会要这些烂铁块子,他们要的是地皮。王进山说,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那人说,你老真是死心眼,你就是一看堆的,管那么多干吗。另一个人说,显达给你多少钱?一千还是两千?你说个数。说话时那人掏出一打钱,都是一百一张的新票。王进山斜眼看着那打钱,那两个人也不错眼珠地看着他。王进山说,我说过,一分钱不要。那两个人明白碰上犟眼子了,后说话的那人笑笑,把钱收起来,说,那算了,不麻烦你了。
两个家伙走后,王进山愤愤地骂起来,骚猴子,打起五车间主意了。又给骚猴子打电话,骚猴子说,他们骗你呢,外甥我有,我哪有什么侄子,我从出生就是独哥一个。转转眼珠子,又说,五车间谁不知道?黄摊子了也人人都知道,你也是犟眼子,破铁块子,卖也就卖了,当酒钱了,你还当那是你的五车间啊,不是了,那地方现在是显达公司。王进山啪地放下电话,心里说,显达就是个屁,老子宁可不喝酒!
王进山一万个没想到,高云和春刚都喜欢他。先前她们还有些看不起他,后来她们发现,厂子里出了什么疑难杂症都找王进山,王进山就像专治疑难杂症的老郎中。这家伙不光技术好,干起活也特潇洒,摔摔打打的,叼着烟卷,眼睛眯眯着,心不在焉似的,手里的活却是又快又好。王进山篮球也打得棒,五车间篮球队从来都是全厂的冠军。
满徒之后,高云和春刚都留在了维修班。这两个女子,一个蔫,一个浪。一个总是甜甜地喊他师傅,另一个很少喊他,却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说,钳子,她就递他钳子,他说扳手,她就递他扳手。这另一个就是春刚。和高云比起来,春刚就是一个闷屁,和她待上一整天,也听不见她说一句话。
王进山还是让春刚闷住了。春刚平时不声不响,那年春节加班却放了一个响屁。午夜时食堂给大家加餐,书记说,你们是不是五车间的,就这么闷着头过年啊?骚猴子说,书记带头,你给大伙唱一段。书记说,我嗓子比脖子还粗,我给你们找一个人替我唱,春刚啊,你来唱一段。书记这么一说,工人们都起哄,书记是乱点鸳鸯谱,大伙偏就喜欢这样乱点鸳鸯谱,谁叫人家长得好技术也好呢。想不到起哄声中,春刚站起来了,只听她唱道:
小路的李子树刮破了裙脚,
姑娘手舞足蹈往家跑。
过了石桥锄头掉在河里她也不知道,
只是一个劲地往家跑,
姑娘的心事谁也猜不着。
这女子唱的是谁?是她自己吗?看她那亮晶晶的眼珠子,那红扑扑的脸蛋子,她是唱她自己。春刚的嗓子不好,还有一点跑调,可她这么一唱,把王进山唱傻了,也唱明白了,穿着16号工装的春刚,在王进山眼里一下子变成了女神。
和春刚结婚是在“五一”,高云没来,骚猴子说她去沈阳了。不过新房却是高云帮着收拾的,新房里挂满王进山和春刚的奖状,那幅结婚的大照片,也是高云逼着他俩照的。那天工人们都来闹洞房,骚猴子拉住王进山说,大王,你小子喜上加喜啊,五一节,入洞房,好事都让你占了,说,你是不是五车间的?王进山说,废话。骚猴子说,五车间的人都是狠家伙,夜里你猛劲干,干得狠生小子,生不出小子你就不是五车间的。
不用王进山发狠,春刚比他还狠,夜里一上床,春刚的两条白腿就把王进山箍住了。从此以后,白天,王进山是春刚的师傅,夜里师傅成了丈夫,只要到了床上,春刚的两条白腿就会箍上来。怪不得白天话少,这女子把劲都留在晚上了,她是人蔫心不蔫啊。王进山高兴春刚这么箍着他,高兴是高兴,时不时地他会想起一个人,那人是高云。高云和他在一起会是什么样,也像春刚这样拿腿箍着他么?想到高云,王进山会狠狠骂自己:王进山,你娘的骑着马还找马,你就是一牲口。
五车间墙外,厂子盖了几趟平房给职工当宿舍,拨了一间给王进山和春刚,儿子就是在平房里出生的,现在,平房里的住户都搬走了,没有住户,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都给掐了。
干得狠果然生小子,而且是当年媳妇当年孩。王进山给儿子起名叫黎明,和厂子同名,那时候职工们都这么给孩子起名,什么李建设,王卫星,刘跃进啦。黎明九岁还不会说话,走路也东倒西歪的。卫生所查不出毛病,市里的医院也查不出毛病,高云说,去沈阳查,我表哥在中国医大。厂子给王进山派了一辆吉普车,王进山抱着黎明,春刚和高云跟着去了沈阳。诊断很快就做出来了,黎明是智障,医生说,九岁的黎明只有一岁的智商。
春刚哭成了泪人,她哭,高云也跟着哭。
黎明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五车间,长到十七岁没离开过五车间。五车间的院子是黎明的天堂,书记特许一条,小黎明可以在五车间院子里玩。五车间的工人们都认识黎明,黎明也认得五车间所有的职工。黎明不会说话会笑,谁喊他的名字他都笑。骚猴子和钳工班的人给黎明焊了一辆三轮车,黎明骑不了两轮的自行车,只要出屋子黎明就会骑着三轮车去五车间,黎明不光是王进山的儿子,黎明也是五车间的儿子。
骚猴子又来了,一照面就说,想不到我还真有一个八竿子打不到的侄子,这包玉溪烟就是他孝敬我的。说着话,把玉溪烟撕开,扔一支给王进山。王进山说,那天来的就是他吧?骚猴子说,不是他,是他朋友,他让我捎话给你。王进山说,什么话?骚猴子说,五车间那些破烂让他拉走,他打一万块钱给你。侄子答应骚猴子,事成之后,另外打给他两千块。两千是个什么概念?可以给儿子交半年社保了,还能余下点烟酒钱。
骚猴子说,我侄子不敢骗我,你同意,钱先打你,一万块啊,有这一万块,满天下找黎明也够你用了。王进山听得一怔,心也咚咚跳起来,骚猴子知道他的痛处,骚猴子专捅王进山的痛处。
黎明不到十六岁时春刚得了胃病,一年以后,黎明失踪了,春刚的胃病成了胃癌。
骚猴子走前放下一句话,成不成你都给我个电话。如果这时候高云在就好了,王进山愿意和高云商量这件事,普天之下没有怕钱咬手的,一万块,的确不少了,一万块到手他就去找黎明。五车间就在他眼皮底下,这座空房子他说了算,显达公司要的是五车间的地皮,他们不要五车间,那些烂砖块子烂铁块子烂车床都不要,现在,那些烂东西属于王进山,只要他开口。那帮人就等着他开口。
五车间归显达公司那天,公司一个副总找到王进山说,老王,你是老王吧,我们需要一个看院子的人,你给我们看院子吧,一个月给你开一千块。王进山说,我还没到退休年龄,为什么让我看院子?那个副总说,不看院子,你就回家。回家,回家不就是退休么?若是回家他和五车间就一点瓜葛也没有了。王进山问,这院子要闲起来么,不生产汽车啊?副总说,我们不生产汽车,我们什么也不生产,我们只管盖房子,这里要盖高层。
王进山没回家,他成了五车间的更夫。
骚猴子等了一个月也没接到王进山的电话。那天,等不及的骚猴子把电话打给王进山,他打了一天,王进山手机一直是忙音。骚猴子气得摔掉手机,狠狠骂道,王进山你个犟驴,你就是个犟驴。
王进山没骚猴子说的那么犟,可是他就是打不了那个电话,把骚猴子电话忘记就好了。怪了去,他的记忆越来越差,脑子里却忘不了骚猴子的手机号,那一串号码像蚊子一样在他脑子里嗡嗡乱飞。
寻找黎明的传单贴遍了大半个东北,黎明还没找到。有一天,城郊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死尸。王进山扶着春刚跌跌撞撞赶了过去,看到那具尸体,他腿一软,一下子跪了下去。那人眼睛都烂没了,只剩两个黑窟窿。但那个人不是黎明,警察很快做出结论,根据骨龄判断,那是一具老人的尸体。
王进山明白,黎明不会回来了,黎明一定死在了他乡,这年头一个智障活得下来么?
那具尸首让春刚魔怔了,她认定尸首就是黎明,她说,头冲着五车间,黎明是想回家。自那以后,厂子给她办了提前退休,她从来不出屋子,成年累月穿着那件16号工作服,胳膊套着套袖,手上戴着白线手套,就像上班一样。再后来,她死了。
自从当了五车间的更夫,王进山不再回家,对他而言,家就是五车间,五车间就是家,睡到哪儿他都是一个人。每天他都搂着一条木棒睡觉,这一晚,王进山把木棒扔掉了,他在心里说,五车间跟我有什么关系,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偷吧,抢吧,卖吧,老子不管了,老子睡觉。蒙蒙胧胧中他做了个梦,梦见黎明回来了,可是黎明找不到五车间了,五车间被大卸八块,夷为平地了,王进山一下吓醒了,睁眼一看漆黑一团,他被人蒙住眼睛,手和脚也被捆住了。他想,我得罪谁了?随即他听到汽车马达声,还听到车间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王进山明白,有人来偷五车间了。
有人来偷五车间了。手和脚动不了,身子还能动,王进山像鱼一样一打挺坐起来,他拿牙咬绳子,嘴被他咬出了血,绳子终于让他咬断了。站起来的时候,他差一点跌倒,但他没忘顺手抄起那条木棒。他悄悄躲在一个角落,眼前的一幕让他呆住了——那台车床已经被装到卡车里了,十几个人正在挖地上的铁轨,铁轨痛得吱吱呀呀乱叫。血一下涌进了王进山脑袋。
他拎着棒子走过去,冲着那帮人吼道,谁让你们来的,都给我住手。
先头,那帮人惊呆了,后来发现就他一个人,就把他围起来,围是围起来,没有谁真敢下手,这边一个,那边一伙,两边都僵着,其实他们都是带了家伙的,锹镐撬杠都在手里攥着呢,那都是致命的铁家伙。领头的正是那天开车的人。他一看这样不行,这么僵下去事情就泡汤了,冲上去就是一棒子,他一下手,就都下了手。王进山只觉得被冰凉冰凉的什么糊住了眼睛,再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帮人看着打死了人,一个一个跳上车跑了。
在沈阳,金杯那个退休高工约高云第二次见面,老工程师花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对高云印象不错,这女人真是个女人。话没说一句,高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骚猴子打来的,他说,高云哪,你快回来吧,王进山出事了。
医院是区里的医院,区医院收费比市医院便宜。
天亮时,王进山被蝈蝈叫醒了,摸了摸头,他摸到一手黏糊糊的东西,眼睛看不到,心里明白那是血,也明白他还没死。手机还在身边,他挣扎着打了120,只说了“五车间”就又死过去了。
现在,王进山躺在四人一室的病床上,满脑袋缠着绷带,腿上也打了石膏,他左腿折了。他睁开眼睛就看到高云。王进山说,你怎么来了?高云说,废话,我怎么就不能来?高云打开一听罐头,喂他吃桃子。王进山爱吃桃子。高云说,显达公司送来五百块钱,还让你留着医药费票子,公司给报销,我把票子替你收好了。又说,现在给钱,以前是给奖状,以前,发你一张奖状你就不知道姓啥了。王进山说,以前的人都傻。高云说,一个傻,两个傻,都傻?王进山说,别说那些了,我问你,钱是谁送来的?高云说,骚猴子,骚猴子报案了,警察抓走了他侄子,显达公司也是骚猴子找来的。王进山说,你怎么知道的?高云说,骚猴子悔得想撞墙,他不敢见你,给我打的电话,他侄子是显达公司的保管。王进山说,到处都是内鬼啊。高云说,你是真犟啊,命值钱还是那些破烂值钱?又不是你家的,你管他内鬼外鬼?
王进山说,不管了,管也管不了,你不是找老头了么?高云说,帮我拿主意啊?正想听听你的意见呢,说吧,你啥意见?王进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想嫁你就嫁。高云点了他一下,说,嫁你个腿。王进山说,我现在可真就剩一条腿了。
王进山从医院回来那天,显达那个副总又来了,他对王进山说,过几天我派铲车来这里平地,然后挖地基盖房子。我看你这人挺踏实,你若是同意,你接着看工地,月薪给你涨一千,加上先前那一千你就开两千了。
王进山说,铲车来,我就不干了。副总说,为什么不干,你怕钱咬手啊?王进山说,这几天我还干,还是那话,铲车来我就不干了,你另外找人。副总奇怪地看着王进山,王进山明白他是啥意思,他的意思是王进山不识抬举。
隔不几天,几辆大铲车开进五车间,几个司机跳下来围着五车间转了一圈,踢踢这儿,踢踢那儿,又跳上车开走了。王进山明白,五车间这样的耐火砖,一般的铲车铲不动,这种耐火砖得用炸药崩,一般的炸药还不行,得用强力炸药。
那几天王进山一直胃痛,腿也痛。那天早晨他拄着木棍出来晒太阳,听说晒太阳补铁补钙。从462路站点走过来一个人,那人摇摇晃晃向五车间走过来。他觉得那人眼熟。王进山拿手遮着眼睛问自己,这是谁啊?很少有人来五车间了。
那人走到他跟前突然站住了。
是黎明。
王进山脑袋轰一下子炸了。
黎明是靠记忆找回来的,他先是想起了五车间,他对民政局的人比画着说,五车间有那么高,他拿眼前一幢四层的高楼比画着,他还做出游泳的姿势,意思是那地方有个游泳池。接下来他告诉他们,那地方生产大客车,他指着马路上的公汽比画。他又告诉他们,那地方是汽车站点。想到五车间,想到大客车,黎明的记忆一下子复苏了,他还在五车间放过风筝呢,五车间外面有好大一块空地,最后他竟然神奇地写了一组数字462,黎明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回了五车间。
黎明变了,他不再是小伙子模样,胡子老长,头发乱得像团草,身上是一处一处的伤,有的伤还青着,有的伤结了痂,痂上又结了疤。黎明还是不会说话,但他会比画,只要他比画,王进山一下子就明白。问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却不会比画。
黎明穿一套破烂工装,看着就像一个刚刚干完活的车间工人。
显达公司很快拉来一车强力炸药,一整天,他们围着五车间打眼装药。他们走到哪儿,王进山像头瘸狼一样跟到哪儿,他想,炸吧,老子就当这是在做梦,要炸你炸,炸没了,我还有黎明。
黎明摇摇摆摆地跟着他,也像狼一样盯着打眼装药那些人。
骚猴子最后一次来,看见王进山,啪啪抡了自个两记耳光。王进山说,你这是干啥?骚猴子说,我他妈的不是人,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要不是我,你折不了这条腿。王进山骂道,你他娘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从小卖店买了两袋散装白,喝酒的时候,骚猴子看着黎明光喝酒不说话。王进山说,你就来这儿喝闷酒啊?骚猴子说,大王,黎明是不是你儿子?王进山说,当然是。骚猴子说,你有几个儿子?王进山说,废话。骚猴子叹了一口气,说,你还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啊?你这个人,只为你自个儿考虑,从来不为黎明考虑。
王进山气恼地说,来这儿说混话,我怎么不为黎明考虑啦?骚猴子说,黎明二十几啦,二十七二十八了?王进山说,二十八虚岁。骚猴子一拍桌子,说,你还知道黎明二十八了,明白吗,你和你儿子缺个女人!王进山脑袋一下子大了。骚猴子又说,五车间眼看就没了,你还守个什么劲儿?趁这机会,把五车间那些没挖出来的烂铁块子折腾出去,去乡下给黎明找个闺女,也算你当了一回老子,人家高云也等着你呢。
眼前的骚猴子越来越模糊,看着不像骚猴子,像一团雾,黎明却是越来越清晰,王进山看得清儿子那硬硬的胡茬儿,黎明二十八了,黎明可不是二十八了?
不光骚猴子,第二天高云从沈阳打来电话,她说,王进山,你到底是啥意思?王进山想,高云是要他口供呢,忽地想起骚猴子缺个女人那句话,答说,你不是又去沈阳了么?问我啥意思,啥意思你知道。高云说,我不知道。王进山心说,我真就等着你呢,我碰上了难事等你商量呢。嘴上却硬气地说,你不就是要口供么,老子又没去沈阳,别看折了一条腿,人还在这儿戳着呢。
高云骂道,屁口供,你等着,回去我打折你那条腿。
责任编辑 李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