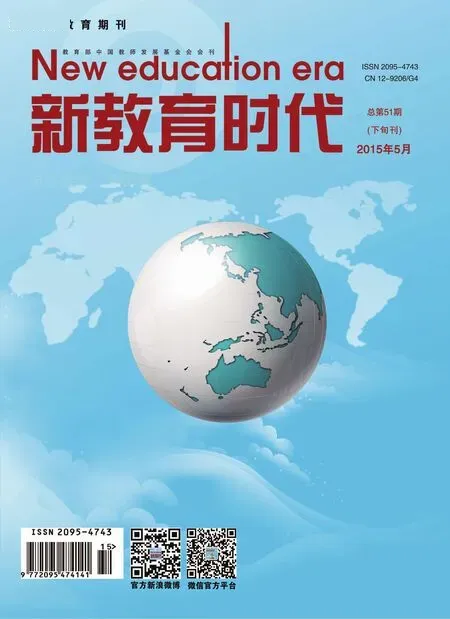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
——论《憩园》中对生命的悲剧意识
崔玉婷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
——论《憩园》中对生命的悲剧意识
崔玉婷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巴金先生创作出的中篇小说《憩园》是来源于对于生命的悲剧意识,它描述的是一个以憩园为背景的俩个家庭的悲惨命运,由一局外人的视角结构全篇,其中的叙述结构时空交错。巴金先生到了创作后期,热烈的追求过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信仰之后,倍受打击,战斗激情消退,开始成熟、理智的看待整个社会,敏感的洞察人性、人情,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抚慰人心,悲悯苍生,去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
巴金 悲剧意识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写道:“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除了受难而外,我们又如何能转向自己而获取到深思的意识呢?”巴金先生创作出的中篇小说《憩园》正是来源于这一点,它描述的是一个以憩园为背景的俩个家庭的悲惨命运,由一局外人的视角结构全篇,其中的叙述结构时空交错。整部家庭剧像是个隐匿着的有关于伦理道德、家庭教育、民族兴衰的多线启示录。巴金本人的对于生命的悲剧意识也在小说中尤为突出。
巴金先生始终是一个充满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的作家。他的所有大多作品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氲氤与难以排遣的来自灵魂深处的伤感。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一些作品中,尽管表面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奔放的叙事激情,但透过这些,那种压在深处的悲悯和伤感成分依然浓郁。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先生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艺术转折,他渐渐褪去早期的一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进人物的灵魂深处,以普通百姓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正如《憩园》中姚诵诗评价黎先生“尽写些小人小事”,但他的悲悯与伤感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他的艺术传达,并非基于自身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而是源于他内心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而《憩园》中姚太太与黎先生的好多关于创作小说的对话都暗中揭示着巴金本人的创作感情:“我总是这样想,写小说的人都坏的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然一个人的肚子里怎么能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一个人的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巴金先生似乎尤为擅长悲剧情节的设置,悲剧蕴含着的是独特的审美价值:教化与解脱。将整部《憩园》的主要悲剧片段分别梳理如下。
一、杨梦痴的灵魂堕落
杨梦痴因吃喝嫖赌而倾家荡产,面临公馆被卖时坚决拒绝,却遭到兄弟、儿子及妻子的反对,骗走妻子全部嫁妆又与“小五”婚外情被发现,屡教不改,终于与大儿子决裂,无家可归。后沦为小偷,病死牢中。他本是个恶人,放着好好的家不顾非与外面的女人“小五”藕断丝连,彻夜不归。这种情况下妻子的次次原谅、小儿子寒儿的频频照顾,他仍不为所动,不改恶习。可巴金先生笔下的杨梦痴又受人怜悯,原因在于作者本人的情感倾向的引诱。他偏偏给杨梦痴设置了山茶花的情节,寒儿摘来了山茶花,杨梦痴久久凝视、深情不减。面对这种种变故,他无力抗拒,一边是继续堕落,一边又深深自责。但一步错,步步错,写好的命运难以更改。当他落魄街头,兄弟路过看见又视而不见,形同陌路。他昔日情人“小五”已嫁做人妇,寄来钱以周济也显得讥讽。最后的悲惨结局令人心生怜悯。
二、小虎的误入歧途
一定意义上小虎和杨梦痴是有一定联系的,他们就像是一个循环圈,小虎则是步杨梦痴的后尘,自小学会赌博,因生母去世的早,受父亲疼爱、外婆溺爱,他盛气凌人的对待一切。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和亲人的溺爱错误的引导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导致其误入歧途。但作者倾注在小虎身上的情感并非引起同情而是包含家庭教育。这一创作灵感与巴金离开的18年的故居有关,故居已几易其主,物是人非,但照壁上的“长宜子孙”依然如故。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为什么我们的子孙会频频遭遇次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及子承父业的传统。这使得孩子们一来人格不健全,二来创造财富的能力有限。而他最后河里淹死的悲惨结局也让人为之一颤。小恶棍年少身亡本是大快人心,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这可以说是个人命运的悲哀,也可以说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道德教育的悲哀,发人深省。但话说回来,这一深刻的哲理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述,出自杨梦痴之口,他说“我到现在才明白,不留德行,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这许多年我真糊涂。”糊涂的人得到清醒的认识为时已晚,糊涂的人得不到清醒的认识酿成大悲。
三、万昭华的清醒与无力
万昭华是姚诵诗的第二任妻子,夫妻感情很好,为人善良贤惠。可以说作为传统中国女性,她是典型模范代表,但不可忽视的是她带有先进的现代思想。比如,她是最早意识到小虎的家庭教育缺失的严重后果,并尝试尽力扭转小虎命运的人。也是改变黎先生悲观思想的先进女性。巴金先生在《寒夜》中写的曾树生同样具有着现代女性特征。她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二人有着相同点,但区别在于,万昭华早早放弃了追求新事物,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丈夫、家庭当中。在整部小说中,她是光明的、温暖的,像太阳般的存在。她说“同情、爱、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但她也清楚的意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她说“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又能够做什么呢?我还不是只有等待。我对什么事都只有等待。我对什么事都空有一番心肠。”在那个封建社会中,的确的,一个女子能做的杯水车薪。万昭华的抱负只有黎先生读得懂,那些苦闷与彷徨把她圈制在封建家庭的牢笼中,读得懂也救不了。
小说娓娓道来的讲述着俩个大家庭的故事,其中隐含着的悲剧主题揭露着整个社会的悲剧式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暗示着巨大的秘密,当一个社会走向衰落,必定会有一个新的社会开始崛起,那就要研究小说的结尾,小虎的意外身亡并非结束,姚氏夫妇的新生命即将出世。它是给人希望的。而且小说结尾,姚诵诗看过《吾儿不肖》后倍受感动得以觉醒,那么新生命之后的命运可想而知,必定会有美好春天。一个大的悲剧结束了,巴金先生还要给人希望让人期待。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巴金先生到了创作后期,热烈的追求过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信仰之后,倍受打击,战斗激情消退,开始成熟、理智的看待整个社会,敏感的洞察人性、人情,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抚慰人心,悲悯苍生,去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