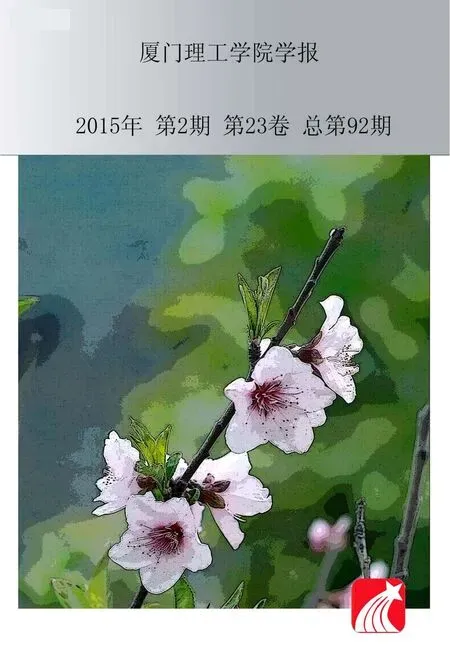从《男人还剩下什么》看毕飞宇小说的男性立场
贺 思,吴培显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从《男人还剩下什么》看毕飞宇小说的男性立场
贺 思,吴培显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在被称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的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中,也有一群平庸无为的男性形象。短篇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是他关注男性生存状态的特写,是他创作中的沧海遗珠,以独特的价值展示着他对于男性生存现状的探究。一方面,他通过对男性形象感情世界的挖掘,展现出当下男性感情世界“失语”的状态:爱的能力与人性纯真的丧失,雄性力量的失落;另一方面,他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和反讽调侃式的个性标识语言,表现男性主体精神。同时,他又在一定上超越了男性立场,让读者感受到男作家的特质以及普世的人文关怀。
毕飞宇;男性立场;异化;人文关怀;《男人还剩下什么》
毕飞宇的小说题材甚广,从早期的历史题材到乡村再到城市题材的转变,是毕飞宇思考一步一步深入的过程。纵观其创作历程,最让人交口称赞的是他塑造了丰满立体的女性形象的作品,如《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玉秀》等 ,毕飞宇因此也被认为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但他自己并不以为然。“说我是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我实在不敢当,这是在夸上帝,我认为只有上帝才了解别人,更不要说男人了解女人。”[1]他认为保持对女性、对男性,包括对生活无知的状态,莽撞一点反而比较有意思。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探究的愿望和勇气。毕飞宇也说过自己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是学界对毕飞宇小说中的女性研究一直热度不减,而对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则缺乏关注。殊不知作者在男性形象中注入了深刻现实思考,其中发表于1998年的短篇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2]可以说是毕飞宇创作中的沧海遗珠,它不像其他长篇引人注目,却以独特的价值展示着作者对于男性生存现状的探究,以及作者鲜明的男性立场。
一、内容创作中的男性立场
很难说性别意识对作者的影响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的创作是无法做到绝对客观的,其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总是受到自身经验、情感的影响。毕飞宇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在创作中难免也会流露出男性主体立场。《男人还剩下什么》是作者唯一开篇点题,直指男性生存现状的作品,探究男人究竟还剩下什么。文本以此为切入点对毕飞宇部分小说展开分析。
(一)爱的能力丧失
毕飞宇是一位情感型作家,他多关注人物的情感世界,尤其是通过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挖掘背后隐藏的情感。短篇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讲述了“我”因一时冲动拥抱了一个女人,被妻子发现后赶出家门,与之离婚,女儿也离自己而去的故事。这是一幕富有意味的家庭剧,剧中人物只有男人、女人、另一女人(阿来)、女儿。人物形象的抽象化、概括化,既使得小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又使小说专注于人物情感的展现。小说中的“我”以一种自嘲似的口吻,展现了自己一无所有的无奈处境。其中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丧失了爱的能力。小说中的夫妻是典型的中国式婚姻的产物,由人介绍,相亲,再到结婚生子,这是一个标准的流程。对于爱,“我”没有提及,只是觉得这样过下去也还不错,可是对于阿来,“我”却坦言“爱过她几天”,这说明“我”年轻时至少有爱的冲动,虽然那份爱并没有什么结果。而现实的家庭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爱做补充,趋于平淡,“每天一个太阳,每夜一个月亮”,日复一日的重复。所以当阿来突然示好出现,“我”被“一团复燃的火焰”驱使着拥抱了她,而这成为了婚姻破灭的导火索。平静的生活磨灭了爱,以至于主人公仅仅因为曾经爱过几天的人便难以自持,犯下了错,而这是妻子所不能容忍的,在激烈的争吵过后,两人离了婚。而后妻子又利用女儿向他开战。从夫妻关系上看,他们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但多年的相处不至于一点感情也没有,可为什么离婚后妻子要向丈夫报复呢?如果说是由爱生恨,那么爱体现在哪里?妻子从看见丈夫拥抱阿来之后,第一反应是让他滚,不肯听解释而且坚决要离婚。如果有爱的话,不该这么不留余地,并且残忍地利用女儿来达到报复的目的。在这里,妻子更注重的是她的脸面和自尊。作为市妇联最出色的干事,她习惯了对人颐指气使,也不能容忍这种伤她自尊的事,她认为男人的行为已经破坏了他们关系的“纯洁性”,是男人背叛了家庭,那么之后的报复就是其咎由自取了。男人的一无所有是妻子所乐见的,可他的犯的错是否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这不得而知。但从作者的态度来看,对于妻子的做法却是不赞同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连最后一点爱的火苗也消失殆尽,流言将他置于受谴责的地位,而他也压抑着自己的人性本能。
除了爱情的失落,还有对血缘亲情之爱的无力表达。离婚之后,主人公“我”突然发现心中空下了一块,那便是对女儿的爱。于是“我”低声下气地向前妻求得了见女儿的权利,只是和女儿的相处并没有填补心中的空白,女儿对“我”又警惕又防范,买吃的给她,她吃坏了也不吭声,沉默以对,父女之间的陌生、隔阂让人心寒。归因于前妻对女儿的洗脑。她把对丈夫的怨恨向六岁半的女儿发泄,说她的爸爸不可靠,说她的爸爸对别的女人耍流氓……小孩子还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当听到她妈妈这么说的时候,自然就接受了这一观念,从而将爸爸隔离在外,甚至冷淡、仇视。孩子被夹在夫妻之间,成了妻子向出轨丈夫报复的工具,孩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不准接受爸爸的关爱,在妈妈的怨气下胆小沉默着,虽然表面上听话乖巧,可心里却受到了沉重的伤害。小说中“我”气急败坏的一句“你对我女儿干什么了?”可以看出一个父亲对女儿失去活泼天真的天性的痛惜,和对自己无法弥补女儿创伤的深深自责。他爱自己的孩子,可面对这样毫无生气的孩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对她的爱,这是身为父亲的悲哀。
在毕飞宇塑造的男性形象中,出现了一类小男人形象[3],他们是女人背后的男人,在婚姻家庭中丧失了主动地位,爱人的能力也变得贫乏。除了《男人还剩下什么》中的“我”,还有《家里乱了》中的苟泉,《青衣》中的面瓜,《生活在天上》中的大儿子甚至宣称“结婚是什么?就是找个人来平分你的钱, 生孩子是什么? 就是捣鼓个孩子来平分你余下来的那一半钱”,“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只要有钱,夜夜可以当新郎。”传统的家庭亲情被世俗金钱所代替,感情变得一文不值。作者通过对这一男性形象感情世界的挖掘,展现出了当下男性感情世界“失语”的状态。爱是人的本能,而消磨了他们爱的能力的是生活,生活的重重压力,日常琐事;是社会对人的异化,社会向前发展,物质文明高度繁荣,个人欲望膨胀,但精神文明却无法与之适应,于是精神危机也就出现了。
(二)雄性力量的失落
《男人还剩下什么》是毕飞宇众多作品中尤为特别的一篇,它与《玉米》《青衣》等作品中所反映的男强女卑社会观不同,展现出新时期以来男性所特有的雄性气质在社会中不断消褪,而女性却表现得越来越强势,丧失了女性特有的阴柔之美的社会现象。《男人还剩下什么》则是他有感于男性生存境况的变动而反思的结果。小说中的“我”不再是传统中的一家之主,而是“副家长”,在与妻子的相处中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妻子说离,“我”毫无办法只得离;妻子掌握了对女儿的所有权,她决定着“我”能不能见女儿一面,为了见女儿,“我”无奈的满足了妻子报复的快感,在她面前骂“阿来是个狐狸精”,“我”对于妻子的报复有心无力,女儿是唯一的寄托,可是连女儿也受妻子的控制,最后“我”的确如妻子所说的“完了”,一无所有。对于这样一个软弱的男性形象,作者是既同情又批判。他被妻子所代表的强权所压倒,处于一个“被欺辱”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作者是抱有同情的。但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丧失了积极反叛的精神,面对欺压,他一味忍让,没有试图为改变现状而奋起努力,在他的血液里已经没有了作为男性应有的血性,这又是可悲的。莫言是毕飞宇最欣赏的作家,毕飞宇对当下男性丧失了雄性力量的反思与莫言的《红高粱》中“种的退化”的主题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当男人变得不像男人,女人变得不像女人,那么就得反思这个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90年代以来,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种新观念、新事物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在拓宽人们视野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消解了人们的精神结构。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来看,男权思想早已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新文化运动后,男女平等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但男性仍然在社会中占着主导地位。可在《男人还剩下什么》中,却展现了一个懦弱的丧失男性原始生命力的形象,女性反而有压倒男性的趋势,这原因可以从两点来看:首先,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入,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自主意识增强,而社会上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的现象,出于对这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反抗,女性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施展拳脚,展现出与男性相抗衡的态势。小说中的妻子就是市妇联最出色的宣传干事,她熟知宣传技巧,对女儿宣传父亲的出轨,让女儿疏远自己的父亲,对邻居、同事、朋友、亲属宣传,让男人陷入丑闻的舆论中,被人看笑话。她一系列的报复措施的成功更加凸显了丈夫的无用软弱。实际上,女性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拨,是对自身力量的一种认可,由于长期处于男权的阴影下,女性习惯了对男性的屈从,然而当她们切实了解了自身的优势和力量后,便能实实在在地顶起半边天。小说中妻子的强势无可厚非,女性表现得越来越有能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而男性变得越发弱势才是反常现象。其次,雄性力量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男性精神的失守。属于男性独有的阳刚之力,拼搏精神被生活所消磨殆尽。《家里乱了》中的苟泉为了在城市中扎根,执着地寻找是城市户口的对象,在妻子身为城市人的优越感之下委曲求全,连妻子在夜总会当“小姐”也不敢指责,身为丈夫的尊严尽失。在毕飞宇都市题材的小说中,众多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权利的化身,他们执着于金钱、权利、欲望的满足,而又被它们所控制,精神上一片荒原。如《遥控》中的那位肥胖的成功人士,他居住在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一只电视遥控器、一只影碟遥控器、一只音响遥控器、一只空调遥控器,外加一部大哥大”,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用这些遥控器操控着自己的人生。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被扒去五脏六腑的生命”还能够表现得如此休闲、雍容,“实在是一种大恐怖”。精神上的空虚,使人的生活变得麻木,今天重复着昨天,完全消解了生命的意义。《男人还剩下什么》中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阿来的出现,他会和妻子平淡如水地生活下去,不会反省自己还剩下些什么。精神上缺乏追求,生活也就没有了动力,正如逆水行舟,不求上进那么自然就退步了,与妻子强烈的控制欲相比,男人当然显得软弱无力。总的说来,无论是女性的强势还是男性力量的衰弱,都是现代社会压迫的结果,迫使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动来适应异化了的社会。作者凭借“睁大眼睛睡觉”的清醒的自知和洞察力,在作品中将这些现象进行了艺术的放大和强化,向男性敲醒警钟,如果他们仍固步自封,不重新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么他们所拥有的将所剩无几。这里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
(三)人性纯真的丧失
当然,如果只把眼光放在对“男人还剩下什么”的关注上,那么解读这篇小说肯定是不到位的。作者不仅仅通过《男人还剩下什么》反思当下男性生存境况,还有更大的人文关怀,即对整个人类人性纯真丧失的惋惜。社会的向前发展总要伴随着某些代价的付出,反映在人性方面则是人的诗性生存与原初的纯真已经逐渐丧失而被卷入一种世俗的、经验的和缺乏想象力的状态。
作者由早期的对历史的追问转向对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通过对一系列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的描摹,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原始人性的消退。《男人还剩下什么》是作者都市题材中代表性的一篇,作品不仅明确地提出“男人还剩下什么”的问题,还提出了人类应该如何诗意地在这个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中生存的问题。社会越进步,物质越丰富,然而人的精神却越贫乏,人们常常热衷于欲望的追求,最终也沦为欲望的奴隶,被异化,被人性中的“恶”所吞噬,作品中的妻子便是这一典型。她缺乏《哺乳期的女人》中惠嫂那样充满母性的光辉,甚至丧失了身为女性的特质,成为了一个异化的符号。她是一家之主,是优秀的宣传干事,她把丈夫当敌人,把女儿当报复工具,一味追求胜利的快感,可这种胜利也是可悲的,家都散了,赢的也不过是面子上的风光。然而更可悲的是妻子丧失了作为“人妻人母”的价值,被权力异化而不自知,陷入了“不男不女”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作者也试图寻找人性中保留的纯真美好及人类诗意生存的可能。例如,初恋时“我”写给阿来的那首十四行诗,其中的情愫不乏真挚,而阿来早期的羞涩与腼腆也体现出人性的纯真和美好,以及作品中提及的夕阳下的丹麦面包店,这些都隐喻或表明了某种与那个诗意的、淳朴的、童真的、纯洁的世界的关联。但是“我”和妻子之间的那种关系,亲属、朋友、邻居、同事有关“我离婚的理由”的“不同的说法”,却体现了意识形态话语对家庭的介入,乃至于女儿也学会了这套话语,使“我”和女儿间交流能力丧失,这种根深蒂固的人间亲情,在市场经济、现代观念的冲击下,被动摇、丢弃;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深广的鸿沟,原本善良的人们变得如此虚伪、冷漠、沉重,这又意味着那种与原初的纯真世界的隔膜和远离。作品中的孩子和动物在文学中往往象征着未被文明污染的自然和纯真,但是作品中的小女孩、动物园中的动物都已经被现代文明所污染。小女孩不再是天真可爱的模样,对“安徒生爷爷吃过的面包”无动于衷,对父亲送的电子猫看都不看一眼,沉默以对,更不要说还保有着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了。至于小说中提到的动物园中的动物,它们脱离了其原初生存的场所,被关进铁笼供人观赏,完全丧失了自由,只能在铁笼中日复一日地虚耗生命。可见,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是不自由的,不断地被欲望驱使,不断地丧失人性的美好。在这里,小说从对男人还剩下什么的追问,上升到对整个人类还剩下什么的追问,作者以更深远的眼光思索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未来,当人们对金钱、权利的欲望不断膨胀,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僵化,当人们被一味追求的东西异化,整个人类只剩下一个物质化的空壳,人类成为没有生机的符号。整个人类生存的世界就会如同小说中所体现的那样成为一个无爱的,缺乏诗意的世界。毕飞宇以其作者的良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向读者呼吁回归人性的纯真美好,重建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际。
二、视角和语言中的男性立场
毕飞宇作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个人化写作风格,给当下文坛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他的小说既存在着与新生代小说的某些相同的特点,如直面当下变动的日常性生活,关注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强调创作的自我意识等等,又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4]《男人还剩下什么》是他前期的作品,尽管写作手法还有待成熟,但作品中所体现的写作特色以及鲜明的男性主体精神一直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5]
(一)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毕飞宇前期的小说大多是用第一人称叙述,如《款款而行》《怀念妹妹小青》《叙事》等。“我”的运用使文章读起来一气呵成,“我”作为叙述人和参与者,将小说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展现出来,这种叙事方式使文本带有浓郁的自传性质,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产生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也便于直接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男人还剩下什么》中,“我”向读者讲述了自己怎么被妻子赶出家门,离婚后怎么被妻子惩罚的故事,使读者不自觉地站在了主人公“我”的男性立场上,因此很容易被作家的主观情感所带动,对文中“我”一无所有的处境感到同情。这是作者男性主体精神的表现之一,作者善于从男性的立场来看待女性、男性的问题,因此使小说带有浓厚的主观性。文中的“我”是作者的代言人,“我”对于如何能“诗意”地生存的反问实际上是作者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思考,而对于男人还剩下什么的反问,作者的回答是“一无所有”。这说法虽太过决断,但未尝不是一种警告,一无所有并不是不可能。这也是作者写作这篇小说的主旨之一,借“我”之口探究说明男性在当下生活中的境况。《男人还剩下什么》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运用得恰到好处,明晰地表现主人公“我”心里变化的过程,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想来结构全篇,很好地表现了男性应对自身开始反省的迫切性。不过,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毕飞宇不会局限在第一人称的视角里,在他2000年之后的作品里,出现了一种介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第二”人称,这种“第二”人称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第二人称”,而是兼容了第一人称的“亲切感”“主观性”,和第三人称的“距离感”“客观性”[6],这种人称叙事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每个人物,将人物的内心活动、思绪变化自由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隐性地表现出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由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到“第二”人称叙事视角的变化,是作者对小说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的探索,也是作者创作手法越发成熟的表现。
(二)反讽调侃式的个性标识语言
毕飞宇说:“一个作家的特征,一个作家的风格,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也就在于语言, 通过语言。”[7]毕飞宇的小说语言极具个性,常于反讽调侃之下蕴涵着深沉的情感。《男人还剩下什么》中,“我”以反讽调侃的口吻讲述了自己与妻子对战而落败的事迹,表面上给人轻松幽默之感,可仔细回味一下又能体会出其中的悲哀,男人在妻子的报复下节节败退,女儿成为陌生人,男人不仅失去了作为丈夫的尊严,也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利。作者将情感隐藏在文本之后,对男人的境遇既同情又批判,对女人的异化也深切关注。“轻盈而凝重”是他的小说理想,而他个人化的语言风格正是对这一小说理想的实践。[8]施战军在《毕飞宇论》中说到毕飞宇小说的语风里常有意识形态性的词汇[9],例如作品中女儿为数不多的两句话:
“你是个不可靠的男人,是不是?”
“你有没有对别的女人耍流氓?”
很难想象这话出自一个六岁的小女孩之口,她还不懂得什么是耍流氓,就已经接受了母亲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话语的灌输,这种成人口吻的质问,让“我”气得七窍生烟,最后“我”大声质问妻子:“你对我女儿干什么了?”便是对这种污染儿童纯真的成人意识形态的抗议。可见这一类语汇对日常生活的暴力性介入,对纯真生活、纯真人性所造成的扭曲。而从妻子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作者鲜明的话语特色和男性立场:
“我嘛”,我的前妻说:“第一,宣传;第二,统战;你完了。你死透了。”
这段话似乎俏皮, 但却是毕飞宇式聪明的体现, 显示出作家个人化的话语特色[6]。将一个神气十足,对男人充满恨意的女性形象展现得活灵活现,富有意味。但是小说的语言对于女性进行了过分的讽刺,这是毕飞宇男性主体精神的表现之二。通篇来看,是一个离婚男人对自身处境的自嘲,可这种自嘲之外还有对女性的讽刺。例如“我们冷战了数日”后,“我厚颜无耻地对我的妻子说:‘女儿才六岁半,我们还是往好处努力吧。’”作者对于妻子的反应用了“最出色”“很迷人”“突然”“大声说”“休想”一系列的词语将妻子变换狰狞的面孔非常细致地表现出来,这与“我”嘲讽地说自己“厚颜无耻”比较起来,对妻子的讽刺反而更加明显,作者艺术性地将妻子性格进行夸大,成为了一个完全被恨意泯灭良知的女人。作者从男性视角对这一女性形象的批判虽然尖锐,但却鲜明地指出了女性在社会压力下异化的事实。可见,作者不仅仅关注着“男人还剩下什么”,也对女性生存状态有着灵敏的把握。毕飞宇曾经说过:“我的小说直指当下”。的确,作者笔下的一个个生存悲剧时时都在警醒着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10]。从这一点看,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男性立场,还原为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注与期待。
三、结语
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或许是毕飞宇众多作品中并不那么显眼的一篇,但其创作价值确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毕飞宇对男性的生存状态做了细致的观察,有感于男性从身心强势变为心理的犬儒,对于他们的精神变异有深刻的感触;其二,小说中体现出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作者无论是关注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这是一个杰出作家所具有的艺术立场。毕飞宇锐利地分析了人性的复杂变化,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原始人性的纯真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11]不过,正如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给毕飞宇的获奖评语所说,毕飞宇要走向宏大、浑厚的艺术境界,还“有待于他对生命和生活更广博、更奔放的感受和把握。”[12]
[1]毕飞宇: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一个日子:毕飞宇做客新浪访谈[EB/OL].(2007-06-29)[2015-01-19].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27646.
[2]毕飞宇.男人还剩下什么[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3]牛贝.论毕飞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4]宁琳.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5]翁菊芳.论毕飞宇小说男性主体精神(之一):男尊女卑的男性思想[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20):102-105.
[6]郭庆杰.话语选择与文本处理中的人文情怀[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18-121.
[7]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8]张权生.凝重的哲思与诗性的轻盈:毕飞宇小说创作论[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
[9]贾梦玮.河汉观星十作家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10]王咪咪.逃离与追寻:论毕飞宇城乡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D].合肥:安徽大学,2011.
[11]田祝. 异乡人的世界:毕飞宇小说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12]银洁.毕飞宇创作论[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辑 马 诚)
Male Position in Bi Feiyu’s Stories from hisWhatIsLeftonMen
HE Si,WU Pei-xian
(Liberal Arts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Bi Feiyu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male writer in describing the female psychology and his stories does include a group of mediocre male images.WhatIsLeftonMenis features story from his attentive concern to men for survival,an unnoticed good writing for male struggle for life.In the story,men are general on the decline,losing the ability for speech,love or human innocence.On the other hand,his first-person narrative style and ironic humor in telling the story shows the male as subject spirit.At the same time,he surpasses the male position in a way to spread the universal human care in a typical male touch.
Bi Feiyu;male position;alienation;human care;WhatIsLeftonMen
2014-12-31
2015-04-21
贺思(199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吴培显(1956-),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wpx@hunnu.edu.cn
I206.7
A
1673-4432(2015)02-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