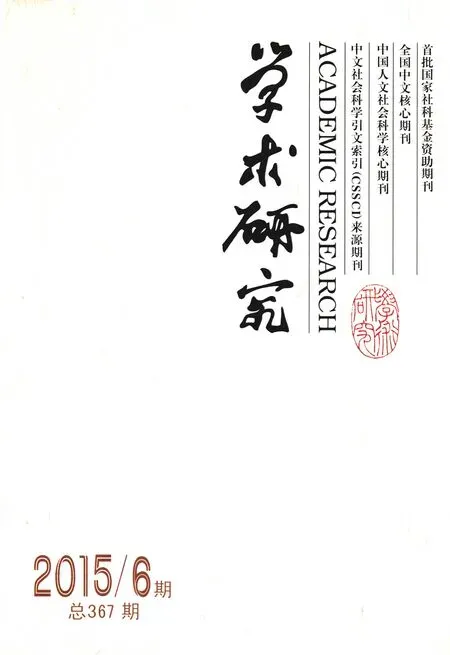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曾大兴
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曾大兴
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问题。自从法国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提出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之后,其他学者也有过类似表述,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要找到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气候不能直接影响文学,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直接影响文学创作,它必须以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为中介。气候影响物候,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影响文学创作。因此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气候 物候 文学家 生命意识 中国智慧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止一个人提到过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法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斯达尔夫人 (1766—1817)在 《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 “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 “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地域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1]斯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 (1828—1893)在 《艺术哲学》一书里,除了一再强调 “精神气候”(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提到过自然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2]自从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到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之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学批评界,也有学者提到这一问题。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讲,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等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点到为止。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具体
问题:一是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二是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问题,笔者已有多篇论文探讨。①参见曾大兴 《岭南诗歌的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气候与戏剧、小说人物之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气候 (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应物斯感:气候 (物候)与文学创作的触发机制》(《文心雕龙研究》第10辑,2013年7月)等。本文的目的,即在试图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笔者认为,要真正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
一、从气候学与物候学的角度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气候是一种自然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文学家为中介,气候只能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那么,气候影响文学家的什么呢?可以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身体,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精神。换句话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 (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长短等等),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包括对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就生命 (或身体)这一方面而言,气候对所有的人都能构成影响,文学家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正是在生命意识 (或精神)方面,文学家对气候有着特殊的反应。
(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 “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 “生命价值论”。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与普通人的生命意识,就其内涵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表现不尽一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比普通人的更强烈,更敏感,也更细腻。尤其是对时序的感觉这一方面,文学家的优势特别明显。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一是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即有关的物候现象。关于后者,英国学者弗雷泽说:“在自然界全年的现象中,表达死亡与复活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了。”[3]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命是异质同构的。人的生老病死,与动植物的生长荣枯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问题是,一般人对人类自身 (尤其是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的生老病死的反应是敏感的,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则不够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 (包括种地的农民)和文学家算是例外。然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例如种地的农民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想到的是季节的早晚,以及农事的安排;文学家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则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时间的流逝,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晋代陆机 《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4]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郁达夫在他的散文 《杂谈七月》中写道:“阴历的七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 ‘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也特别的多。诗人善感,对于秋风的惨淡,会发生感慨,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
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缘故。”[5]由此可见一般人和文学家对于物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清代黄宗羲 《景州诗集序》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6]所谓 “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就是指诗人能够敏锐地、细腻地、强烈地体验和感知动植物的生命律动;所谓 “能结之不散”,就是指他们能够抓住这种体验和感知,并且把它用诗化的形式 (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家对生命的体验、感知和表现,又可以唤起或强化更多的读者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所以说,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对文学家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 (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乃至他 (她)的生命质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也与气候的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 《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 “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7]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而所谓物候,按照 《现代地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8]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9]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通过物候,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时序的更替和各地季节的迟早,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
物候被称作是 “大自然的语言”。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 (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物候这门知识,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中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 《礼记·月令》讲:“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至之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10]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物候学最早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是物候学的故乡。
(三)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在中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 《诗经》。 《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 (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 《秦风·蒹葭》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邶风·北风》之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王风·黍离》之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则是西周时期的秦 (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邶 (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邑 (今河南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也说明文学家对于
物候现象的感受、观察和描写,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出现,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蟋蟀在堂”,这是西周时唐地 (今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还得顾及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 “忧深而思远也”。[11]这就是文学家由“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样。中国文学有着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情感、思想、表现方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是什么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是时间。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 “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 (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 (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侯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二、用中国古代文论智慧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除了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笔者发现,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 (约466—约537)和钟嵘 (约467—约519)就曾经不自觉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 “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12]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讲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 (词语)的内涵:一是“气”、“阳气”、“阴律”;二是 “物”、“物色”;三是 “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先看第一组概念 (词语)。 “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在 《文心雕龙·物色》的这
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英华秀其清气”的 “气”当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 “气”当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 “气”当是指天气,这三个 “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 “气”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 “阴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 “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 “阴律”二字,就是指 “阴气”。詹瑛 《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 ‘阴律’代替 ‘阴气’。”[13]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 (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14]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代崔骃 《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鸧鹒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15]阳气萌发而鸧鹒 (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呻吟,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 “气之动也”。清代宋荦 《〈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16]可以看作是对崔骃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这两句是由崔骃而来,崔骃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再联系 “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当 “气”字与 “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 “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 “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总之,当 “阳气”与 “阴律”(阴气)并举,又与 “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 “气”字,就只能是指 “气候”了。既然 “阳气”与“阴律”这两个词是指气候,那么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的“阴”与 “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也是与 “春秋”这个表示时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 (词语)。 “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 “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 (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 《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 ‘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17]由此可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 “物”,是指 “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 《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 “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 “物色”的含义。 “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 《淮南子》、《礼记》等书。 《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 《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 “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 《文选》 “赋”的“物色类”中,收有 《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 “四时所观”,可见 “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即属于物候学所讲的 “物候”。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 (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 (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而 “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 “‘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组概念 (词语),即 “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这一组概念或词语,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 “七情”,[18]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 《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 “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今年花开叶落,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人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今年见到花开叶落,明年不一定还能见到花开叶落。此即所谓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19]所以 “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 “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所以为之欣喜。所谓 “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 “瞻万物而思纷”。所谓 “万物”,在这里就是指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谓 “思纷”,就是指由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人的 “七情”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季节性的,不可笼统言之。同样,刘勰所谓 “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 “霰雪无垠”是说四时物候,而 “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 “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四时之物候,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中的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一是 “气候”(阴阳)与 “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 “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 (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 (心或情)与文学 (辞)的关系。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要比斯达尔夫人全面得多,也具体得多,只是历来研究 《文心雕龙》的学者未曾察觉而已。历来研究 《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 《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 (辞)将它表现出来,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感人的力量。”[20]刘大杰 《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说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21]他们都强调文学 (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 (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自然景物 (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 “阳气萌”和 “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起物候的变化 (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 (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心亦摇焉,情以物迁),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 (心亦摇焉,情以物迁)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 (辞以情发)。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 “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 “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 “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 “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 《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2]这里的 “气”,也是指 “气候”。郭绍虞主编的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在讲到钟嵘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23]把 “气之动物”的
“气”解释为 “气候”,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条解释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的 “物”笼统地解释为 “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 “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所讲的 “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 “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钟嵘这里所讲的 “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括“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以及逐臣去国的悲哀,弃妇离宫的伤痛,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思妇独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笔者认为,钟嵘 《诗品序》中的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中的那两段话的一个概括,它们的价值,就是揭示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从而帮助我们解答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命题,这就是: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 (气之动物),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物之感人),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 (摇荡性情),才有文学作品的产生 (形诸舞咏)。当然,钟嵘的表述和刘勰的表述一样,也是不经意的。钟嵘的本意并不在考察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更不在探讨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而是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之得失。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探讨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的意图,所以后人在解释这几句话时,也就顺着他的本意进行,而没有把这几话当作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来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发现,实际上要比西方学者早得多;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也比西方学者要全面得多,具体得多。只是他们的这种发现和解释都是不经意的。今天我们结合气候学与物候学的有关知识来总结他们的这些认识,对于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世界性学术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6-147页。
[2][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49页。
[3][英]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江培基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489页。
[4][晋]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70页。
[5]郁达夫:《杂谈七月》,《郁达夫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6][清]黄宗羲:《景州诗集序》,《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页。
[7][8]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99页。
[9]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10]《礼记·月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47-2949页。
[11][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8页。
[12][18][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3-694、65页。
[13][南朝梁]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30页。
[14]曾大兴:《中外学者谈气候与文学之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15][汉]崔骃:《四巡颂》,[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0页。
[16][清]宋荦:《明遗民诗序》,[清]卓尔堪辑:《明遗民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页。
[17]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6页。
[19][唐]刘希夷:《白头吟》,《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7页。
[20]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32页。
[21]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32页。
[22][南朝梁]钟嵘:《诗品序》,曹旭:《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 312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I206.2
A
1000-7326(2015)06-0152-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08BZW044)、理论粤军·广东省地方特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015)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经典的认同作用研究”(2014WZDXM021)、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项目 “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13C05)的阶段性成果。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