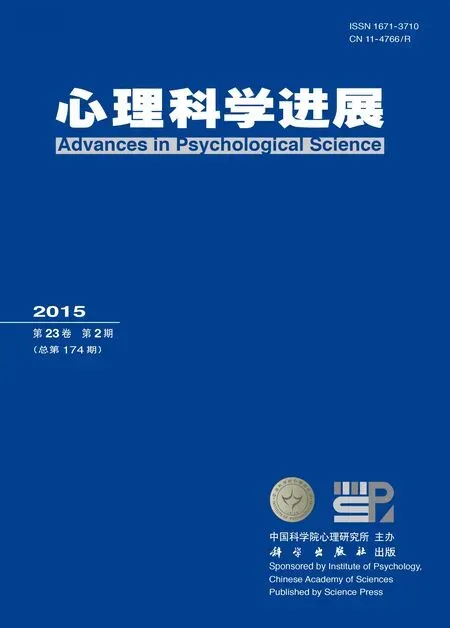内隐追随理论:概念、测量、前因及后果
曹元坤 祝振兵,2
(1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南昌 330013) (2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南昌 330013)
1 引言
Rosch, Mervis, Gray, Johnson和Boyes-Braem(1976)指出, 对环境刺激进行分类是所有生物体最基本的功能之一。研究表明个体是一个认知节约者, 他们会本能地对他人进行分类, 以便于简化外部世界, 实现认知节约(cognitive economy)(Macrae & Bodenhausen, 2000)。Lord等人将这种认知分类的思想引入到组织背景中, 发展了内隐领导理论(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ILTs)的概念——指个体心目中关于领导者的特质和行为的假设和预期, 其核心是关于领导者原型的认知结构或图式(Lord, Foti, & De Vader, 1984)。ILTs主要从追随者(本文中与员工或下属同义)的认知过程的角度来审视领导力,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如Kenney, Schwartz-Kenney, & Blascovich,1996; Martin & Epitropaki, 2001; 凌文辁, 方俐洛,艾尔卡, 1991; 杨艳, 胡蓓, 2009; 卢会志, 刘永芳, 许科, 2008)。ILTs解释了追随者如何依赖于其心目中的领导者原型对领导者进行分类, 以及关于领导者的假设和预期如何影响了追随者的工作态度和行为(Lord & Maher, 1990)。但在过去的30多年中, 领导力的研究只是关注于追随者心目中的领导者原型, 忽视了与追随者原型有关的认知结构(Sy, 2010)。Avolio, Walumbwa和Weber (2009)指出今后应加强领导者的认知过程的研究, 以更综合的视角来探讨领导力问题。最近组织行为学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新的概念——内隐追随理论(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 IFTs)——响应了Avolio等人的号召。IFTs的研究关注于个体(尤其是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假设和预期, 弥补了当前对领导者认知过程研究的不足, 有助于我们理解IFTs如何影响了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分类和评估,以及这种分类和评估对追随者行为和态度的影响(Van Gils, Van Quaquebeke, & Van Knippenberg,2010)。虽然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 但IFTs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领导力研究领域的权威杂志《The Leadership Quarterly》在其2014年第1期上专门就该议题刊发了约稿文章(Foti, Hansbrough, Epitropaki, & Coyle, 2014)。因此开展IFTs的研究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即是基于这一背景, 从IFTs的概念、研究基础、测量、前因变量、后果变量等五个方面对当前IFTs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并对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中亟待探索的问题略谈浅见。希望能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学者的思考与关注。
2 IFT s概念
IFTs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McGregor的X-Y理论。McGregor (1966)认为不同的领导者对追随者有不同的假设:一种假设认为追随者是懒惰被动的; 另一种假设认为追随者是积极主动的。但这种IFTs的思想萌芽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处于沉寂状态, 直至近几年IFTs的概念才得以正式提出。Carsten和Uhl-Bien (2009)将IFTs定义为个体(可以是领导者, 也可以是追随者)心目中关于有效追随者的特质和行为的认知结构或图式。Carsten和Uhl-Bien的定义主要关注于“有效”或“优秀”的追随者是什么样的。而Sy (2010)随后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扩展, 将其定义为个体心目中预先存在的、关于追随者的行为和特质的预期和假设, 其核心是关于追随者原型的认知结构或图式。Sy的定义不仅包含了“有效”的追随者原型,而且包含了现实中“无效”的追随者原型, 是一个外延更为广泛的概念, 得到当前多数研究者认同(Whiteley, Sy, & Johnson, 2012)。需要注意的是,IFTs并非个体对现实中某个或某些追随者特质和行为的客观描述或感知, 而是个体心目中的追随者原型所具有的特质和行为。这些追随者原型是个体“意义建构”的基础, 当现实中追随者的表现与领导者心目中积极追随者原型匹配时, 领导者就会对追随者有更积极的评价; 反之, 当与领导者心目中积极追随者原型不匹配时, 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评价就更消极。为了更清晰地理解IFTs的边界, 澄清其与相关概念或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是有必要的。
2.1 IFT s与X-Y理论的比较
McGregor (1966)指出持有X理论的领导者认为追随者本质上是懒惰的、不喜欢工作的、缺乏自我引导能力的; 持有Y理论的领导者认为追随者本质上喜欢工作, 并把工作视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能够自我控制, 愿意承担责任。McGregor认为, 领导者的不同假设会影响其对追随者的行为:X理论的领导者一般会采用严密的控制、强迫、惩罚的方式来管理追随者; 相反, Y理论的领导者会给追随者更多的尊重、自主权和参与的机会。IFTs和X-Y理论的相似之处体现在, 两者都试图解释领导者对追随者特征的不同假设会影响个体或组织层面的一些后果(如领导者管理方式)。其不同在于, IFTs整合了认知分类和原型匹配的过程, 并且还认为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假设和期望在本质上是多维度的, 如Sy(2010)研究发现IFTs包含6个维度(如好公民、不称职等)。
2.2 IFT s与内隐绩效理论的比较
内隐绩效理论(implicit performance theories)是指领导者心目中预先存在的关于追随者工作有效性的认知结构或图式, 依赖于这些认知结构,领导者形成追随者工作有效性程度的判断(Engle& Lord, 1997)。Engle等人指出, 领导者会将实际工作中的追随者的表现同其内隐绩效理论原型进行比较, 当追随者的行为与高绩效原型一致性程度高时, 领导者就会对追随者的绩效有更积极的评价, 反之评价更差。内隐绩效理论与IFTs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涉及到原型匹配和比较的过程。不同点在于, 前者的内容范围比较狭窄, 只限于与绩效有关的期望和假设, 而后者则范围要更宽泛, 涵盖了更多追随者的个人特质和行为, 比如提建议、积极主动做事、热情等(Sy, 2010)。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内隐绩效理论是IFTs的一个子集。
3 IFT s研究的理论基础
IFTs是研究者类比ILTs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虽然在探讨领导力过程时两者在研究视角上存在明显的区别——IFTs是基于角色(role-based)的视角, ILTs是基于追随者中心的(follower-centered)视角(Uhl-Bien, Riggio, Lowe, & Carsten, 2014),但两者所基于的理论基本类似。这里我们借鉴ILTs研究的已有成果, 结合当前关于IFTs的研究,将IFTs的认知科学理论基础归纳为以下三个模型。
3.1 认知分类模型
Rosch等人(1976)最早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对物体分类的认知模型, 她们认为:在垂直方向上人们对物体的分类可归为三个层面, 即最高水平(superordinate level)、基础水平(based level)和最低水平(subordinate level), 而在每个层面或每个水平上, 又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类别; 更低层次的类别包含与其相连的更高层次类别的所有属性或特征, 处于同一层次的不同类别之间又存在着区别性的属性或特征。Lord等人(1984)最早将这种分类的思想移植到组织行为研究中提出了对领导者分类的理论(即, 内隐领导理论)。在Rosch、Lord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者又将这种思想移植到了追随者的分类上(即, IFTs), 认为IFTs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水平, 这一水平主要是区分“追随者”和“非追随者”, 这一层所包含的特征适用于所有领域中的追随者; 基础水平是指不同情境或领域中的追随者特征, 如宗教、军队或商业中的追随者特征; 最下层是特定领域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追随者的特征, 比如在商业领域中的机械工程师, 或者软件工程师(Sy, 2010; Epitropaki, Sy,Martin, Tram-Quon, & Topakas, 2013)。如下文所述,Sy (2010)的研究是基于这种认知分类理论。
3.2 信息加工模型
Lord和Maher (2002)认为, 人们获取和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通常情况下, 人们会使用控制的或自动的信息加工方式来认知领导, 并对领导行为进行推理判断。控制的加工和自动的加工的区别在于信息加工中个体的意识水平和付出的努力程度不同:控制的加工是有意识的、付出努力的加工, 而自动加工则是无意识的且无需深思熟虑的努力。Lord和Maher (2002)进一步提出人们对于个体的认知——无论是控制的还是自动的——是建立在原型同目标个体(被感知者)的现实表现之间的匹配比较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 目标个体的行为或特征会激活感知者头脑中的原型,在自动加工情况下, 感知者将会依赖所激活的原型直接形成对目标个体的感知和判断; 而在控制加工情况下, 通过感知到的目标个体的行为或特征同感知者原型之间的多次反馈匹配来形成感知者对目标个体的判断。信息加工模型一方面强调了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对原型或内隐理论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信息加工匹配的过程。Hoption,Christie和Barling (2012)、Whiteley等人(2012)对IFTs的研究均是基于信息加工模型(详见第五部分)。
3.3 联结主义网络模型
该模型类比现有的认知网络理论模型, Lord,Brown, Harvey和Hall (2001)将联结主义网络描述为“类似神经元加工单元的网络, 该网络持续从输入源整合信息并且传递产生的激活(或抑制)到联结(输出)的单元”。该理论认为:感知到的外部刺激能够迅速激活所建构的网络或图式; 网络中单元与单元之间连接的路径有一定的权重, 权重的大小决定了信息从一个单元向另一个单元传递时激活或抑制的程度; 这些权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正因为此, 路径在所建立的网络中获得相对稳定的权重是可能的, 同时随着进一步学习的发生, 权重也会逐渐改变(Lord et al., 2001)。联结主义网络模型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更清楚地阐述了个体的内隐图式如何被激活, 以及如何在外界环境影响下而发生调整或改变。相对于前两个模型,该模型更具动态性和灵活性。Carsten, Uhl-Bien,West, Patera和McGregor (2010)对追随者心目中的内隐追随图式的研究便是基于这种联结主义网络模型。
4 IFT s的测量
测评工具的开发和完善对于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IFTs仍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关于其测评的研究刚刚起步, 急需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当前关于IFTs的测量主要有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类, 也有学者称之为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Tram-Quon, 2013)。Payne和Gawronski (2010)指出“直接”和“间接”反应的是测量程序的特征, 而“内隐”和“外显”更多地是表示认知过程的差异。本文更倾向于Payne和Gawronski的观点, 所以这里我们用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表述。直接测量是指通过直接询问个体对特定对象的感受来获取个体的对该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间接测量是指基于个体对其他任务的反应(如反应时)来间接推断其对某个对象的态度和看法。本文就现有对IFTs的两种测评方式进行简要介绍。
4.1 IFT s的直接测验
Carsten和Uhl-Bien (2009) 依据其所建构的“被动(passive)——积极主动(proactive)”的连续体模型(Carsten et al., 2010)** Carsten和Uhl-Bien (2009)是在2009年11月“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上报告的一篇会议论文, 而Carsten等(2010)是2010年3月刊发在《The Leadership Quarterly》上的期刊文献, 由于期刊文章存在较长审稿周期, 故作为理论基础的Carsten等(2010)引用日期更为滞后。, 编制了IFTs问卷。该问卷采用Liket 6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 6=非常同意), 由9个项目组成:其中5个项目(如:“追随者应该表达他们的观点, 即使他们知道会得到领导者的拒绝。” “追随者应该积极主动地识别那些可能会影响组织发展的问题。”)代表了积极主动的方面; 4个项目(如:“作为一名追随者, 个体不用担心被卷入到决策制定中去。”“作为一名追随者意味着你不需要思考改善完成工作的方式。”)代表了被动的方面。研究者对问卷进行了多样本的施测, 虽然在因素分析时析出现了主动、被动两个维度, 但她们主张在统计时对被动方面的4个项目分数进行反向计分, 整个问卷作为单一维度来处理。早期问卷开发时发现问卷在三个样本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较为理想, 分别是0.86、0.78、0.80, 且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但需要注意的是, 最近Carsten指出(电子邮件沟通)在后续测量中该问卷的结构并不太稳定, 因此应谨慎使用并进一步完善。
Sy (2010)以形容词为问卷项目, 遵循严格的问卷开发程序, 完成了IFTs问卷的开发。研究结果发现所开发的IFTs问卷由18个项目组成(如忠诚的、可信赖的、粗鲁的等), 这些项目可归属于6个一阶因子, 包括, 勤劳(industry)、热情(enthusiasm)、好公民(good citizen)、依从(conformity)、反抗(insubordination)、不称职(incompetence)等,各因子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5~0.81之间。并且发现这6个因子可以汇聚为IFTs“原型(prototype)”和IFTs“反原型(anti-prototype)”两个二阶因子:前者代表了积极的, 领导者心目中优秀的追随者所拥有的特征, 包括勤劳、热情、好公民三个一阶因子; 后者是指消极的, 领导者心目中拙劣的追随者的特征, 包括依从、反抗和不称职三个因子。两个二阶因子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0和0.90, 且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问卷的重测信度、区分效度等也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4.2 IFTs的间接测量
Tram-Quon (2013)试图使用单靶内隐联想测验(Single-target IAT, ST-IAT)的方法来测量个体的IFTs。在Tram-Quon (2013)的测量程序中“靶(target)”是追随者(包含了一系列近义词, 如工人、员工、下属等), 属性维度及各维度所包含的词汇均来自上述Sy (2010)开发的IFTs问卷。具体来讲,两个属性维度“积极”和“消极”分别对应Sy的问卷中的“原型”和“反原型”两个二阶因子; 积极维度包含了原型因子中的9个项目(如忠诚、可信赖、努力工作等), 消极维度包含了反原型因子中的9个项目(如粗鲁、傲慢、易受影响等)。Tram-Quon使用D分数计算ST-IAT IFTs的得分。结果发现,ST-IAT IFTs的校标效度、预测效度和汇聚效度均不理想。
但Tram-Quon (2013)同时还对Sy提出的IFTs的投射测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检验。Sy (尚未发表,引自Tram-Quon, 2013)提出用投射(projective)的方法来进行IFTs的测量, 其程序包括两个步骤:首先, 呈现三个情节(如, 员工被调换到一个新的部门), 让被试依据这三个情节分别创造三个与其心目中的“典型员工”有关的小故事; 故事完成后,要求被试评定该“典型员工”在Sy (2010)的IFTs各个项目上的得分。Tram-Quon在三个研究中发现投射的IFTs量表的原型和反原型两个二阶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ɑ均在0.84~0.93之间, 并且这种投射的测验具有较好的校标效度、区分效度和预测效度。
虽然对于IFTs的测评取得了一些进展, 现有的无论是IFTs的直接测验还是间接测验, 均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所开发的, 而有研究表明内隐理论会受到文化的影响(Sternberg, 1985), 所以这些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中未必具有普适性。因此,对IFTs的内容和结构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进行本土化研究是有必要的。
5 IFT s的前因变量
个体的IFTs源自何处?很少有研究者对其探讨。Epitropaki等人(2013)指出, 由于一般观念认为内隐理论在个体成长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形成,所以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也许这种观点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对IFTs前因变量的研究比较鲜见。检索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文献, 发现仅有几篇文献涉及到IFTs的前因变量。
Carsten等人(2010)基于社会建构理论和认知的联结主义网络模型对追随者的IFTs作了一个质性研究, 通过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她们发现环境变量(主要是组织氛围和领导风格)对个体的IFTs建构有重要影响。比如他们发现:在严格的官僚体制的组织氛围或者强调权威型领导风格的组织中,追随者所建构的追随者图式更为消极被动, 因为这样的组织氛围和领导风格倾向于扼杀个人的创新性和主动性(Blau, 1968); 相反, 在强调授权的组织氛围或参与型领导风格的组织中, 追随者所建构的追随者图式更为积极主动, 因为这样的组织氛围和领导风格倾向于给追随者机会敞开心扉、鼓励参与决策(Srivastava, Bartol, & Locke,2006)。但该研究是基于横向数据的质性研究, 对于组织氛围和领导风格是否对个体的IFTs建构有影响, 以及影响作用的大小等问题并不能给出定量的证据。
在另一个研究中, Kruse和Sy (2011)基于内隐理论的联接主义视角, 把个体的情绪状态作为操纵变量(自变量), 将个体的IFTs评定作为因变量(采用上述Sy (2010)开发的工具进行测量), 研究了情绪对IFTs的影响。研究者设计了四个实验,分别诱发了被试的多种情绪状态(悲伤、愤怒、愉快和无情绪诱发), 结果显示情绪激活了相应的IFTs:被诱发悲伤或愤怒情绪的被试所报告的在反原型因子上得分明显高于无情绪诱发的控制组被试得分; 被诱发愉快情绪的被试所报告的在IFTs原型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无情绪诱发的控制组被试得分。虽然该研究致力于情绪对个体IFTs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Kruse和Sy的研究所探讨的只是不同情绪状态对个体的IFTs不同内容的激活, 其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个体IFTs的结构和内容, 并且这种不同情绪状态所带来的对个体IFTs评定的改变可能也只是暂时的。
6 IFT s的后果变量
关于IFTs的作用或后果变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其一, 领导者的IFTs, 主要研究领导者的IFTs对其态度、行为及对追随者后果的影响; 其二, 追随者的IFTs, 探讨追随者的IFTs对自己态度、行为及对领导者的影响。
6.1 领导者的IFTs及其后果
如前所述, McGregor (1966)很早就指出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假设会影响领导者的管理方式, 即持有X理论的领导者倾向于使用严格的监督和控制的方式对待追随者, 持有Y理论的领导者倾向于松散诱导的方式对待追随者。半个世纪后, Sy(2010)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领导者的IFTs对领导者本人及其追随者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他发现:领导者的IFTs原型与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喜欢、追随者对领导者的信任、追随者评定的领导——下属交换关系、追随者的工作满意度等变量存在显著正相关; 领导者的IFTs反原型同上述追随者变量存在显著负相关; 领导者IFTs原型同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喜欢和领导者评定的领导——下属交换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 领导者IFTs反原型同上述领导者变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并且在控制了领导者的其他内隐理论(内隐绩效理论和内隐领导理论)后, 所有以上相关仍然达到统计显著水平。但领导者的IFTs是如何影响了追随者的态度和行为?或者说领导者的IFTs同这些后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是什么?Sy并未给予解释。Whiteley等人(2012)试图回答领导者的内隐追随理论对追随者工作绩效影响的机制。他们研究发现领导者的IFTs原型作用于追随者的工作绩效的两条路径:其一, IFTs原型会影响到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喜欢以及领导者和追随者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而这种喜欢和高质量的领导者——追随者交换关系又会进一步影响追随者的工作绩效; 其二, IFTs原型会影响领导者对追随者的绩效期望, 而绩效期望又会影响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喜欢和高质量的领导者——追随者交换关系, 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喜欢和高质量的领导者——下属交换关系又会影响追随者的绩效。
6.2 追随者的IFTs及其后果
虽然当前关于领导者的IFTs的研究相对较多,但追随者亦有其关于追随者的内隐理论。Carsten等人(2010)探讨追随者的IFTs对追随者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基于访谈, Carsten等人发现追随者所持有的IFTs可分为被动(passive)、主动(active)和积极主动(proactive)三类。持有被动图式的追随者更乐于被动接受领导者指令, 喜欢保持沉默,逃避责任; 持有主动图式的追随者会在适当的时候给领导者建言献策, 但仍然会忠于领导者的决策; 持有积极主动图式的追随者勇于承担责任,强调其对领导者的影响, 对领导者的决策会积极反馈甚至提出挑战, 类似于一种自下而上的“领导者”。在另一个研究中, 研究者探讨了个体被动或主动给自己贴上“追随者”或“领导者”的标签对其行为的影响(Hoption et al., 2012)。研究者选取组织中的领导者或追随者为被试, 以角色变量(追随者——领导者两个水平)为操纵变量, 被试的情绪体验和角色外行为作为因变量。通过两个实验研究, 他们发现:与被标签为“领导者”的被试相比,被标签为“追随者”的被试报告了更低的与工作有关的积极情绪体验和更少的角色外行为(如:“提交工作经验报告”, “周末与小组成员开会”等)。虽然Hoption等人(2012)的研究并未直接谈到IFTs,但其研究的潜在前提假设却与此有关。因为对被试设定或被试自己设定的不同标签(“领导者”或“追随者”)激活了其记忆中既存的认知结构或图式(本研究主要是ILTs和IFTs), 正是这种激活影响了被试的情绪体验和做出角色外行为的意愿。
7 总结与展望
综上, IFTs关注于个体对追随者的认知结构或图式, 是认知科学的成果在组织行为领域的新拓展。IFTs的研究不仅弥补了领导过程中对领导者认知过程研究不足的现状, 而且对于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领导者和追随者各有其关于追随者的图式(Sy, 2010; 原涛, 凌文辁, 2010)。对于追随者而言, 了解领导者的IFTs和自己的IFTs的差异, 可以据以调整自己的行为, 改善同领导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领导者而言, 了解自己的IFTs和追随者的IFTs的不同, 可以有针对性的改变管理方式, 调整自己或追随者的IFTs, 以提升管理效率。本文通过相关概念的比较进一步澄清了IFTs的独特内涵, 并分析了当前IFTs研究所依赖的理论基础, 继而从IFTs的测量方式、IFTs的影响因素、以及IFTs的后果变量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关于IFTs研究进行了剖析。由于IFTs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当前对于IFTs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问题有待今后继续探索, 我们认为未来研究中加强对以下几个方向的关注可能是有价值的。
第一, 加强测量工具的检验与开发。虽然IFTs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但如前所述, 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对其进行测量, 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然而仍有一些问题有待后续深入。首先,直接测量方面。虽然一些测量工具(如Sy开发的IFTs的直接测量工具)总体的信效度在一些研究中基本得到了支持, 但对于某些结构和内容, 不同研究者的观点却不尽一致, 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Sy (2010)将“易受影响(easily influenced)”和“追随倾向(follows trends)”项目归于反原型维度,认为是非追随者的特征, 而Carsten等人(2010)却认为被动追随行为也是有效追随图式的内容。因此, 今后有必要对Sy (2010)的反原型维度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此外, Sy (2010)开发的测评工具旨在区分不同领域中的追随者和非追随者, 但目前其所使用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商业组织中,测量工具的外部效度, 尤其是其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如教育、商业、军队等)中的有效性也有待进一步检验。其次, 关于IFTs的间接测量。Tram-Quon(2013)采用单靶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来间接测量个体的IFTs, 但发现其与直接的IFTs测验几乎不存在相关; 另一方面, Tran-Quon在其研究中发现Sy (2010)所提出的IFTs的投射测验与IFTs的直接测验存在较高的相关。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关系究竟如何?所测量的内容相同吗?Tram-Quon(2013)认为两者应该存在较高的相关, 因为它们所测的是相同的结构。所以当其所使用的IFTs的ST-IAT测量和IFTs的直接测量结果不一致时, 他们认为IFTs的ST-IAT测验是失败的。但也许两类测验反映的是不同的认知结构(如Epitropaki et al., 2013), 今后可能需要使用多种间接测量方式(比如, Uhlmann等人(2012)提出的“基于易接近性的测量”、“基于联想的测量”等方式)测量IFTs, 并对不同测量方式的结果进行比较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最后, 采用模式取向的方法(pattern-oriented approach)来测量个体IFTs应该是有价值的。一直以来, 组织行为研究中更多采用的是变量取向的方法(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 该方法的兴趣点是变量, 探讨的是单个变量的变化或变量之间的关系; 而模式取向的方法关心的是个体的功能或格式塔(Foti, Thompson &Allgood, 2011)。因为个体IFTs涵盖了诸多变量(如前述Sy提出IFTs的6个维度, 每个维度又分别包含3个项目), 基于变量方法来测量个体的IFTs是支离破碎的, 无法看到各个变量集合在一起的整体功能。而模式取向的方法将个体看作一个完整的、动态的、与周围发生着交互关系的格式塔,这与现实更为一致。
第二, 丰富对IFTs的影响因素或前因变量的研究。通常认为个体的内隐理论是在个体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所以多数人将IFTs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Epitropaki et al., 2013),而忽视了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IFTs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个体IFTs的变化?个体的IFTs如何随个体的成长而变化?这些仍是有探索价值的问题。具体来讲, 从下面几个方面开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许是可行的。①探索早期与父母关系模式、教养方式对个体IFTs的影响。作为与IFTs在时间上相伴而生, 在内容上相互对应的一个认知结构(Sy, 2010), ILTs的有关研究对于我们研究IFTs的前因变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Keller(1999)指出个体会内化其最初的照料者(caregiver)的特征, 并据此创造其对领导者的期望(即,ILTs)。比如:专制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体, 其领导力原型也倾向于具有专制特征。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推论, 具有专制ILTs的个体, 其IFTs也更为被动服从。②探索人格特质对个体IFTs的影响。如前所述, Kruse和Sy (2011)采用实验的方法探讨状态情感对个体IFTs的影响, 积极状态情感激活了积极的IFTs原型, 消极状态情感激活了消极的IFTs原型, 遵循相似的逻辑, 有理由相信作为人格特征的特质情感也会影响个体的IFTs, 积极的特质情感有助于积极IFTs的形成。当然, 今后也许还可以探索其他人格特质对IFTs的影响, 如大五人格对IFTs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会影响个体的ILTs (Keller, 1999)。③探索组织环境因素对个体IFTs的影响。虽然Carsten等人(2010)在其质性研究中已经发现了领导风格、组织氛围可能会影响IFTs, 但其影响效果仍有待实证的检验, 并且该研究中组织环境只是起到了调节作用,我们认为探索组织环境如何影响了个体IFTs的内容和结构的改变也许对于组织实践更有意义。这方面的探索可以从内隐理论的联接主义网络模型获得部分启发, 该模型认为个体的内隐理论是一个短期相对稳定, 但又可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认知结构(Lord et al., 2001)。今后可以开展一些对比研究(比如:对同一个个体入职前和入职后IFTs变化的对比, 对IFTs相似的不同个体在进入不同组织环境后IFTs变化的对比),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组织环境对个体IFTs的影响。
第三, 改善IFTs与后果变量的研究。今后在这一方面的拓展可以考虑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向进行。其一、就研究内容而论。虽然McGregor早就提出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认知会影响领导风格, 但一直以来关于领导者对追随者认知和领导风格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Shondrick, Dinh和Lord (2010)指出, 这种认知更多的是提取头脑中已有的语义记忆知识(即, 内隐理论)而非对追随者行为的真实评估。因此, 有理由相信领导者的IFTs是其领导风格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今后研究领导者IFTs的哪些内容影响了, 以及如何影响了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公仆型领导、辱虐式领导等等诸多不同的领导风格是有意义的。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当前关于IFTs的研究几乎均是横向研究设计, 很难深入地检验IFTs和后果变量的因果关系。今后可以借鉴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的思路。比如:Epitropaki和Martin (2005)运用交叉滞后的纵向研究设计探讨了追随者理想——现实ILTs和领导者——下属交换关系的因果关系, 这种交叉滞后设计也可以运用到IFTs和追随者的工作绩效等变量的因果关系研究中, 通过计算不同时段所获取的数据之间的关系来检验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此外, 还可以探索利用实验研究的范式, 通过操纵个体的IFTs(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在一定情况下内隐理论是可以操纵的。比如:利用外部刺激启动IFTs的不同内容(如Hoption et al.,2012), 来探讨IFTs与后果变量(如领导者——下属交换关系、工作绩效等)之间的关系。
第四, 进行IFTs的本土化研究。研究表明文化是内隐理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比如:Gerstner和Day (1994)在多个国家(法国、德国、中国、日本、美国等)检验了个体关于领导者的图式(即ILTs), 发现ILTs的内容在不同文化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 西方国家更强调“坚定(determined)”是典型领导者的特征, 而东方国家更看重“智慧(intelligent)”)。文化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IFTs。比如:西方领导者心目中的高潜力追随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激情” (Sy, 2010), 而我国文化中更看重稳重。此外, 与西方文化相比, IFTs在我国表现可能相对更为被动。比如:陈文平、段锦云和田晓明(2013)指出, 受中庸思想、高权力距离、面子等的影响, 员工建言行为在我国表现更少, 因此很难产生所谓的联产的(Carsten & Uhl-Bien, 2012)或者自下而上影响(Carsten et al., 2010)的追随者图式。因此, 开展IFTs的本土化研究也应该是有价值的。具体而言, 我们认为在IFTs的本土化研究中考虑下面这些问题是有必要的。(1)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IFTs的结构怎样?包含哪些内容?(2)具体从哪些方面来衡量文化?文化的哪些方面影响了IFTs在我国的具体表现?(3)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IFTs如何影响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态度和行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GLOBE项目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们也许是有启发意义的。GLOBE旨在探讨文化对领导力的影响, 该项目搜集了世界上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从9个具体的维度(譬如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人本取向等等)来解析文化(House, Javidan, Hanges& Dorfman, 2002)。在IFTs的本土化研究中, 我们可以借鉴GLOBE对文化解析的方法来具体探讨我国文化对IFTs的内容和结构的影响。此外, 有必要基于质化研究的方法, 开展广泛的访谈调研,提取归纳在我国文化中IFTs的内容和结构, 并辅之以量化方法的检验。总之, 今后可以结合我国文化的特点, 对IFTs的内容、结构、影响因素、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本土化研究。
陈文平, 段锦云, 田晓明. (2013). 员工为什么不建言: 基于中国文化视角的解析.心理科学进展,21(5), 905–913.
凌文辁, 方俐洛, 艾尔卡. (1991). 内隐领导理论的中国研究——与美国的研究进行比较.心理学报,(3), 236–241.
卢会志, 刘永芳, 许科. (2008). 内隐领导理论: 认知革命在领导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心理科学,31(1), 242–244.
杨艳, 胡蓓. (2009). 基于认知视角的内隐领导理论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31(8), 28–35.
原涛, 凌文辁. (2010). 追随力研究述评与展望.心理科学进展,18(5), 769–780.
Avolio, B. J., Walumbwa, F. O., & Weber, T. J. (2009).Leadership: Current theories,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1), 421–449.
Blau, P. M. (1968). The hierarchy of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4), 453–467.
Carsten, M. K., & Uhl-Bien, M. (2009).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 (IFT):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n IFT scale for the study of followership.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shville, NC, USA.
Carsten, M. K., & Uhl-Bien, M. (2012). Follower beliefs in the co-production of leadership.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220(4), 210–220.
Carsten, M. K., Uhl-Bien, M., West, B. J., Patera, J. L., &McGregor, R. (2010). Exploring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followership: A qualitative study.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1(1), 543–562.
Engle, E. M., & Lord, R. G. (1997). Implicit theories,self-schemas,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4), 988–1010.
Epitropaki, O., & Martin, R. (2005). From ideal to re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ole of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on leader-member exchanges and employee outcom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0(6), 659–676.
Epitropaki, O., Sy, T., Martin, R., Tram-Quon, S., &Topakas, A. (2013).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 “in the wild”: Taking stock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es to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4(6),858–881.
Foti, R. J., Thompson, N. J., & Allgood, S. F. (2011). The pattern-oriented approach: A framework for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4(1),122–125.
Foti, R., Hansbrough, T. K., Epitropaki, O., & Coyle, P.(2014). Special issue: Dynamic viewpoints on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5(2), 411–412.
Gerstner, C. R., & Day, D. V. (1994).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leadership prototype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5(2), 121–134.
Van Gils, S., Van Quaquebeke, N., & Van Knippenberg, D.(2010). The X-factor: On the relevance of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 for leader–member exchange agre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3), 333–363.
Hoption, C., Christie, A., & Barling, J. (2012). Submitting to the follower label: Followership, positive affect, and extra-role behaviors.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220(4),221–230.
House, R., Javidan, M., Hanges, P., & Dorfman, P. (2002).Understanding cultures and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across the globe: An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GLOBE.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37(2), 3–10.
Keller, T. (1999). Images of the familia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TheLeadership Quarterly,10(4), 589–607.
Kenney, R. A., Schwartz-Kenney, B. M., & Blascovich, J.(1996).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Defining leaders described as worthy of influen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2(1), 1128–1143.
Kruse, E., & Sy, T. (2011).Manipulating implicit theories by inducing aff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Conference, New York.
Lord, R. G., Brown, D. J., Harvey, J. L., & Hall, R. J. (2001).Contextual constraints on prototype generation and their multilevel consequences for leadership perception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2(3), 311–338.
Lord, R. G., Foti, R. J., & De Vader, C. L. (1984). A test of leadership categorization theory: Internal structure,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leadership perception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34,343–378.
Lord, R. G., & Maher, K. J. (1990). Alternative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5(1), 9–28.
Lord, R. G., & Maher, K. J. (Eds). (2002).Leadership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Linking perceptions and performance.New York: Routledge.
Macrae, C. N., & Bodenhausen, G. V. (2000). Social cognition:Thinking categorically about other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1(1), 93–120.
Martin, R., & Epitropaki, O. (2001).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ILT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work attitudes.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4(3), 247–262.
McGregor, D. (1966). 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Reflections, 2, 6–15.
Payne, B. K., & Gawronski, B. (2010). A history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Where is it coming from? Where is it now? Where is it going. In B. Gawronski, & B. K. Payne(Eds.).Handbook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Measurement,theory, and applications(pp. 1–15).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osch, E., Mervis, C. B., Gray, W. D., Johnson, D. M., &Boyes-Braem, P.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Cognitive Psychology,8, 382–439.
Shondrick, S. J., Dinh, J. E., & Lord, R. G. (2010).Developments in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pplication to improving measurement and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s to hierarchical leadership.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1(4), 959–978.
Srivastava, A., Bartol, K. M., & Locke, E. A. (2006).Empowering leadership in management teams: Effects on knowledge sharing, efficacy, and performa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9(6), 1239–1251.
Sternberg, R. J. (1985).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creativity, and wisdom.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3), 607–627.
Sy, T. (2010). What do you think of followers? Examining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13(2), 73–84.
Tram-Quon, S. (2013).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mplicit Measure of 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y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hl-Bien, M., Riggio, R. E., Lowe, K. B., & Carsten, M. K.(2014). Followership theor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5(2), 83–104.
Uhlmann, E. L., Leavitt, K., Menges, J. I., Koopman, J.,Howe, M., & Johnson, R. E. (2012). Getting explicit about the implicit a taxonomy of implicit measures and guide for their use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5(3), 553–601.
Whiteley, P., Sy, T., & Johnson, S. K. (2012). Leaders'conceptions of followers: Implications for naturally occurring Pygmalion effect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3(2), 82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