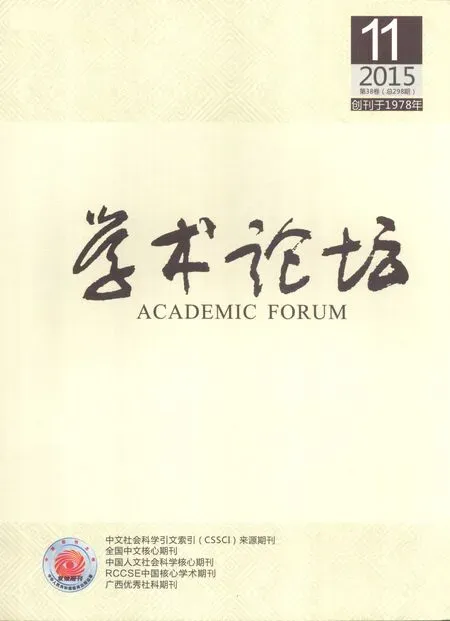清末政治变革中的海外华文报刊——基于方汉奇、谷长岭、叶凤美纂辑之未刊稿《海外华文报刊表》的考察
程丽红,顾颉琛
清末,伴随着近代中文报刊的问世以及华侨、留学生、政治流亡者的渐次增多,迎合华人社会的信息、商业、文化诉求,加之境外各派政治势力吸纳新生力量、宣传鼓动的需要,19 世纪50 年代后,在东南亚、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等异域他国陆续涌现了大量华文报刊。 海外华文报刊是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清末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们虽远离国土,却与国族命运声息相通,因之,厘清其历史,探索其规律,发掘其生长迁演之社会历史根源,极具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清代海外华文报刊作为海外华文报业的开端,在通史或宏观整体研究的著作中皆有所反映。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辟专节呈现其渊源与流脉,揭示其基本的生态、特色及意义;此外,如方积根、胡文英著《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2]、杨力著《海外华文报业研究》[3]、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4],以及程曼丽所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5]等,对清代海外华文报刊,亦皆有不同程度的观照。 但总的看来,把清代海外华文报刊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全景扫描,以清末社会变迁及报业运演为背景,透过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峰起并作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宏观剖视海外华文报刊的总体趋势和规律者,尚属罕见。 2005 年,方汉奇先生撰文《〈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6],根据他参与大清史编撰所掌握的数据,对清代海外华文报刊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尤侧重创办人群体的勾稽与分析,其中《1815-1911 年各时期海外各地创办报刊的数字统计表》《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出版地点分布情况统计表》和《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创办人情况统计表》,使得清代海外华文报刊的生长轨迹一目了然。 本来,以笔者的学养,触碰这一论题实力有所不逮,所幸的是,当方先生得知笔者正着手于“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国家课题后,慨然惠赐他与谷长岭、 叶凤美两位先生参与大清史编撰而精心整理辑录的未刊稿 《清史·史表》之《报刊表》,使笔者有了参与讨论的先决条件。 本研究主要依据该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表》及其注本与考异, 其收录了“清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644年2 月8 日) 至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 月12 日)”外国人、华人、华侨在中国境外出版的中文报刊,比之史和、姚福申、叶翠娣所编著《中国近代报刊名录》[7]不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而且重新发掘增添了一些报刊。 因而基于新史料的深入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本研究无意于细枝末节的微观考察,而重在规律的探索与总结,着力于对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历史进行整体、宏观审视,勾绘其基本的生长轨迹、 阶段性特征及生态环境与因素, 探索其发展的规律和个性, 进而揭示社会变迁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力图从与方先生文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重温这段历史。
一、报刊数量之起伏:内、外报刊体系的聚散离合
整个清末,海外华文报刊共有255 种①这与方汉奇先生《〈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文中提供的数据248 种显然有出入,但考虑到先生之文成于2005 年,而笔者手中之表标明为“2012.7 上报本”,其间跨越7 个年头,报刊表处于不断修润和完善过程中,很可能有所增补;再者,本文将各种刊物的增刊,以及承继前刊另立名目出版的刊物,都算作独立的报刊,单独计数,或许与先生存在着统计方法的不同。,其中包括各种报刊的增刊,以及承继前刊另立名目出版的刊物。 比之国内出刊总数的两千余种,即“国内汉文、少数民族文报刊表”收录1970 种,“国内外文报刊表”收录459 种②方先生的《清史·史表》之《报刊表》,主要由《国内汉文、少数民族文报刊表》《国内外文报刊表》《海外华文报刊表》三表组成。 其中,《国内汉文、少数民族文报刊表》收录清代在中国国内(含港、澳、台)出版的汉文(含文言、白话、方言、汉语拼音)报刊、少数民族文报刊和定期出版的报刊文字选编本;《国内外文报刊表》收录清代在中国国内(含港、澳、台)出版的葡、英、法、德、日、俄、意等外文报刊,包括外文与汉文合刊、外文与外文合刊。,仅是其十分之一,数量并不可观,但考虑到华侨数量以及异域他乡的办报环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菲。
海外华文报刊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端绪。早在19 世纪初《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南洋之时,国人尚不知报纸为何物,直到三四十年代,方有零星华字报闪现港澳穗等地,但是比起国内新兴报业的生长势头,海外华文报业则不免逊色,从1815 年到1875 年,60 年间仅出有12 种。 而两次鸦片战争门户洞开后, 国内仅60 年代就出刊10种,70 年代前半期发展愈发迅速,竟达到36 种之多,其中,日后声名卓著的大报《申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等,都于此间创刊。 究其实,早期海外华文报的目标读者在中国境内,只是迫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在南洋一带徘徊,俟时机成熟便转往国内,因而呈未兴反衰之势。 70 年代后期开始,海外华文报刊才摆脱目注大陆的内容基调,走上顺应在地文化与需求的发展道路。1876 年,成为早期海外华文报刊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年内共创刊6 种,为前60 年总和的一半。 就在此前一年,即1875 年,破天荒增新刊2 种,恐怕是这个高峰期的前奏。 对比整个清末报业的发展轨迹,海外华文报刊的这波高潮,似乎与早期国人办报的浪潮相吻合。 但是,细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着根本的性质差别。 早期国人所办皆商业报刊,办报人以思想趋新的亦绅亦商者甚至洋务官员居多,其中不少有官方背景,故明显表现出同情洋务、鼓吹西学的价值取向,亦不免流露向封建官府妥协的精神特质,但对待外国势力则富有抗争精神。 由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实助成之”[8](P153)、上海县知县叶固之“首先倡捐”[9]的《汇报》,便围绕各种议题与英商《申报》《字林西报》展开了多次笔战,发专文抨击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指斥其“以为华人可欺而任意上下其手”,“得寸入尺,犹不知止”[10]。 时值中法战争期间出刊的《述报》,则强烈谴责法国侵略者,坚决主张抗法,反对“输金议和”[11](P174)。 凡此种种,说明正处于身份转换中的绅商,仍保留着传统士人以道自认、关注国族命运的人文情愫,其所办报刊自然浸透着强烈的政治关怀。 而同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除《檀山新报》和《华夏报》言论有革命倾向外,大多是单纯的商业报刊,以刊载商业信息为主,服务于华侨的商务活动,与政治保持距离,稍事涉及政治的,也一律持保守立场,甚至反对西方文化,对国内的洋务思潮似乎并未觉察。1881 年创刊新加坡的《叻报》,设有京报选录、皇畿新语等栏,专载清廷谕旨、奏折,其社论、评论政治上即偏于保守,但始终维护华人权益。1890 年创刊新加坡的《星报》,更是思想保守,反对华人剪辫与学习西方文化。 此后至1898 年戊戌政变发生前,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比较平稳。1883 年出刊3 种,其后四年断档,但自1888 年后每年都有新刊面世,年创刊量大致1 到2 种,最多不过3 种。由此看来,海外华文报刊发展的第一个小高峰,显非迎合国内的洋务思潮,也并非与国人第一办报高潮同步调,境内与海外两支报刊力量远未实现统合,这在随后到来的维新运动中,又有很好的印证。
戊戌维新期间,海外华文报界的表现颇让人意外。1895 年8 月《时务报》创刊至1898 年9 月政变发生,国内改良运动狂飙猛进,将中国报业发展推向一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时期——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陆续问世的近代报刊达几十种之多,且大都谈时务、说变法,近代报刊成为维新宣传的重要工具。 而此间海外华侨却只创办了9 种报刊,其中,仅见吉隆坡《广时务报》与上海《时务报》及澳门《知新报》等遥相呼应,鼓吹维新变法,新加坡《天南新报》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算是对国内的政治思潮有些许回应,多数报刊则无明确的政治立场,以刊载商情为主,与国内如火如荼的变法宣传盛况极不相称。 显然,维新运动主要在国内开展,尚未向海外广泛拓展,尤其这一时期的变法活动过分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圈子,维新派的宣传也重在“开官智”,试图通过引导和影响统治阶级上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关注重心在朝廷各级官员,根本没有理会下层民众,更不可能把注意力投向海外的华侨。
1898 年戊戌政变,是海外华文报刊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或可说是另一个高潮的起点。 这一年创刊了4 种报刊,随后的一年也有4 种报刊问世,加上3 种具体创办时间不详但可以初步断定为19世纪末20 世纪初创刊的,政变发生后两年间,大致有11 种新刊出现,显示了向上生长的趋势。 主要是因为政变后,国内的维新报刊全部被封杀,大批改良派流亡海外,其宣传阵营也随之转向境外。接续这一势头, 海外华文报刊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10 年的高潮期。 1900 年达到了8 种,自此直至清王朝覆亡,不但每年都有新刊问世,更重要的是,发展势头始终不减,年出新刊最少的1901 年和1902 年,也在六七种,多则达到每年30 余种。其间尚有两个高峰:其一是1903 年,出刊18 种,比之前一年的7 种,与后一年的13 种,显得格外突出。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先锋,留日学生报刊为其主力。 另一个则在1906 年至1908 年,海外华文报刊达到前所未有的创刊高峰,3 年分别问世新刊20、35、30 种。 此时,中国道路进入了最后的选择期,各派政治力量针锋相对,殊死决斗,宣传战役尤为激烈,中国报业史上著名的保皇派与革命派报刊的大论战,主战场与分战场几乎都在境外,海外华文报刊壮大便顺理成章。 不难看出,戊戌政变不仅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同时也是一个颇富历史意义的界标,海外华文报业由此改变了在异邦联结华侨,争得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价值取向,转而以引导、策动、配合国内的政治变革为宗旨,汇入报业“政论时代”的洪流,国内与海外两大报业体系也最终完成了统合。
二、报业基地之迁演:从疏离国内政治变革到置身激流中心
华文报刊散布于华侨寓居的世界各地,从创办地点乍看显得杂乱无章,但详加查考,仍有规律可循,基本遵循着华侨流动的轨迹;反之,亦是华人移民大致线路、轮廓的投影。 形成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报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由于清廷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急于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外国传教士无法深入境内传教,于是把紧邻大陆、华侨聚居的南洋作为桥头堡,在这里办报传教,试图对国人施以间接影响。所以,近代报刊发端于南洋,早期的海外华文报刊也大都汇集这一带。 1858 年以前,共出刊7 种,其中4 种在南洋,另外3 种在美国。南洋的华文报刊主要是传教士面对华侨所办,且不时向中国境内发行,主要目的是传教,意在向国人灌输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 被称为姊妹刊的马六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巴达维亚《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皆是由基督教伦敦会英籍传教士所办、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的宗教报刊;既是重在新闻报道的马六甲《天下新闻》,也间刊宗教、伦理等内容。同时,美国出版的《金山日新录》《东涯新录》也不免展现浓郁的宗教文化意味。
1866 年至戊戌变法前夕,办报地点有西移的趋势。 此间海外华文报刊共有30 种,其中21 种在美国,欧洲也有出现,即伦敦的2 种,与先前集中于南洋的局势迥然有异, 显然是顺应了华侨向西方世界拓展的步伐。 另外,澳洲和日本亦现华文报刊,悉尼与东京各1 种,其他5 种在南洋。 南洋创刊数虽未衰减,但显然不敌美国的大幅度增势。 由此,华人流动的基本行迹已显而易见。
1895 至1898 年,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海外华文报刊发展比较平稳,仍集中于美国和南洋,欧洲国家偶有闪现, 说明国内蓬勃开展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波及海外。 戊戌政变则是个大的转折点,虽然之后的三四年间,美国新出刊仍为最多,这与康有为政变后以北美为基地组建保皇会, 发起新一轮宣传攻势密切相关,但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日本的华文报刊亦迅速成长,达到8 种,尽管不及美国,但较之此前零星出现的一二种,成长势头可谓更加迅猛。 特别在1903 年以后,日本新创办华文报刊始终居于首位,1903 年到1905 年底,共出刊46 种,日本就占26 种;1905 年底《民报》创刊以后,共出刊134 种,日本达72 种,其中东京就有70种,超过总数的一半。 不言而喻,与大陆比邻而居的日本在新世纪初年便迅速取代美洲,成为海外华人文化与政治活动的中心。
总的来说,清代海外华文报刊先后形成三大据点,南洋、美国和日本。 两次鸦片战争前,主要在南洋;其后至1903 年,重心转至美国;但癸卯年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以及日本成为保皇派、革命派活动的中心,这里又演变为海外华文报刊的重镇。报业基地的迁演固然与海外华人的足迹亦步亦趋,却也昭示了华侨同胞对国内政治变革从隔绝疏离到置身激流中心的艰难旅程,即从早期近处南洋却被动接受西方文化渗透,对国内政治思潮无知无觉,到远处美洲却心系国政,终至向近邻日本——政治活动中心聚拢回归的历史轨迹。
三、办报宗旨之流变:话语权的转换
从创办人和创办宗旨来看,清代海外华文报业也展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1855 年以前共有5 种,皆为传教士创办并主持,其中只有1 种由华人任中文编辑,显然这是一个外人操持华文报刊话语权的时期。3 种为宗教报刊,主要用于传教,其他2 种以新闻为主,但仍保留宗教内容。 尤其是旧金山的《金山日新录》自“称以解决华人在宗教上的无知,向华人解释美国法律,利商贾,资见闻,达舆情,而通官事等为宗旨”,显然是传教士向华人渗透宗教思想的重要渠道。 即便不以宗教相标榜的《天下新闻》,也有着对华人实行文化影响的宏远目标,试图改变华人对外国的偏见、错误的世界观念,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作舆论的、文化的准备。1855 创刊于旧金山的《东涯新录》,乃基督教长老会美籍威廉·斯卑尔(W. Speer)创办,华人Lee Kan(李根)任中文编辑,则以传播加州华人消息及基督教义为宗旨。
1856 年是个具有历史界碑意义的年份, 一方面,这一年由华侨司徒源创办、主编的《沙加缅度新录》问世于美国城市萨克拉门托,是为华人在海外自办的最早的中文报刊,属商业报纸,亦为在美出版之第一份中文日报。 另一方面,这也是宗教之外人士办华文报刊之始。自此,商业报刊明显增多,且大多为外人创办, 话语权仍由外人掌握。 1856-1880 年间,共出有华文报刊15 种,在外人创办主持的8 种报刊中,唯2 种由华侨与外人合办,旧金山《唐番公报》乃华人黄卓(Chock Wong)、美籍霍夫曼(J.Hoffman)合办;《文记唐番新报》乃美籍霍夫曼(J.Hoffman)、李文廷合办,李文廷主编。 此外,美国人主办的 《旧金山唐人新闻纸》 亦由华侨主编。 随着中国移民的不断增加,外人在华侨圈子看到了商机,遂利用中文报刊推广商品,扩大市场。另外7 种尽管没有明确的创办人,但从其“内容以当地华人社会新闻及娱乐、服饰、文艺等方面文字为主,多转自香港报刊”(纽约《星报》),以及《文记印字馆周报》富有中华文化印记的报名,可以初步判断不止一种为华人自办,显示了一种话语权过渡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漫长的开拓、蕴蓄和发展,华侨终于有了自办报刊的意识和能力。
总的看来,19 世纪60-80 年代,海外华文报刊以商业为主,且多为外人创办主持,个别由外人创办华人主编。 这期间可以明确为华人自己创办的只有《沙加缅度新录》和《华番汇报》两家,其中旧金山《华番汇报》还是承中外合办的《唐番公报》,由华人林赞(Lim Danc)接办。
1880 年以后,外人创办的华文报纸锐减,只有3 种,且都主要出于行业目的。如1894 年创刊于伦敦的《中英商工机械时报》,面向中国与朝鲜发行,由伦敦白来公司(Pelham Press)主办。 申明欲使读者明欧亚文明之所因异,与东西强弱之所因歧。 以介绍机器用途为主,刊有大量广告,旨在推销英国机器。1895 年创刊于不来梅的《日闻》,由东方语言学者德国人布来恩(B.Brin)主办,以介绍中国及中德商务发展情况为主。 与此同时,华人主编的报纸急剧增加,达16 种之多。 其中大多为商界华侨所办的商业报刊,主要服务于华侨,报道当地侨界消息,联络华侨,维护华人权益。 如芝加哥《华美新报》即宣传华人放弃陋见,团结起来,在华人区杜绝烟、赌、嫖,以树立华人自重自尊的新形象,进而推动华人进入主流社会;悉尼《广益华报》亦自称以为广大华人谋利益为宗旨,内容以广告为主,兼刊澳洲各地华人社区动态报道。 可见,从19 世纪80 年代开始,华人终于夺得了话语权柄,海外华人报刊创办人与主编,主要为华人。 但初期也以商业为主,多为商业报刊。 个别如旧金山《美国正埠救世军报》、纽约《华英经报》则重在传教布道,后者为基督教教会刊物。
1898 年应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此前即便是华侨所办报刊,也多属商业性质,服务于华商业务;此后,政治性较强的报刊,尤其是党派机关报如保皇党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革命派的《民报》等大量涌现,党派报刊与政治倾向鲜明的民办报刊占据了绝大比重。 海外华文报刊不再单纯为华人利益与团结造势,转而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声息相通, 即便是非党派的民办报刊,也展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向。 如侨商潘庶蕃创办、陆伯周主编的岷埠《益友新报》,其言论便倾向保皇会;华侨主办的棉兰《苏门答腊报》,则支持反清民主革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戊戌政变后,保皇派的宣传阵线转向海外, 特别在1905 年以后,革命派的宣传活动进入高潮,而其报刊的主要阵地皆发端于海外, 遂成为海外华文报刊崛起的根本致因。 尤有甚者,清末十年,乃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总决战的时期, 因而宣传战役也进入了最后的会战阶段,海外华文报刊迎风逐浪、繁荣壮大自在情理之中。 而作为海外华文报刊队伍最重要的生力军,留日学生报刊自1900 年不断涌现,整个清末大致创有64 种之多,成为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由于学费偏低,科举制废除,特别是甲午战败师法日本的直接动力, 使大量青年学子负笈东渡, 寻求人生发展和救国道路。 据载,20 世纪初年中国留学教育出现第一次高潮期间,仅留学日本人数就曾达到过近2 万名;而留日史上最高峰的1905、1906 年, 两年间留学人数累计8700 人[12](P36-39)。此时的中国,正经历从器物到制度改革失败后的彷徨与迷惘,寻找新的强国之路、摆脱覆亡之命运成为时代主题。 围绕中国向何处去问题, 资产阶级保皇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主战场即在日本。 对新思想有着特殊敏感、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投身时代激流,办报立言,声援社会政治运动,致留日学生报刊数量剧增,当然在所难免。 但受留学时限的制约,留日学生报刊大都寿命短暂, 且集中于留日学生居多的东京和横滨等地。
综上,清末海外华文报刊从弱小到壮大,从外人掌控话语到国人自主舆权,从疏离国内政治变革到置身政治激流中心,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但终不失传统媒介文化的精神底蕴,与境内报刊相应和,引导、策动、推助着各时期的政治运动,对清末社会变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3] 杨力. 海外华文报业研究[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4] 王士谷. 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5]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6] 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 J].国际新闻界,2005,(5).
[7]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 论新闻日报馆事[N].申报,1874-02-17.
[10] 论中外涉讼事[N].汇报,1874-07-27.
[11] 李磊.述报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12]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