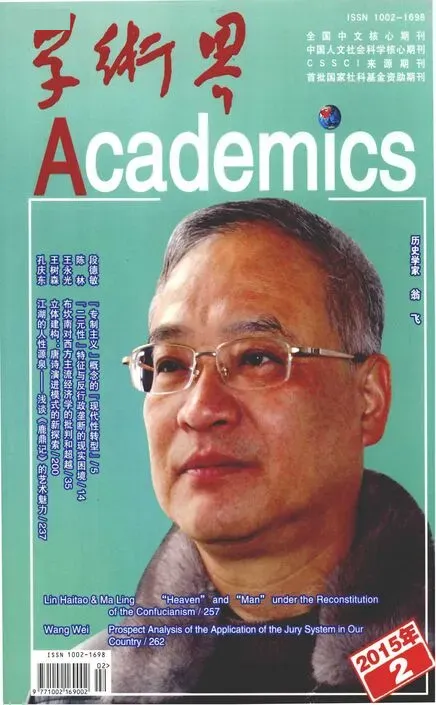傩的泛化:“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傩文化理论探讨之二
○任 伟
(1.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2.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作为一种由原始先民的狩猎、巫术活动发展而来的文化实践行为,〔1〕傩活动可谓历史悠久。分析傩文化活动的衍变会发现,客观而言,傩文化在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泛化”现象,这种“泛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间的泛化、空间的泛化和鬼神的泛化。正是这种“泛化”,使得傩文化活动突破了“礼”的囿限,从而走向了世俗化、生活化和地方化,由“千人一面”渐变为“千人千面”,最终为傩的“戏化”、傩戏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一、时间的泛化
考察傩文化发展史,在时间发生上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是时间上经历了由一年三次到集中岁末再到和节日民俗结合的相对固定,最后发展到不再固定、随时可行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一年三傩”到“岁末驱傩”
关于傩文化活动最初进入礼制,饶宗颐先生据《太平御览》引《世本》有“微作禓”的记载,认为“傩肇于殷,本为殷礼,于宫室驱除疫气。”〔2〕《礼记·月令》记载的傩则为调和阴阳之气、促进四季有序而举行:
(季春)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郑注: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至,害将及人。……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殴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3〕
(仲秋)天子乃傩,以达秋气。郑注:此难,难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于是亦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难之。〔4〕
(季冬)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5〕
从以上记载看出很明显是“一岁三傩”,而大暑之际,正是阳气极盛之时,万物生长均需阳气,故不举办傩事。其余几次分别是为“毕春气”、“达秋气”、“送寒气”,均需以傩磔禳建福、调和阴阳。虽然在《周礼·夏官·方相氏》的主要职责上也规定大丧入圹先驱,但主要的驱傩活动还是一年三次。《太平御览》卷五三〇《礼仪部九·傩》引《礼记外传》云:“方相氏之官,岁有三时,率领群隶,驱索疫疬于宫室之中,亦攘送之义也。”〔6〕
两汉的宫廷傩制,第一次把傩祭和年终的腊祭结合起来,从而拉开了傩的“礼仪化”、“程式化”的序幕,由“一岁三傩”渐渐发展到固定在年终岁末的驱傩。虽然隋朝时期尝试恢复一岁三傩的旧制,但并不持久,到唐代开始又恢复到年终驱傩。
(二)节庆化
与集中到岁末的固定行傩相比,节庆化的行傩带有相对固定的意味,因其大多不是在年终而是在其他时间,因而明显具有从固定到随时的过渡意味。
节庆化的发展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单线条性,而是呈现出一种交叉的态势,也是其受到傩祭活动娱乐化、世俗化影响的结果。
节庆化驱傩活动最典型的是与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结合,因其与祖先祭祀和鬼魅亡灵的度脱救助相关联而被纳入傩活动的视野,很多地方都会举行驱傩活动,自然地把逐除还愿和祭奠祖灵、超度亡魂结合起来,由一个“幽灵的节日”(太史文语)过渡到一个“幽显同欢的节日”〔7〕。今天也是如此,如贵州安顺的“地戏”。在七月半表演时称作“跳米花神”,“寄托逐除还愿和超度鬼魂之意”。〔8〕特别是期间常演的目连戏,在宋代就开始流行,后世则更与行傩结合起来,而且不限于中元节表演。如清人昭梿《啸亭续录·大戏节戏》:“……又演目犍连尊者救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於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9〕汪晓云也认为:“目连戏实际上是傩仪的佛教形式,诞生目连戏的盂兰盆会与诞生傩戏的傩仪一样,都是为了驱鬼,盂兰盆会只不过是佛教对傩仪的‘加工’与‘改造’”〔10〕
这种节庆化也表现在傩与节气的相关性。如“白露”在二十四节气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秋季节气。白露的到来,意味着阴气上升,天气转凉。《管子》卷第十四《五行第四十一》就指出:“凉风至,白露下”。〔11〕《逸周书·时训解》也云:“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12〕在古代,仲秋是举办“时傩”以磔禳的时令,《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郑玄注曰:“此难(傩),难(傩)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气佚则厉鬼亦随之而出,于是亦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难(傩)之。王居明堂礼曰:‘仲秋九门磔禳,以发陈气,御止疾疫’。正义曰:秋凉之后,阳气应退,至此不退,是凉反热,故害及于人。”〔13〕若暑气当退不退,“秋气不达”即所谓“仲秋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14〕自然也容易给人带来疾病。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有白露道场活动,也是古傩“以达秋气”习俗的遗留。〔15〕而且,对于地处西北的敦煌地区,白露之前,秋收已经结束,一年的稼穑农事活动均已完成。白露道场的举行,也有着酬佛酬神的意味。今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还傩愿活动就选择在秋收后举行,即所谓“如今秋收般般有,总是酬神还愿时”〔16〕。也可以说,这时的傩已经扩大为驱除疠疫,兼有酬神酬佛的意味。
明清时期,驱傩有在十月举行的,也是傩事活动节庆化的一种表现。如明朝时期,广东十府“十月傩,数人衣红服,持锣鼓,迎前驱,辄入人家,谓逐疫。或祷于里社,以禳大灾”。〔17〕再如据光绪《广西省临桂县志》载:“今乡人傩,率于十月,用巫者为之,谓之跳神。……”〔18〕
同时,这一时期的行傩已经大大突破了时间上的相对固定,而且名目更多,一年之中几乎每个月都可举行。如研究者考述江浙一带的民间傩事:
延至清末到民初,江浙一带傩戏大兴,几乎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迎傩之举。如一月有“上元傩”(民国《昌化县志》卷六)、二月有“立春傩”(光绪《遂昌县志》卷十)、三月有“上巳傩”(光绪《永嘉县志》卷六)、四月有“清明傩”(光绪《松阳县志》卷五)、五月有“端午傩”(民国《衢县志》卷八)、六月有“保安傩”(民国《龙泉县志》卷十一)、七月有“中元傩”(民国《衢县志》卷八)、八月有“驱蝗傩”(光绪《上虞县志》卷三十八)、九月有“朝案傩”(民国《汤溪县志》“文征”)、十月有“立冬傩”(民国《鄞县志》卷二)、十二月有“祀灶傩”(光绪《宁海县志》“风俗”)。〔19〕
很显然,这些时日不定、名目繁多的行傩活动,与传统的节庆礼仪融合在一起,也间接地延续了古傩“调和阴阳”之用的传统。
傩事活动的“节庆化”还表现在和佛教其他节日的融合。这种现象,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就已经出现,典型的如“踏悉磨遮”。“悉磨遮”又称“苏摩遮”,本是传自西域的一种傩戏,目的是禳灾祈福。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苏幕遮冒”条的解释云:
……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20〕
显然,慧琳所记“作兽面”、“象鬼神”的“苏幕遮”并非在岁末除夕举行,而是在七月“公行”,且“七日乃停”。活动的目的也是“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这里已经包含了驱傩活动节日化到常态化的一些因素。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则更是和佛教节日融合在一起,如敦煌文书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记载:“(庚申年)二月七日,支与悉磨遮粗纸叁拾张。”〔21〕S.1053《己巳年(909 或 969)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残卷》有:“粟叁斗,二月八日郎君踏悉磨遮用。”〔22〕结合前件文书可知,头天支取粗纸,以供第二天使用。“踏悉磨遮用”的时间是“二月八日”,恰是佛教僧徒颇为重视的“佛诞日”。
需要指出的是,本为“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而设的“悉磨遮”和佛教节俗融合在一起,但其祀神祭鬼、驱傩求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傩的“节庆化”打破了时间上的固定性,拓展了傩的主题,突破了傩作为“礼”的局限,使“傩”进一步走向“民间化”。
(三)随时化
行傩之举走到相对固定的“节庆化”,离完全打破时间的约束,成为民众“祈福禳灾”、“驱邪除难”的随时可办的仪式活动也就一步之遥了。从“节庆化”到“随时化”不过是傩文化一种合乎情理的延伸。〔23〕典型的如常在傩事活动中搬演的“目连戏”,唐宋以来固定在七月十五的“鬼节超度”仪式到后世则演变为“驱邪禳灾”的演剧,尤其用在地方性大疫、兵燹之灾后的超度、祛邪活动中,已经不再局限于和节庆的融合了。如清同治间莆人郭篯龄《山民随笔》记云:“吾莆兵燹大疫之后,类集优人演《目连》,俗谓可消殄戾。”〔24〕宣统《广安州新志》卷34也说:“祈祷雨泽,有东窗戏。驱逐疫厉,有目连戏”。〔25〕
傩事活动“节庆化”趋势的继续发展,自然就会完全打破时间的规定,由官方的意愿变为民众自己的安排,这也是今天仍然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愿傩”一类活动出现的契机。如据傩学者调查,今天的土家族中间,“治病、消灾、求子、保寿,都要请土老师(傩法师,引者注)施法;打扫屋子,要请土老师‘跳神’,祈保一年中无灾无难,平安无事;壮年夫妇无子,要请土老师‘冲傩’,许愿还愿,以求生子;生了病,要请土老师扎‘茅人’、‘冲消灾傩’,以求病愈;家里逢凶事,要请土老师‘开红山’,化凶为吉;老人生日要请土老师‘冲寿傩’,祈求高寿;在孩子十二岁前,要请土老师‘打十二太保’、‘跳家关’、‘保关煞’,以保小孩过关,不遭灾生病,易长成人”。〔26〕
另据晏晓明先生实地考察,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仅表达诉求、祈福纳吉的“傩愿”名目就有61种,而且相传更多,达120多种,这些“傩愿”流传的民族地区及流传的名目大致如下:
仡佬族地区:青草愿、招亡愿、竹愿、过关愿、过山愿、财愿、敬白虎愿、河婆愿、傩愿、猖王愿、秧苗愿、请阴府愿。
土家族地区:敬磨子坛、斋愿、押愿、罗侯愿、戏愿、消财愿、半傩半霄(愿)、敬龙神愿、赶山愿。
苗族地区:苗愿、魈愿、童子愿、贺喜愿、灯花愿、封社愿、秋愿、耕春愿、结拜兄弟愿、笑和愿、富家愿、敬龙(火)神愿、庆坛愿、青山愿、人头愿。
侗族地区:喜傩愿、侗愿、五丧愿、寿愿、跳鼓愿、药愿、烛愿、祭祖愿、端午愿、敬老鹰愿、和愿、立夏愿、喜愿、子孙愿、劝和愿、敬雷神愿、花船愿、团圆愿、月半愿(又名回阳愿)、口愿、收魂愿、祭牛愿等等。〔27〕
从这些资料也可看出,傩文化发展到随时可行,主题也更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中各个时期的重要内容。
二、空间的泛化
傩的泛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空间的泛化。空间的泛化又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大的范围从宫廷傩到乡人傩,并出现在寺院和军营,最终进入寻常百姓家。
根据《礼记·月令》,“一岁三傩”(季春、季秋和季冬“国傩”)在规定时间的同时,也规定了行傩的空间,局限于国都所在。〔28〕
直到唐代“诸州县傩礼”的规定,才为地方傩开了“绿灯”,真正拓展了行傩的空间,标志着傩礼由京城走向地方的开始。随着宋室南渡,傩也向着南方特别是一些巫风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蔓延,并迅速和当地民俗融合,产生出花样繁多的地方性傩文化品类。
进入军营的傩活动,零星见载于一些史料中。军队本来就是很特殊的一支力量,驱逐鬼疫的傩事活动应该很早就进入军营了,惜并不多见于记载。《荆楚岁时记》引《晋阳秋》载:“王平子在荆州,以军围逐除,以斗故也”〔29〕。这当是地道的“军傩”,兼具祭祀驱傩和鼓舞士气的双重意味,算得上后世军傩的先机了。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的“静江诸军傩”〔30〕同样不过是诸州县傩、乡人傩向当地驻军一种合乎情理的延伸。明清以后还有贵州的地戏和云南的关索戏,也是军傩的遗留。
寺院里行傩,最早应是随着佛教进入驱傩活动而来,但成为一个傩的品种则要很晚。〔31〕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本土化,特别是中唐时期密教的发展,寺院傩兴起,傩进一步扩展到寺院之中。寺庙也成为了相对固定的驱傩场域,比较典型的如藏传佛教寺院举行的“羌姆”仪式。自公元八世纪由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创立,至今久演不衰。“羌姆”仪式演化到清代,还由寺庙进入了宫廷,即所谓“跳布扎(打鬼)”活动。据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记载:“(乾隆年间),(中正殿)殿侧束草为偶,佛事毕,众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门外送之。盖即古者‘大傩逐厉’之义。清语谓之‘跳布扎’,俗谓之‘打鬼’”。〔32〕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云:“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根除不祥也。每年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33〕其表演显然类似于今天藏地寺庙的年终傩戏“羌姆”活动。
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有寺院组织的傩队,但未见到受密教影响在寺院表演“羌姆”活动的记载,这只是僧人组织傩队参与驱傩。
随着傩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蔓延,傩和民间巫术等地方民俗文化的联系也日渐紧密,尤其是和许愿、酬神还愿等活动融合而产生的傩愿活动,使其在空间上进一步拓展,并进入寻常百姓家,从而更加灵活,可集中举办,也可分散进行。对举办傩事活动的约束进一步减少,傩的发展更加自由,和宗教、地方民俗结合得更加紧密,也为傩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还需说明的是,后世将傩分为宫廷傩、乡人傩、寺院傩和军傩,正是就傩的空间变化而言的。
(二)从索室驱疫、沿门逐疫到结坛堂傩,从分散到相对集中,逐渐向场域化表演过渡。
傩在空域上的变化大体趋势是从索室驱疫、沿门逐疫过渡到坛场傩、堂傩,但并不是后者完全取代前者,而是二者的并行。
索室驱疫、沿门逐疫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普遍的驱傩方式。早在《周礼·夏官》中记载的傩仪就有“索室驱疫”,即“逐室而索”之举。《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国人傩,九门磔禳”也云:“命国人傩,索宫中区隅幽暗之处,击鼓大呼,驱逐不祥,如今之正岁逐除是也。”〔34〕可见东汉时期也是如此。直到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记载南宋时期的乡人傩:“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35〕从其中“敲锣击鼓,沿门乞钱”可见,还是“沿门逐疫”的形式。
又,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三《风俗》“除夕”条云:“是夕,具牲礼,扎草舡、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吼怒,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36〕直到今天,索室驱疫、沿门逐疫还是在傩事活动中出现。如云南哈尼族每年七月天气暑热、瘟疫流行之际举行的“那梭咧”活动,就是走村串户驱病逐邪的。〔37〕索室逐疫、沿门逐疫是驱傩活动的最基本形式,这种传统今天依旧保留,足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傩的泛化在空间上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从流动性很强的“游傩”(分散驱傩)渐渐趋向于集中性的“堂傩”,但并非单向的线性发展,而是多种形式的交叉。后期的傩同样有流动性的活动形式(已见前述),但总的趋势是由分散走向集中,尤其随着傩的“戏化”,傩戏产生,这种特点更为明显。
实际上,早在《周礼》中记载的“堂赠”礼,就是一种傩仪集中的雏形,但后世未见记载,可谓“昙花一现”。直到唐代,“堂赠”大傩又一次出现。作为初唐的傩制,刺激了傩的堂室化。〔38〕
坛场傩的出现同样与佛教介入驱傩活动有关。佛教的佛事法会活动,尤其是密教活动,常常要设坛置场。唐代出现的坊巷傩,也是集中结坛以驱傩的活动形式,同时体现了傩和密教仪轨的结合。如敦煌地区流传的傩词《儿郎伟》中就有“请佛九处结坛”。〔39〕显而易见,也是盛行当地的密教仪轨和傩俗的结合。
需要补充的是,寺院傩也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场域化表演的傩活动,对傩戏的产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三、鬼神的泛化
从整个傩文化的发展来看,鬼神的泛化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驱傩鬼神到宗教的鬼神介入,而随着古傩向地方的蔓延,在鬼神信仰观念的影响下,傩神谱系也吸收了地方鬼神,并加入社会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庞大、也更为繁杂的鬼神体系。
(一)传统傩事中的鬼神不断变化,由个体转向群体,宗教和地方鬼神渐成主力。
传统傩事中,最早职司其事的是方相氏,《周礼·夏官》中规定其职责,既率百隶参与驱傩,同时又参与丧仪,“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40〕
汉代傩礼加入“有衣毛角”的“十二兽”,〔41〕作为方相氏的助手,说明随着鬼神信仰观念的发展,傩神的队伍有所增加。
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傩公、傩母,据唐人李倬《秦中岁时记》引:“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傩公、傩母。”〔42〕唐宋时期,开始出现一个后世人所共知的驱傩神——钟馗,取代方相氏。宋以后还附会出小妹,并陆续加入了城隍、判官、六丁六甲、童男童女等民间传说神。
传统傩神不断变化的同时,宗教鬼神也加入了驱傩队伍,而且和地方傩神渐成驱傩的主力。
巫术和宗教先天就有着姻亲关系,宗教介入傩仪,主要是宗教的鬼神进入驱傩活动,扮演着傩神的角色。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宗教,直接介入傩活动,则要晚一些。〔43〕各种宗教中,较早介入的是佛教。〔44〕南北朝以降,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成熟,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日渐明显,佛教越来越多地介入民俗,这种特点也越来越突出。唐以前的民间傩少见记载,具体情形不易推知。从敦煌现存的相关资料看,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作为“华戎交汇之枢纽”,佛教十分盛行,受其影响,敦煌的民间傩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不但有专门的寺院傩队,敦煌民众也把佛教的众多神灵,像观世音菩萨、阎罗王、牛头狱卒、五道将军等纳入到傩神谱系中,密教的仪轨、坛场也渗透到傩事活动中。此外,敦煌还有祆教傩队的参与。〔45〕
随着傩文化地方化,傩和本土民俗结合得更加紧密,在地方性鬼神信仰观念的影响下,地方神怪也渐渐出现在傩事活动中,并由此影响到民众驱傩的内容、结构以及形式的变化,催生出“千人千面”、地域特色鲜明的各地傩文化。典型的如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有三危圣者、金鞍毒龙等明显具有地方特色的山川神灵。后世进入傩神行列的还有南方的梅山神、西南地区的昭明太子、二郎神和驱蝗神刘猛将军以及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神怪灵鬼。今天各地的地方神灵鬼怪更是层出不穷,难以胜数。
驱傩毕竟是以鬼神的存在为前提的,而民众的鬼神信仰观念则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变化,就使得原有的鬼神队伍因后来者的加入而不断壮大。从地方观念而言,各地又本来都有自己原始的宗教话语体系和地方神灵谱系,随着宗教的成熟和对民间信仰的介入,地方鬼神信仰观念和宗教话语体系得到整合,道教、佛教的鬼神也被叠加进入傩神的行列,从而使得驱傩的鬼神队伍越发庞大而杂乱,而且由于地方鬼神的引进,地方傩的鬼神谱系也呈现出“众神杂糅、一神独尊”的格局。〔46〕
余大喜先生曾著《中国傩神谱》按照主神、善神、凶神、动物神对中国的傩神作了分类,收录了166种图谱,并分别从其来源、功用等作了分析。〔47〕但实际上若对各地的傩神完全进行分门别类、归纳统计,显然远超此数。吴电雷先生仅对西南地区阳戏神祇做的统计,就已达到183种。〔48〕今天各地的傩戏种类繁多、各成体系,要细加整理,无疑是一项不小的文化工程。
正如巫瑞书先生所言:“缘于原始宗教系多神教,傩祀活动及傩戏唱演的地域相当宽广,各地区、各民族的傩神也往往因地而异。在众多的傩神中,既有本民族、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傩神;也有外地因移民、战争、文化交流等社会原因而移植的傩神。……因而,傩神呈现出来的是颇为繁纷、复杂的现象。”〔49〕
随着本地鬼神的加入,傩文化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驱傩鬼神的队伍则更加庞大,新旧杂糅、纷缛交错。更因地方鬼神的加入,扩展了傩文化的功用,傩活动不再局限于“驱鬼逐疫”。如前所述,大凡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大难小疫,乃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以及事业、生活中的任何不顺心、不满意都可以请傩法师予以禳除或以之祈福求祥,从而大大拓展了傩活动的领域,使傩进一步“生活化”,同时也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仰上的补充。
(二)社会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及敌对势力也被看做是鬼神,加入驱傩活动。
值得提及的是,傩文化的鬼神谱系中,也渐渐出现了社会历史人物,特别是古圣先贤和英雄人物被附会为鬼神。比较典型的如西南各地流行的驱蝗神刘猛将军,罗振玉《俗说》引朱坤《灵泉笔记》:“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敕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蝗遂殄灭。”〔50〕认为是宋代抗金名将刘锜,也有认为驱蝗神是元人刘承忠。〔51〕而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52〕又以南宋进士刘宰为驱蝗神,但都是以历史人物作为傩神的。
又如关公、张巡、许远等或因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被怀念,或因其英勇无畏、安定乡里而被敬重,也同样出现在后世的傩神谱系之中。
据前述余大喜先生《中国傩神谱》一著,收集的历史人物就有姜子牙、关公、包公等,其中甚至还有柳宗元等文人。而据前述吴电雷先生统计,仅西南阳戏中出现的历史人物除去和余大喜先生所统计的重复的,有孔子、李冰、项羽、华佗、姜维、秦叔宝、尉迟恭,此外,还有如西南地方公认的驱蝗神刘猛将军等,既是历史人物,又与地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说明各地傩神谱系的繁杂。
值得注意的是,中古时期的敦煌民众不仅驱逐虚幻的鬼怪,也把现实中敦煌周围屡次犯境、带来战乱和不安的少数民族势力看作“鬼怪”,期望借着岁末驱除鬼怪的傩事活动一起逐除,敦煌现存的一些傩歌中屡屡提到的“大王是上方菩萨”等则把对地方长官的功绩赞颂也融进傩事活动中,从而给驱傩增添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扩大了行傩驱疫的范围,也是傩事活动中鬼神泛化的表现。
四、傩的“泛化”的意义
(一)从礼到俗
傩的泛化既是古傩世俗化的原因,也是其世俗化的结果:泛化导致俗化,俗化更加速其泛化。傩的泛化打破了“礼”的约束,拓展了傩的功用,使傩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种泛化实质上是对傩作为“礼”而表现出的程式化的突破。大凡载于典籍的每一种“礼”,都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时效性。也就是说,古代《礼志》中所记述的形形色色的礼仪活动,无论是吉礼、凶礼,还是军礼、祭礼,必然都有举行的时间、地点和严格的操作程序。事实上,作为“古礼”列于正史的傩也曾经一直符合这一特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一方面彰显出“礼”的庄严性、隆重性,更主要的也是作为“礼”的可操作性。但傩文化活动本身是在鬼神信仰前提下的“驱鬼逐疫”,这已暗含着操作上一定的灵活性,也暗示着后世发展中的变异性。可以预期,只要鬼神信仰观念这个前提发生变化,则其影响下的以“驱鬼”为旨归的大傩活动必然相应发生变化。从前代方相氏职责的多样化到两汉傩制傩的功能的拓展,〔53〕再到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的“腊鼓鸣,春草生,村人打细腰鼓,戴胡公头,乃作金刚、力士以逐除”(见前)以及佛教、道教神祇及仪轨融入驱傩,不过是这种信仰观念合乎规律的衍变和递增。
从傩的发展来看,这种程式化大致在汉代定型。《后汉书·礼仪志》详细记载了这套近似“固化了的程序”的仪式举行的整个过程。〔54〕(已为研究者熟知并广为引用,不再赘述)自汉至唐,这套近乎固化的程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大唐开元礼》详载的傩礼过程中,只是增加了一个祝告太阴神的礼仪。〔55〕
傩的程式化、定型化,凝固了驱傩活动的模式,虽然带来了傩作为“礼”的操作上的便利,但同时也僵化了其运行机制,约束了其变异的幅度,使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一种文化,若没有新鲜血液的输入、更新,最终必然走向萎缩和消亡。这也是古代诸多礼乐文化的种类和范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作为“礼”范畴的傩文化,之所以能突破“礼”的约束而冲出重围,恰恰得力于其“虽古礼而近于戏”(朱熹语)的特点,先天地具有“泛化”的因素。正是这种突破时空、鬼神谱系的“泛化”,使得傩一步一步淡化了“礼”的色彩,终于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俗的舞台并在其中大显身手,找到了自己广阔的天地。而摆脱了由僵化而趋于消亡的命运,对傩文化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大幸。
(二)从戏傩到傩戏
宋代理学家朱熹就古傩那句很有见地的断言:“傩虽古礼而近于戏”,代表着南宋文人对作为“古礼”的“傩”的评判。实际上这种“近于戏”的“古礼”,在长期的发展中,其先天而来的“戏”的成分一直在潜滋暗长,并随着宗教的介入日渐明显。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扮胡公头、金刚力士”,“戏傩”的意味已经初见端倪。发展到唐代的傩虽然仍列于正史,而且《大唐开元礼》明确规定了宫廷傩和州县傩的规模、程序,但“戏”的成分更加明显,特别是统治者“阅傩”活动明显带有排练、预演的意味。两宋宫廷傩虽然照常举行,但参与者主要是教坊艺人,其表演的性质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说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结合佛教节俗举行的“踏悉磨遮”等活动,仪式的意味还很明显,那么在两宋时期,我们看到频频出现在搬演现场与傩相关的内容仪式的色彩已经淡化了,似乎也正可印证朱熹的论断。〔56〕
当然,这时候的傩要素还是夹杂在准戏剧的演出中,作为点缀。南宋以后,作为文艺形式的戏剧成熟,并进而影响到傩文化,傩事活动吸取了戏剧的一些因素,推动着傩由戏傩发展到傩戏阶段,并在辗转流播的进程中融入了地方元素,以独具特色的“地方傩”的面貌出现,并沿着各自的传承脉络延续至今。
五、结 语
傩的泛化从时间、空间和鬼神几个方面打破了“礼”的约束,也打破了傩的“千人一面”,为傩的地方化打开了大门。今天,傩文化成为涵盖几大洲、遍及东亚、东南亚的一种文化事象,并在国内繁衍孕育出云南的关索戏、贵州安顺的地戏、湖南辰州的土家傩、武安的打黄鬼、西南重庆贵州等地的阳戏、广西壮族、瑶族的师公戏等名目繁多、种类各异的地方品种,呈现出“千人千面”的崭新风貌。〔57〕
注释:
〔1〕关于傩文化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但多数研究者认可傩文化起源于先民的狩猎和巫术活动。
〔2〕饶宗颐:《殷上甲微作禓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35页。
〔3〕〔4〕〔5〕〔13〕〔1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1-572、615、653、615-616、620页。
〔6〕〔宋〕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05页。
〔7〕王馗:《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台北:国家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8〕张华:《中国民间舞与农耕信仰》,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9〕〔清〕昭梿撰:《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7-378页。
〔10〕汪晓云:《傩仪:中国戏剧的仪式发起点》,白庚胜、俞向党、钟健华主编:《追根问傩国际傩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11〕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76页。
〔12〕黄怀信等编:《〈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15〕由敦煌文献S.4664《某寺为白露道场告诸团僧课念帖》、P.2255V《祈福发愿文》可知,当时敦煌僧俗民众要举行“白露道场”活动。(图版见于《英藏敦煌文献》第六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法藏敦煌文献》第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
〔16〕刘兴禄:《愿傩回归:当代湘西用坪瓦乡人还傩愿重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31页。
〔17〕〔明〕戴璟、张岳等纂修:《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38页。
〔18〕光绪六年补刊《临桂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191页。
〔19〕转引自张爱萍著:《中日古代文化源流——以神话比较研究为中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20〕〔唐〕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徐时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1页。
〔21〕〔22〕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61、340-341页。
〔23〕傩的本旨就是“驱鬼逐疫”,人们往往把大灾小病特别是一些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都归因到鬼怪妖魅的“作祟”上,疾病灾害随时都会发生,与之相应,行傩逐疫之举也逐渐走向“随时化”。如据杨化育等修纂的民国《沿河县志》记载:时人“信巫不信医”,得病后往往请端公“跳神”、行傩,“城乡均染此习,冬季则无时不有”。从这一记载看,其时傩的举办即已渐趋“随时化”了。
〔24〕转引自林庆熙:《福建莆仙戏〈目连〉》,《戏曲研究》第37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25〕《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58》《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18页。
〔26〕刘锡诚:《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27〕晏晓明:《思州傩愿脚历史轨迹及愿目特征考述》,《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5期,第77页。
〔28〕包括诸侯和天子的国都。虽然《论语》中记载“乡人傩”,但没有证据表明是在国都以外的地方,所以很可能还是在国都举行大傩时允许乡人参加而已。《太平御览》卷五三〇引唐人成伯玙《礼记外传》即云:“大傩者,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命国傩者,但于国城中行之耳。”
〔29〕〔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3页。
〔30〕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6页。
〔31〕虽然据宗懔《荆楚岁时记》,村人戴胡公头、扮金刚力士参与驱傩,但未见寺院里行傩的记载,推测寺院傩的出现要晚得多。
〔32〕〔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4页。
〔33〕〔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34〕〔秦〕吕不韦等撰:《吕氏春秋》,〔汉〕高诱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25页。
〔35〕〔宋〕吴自牧:《梦粱录》,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81页。
〔36〕〔明〕王耒贤修、许一德纂:《(万历)贵州通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37〕卢朝贵《哈尼族哈尼支系岁时祝祀》原载于《云南民俗集刊》第四集,转引自王胜华:《中国早期戏剧的巫傩形态》,《戏剧艺术》2001年第3期,第82页。
〔38〕《周礼·占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荫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即傩),殴疫。”按照古人的观念,恶梦显然也是鬼神为祟的结果,堂赠即是大傩的一种形式,二者当是一回事。所以《旧唐书·礼仪志四》:“季冬晦,堂赠傩,磔牲於宫门及城四门,各用雄鸡一”就直接称为“堂赠傩”了。
〔39〕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951页。
〔4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周礼注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71-972页。
〔41〕〔54〕〔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7-3128页。
〔42〕〔唐〕李淖:《秦中岁时记》,《岁时习俗研究资料汇编》第三十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第3页。
〔43〕虽然《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的唱和傩歌类似于今天道教的咒语,但尚没有证据表明其时道教直接参与驱傩活动。
〔44〕早在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村人扮胡公头、金刚力士驱疫。(参宗懔:《荆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3页。)
〔45〕可参李正宇先生《敦煌傩散论》。李先生此文是研究敦煌傩文化较早的一篇文章,曾在1991年中国少数民族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见载于《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1-122页,后来的研究者,大都采用了李先生文中的一些内容,故不再赘述。敦煌驱傩歌词可参黄征、吴伟先生编:《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943-965页。
〔46〕尹虎彬先生认为,河北后土地祇祭祀呈现出“多神崇拜、一神独尊”的格局,实际上各地的傩仪活动也同样如此。各地因自然地理、生活环境的不同而视不同的神灵为主祭的傩神,如黄文虎先生所言:“在崇山峻岭中需要开山;东海之滨需要神鞭来赶山塞海;杨泗将军和耿七公能制服险风恶浪,以保障舟楫安全和渔业丰收;干旱的北方需要驱除旱魃,多雨的南方需要祠山大帝张渤疏浚河道、消除洪涝;……”(参尹虎彬:《多神崇拜与一神独尊——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庙祭考》,《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第11-14页;黄文虎:《此间神魅皆世俗——傩坛诸神试析》,白庚胜、俞向党、钟健华主编:《追根问傩国际傩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47〕余大喜:《中国傩神谱》,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48〕吴电雷:《西南地区阳戏神祇叙录》,《四川戏剧》2013年第10期,第131页。
〔49〕巫瑞书:《楚湘傩神探幽》,《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第46页。
〔50〕〔清〕王应奎:《柳南随笔》,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页。
〔51〕《俗说》,收于《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52〕如嘉庆《莒州志》卷四《秩祀》“八蜡庙”条,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53〕余大喜先生即认为,两汉傩制说明“傩的功能已经从‘大丧先柩’、‘及墓入圹’,扩展到驱赶人间所有鬼魅魍魉和一切不祥。”(见《中国傩神简论》,《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47页。)
〔55〕〔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九十《军礼·大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23页。
〔56〕如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记载了北宋徽宗时期演出的作为“百戏”内容而出现的傩舞,其中的“爆仗”、“抱锣”、“硬鬼”、“舞判”、“哑杂剧”、“歇帐”、“抹跄”、“扳落”等表演或作鬼神、金睛白面,或作钟馗,显然还能看出傩事活动的影子,或者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傩活动的移植。该资料已为研究者熟知并屡见引用,不再赘述。
〔57〕详参曲六乙先生《中国各民族傩戏的分类、特征及其“活化石”价值》,《戏剧艺术》1987年第4期,第91-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