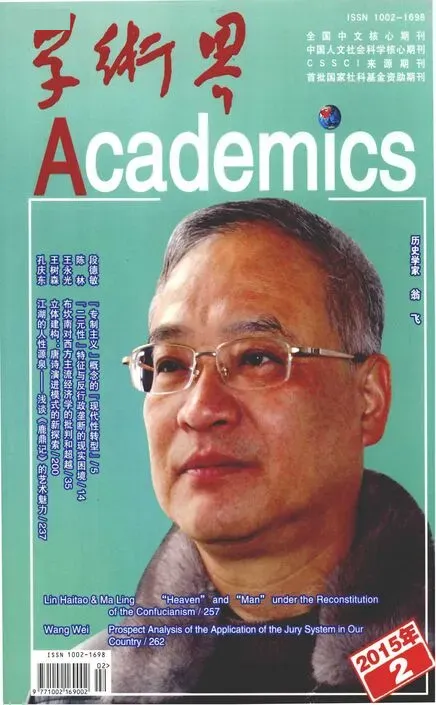傩面具的意象美及其文化意义〔*〕
○刘 静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美学范畴。自《周易》指出“立象尽意”后,两千多年来中国意象说经历了“表意立象”、“内心意象”“泛化意象”和“至境意象”等不同阶段。〔1〕何为意象?先秦时庄子提出“得意忘言”,魏晋时王弼提出“得意忘象”,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的“意象”指的就是“内心意象”,即是指在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主观思想融入,经过艺术语言或物质材料传达,创造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
意象是我国独特的审美范畴,运用到艺术的各个领域,亦已成为其无形的灵魂与精神。
傩,起源于旧石器中晚期的驱逐术,商周时期,傩作为古代逐鬼驱疫的巫术仪式已经形成固定的制度,在周代傩被纳入“礼”的范畴,成为仪典;汉代时规模扩大,将傩仪的咒语与音乐舞蹈结合起来,是为“大傩”;到了唐代,傩在民间盛行,成为百姓欢庆同乐的年节歌舞活动,显现了傩戏的雏形;直至明清时期傩活动内容日益繁多,形式日趋完整,以致形成“沿门逐疫”的风俗。正如钱茀先生所说“明清以来,傩与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更广泛地杂交,形成许多傩戏品种与傩俗事象。”〔2〕
从上古到明清直至近代,傩贯穿于整个人类史,遍及全国24个省市地区,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与艺术特征,因其“数百年世代沿袭,很少受外来影响……风格古朴粗犷原始蛮赫,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的‘戏曲活化石’”。〔3〕傩面具俗称“脸子”,是傩文化的象征符号,是以戴木制彩绘面具为表演特征,以祭祖、驱邪纳吉为目的的古老艺术形式。在傩事活动中,面具被视为神的载体,是最重要的道具,无论仪式、傩舞、傩戏都是围绕着面具进行的,佩戴面具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
美学家苏珊·朗格曾说:“艺术符号是一种终极的形象——一种非理性的不可用语言表达的意象,是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生命与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于感受的活的东西。”〔4〕傩面具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符号,是典型的主观之象,是凭借生活感受与想象创作出来的,是人的想象的具体表现。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它始终以大众熟悉与接受的形象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从现存的傩面具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沿袭经年、亘古不变的自然崇拜的原始风貌,又能读出民间群体朴素的审美意象。
笔者认为,傩面具深受地域习俗、民族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意象美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傩面具的精神意象
“鸣金跳号,谓之逐疫”,〔5〕傩本身是一种驱疫的仪典,根植于远古先民的图腾崇拜与巫术意识,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应的精神意象。
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为傩的生存提供了温床。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他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他的境况归根结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他的生产关系制约的。”〔6〕在封闭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恶劣,“各村族居深山中,冬暖夏凉,得四时之正,惟地多卑湿,云雨时常有,暴风昏雾感者多病”,〔7〕人们没有能力提高生产力,更没有能力探求自然规律,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息与繁衍。所以当人们面临种种忧患时,先民就只能“寄希望于神袛和巫觋去祛除灾祸、疾病和祈求丰年。”〔8〕于是,万物有灵的观念与各种巫术仪式就应运而生,这也是傩文化的源头。
傩面具作为傩文化的标识,在傩祭中是巫师手中最重要的法器,是神鬼灵魂寄居的载体,是身份转换的工具。它的产生符合先民混沌思维的逻辑,寄托了他们理想的原始动机,是他们借以影响自然、保护自身生存繁衍的产物,迎合了先民笃信神灵的宗教祈求心态,满足了他们的现实生活需求与心理平衡。
曲六艺先生就曾把傩归为“宗族傩”,在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因逐疫祈福的需要,各宗族于每年祭社时在各自祠堂择日演傩驱邪。傩面具作为神灵的象征和载体,伴生于宗族活动中。由于带着浓厚的宗族色彩,各宗族都会拥有自己的一套面具,绝不会与其他宗族混用,演员也皆由各自宗族男丁担任,自演自看,按照“口传心授”的民间传袭方式世代相传。在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神灵、祭奠祖先的系列活动中,体现了较为完整的原始宗教情感及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宗族已经习惯借助傩的神秘力量来寻找生命的寄托,用面具编织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对待面具,必须严格遵守宗族定制的各种清规戒律。在未经“开光”法事前,傩面具仅是一件普通的木雕作品,可随意放置。一旦经过杀鸡血祭、拗诀打醮的神秘法事后,则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了神的化身,请进傩坛,奉为“傩神”,将之供奉,对之顶礼膜拜。“各家族在傩戏演出前后,均需进行‘迎神下架’和‘送神上架’的仪式(对神灵的迎送,在楚地是古已有之的——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其‘架’位一般在祠堂的阁楼上,个别家族在祠堂的一角专辟一‘神台’以供奉面具。”〔9〕而当他们带上面具时,就会将自己幻想成带有神秘意味的神象,实现了人神的转化。他们希望借助于傩神的力量,护佑着他们,能占卜世间难事,因为他们相信,每副面具在经过肃穆的宗教仪式后,就会拥有超自然的神的属性,就能盛载着民众的希望——祛灾逐疫、驱邪避难,使他们得到一种图腾式的心灵慰藉。
亨利·摩尔说:“一切原始艺术中最感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强烈的生命力,它产生于人对生活的直接的或即兴的反映。对原始人来说,雕塑和绘画不是一种预期的或学术的行为,而是一种强烈的信仰,希望和恐惧的方式。”〔10〕巫术信仰使傩面具得以产生,而人类文明的进程,傩面具被赋予了新的宗教内涵,社会文化功能的需求与世俗化的价值要求逐渐成为了主要内容,傩面具既具有宗教信仰性又具有世俗性。从国之大傩到流行于民间的民俗民风,傩神信仰吸附儒、道、佛的一些思想内容,隐含巫窥法术而流布于下层社会,〔11〕逐渐回归到民众中来。受傩文化的世俗化影响,傩面具的种类也逐渐的世俗化,傩面具的诞生之初,人们并未在意他们的性别,因为他们只是人们崇拜的对象,是冥冥中的神灵和图腾,所以大多为动物形或自然形或人兽结合形,然而当民众的思想信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傩面具就有了明显的性别区分,等级之分,性格差异,甚至民间传说及神话人物也被赋予了人性的特征,傩面具从人神对立的状态逐渐向人神合一的趋势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其演变轨迹大略与汉乐府相仿,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焉。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还可以将傩神与西方人格神在特征、谱系上进行比较研究。限于篇幅,不赘述。
傩面具从神灵出发,最终落脚于民间,不论是人格化的神还是神格化的人,傩面具都不可避免的渗透着大众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及审美价值观,其目的都是满足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需求与情感需求。傩面具的创造者与欣赏者都是民间大众,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千姿百态的面具的同时也传递出大众质朴的情感及信仰的演绎轨迹。
二、傩面具的色彩意象
色彩是视觉艺术中最情感化的因素,它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与人类文化情感有着甚为复杂、微妙的联系。〔12〕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语言中,色彩不仅仅是对客观自然色彩再现,更多的是从传统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出发,赋予颜色不同的象征喻意是人们表达精神情感的一种方式。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方色彩体系——“五色观”。《尚书·洪范》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阴阳五行说中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物质构成,而各种现象与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结果。到了汉代,五行说发展出五方说,并以五色代替五方:青龙为东方,白虎为西方,朱雀为南方,玄武为北方,四方之中主位为黄色。“青、白、红、黑、黄”五色可以说是五行的用色意识,自始至终贯串于中国的传统设色观念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丰富的比附性意义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宗教礼仪中,并在多种艺术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
传统的“五色”观念为傩面具的色彩运用提供了传承依据,在傩面具的用色上通常以五色为主,辅以金、银、褐、棕、紫色。一般戏曲脸谱都有一定的谱式,如京剧脸谱的基本谱式就有八种之多,而傩面具的赋彩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在色彩的选择上无视色彩的写实性,单纯的从色彩的情感表达出发,讲究色彩的功利意识,注重色彩的性格语言塑造,用色极其自由单纯、鲜艳强烈。每尊面具以纯色上脸,赋彩一般不会超过三色,以人物的品格和气度确定一种色调为主色,用黑线勾勒五官,嘴唇施以红色,如世俗人物萧氏女、刘文龙等;即使是表现神灵武将时,也不过在其夸张变形的眉、眼、额头处施以红、青、白色以彰显个性。
虽然傩面具的赋色单纯,但也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其色彩依然表达了民众的道德观,表现出了对人物的褒贬。根据角色运用不同的色彩赋予面具特定的象征意义,暗示人物不同的品德和性格特征。如以红或重枣色为主色的关公、钟馗,表示忠勇刚直、正义,能够驱魔避邪;皇帝、万民伞、龙亭则以居五方之中象征皇权与地位权力的主宰之位的黄色描绘;小鬼及部分武将的角色则施以青色,以示其凶悍、诡异及桀骜不驯的性格;表现英俊美貌的少将军如薛丁山、罗成则以白色示之,以表文静善良;黑色是平民的颜色,是风吹日晒者的肤色,同时又代表着正义,所以傩面具中的黑色多表现人物朴直、率真、刚正的性格,如包拯、渔翁、招魂使者等。(见表1)
从傩面具的色彩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匠人们在进行面具赋色时完全处于一种主观的意识,他们并不顾及色彩的真实性,较少有理念色彩,注重的是色彩情感表达,追求的是表现主观意象的自由理想色彩。他们凭借着历代传承的经验和直觉对表现对象进行大胆主观的设色,以色彩来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情、气度精神。这种随“意”赋彩带有一定原始意味,真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内心感受与善恶情感,具有较强的道德评判、引导意识;同时也是积极乐观的视觉心理反映,折射出中华民俗从善向上的情感色彩特质。傩面具红、黄、青、白、黑五色的搭配,既遵循着五色的崇尚与禁忌,又遵从着与道德伦理相关的色彩习俗,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比附和观念性的阐释,具有明显的伦理与宗教化痕迹,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国画随类赋彩间接影响下的产物。

表1 五行、五方、五色及色彩喻意的关系
三、傩面具的造型意象
“任何有价值的艺术形象的创造,都不是客观对象原封不动的、机械的、纯客观的再现与攀仿,而是要经过艺术家的能动反映并要经过加工、改造和创造的。”〔13〕大多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经过二度创作的。如郑板桥的竹子,通常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这是第一度创作;而后的“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则是二度创作,在这个过程中,“手中之竹”已不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充满活力、孕育生命的过程。这种以己度物的二度创作在中国民间艺人的创作中尤为明显,他们在处理物象原型时毫不迟疑地把主观意念纳入其中,让客观对象按照自我意愿重新结体构造,我们称这种造型方式为“意象造型”。
中国传统的意象造型很注重概括取舍,张彦远所谓的“形似之外求其画”即是说造型与变形是结伴而行的,在不失常态的前提下通过把物象简化,取舍概括,夸张变形处理,可以使造型更加强烈、充实,更有利于表现描绘对象的神态气质。傩面具的造型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们有意的加工创造。它的创作基本是建立在人鬼神三界的基础上,面具制作者在主观知觉的引导下,在人形的架构上将其关联的鬼神形象进行嫁接再创作,忽略形象的生理结构,抓住其精神内涵,不注重对象的形体真实性,在意于整体的真实与神韵,通过夸张与写实结合的雕刻技巧,创作出三界共通的造型,充分显现了“以形写神”的意象美造型特点。
在制作傩面具时,面具雕刻匠人通常是依据祖辈传承的图样,按照一定的规矩和口诀,一代一代口手相传。在造型手法上分为“取形”和“离形”两大类,“取形”类的面具只是对生活原型的自然形态进行了适当修饰,是概括性较强的面具,如历史人物、世俗人物等。而招魂使者、钟馗等神祗形象则属于“离形”类的面具,这类面具的造型对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进行夸张变形,凸显角色的身份特征,富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在雕刻“取形”类面具时手法柔和、用刀简练,刻划细腻,线条流畅,突出表现人物的温良性、亲和性。如《陈州放粮》中的张妃,眉如柳叶,眼似丹凤,面相丰满。“离形”类面具塑造时手法夸张,用刀粗犷有力,线条粗扩,注重个性张扬,尤其表现在眼、口等部位。以招魂使者来说,面具艺人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对其面部进行了大胆的联想与想象,头戴红头盔,嘴角下扯,满脸煞气,双眼镂空,咄咄逼人,眉毛、宇间、鼻根紧紧拧在一起,将一个暴躁、狰狞的精神气质活化出来。
傩面具的造型特征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形象与比例。傩面具在其形成之初充满了神性的光芒,多是动物、图腾和神灵的化身,以方相氏为代表的古傩神,其面目“可畏怖”,堪比青铜器发展史上早期的饕餮纹;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中近代的傩面具造型慢慢减退了上古时期的恐怖狰狞与神秘诡异的特征,世俗意象逐渐清晰,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民间故事都纷纷走进了傩坛,面具形象也日益丰富,这些面具造型自然的融入了民众生活的期许愿望与爱憎情感,如有的造型眉目清秀、五官端正,体现了忠厚善良的个性,有的则是细眉鼠眼、嘴歪眼斜,表现出奸诈可恶的人物特点。但无论是温文尔雅还是粗旷豪迈,无论是“取形”还是“离形”,都是民众对社会生活情感的自然流露。
虽然傩面具的种类繁多,造型丰富,但其形态与神态却各不相同,民间艺人在造型艺术上特别注重不同角色性格的刻画,每副面具都是数千年来面具匠人们集体创造和技艺传承所积聚的丰富经验的结晶,都是他们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原型结合自身的丰富想象的“意象”表现。他们不拘泥于自然形态,不束缚于透视比例,根据作品传神造意的表现需要,通过对客观对象的领悟,进行主观的取舍,由心具形,在进行面具的性格特征刻画时他们带着明显的道德评价观念,分善恶,明褒贬,将世俗生活中的素材与人文气息纳入面具中,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匠造出一个个意与象交融相通的鲜活形象,使人一目了然。这些原生态的艺术造型虽无专业的雕刻技巧,但却是他们从感性出发对理性的扬弃,是朴实的审美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融为一体的集中表现,将民族传统的古拙审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结 语
中国傩文化是中国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形式,〔14〕傩面具是傩文化的标志,是其最具特色的道具,历经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由最初的驱逐疫鬼发展到祈福纳吉,经历了从尊神、娱神再到娱人的转化;傩面具从神坛走向民间,完成了从巫术到艺术的华丽转身。丰富多彩的傩面具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透过一张张古朴的面具我们看到了鲜活的历史演变,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到了民众的思想信仰、思维方式的变化。
如果对傩文化在时空上加以观照:在空间地域上,傩文化,至少是池州地区的傩文化至今仍然延续着古楚地的风俗——“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在时间上则显示了不同文化、习俗的交融。从驱逐疫鬼、祭祀神灵到颂扬关公、包拯等忠正之士的演变,可见中原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另外,傩戏的招魂在哲学上可以解释为一生一世同时主张神不灭的产物,这与佛教的“三世轮回”说相映成趣。因此,傩文化因地域而根深叶茂,因嬗变而多姿多彩,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傩面具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民间艺术现象,在人们的心中始终是神秘而神圣的。它依靠代代手口相传得以流传,时至今日仍是许多地区重要的民俗活动,一副面具就是一尊神、一个鬼、一位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人物,面具艺人们按照特定的程式和象征性的色彩与写意的造型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寓褒贬、分善恶,将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道德价值等各种现象集中体现。无疑,在新的历史时期,傩戏依然值得传承,我们对傩文化的研究必须继续深入。
注释:
〔1〕顾祖钊:《艺术至境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0-134页。
〔2〕钱茀:《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3〕何根海:《安徽贵池:中国傩戏之乡》,《池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
〔4〕〔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34页。
〔5〕〔7〕谈家胜:《宗族社会与池州傩戏》,《第三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0-201、201页。
〔6〕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三联书店,1983年,第47页。
〔8〕王兆乾:《池州傩戏》,《黄梅戏艺术》1983年第1期。
〔8〕成复旺:《中国传统美学与人》,《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990年第4期。
〔9〕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的背后——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10〕何政广:《二十世纪雕塑大师——亨利·摩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11〕翁利:《中国傩面具的发展和艺术表现形式》,东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页。
〔12〕翁利:《长江流域傩面具艺术造型及其文化审美根源》,《文艺百家》2007年第6期。
〔13〕李青:《中国艺术与意象美学》,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
〔14〕刘芝凤:《戴着面具起舞——中国傩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员工绩效提升的机制研究〔*〕
- 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1〕
- 刑事和解的博弈论〔*〕
- The Cognitive Study of Courtroom Examination〔*〕
- On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 with Instant Death Being the Object of Research〔*〕
- On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