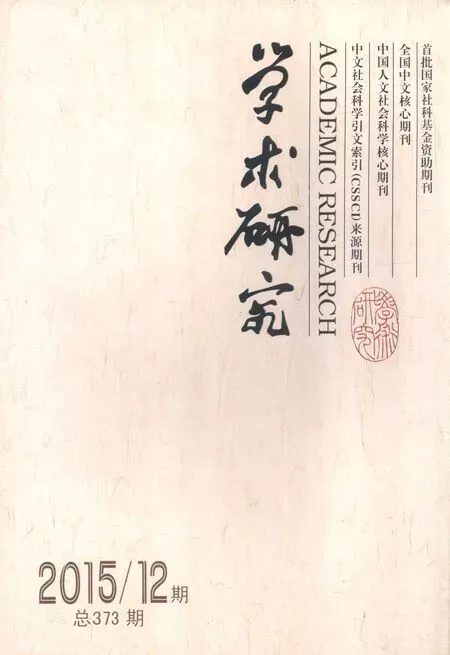社区与文明化理论
——埃利亚斯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及其反思
杨渝东
社区与文明化理论
——埃利亚斯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及其反思
杨渝东
埃利亚斯是文明化理论的倡导者,在其历史化的研究之后,他将此理论引入现代城镇社区研究当中。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中,他以文明化理论分析社区中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社区群体间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一个群体内部逐渐形成了对个体具有约束力的礼仪规则,个体越来越需要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与群体所造成的后果。遵守这样一种礼仪规则的人共同构成局内人群体。而外来者往往因缺乏相应的礼仪规则,而出现行为取向上的诸多“偏差”,成为局外人。他用此个案经典地诠释了局内人—局外人的分析模式。此模式对当代中国的社区研究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埃利亚斯局内人—局外人社区研究文明化理论
一、引论
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①即Process of civilization,国内一开始译作“文明的进程”,最近有学者如李康重译为“文明化过程”。笔者认为后一种译法更能表达埃利亚斯的本意。更多地表现出较为宏大的关怀,比如欧洲人的文明礼貌,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宫廷社会的行为方式,德国中产阶级为何接受贵族阶层的礼仪等等。这些著述都反映出埃利亚斯的理论宗旨,是力图解释某一类群体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如何发展出他们的心理结构与行为取向,以实现他们在与其他群体交往时欲图达到的目的。在埃利亚斯看来,这个过程都是在一个群际关系的结构当中历经较长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的。譬如宫廷社会当中,路易十四的近臣们为了获得皇宫内的地位,就不得不千方百计讨好于他,并不择手段压制竞争对手。于是宫廷社会就渐渐发展出一套谨小慎重、工于心计、礼仪色彩浓厚的行为方式。在宫廷社会中,君主、皇室成员与诸贵族之间构成了复杂的结构性关系,并按照权力的拥有与赐予,稳固与不稳定形成了所谓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1]
可以说,埃利亚斯的社会观不同于涂尔干。虽然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构成基础是社会分工,承认社会的分化,但他依然强调集体意识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并在晚年倡导从宗教层面重建“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埃利亚斯对这样一种全体成员共享一种精神或意识的社会观表示怀疑,他认为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关系与过程构成了社会。因此,埃利亚斯的理论似乎与从涂尔干理论中衍发出来的社区研究格格不入,后者的静态描述与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都与埃利亚斯的风格相去甚远。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面临挑战的时候,埃利亚斯做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尝试,他将自己的文明化理论引入到社区研究当中,从动态的角度讨论社区结构的变迁,展示了“文明化”视野在一个微观世界中的解释力。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这项微观研究详细阐述了纵贯其所有研究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范式,使得这项特殊的社区研究在其理论脉络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与他之前侧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风格不同,埃利亚斯所选择的这个社区,不是一个传统类型的社区,而是一个发达国家中的现代社区。它位于城市边缘,本地人与大量外来工混杂居住在一起,内部关系复杂,与今天中国大城市周边的社区颇为类似。那么,在这些社区中有什么样的文明化问题?或者说,把文明化的理论引入到这样的社区中,能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新东西。由于在个人生命历程与学术生涯中长期游弋漂泊,他常常有“外来者”之感。他也通过其文明化理论塑造了宫廷社会的廷臣、白人社会中的黑人、芸芸众生中的天才、德国贵族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德国的犹太人等等诸多“外来者”的形象。那么,当他把文明理论用到社区,又塑造了怎样的外来者形象,这种形象与其他理路的建构有何不同,其塑造机制对我们今天看待这类社区又有何意义?本文将尝试对埃利亚斯在社区中讨论文明化理论的脉络进行梳理,并简略地提出它在中国当代社区研究中可能会具有的理论价值。
二、文明化理论
埃利亚斯与学生斯科特森(John Scotson)合作,于1965年出版了《局内人与局外人》一书。该书源自斯科特森的硕士论文,当时他在莱斯特大学师从埃利亚斯。1960年代初,英国社会学界盛行社区研究,学生都要去做田野调查,进行参与观察,才能动笔写学位论文。于是斯科特森选择了莱斯特附近的Winston Parva社区(以下简称WP)进行研究。一开始他想研究当地的“越轨”青少年群体,但在埃利亚斯的指导下,他转而描述和分析整个社区结构与生活,并着重讨论其内部的阶层关系问题,这使得该书颇具有人类学民族志的风格。在发现该社区的资料的重要性之后,埃利亚斯决定与斯科特森一起赴该社区从事调查,并对原文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改,将其文明化理论的关照注入其中,从而把这本民族志转变为一本经典的社会学论著。
因此,这本颇具人类学风格的社会学著作带有超越社区的理论视野,它寻求回答的是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亦即,不管怎样的社区,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来看,都存在一个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更细化地说,就包括哪些人对哪些人有权力,为什么会如此,以及这种权力的展演又以何种方式来进行?它对人的思维取向与行为方式进行了怎样的型构等等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作《宫廷社会》时,埃利亚斯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此后他一直通过关注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来进行解答,并提出了自己的文明化理论。30年之后,当他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现代社区研究当中,并提出“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模式时,[2]就更明确地表明他的理论关怀是在当代社会与现代性。
何为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简单而言,就是讨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个人自我控制的倾向变得越来越强了,个人的行为举止也倾向于服从更大范围内的标准,而越来越缺少选择的个体性与情感的爆发性。在他看来,这是长时段的历史所塑造而来的。具体来说,埃利亚斯假定了我们生活得比过去更干净、更整洁、更卫生、更讲礼貌,更有秩序,而之所以能如此,是每个人注意控制自己的行为了,不随地吐痰,交谈前先刷牙,克制自己不过激地与别人发生争执。这种自我控制,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历经长时段的演化形成的。这种动态的眼光,在其后期的《什么是社会学?》中,被归纳为“发展社会学”。[3]
拿其在《文明的进程》的经典理论来说,埃利亚斯认为欧洲的文明化过程是个人的情感结构与外在社会结构相互型构的过程,是个人不断内化外在社会结构所提出的文明标准,表现出更加“礼貌”和“理性”的行为标准的过程。埃利亚斯把个人对情感的控制视作文明化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随着社会从简单走向复杂,人所依附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庞杂,以前可以随意或直接释放情感的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工的拉长使得个人无法把握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这就使得个人日愈变得理性,朝着小心翼翼释放自己情感的方向在发展。而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伴随着对暴力地方化与私人化的终结,过去权力分散可以由个人或地方自由处置的离心趋向变成了一个单独的机构垄断暴力的向心趋向,于是情感的收敛也成为权力控制的目标。同时,分工的细致化使得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彼此的行为模式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上层的人与中下阶层的人之间的界限在淡化,而中下阶层也愿意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模仿上层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一种更加文明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性的要求,并逐渐内化到个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去,使得个人行为举止的羞耻和难堪界限被往前移动了,过去一些让人可以忍受的行为现在变得难以让人忍受了。所以文明化的过程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阶序拉平的进程中,形成一种向上指向的理性化过程,它使得个人也强化了对自我情感的控制而变得更加的“文明”。[4]
埃利亚斯认为难堪的界限是下层效仿了上层行为之后才得以推移,这是文明化进程的路径。这个观点后来遭到包括社会学家鲍曼(Z.Bauman)[5]与人类学家古迪(J.Goody)[6]在内的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埃利亚斯把上层的行为标准对下层的影响过分理想化了。而实际上,埃利亚斯并非简单地看待阶层与文明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阶层是职业与经济的概念,而文明化则是个体自我控制与形象的塑造过程,相同阶层的人可能经历不同的文明化进程,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标准与方式。如果这两类人恰好居住在了同一个社区,那么他们也会因为行为文明化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阶序,出现类似杜蒙在《阶序人》一书中出现的包容性等级现象。[7]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化理论与阶层观,埃利亚斯进入了WP这块社区的试验田。
三、局内人与局外人
WP社区位于英格兰中部,是一个典型的随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现代小城镇。社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标识为Zone1、Zone2和Zone3(以下简称为Z1、Z2、Z3)。Z1为中产阶级居住区,居民主要是企业主和原属Z2但事业有成的人。Z2是该社区的主体部分,位于中心,居民为长期定居于此的工人阶层。Z3则居住着外来的工人阶层,他们与Z2中的工人阶层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外来者,选择了社区较为边缘的地方居住。
按照一般的阶层理论,同阶层的人更容易相互交往接纳,不同阶层之间则会彼此区隔。但在WP,事实却正好相反,Z1的中产与Z2的工人之间并没有太多隔离感,相互间隔离感比较强的反而是Z2和Z3这两个工人区。虽然他们具有类似的职业和收入水平,但Z2的居民比Z3的居民更具有对该社区的支配权。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自认为比Z3的居民地位更高,更具优越感。Z3的居民也感受到这样的身份差距,故而与Z2的居民交往不多,也很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三个居民区在WP社区形成了如下结构。Z1是较晚迁入的外来户,但属中产阶层,社会地位较高,但他们并不主导社区事务。Z2是最早的本地人,他们属工人阶层,但在社区中享有的地位并不比Z1低,并远远超过Z3的居民。Z1和Z2并非完全陌生,而且还存在着各种联系,包括亲属、邻居和朋友关系。Z3的居民则为最晚的外来者,他们虽然与Z2居民同属一个阶层,但在社区中居于最低的位置,他们中从未有人成功地迁入Z1社区,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和Z2的居民建立权力均衡的社会关系。[8]
要理解Z2与Z3缘何成为埃利亚斯所说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就必须从一个动态的眼光来看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WP最初是个村庄,于19世纪80年代由商人威尔森(CharlesWilson)辟为工厂。他一共建造了约700间砖房,包括屋舍、工厂、商店和教堂。那些最早进到工厂中的工人变成了社区的主体,亦即Z2居民区。Z1位于村庄的北面,是满足一些商人的需求于20世纪20—30年代建造的,建成后不久就有外地的职业阶层入住进来。Z3居住区的开辟则带有强烈的“拓荒”色彩。它以前是块位于村庄之外的藻泽地,不属于威尔森开发的区域。那里耗子成群,被蔑称为“耗子谷”。建成后虽然租金不高,却无当地人问津。Z3人口的激增要归功于二战中德军对伦敦的轰炸,当时很多工厂被迫从城区搬到郊区,工人与难民于是如潮水般涌来,使得该区很快人满为患。[9]
那么,社区的“局内人—局外人”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社区的转型过程中,有了三种不同身份的人。Z3的外来客成分复杂,除了伦敦人之外,还有威尔士和爱尔兰人,其中既有熟练工人,也有非熟练工人,他们相互之间很少有血缘关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属于下层的工人阶级,他们在都市的贫民窟里养成一种游手好闲、肆意妄为的习气,很快就在这个新地方复制了原来那套行为方式。他们带穿着邋遢、好酗酒、爱惹事、有暴力倾向。而Z2的普通工人,在社区中已经繁衍生息了60多年,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居民在相同的工厂上班,有自己的酒馆、俱乐部、教堂,定期举行宗教仪式和庆典。由于相互联姻的家庭增多,彼此之间除了邻居之外,还更有亲属关系。Z1的中产阶级,他们既游离于社区之外,但也不时参加社区的活动,Z2居民仰慕他们,期待着通过奋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欢迎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资助。
再进一步分析,Z1中的居民是高度个体化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住在相对分散的公寓中,平时在社区外面工作,交往的朋友主要来自于社区之外,日常偶尔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也使得Z1居民与Z2居民之间存在着某种陌生感。不过,Z1居民大多数生活较为体面,行为举止符合中上层社会的标准,并不会贸然对社区原有的生活形成干扰,因此,Z2的居民仍然把他们想象为较为成功的人。同时,Z1中还有少部分人热衷于社区的公共事务中。凭借他们过人的经济能力,他们可以组织社团,资助娱乐活动,赞助宗教仪式,参加地方政治选举,成为不可或缺的社区公共人物。
相反,Z3的居民则不具有这类能够吸引或征服Z2居民的物质和象征条件。尽管他们与Z2居民同属一个阶层,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剥离了“社会”的支持,这使得他们的生活面临更大的困难,并同时也失去了来自“社会”的约束,这反过来使得他们的“社会”显得更加具有个体性。实际上,并非每个Z3的成员或家庭都是行为不端,缺乏自我控制;有很多家庭,尤其是那些熟练工人的家庭依然能够遵守普遍性的行动准则,尽力搞好工作和照顾家庭。但还是有少部分家庭和个人缺乏基本的行为准则,表现出粗俗与缺乏教养的“不文明”行为。正是因为这些局部不端行为的存在,使得Z3居民整体遭到Z2居民的蔑视和排斥,从而处于一种相对身份较低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局内人对局外人所施加的一种认识的取向。它不仅生成了局内人的优越性,同时也造就了局外人的低劣感。因此,靠这样一种相对于他人的不端行为而建立起来的自我认同型构为一种权力的不平衡关系,几乎展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类型、公共事务、宗教仪式的参与、污名化机制等等。
首先,部分Z3居民缺乏良好的技术,只能在附近工厂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这类工作的收入并不算低,但被Z2居民认为是比较低劣的工作,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典型工作类型”。其次,Z3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与Z1和Z2的居民依然界线十分清晰。这一点,通过三地居民加入当地基督教崇拜组织的人口数就能看出来。Z1与Z2各有十分之一强的人参加,而Z3则为三十分之一。第三,Z3是一个社会连接松散的小区,和Z1的人忙于外面的工作,Z2的人相互间有很好的社会控制不同,Z3当中有一些个人表现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的特征。这些人落到Z2人的眼中,更加强化了他们对Z3整个社区的污名化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Z3中的大部分居民成了少数人的“替罪羊”。而在这样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中,Z2与Z3形成典型的“局内人—局外人”格局。[10]
如前所说,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化即个人对自己行动的控制(内在控制)与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控制的发展程度是紧密关联的。个人逐渐开始控制自己的情感,减少或避免它随时失控般的爆发,并非从来皆是如此,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人越来越注重对自己行为后果的判断,显得更加具有“礼貌”,更守规矩,更懂卫生,更加理性地计算,这样一种社会控制内在化不断增强的过程,就是埃利亚斯所提到的“文明化”的概念。那么,这种理论如何在用于这样一个局内人—局外人为特征的社区当中呢?
Z2居民作为局内人,由于共居的历史久远,社会关系高度整合,居民之间除了邻里、同事等关系之外,还结成了一个社区内婚姻与血缘的关系网络,诸多社会关系重叠在一起,彼此之间对家庭过往的了解,再加上社区共同的宗教仪式,建构起一种其他人很难进入的地方感。在这种地方感当中,特征最明显的就是年长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凸显,因为男性和青年人都要工作,维护家庭功能和社区日常事务的运转,就成为母亲的职责。她们代表着该居民区秩序的准则,并在个人行为出现偏差的时候予以适时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该居民区的个人的自我认同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层面在自我形象中意识中非常强大。个人被隔绝的部分要远远小于自己被包容的那个部分。
于是,在个人行为的控制中,Z2小区便达到了一种高度“文明化”的形态。那里的小孩如果做什么出格的事,他们都会立刻被别人“认出来”,“你再这样,我去告诉你妈妈。”这样看似简单的一句警告,其发挥效应的社会因素却极为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羞耻与难堪的界线被往前推进了,个人对自我的控制内在化并达到很高的高度。任何与外界交往并导致社会身份降低的事情都会引起个体的不适与警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对日常时间的安排就带有了浓厚的价值判断。与成长相伴随的学习和娱乐就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对于一个由完整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支配,并且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持向往态度的群体来说,青年通向成就之路就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学习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社团活动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娱乐时间就带有很强的模糊性,并不受到Z2居民区的推崇,尤其是娱乐往往意味着自己居民区的青少年将跨越边界与Z3的居民区的同龄人搅在一起的时候,更让他们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因此,社区中的公共空间之一,电影院也被视作一个不安定的象征,Z2的居民常常用带有负面的词汇来描述它。同样,交异性朋友都会迅速招致非议,并引发大量的“谣言”。[11]
相比较而言,Z3居民区对其居民的自我约束能力就要弱得多。小区中大部分家庭相互之间互不相识,人与人之间除了所谓的“邻居”关系之外,没有其它关系的交叉重叠,这就造成彼此之间的陌生化,并导致小区整体性道德约束的缺失。自我约束成为了靠个人自己来把握的事情。父母辈不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状况强化了他们的“被遗弃感”,他们便失去了对人生的长远规划,也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长线后果的顾虑。个体行为显得带有更强的随意性而不顾整体性的规范。Z2的居民对Z3居民的优越感,并非源自一种阶层划分的差异,而是一种文明心态的差异。他们的自我意识建构中,秩序与向上整合成为一种基调,这种基调要求他们从行为举止、情感的表达、知识的把握都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而这一切自我形象的建构,如果看到Z3居民的奇装异服、酗酒滋事、无所事事等,都会自然产生社会等级上的差异,而为了净化这种文明性的污染,暴力的驱赶和消灭已经不太可能,唯一的方式便是制造“谣言”。
从文明的角度来讲,Z2居民区针对Z3居民区制造的“谣言”更多的是从“礼仪”的角度,而不是从“贫富”的角度来制造。“谣言”成为了“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经济水平高低的衡量指标。比如Z2居民认为Z3居民的住房都很“脏、乱”,他们对孩子都不加以管教、这些孩子长大后都无所事事,成为问题青年,整天游荡在电影院附近,随意和异性交往等等。在这些谣言中,既有因“眼见为实”而感到惊讶或难堪而加以诋毁的,也有仅凭想当然而贴上的标签。比如根据埃利亚斯的实地考察,尽管Z3居民的住房大多数都比较整洁卫生,但依然被Z2居民视作脏乱。[12]
于是,从这样一个貌似社区研究的经验分析中,埃利亚斯以其“文明化”的惯常思路提出了“局内人—局外人”的理论模型。局内人与局外人在相互比较的关系层次上,被赋予了“文明—野蛮”的意向,权力关系的失衡并不在于经济实力的差距,而在于空间格局和时间历程所型构的不同社会关系,它们共同造成了真实或虚构的彼此不对等的想象与互动方式。虽然埃利亚斯在其他研究中也曾不断强调,社会阶层之间的行为方式的差距随着文明的进程在渐渐缩小,但他却在这个社区研究中指出,“文明”是一个相对化的概念,是一个关系的“型构”过程,即便在现代国家的内部,在相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同样存在着文明的型构问题。在我们貌似简单的政治—经济分层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更加深刻的文明心态的隐匿格局。
四、反思:社区内与外
对这个“局内人—局外人”模式,埃利亚斯的研究者门内尔(Mennell)有一个简略地概括“(这个模式)在研究群体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考虑他们之间如何建构相互依赖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在群体的型构过程中直接产生权力的关键平衡。在估计权力比例朝一方或另一方倾斜,以及它们是稳定还是波动之时,需要考察两方所追求的目的和目标,以及他们实际所需要的人类的要件,并询问其中的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垄断了另一方所需求的人类要件。如果权力平衡非常不稳定,那么就要注意群体的荣耀和羞耻,这是个污名化的过程,局外人在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吸纳了这种局内人的看法,导致即便矛盾依然存在,但他们已有高度顺从之意”。[13]在此,门内尔亦注意到了群体的相互依赖与边界的确定是自我建构的重要前提,权力关系并非支配关系,而是基于文明想象基础上的相互关系。
埃利亚斯选择这个模式来对社会群体的阶序关系进行分析,也是刻意对当时较为流行的阶层分析区分开来。按美国人类学家奥特纳(Ortner)的分析,西方的阶层分析分为两个主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阶级说,一个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分层说”。在分层说当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按客观指标(如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划分阶层的理论,其代表作为李普塞特(Lipset)和本迪克斯(Bendix)1957年的《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另一类则是按当地人自己的观念来创建的阶层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人类学家沃纳(Warner)最早以工业社会为蓝本的《扬基城》,后期的代表作为科尔曼(Coleman)和雷恩沃特(Rainwater)1978年出版的《美国的社会地位》。[14]不过,这两类学说,都把阶层看作分裂性的个别存在体,他们具有明显区分的社会特征或心理状态,而这些特征又是他们区分的重要原因。阶层就像一个阶梯,个人在阶梯当中上上下下,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而在埃利亚斯看来,阶层差异固然存在,比如Z1与Z2,但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往往是阶层观无法解释的,或者说过去生成的差异现在越来越被倾向于用阶层的观念去看待了,而我们却被阶层的理论所蒙蔽而忽视了对更加根本的差异的探讨。因此,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中,他似乎也有意避开阶层色彩较浓的等级观,他选择的这个社区中的两个群体都属于工人阶级,他们从“国籍、族群遗传、肤色或种族、职业类型、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等都没有明显的差异。而这两个群体之所以还会出现等级的差异,在权力关系上依然不平衡,完全是由于两个群体在同一个空间中的时间积累和沉淀的程度差别很大。居住时间长的那个群体,因培育出反复的社会关系网而有力地控制的该社区与自己,成为“局内人”。而后迁入的群体,则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该地,对社会与个人都缺乏明显的控制,成为“局外人”。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不是阶层差异,而是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型构过程与结果的差异。
在埃利亚斯的“局内人—局外人”模式中,他更加强调权力不平衡关系在个体内心的表达。Z2对Z3居民的污名化过程反映了一个权力占优势的社区或群体对另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社区或群体的心理投射方式。这种心理模式在埃利亚斯看来就属于一种“文明化的过程”。在1990年去世之前三个月,埃利亚斯特意借用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把WP的社区群体模式扩展到了族群关系的分析当中,提出了梅岗模式(Maycomb Model),进一步阐发了这种社会—心理关系。[15]在梅岗,族群间的对立压倒了所有的关系所有白人把黑人视作劣等族群,可以随意地践踏和欺辱,甚至是杀害。黑人预先被白人定为“有罪”,他们犯了错,那就是罪加一等;即便不犯错,也时刻是犯罪的嫌疑者。在这种固有的心理模式下,被冤枉强奸了白人女儿的黑人鲁滨逊(Tom Robinson)无需审判,便在当地白人社会中被定了罪。而试图拯救他的唯一一位白人,律师芬奇(Atticus Finch)则代表了国家对社会暴力加以控制的进程。但是,尽管他拼尽全力,仍然没有挽回鲁滨逊被白人射杀的命运。梅岗模式与WP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社会阶层的理论无法解释群体的隔阂。在梅岗,被冤枉的黑人已经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较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他比制造自己冤案的白人贫困家庭要更为富有,然而这并没有使他们被白人群体尊重、善待。两个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梅岗代表了社会暴力还没有被国家所垄断的一种“文明化”程度,地方社会操控法律;而WP社区,文明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国家垄断暴力机制的前提下,一个社区严格地组织化,他们的行为具有更高的约束;而另一个社区虽然组织松散,但也无法使用暴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因此,在这里,两个群体之间更多的是靠另一套机制来相互制衡与攻击,即“谣言”机制,而这也是埃利亚斯试图从“文明化”机制来对一个小社区的社会型构进行阐释的最核心的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局内人—局外人”的模式也值得中国学界的反思。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阶层化”的趋势,无论是就业、教育、居住、消费、婚姻、社会流动等等,阶层化的等级差异都成为了一个极为核心的关键词,整个社会陷入用数字进行比较的攀附型社会。“屌丝”一词的出现与日常化,表达的就是弱势阶层对这种趋势的一种无奈之情。而在学界,阶层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他们大多都采取明确的划分标准,以数字的界线将社会整体切分为各个不同阶层,并讨论他们在日常行动、社会态度、消费模式、教育程度、代际流动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与彼此差异。无疑,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往往表达了用阶层化所构造出来的社会现实,但我们也要注意,阶层概念所遮蔽的也可能与它揭示的一样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往往很难采取一个明确的标准。一个拆迁的农村社区常常获得巨额经济补偿而一夜暴富,他们可以集中居住在城市边缘,具有比城市中心人群更多的财富。然而他们往往又被视作“局外人”而得不到城里人的尊重,这就需要我们从局内人—局外人的模式来看他们关系是如何“型构”出来的。这个动态且相互衡量的过程往往是我们现在的阶层分析所缺乏的。
比如,以文明化理论来看待中国当下的外来工社区融入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外来工“融入”不了社区,既有制度性的问题,但更多的应该考虑“局内人—局外人”的模式,以及文明化关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结构性生产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外来工大多都来自于乡村,在进入城镇社区后,存在着“阶层”(工农)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则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被转化为文明化程度的差异,型构出局内人对局外人在观念上的压制。“脏”、“乱”、“素质低”,甚至“长得黑”都能成为局外人受局内人干扰的观念来源。
这个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从制度上改善或者通过农民工社会化这样一种短时段能够解决所谓“融入”问题的视野到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中来。同时也可能把农村的传统文化模式放入到城市社区中去认真体察,看它在一个时期之内是如何变化,并与城市社区文化相互互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社区融入是一个漫长的文明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户籍与机构能够解决的问题。
不过,埃利亚斯在社区研究当中,显然过于强调了掌握权力一方对于无权一方的话语塑造,而没有看到后者对前者的应对与表达。局外人显然也可能对局内人进行挑战与攻击,如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所看到的那样,外来工也会编造出对于局内人的谣言作为“弱者的武器”,批评后者在行为方式上不符合自己认同的标准。所以,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它们对社区的文明进程会起到什么影响,是埃利亚斯没有深入讨论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埃利亚斯理论中何谓文明准则值得商榷的地方。
[1]Elias,N.,The Court Society,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1983,pp.146-181.
[2][8][9][10][11][12]Elias,N.&J.Scotson,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Dublin: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2008,p.16,pp.43-47,54-59,115-121,130-136,188-189.
[3]Elias,N.,What is Soc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132.
[4][德]诺贝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4-235页。
[5][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6][英]杰克·古迪:《偷窃历史》,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0-212页。
[7]Dumont,L.,Homo Hierarchicu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38.
[13]Mennel,S.,Norbert Elias: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89,p.138.
[14]Ortner,S.,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0-27.
[15]Elias,N.,“Further Aspects of Established-outsider Rrelations:the Maycomb Model”,In Elias,N.&J.Scotson,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Dublin: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2008,p.222.
责任编辑:王雨磊
C912.81
A
1000-7326(2015)12-0042-07
杨渝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江苏南京,210046)。
——以两个音乐实地调查案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