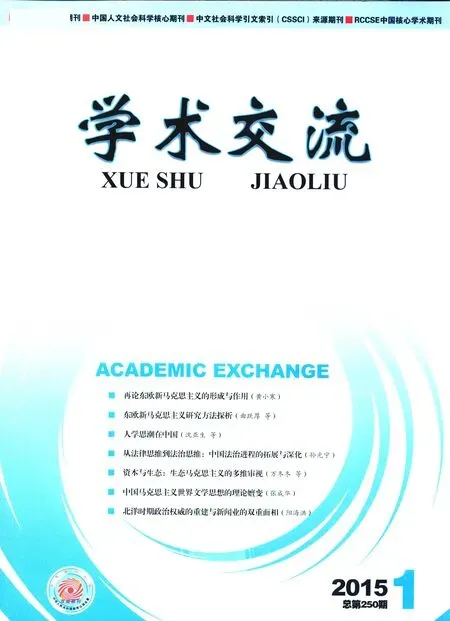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利维坦”:关于霍布斯学说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罗时文,姚啸宇
(1.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2.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政治理论研究
“利维坦”:关于霍布斯学说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罗时文1,姚啸宇2
(1.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2.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了现代国家秩序的基本原则,而他以“主权学说”为核心的国家理论又来源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独到见解。霍布斯通过“自然状态”理论表达了他对战争原因的理解,在缺乏统一政治权威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相互为敌的激情与对善恶问题不可调和的主观理解必然引发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唯有代表国家的主权者能压制人们的激情,并提供关于善恶问题的统一标准。霍布斯将恐惧作为和平秩序的根基,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古典传统的崭新的政治原则。
霍布斯;国家学说;利维坦;战争;和平
在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中,对战争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物,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可谓首屈一指。把战争作为根本的问题意识,贯穿着霍布斯几乎所有的政治思考。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指出,霍布斯之所以反对当时共和主义自由论者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倘若像共和主义自由论者所宣称的那样,每个公民都成为自己的统治者,而排除任何专断权力,必然将使国家陷入战争之中[1]。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则认为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旨在解决英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神学困境——正是英国在信仰问题上的分裂状态引发了政治上的分裂和内战[2]。透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霍布斯终身思考的问题在于,战争因何起源?如何防范战争并维持和平?霍布斯最终给出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不受限制的主权者所统治的绝对国家——“利维坦”来扑灭战争的火种。由此可见,霍布斯笔下“主权”的特性和他对战争的思考密切相关,我们要理解霍布斯的主权学说,就首先要理解他对战争源头的认识。霍布斯对战争最为直观的体验来源于他对英国内战的经历,正如奥克肖特所说,激发霍布斯思想的是“对我的国家眼下灾难的悲伤”[3]。而他对战争的思考在文本上最集中的体现则是关于“自然状态”的分析,“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则是竞争、猜疑和荣誉[4]95。但假如我们就这样“轻信”了霍布斯的论断,那很可能就上了他的圈套,而忽视了霍布斯对于战争起源问题的根本预设。而我们的关切则在于,为何霍布斯如此看重战争与和平?这种政治理论关切中心的转移背后,除了来自霍布斯本人经历的直观体验之外,是否还有来自更深层的哲学思考的支撑?本文将立足于霍布斯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找出其关于战争起源问题的基本认知。并且笔者试图证明,这一基本认知直接影响了霍布斯对主权这一概念的理解,造成了他国家学说中的一个棘手的难题。
一、自然状态——无政府与战争
霍布斯关于战争起源问题的思考,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无疑就是所谓“自然状态”的学说。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认为霍布斯将“自然状态”设定为一个政治秩序建立之前人类社会的状态,但这其实并非霍布斯的本意。在著名的《利维坦》第十三章,即“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这一章中,霍布斯明确表示,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战争状态并未真正存在过,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状态不会在世界上普遍存在[4]95。但霍布斯宣称许多地方的人现在依旧是这样生活的,譬如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它们除了小家族之外并无其他的政府。他接着提醒人们注意发生在眼前的现实: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人们畏惧的地方,一场内战会使原本生活在和平政府领导下的人们堕落到何种地步[4]96。英国的内战直接刺激了霍布斯的问题意识,而他对“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的直观感受,很有可能也大多来自于这场内战。因此“自然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一旦失去了统一的政治权威,原本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们也会立即沉沦到这种野蛮而残忍的自然状态中去。
统一政治权威的丧失必然导致“自然状态”的出现。霍布斯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他不像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在理论上区分开来,或者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社会自身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便没有政治权力的干预,也能使社会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运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著名的“第十三章”进行透彻分析。在第十三章的开篇,霍布斯就抛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断——“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4]96。霍布斯并没有断定,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能力上的差距,关键在于,这种差距在“自然状态”下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最弱的人运用计谋或者互相联合的方式也足以杀死最强的人[4]92。在可以相互杀戮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因此没有什么人天然地就可以统治他人,或者就该接受他人的统治①稍加注意的话,我们会发现,霍布斯在这里特别有意地改变了对“审慎”之德的看法。在古典政治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人与人之间最大也最难以逾越的差距是智慧的差距,而运用审慎之德的能力,则直接被看作统治权的依据。霍布斯则贬低了“审慎”的地位,他认为审慎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任何人只要经历了相同多的事,都能获得同样水平的审慎。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比他人聪明,是因为他们被对自己智慧的自负蒙蔽了双眼。因此在古人看来最自然的统治资格,在霍布斯的学说中已经被取消了。详见: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3、92;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92。。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是不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每个人都能任意决定自己该干什么而不必服从其他人的命令。霍布斯从能力上的平等就直接推出了“目的和希望的平等”,当两个人欲求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分享它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仇敌[4]92。因为所有人都有可能将自己摧毁,生活在疑惧中的人,为了自我保全,先发制人就成了最合理的办法。不仅利益的冲突会导致战争,人性中的骄傲和虚荣同样会加剧战争状态的紧张程度,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他人对自己的估价与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4]93。当被别人轻视时,哪怕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对他们本人的藐视,或是间接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的藐视都会引发你死我活的争斗[4]94。这种战争被霍布斯称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战争的性质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为所有人共知的互相之间的战斗意图。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产业都得不到保障,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4]95。
回到先前的问题,为什么霍布斯会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在他设想的“自然状态”之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以至于除非产生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否则几乎看不到丝毫和平的希望。我们可以从洛克那里找到一丝灵感。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有所指涉地批评了将“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混为一谈的观点[5]。笔者认为,洛克之所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不会必然地走向战争,一个原因在于洛克“自然状态”下的人远比霍布斯所以为的离“上帝”更近,“自然法”直接从“上帝造人”这一前提中推出,人是上帝的所有物,因此就没有毁灭自身和他人的自由。洛克的“自然状态”仍然隐隐有一个先验秩序的存在,这一秩序直接来自于上帝。霍布斯则完全不这样认为,或许在他看来,即便同样信仰上帝,也不意味着大家就能和平相处,历史上许多惨烈的战争都是发生在基督徒之间的,甚至信仰问题本身就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②信仰和主权的关系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着力处理的问题,卡尔·施米特在他的霍布斯研究著作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见卡尔·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9-101.尤其应注意施米特指出的霍布斯在信仰和神迹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立场。。尽管霍布斯将人性描绘成贪婪和骄傲的,但他并非一个“性恶论”者,因为性恶论首先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善恶的客观标准。而在霍布斯看来,这种先验标准是子虚乌有的,他特别声称他并没有攻击人类天性的意思:“人类的欲望和其他激情并没有罪。在人们不知道有法律禁止之前,从这些激情中产生的行为也同样是无辜的;法律的禁止在法律没有制定以前他们是无法知道的,而法律的制定在他们同意推定制定者前也是不可能的。”[4]95绝对的主权者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善恶必须依靠法律来规定①这种说法也并不绝对,施特劳斯就认为,霍布斯已经事先就把所有道德建立在“死亡恐惧”的基础之上,而彻底否定了与虚荣自负相关的“贵族式德性”,因此霍布斯的道德哲学并非完全“自然主义”的。参看[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7-35,53-70.但不可否认的是,对霍布斯来说,道德上可供人为建构的余地要比古典政治哲学大得多。。主权者的权力之所以是没有边界的,不仅在于他生杀予夺,无人掣肘,同时也在于他是人间最大的立法者。
二、利维坦诞生——恐惧与和平
既然自然状态中的人既贪婪、猜疑,又骄傲自负,并且不存在任何先验秩序,那么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状态”的飞跃又如何可能?或者说,是什么促使一盘散沙、互相为敌的个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有秩序的政治共同体?霍布斯在人的众多激情当中找到了“对死亡的恐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4]97只有对死亡的恐惧能制服那些会导致战争状态的其他激情,而人的理性则充当着这一激情的顾问,使人们放弃“自然权利”,缔结契约,加入到一个“利维坦”国家中去。换言之,这样一个国家之被建立的目的就在于和平,在于自我保全。霍布斯的“利维坦”看似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但信约本身并无约束力可言。他针对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观点,提出蜜蜂、蚂蚁这些动物比起人来,更符合“政治动物”的特征:“这些动物的协同一致是自然的,而人类的协议则只是根据信约而来,信约是人为的。因之,如果在信约之外还需要某种其他东西来使他们的协议巩固而持久并不足为奇了,这种东西便是使大家畏服、并指导其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的共同权力。”[4]131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的过程,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霍布斯将正义定义为遵守信约[4]108,但他也意识到,正义自身是脆弱的,它完全是人为的,不具有让人自然地就愿意遵从的特质,“神的王国是凭暴力得来的,如果能用不义的暴力获得,那又怎么样呢?当我们像这样获得神的王国而又不可能受到伤害时,难道是违反理性的吗?不违反理性就不违反正义,否则正义便永远不值得推崇了。根据这种推理,获得成功的恶便得到了美德之名,有些人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不曾容许背信的事情,但却容许背信以窃国。”[4]110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义之人只要敢于将恶事做绝,就不仅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还能获得“美德之名”。“利维坦”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假如违背契约而不用付出代价,那么国家的崩溃就是必然的,人们就要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中去。这样的问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出现过,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央求苏格拉底向他们证明,正义因其自身就比不正义更值得追求[6]。苏格拉底通过在言辞中构建一个理想城邦,表明只有选择正义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霍布斯必然会对这种论证嗤之以鼻,因为在他看来,原本就不存在一种作为“最高善”的恒定的幸福状态,因为“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而全人类共同的普遍倾向则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4]72。幸福不再和正义相关,不再和正确的灵魂秩序相关,取而代之的是“权势”,如果想让自己的欲望能不断获得满足,就要不断攫取并保持住自身的权势,这和“正义”的要求以及维持国家和平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霍布斯的告诫则是,一个违背信约的人将不再受到其他人的信任,因而会被逐出国家,回到自然状态中去,等待他的必然是死亡。这一观点在第二十七章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述,霍布斯认为“畏惧”是所有激情中最不易使人犯罪的激情,假如破坏法律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利益的话,它甚至是唯一能使人守法的激情[4]232。
在霍布斯看来,语词对人的约束过于软弱,如果想要约束人们的野心、欲望和愤怒,就只能依靠人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之心[4]103。自然状态下的人因为畏惧死亡而进入政治社会,同样因为畏惧的激情而服从法律。主权者为了维持和平,必须让每一个人都时刻感受到这种不受限制的惩罚力量的存在,让任何一个有意犯禁的人都因为恐惧而不敢轻举妄动。和平就这样被恐惧维系着,没有对惩罚的恐惧,和平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言辞上而无法变为现实。霍布斯不指望通过道德教化让人们遵循正义,在他看来这种办法太不可靠了,古代人基于“目的论”的人性理解根本没有客观依据,而依据人事实上怎样生活的真实情况,依据每个人都具有的对死亡的恐惧设计出的“利维坦”才能确保和平的实现,“利维坦”是骄傲之王,只有国家强大的力量能降服那些骄傲的个人,让他们安分守己地生活。
三、利维坦何以死亡?
没有统一权威的自然状态意味着战争,唯有对死亡的恐惧才能迫使人们遵守信约,从而维持和平。这是不是说,这种和平的状态一旦形成就一劳永逸了呢?霍布斯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并且他深知即使国家已经建立,统一政治权力的威慑已然形成的情况下,“利维坦”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仍有可能走向瓦解和死亡,使人类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中去。在《利维坦》第二十九章中,霍布斯着力探讨了“国家致弱或解体的因素”。首先,霍布斯认为保障和平与国家的防卫所必需的权力的不足会导致国家的“疾病”,这种说法与后文中的第四种原因,即认为“具有主权的人要服从民约法”,第五种说法“每一个平民对其财物都具有可以排斥主权者权利的绝对所有权”,以及第六种认为“主权可以分割”的说法相类似。这些说法都认为主权存在界限或者可以被限制,甚至可以被分割。而这种观点一旦流行起来,在霍布斯看来必然将是国家的灾难。霍布斯认为,一旦主权被限制或被分割,那么就会在国家之内出现多个主权,而这些主权之间必然会相互摧毁,引发战争。就像主权国家之间处于自然状态中一样[4]96,一个国家内部的主权之间也会陷入战争状态当中,英国内战的直接起因,就是议会反对王权的独断专制,要求限制王权。同样的,教权和俗权的对立,也会让国家陷入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4]256。
另一类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与前一种相关却又不完全相同,那就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因为假如人们都遵从这种错误的理论,他们就会质疑国家的命令,根据自己私人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服从主权者的命令,私人意见的泛滥必然导致国家力量的削弱,从而使国家陷入混乱[4]252。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霍布斯并不相信存在先验的客观善恶标准,同时也不认为人们通过理性地辩论能够对这些关于善恶、正义等价值问题达成一个一致的观点,甚至这种辩论本身就会威胁政治秩序的稳定,尤其是这种辩论一旦和修辞术等结合起来,必然会造成混乱[7]。假如没有一个最高权威做出决断,终结争论,那么争论将永远进行下去,并且导致争斗[4]28。霍布斯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在有关宗教信仰的事物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达,在各种相互冲突对立的关于《圣经》的解释中,人们应当信仰哪一种?霍布斯的答案是,这应当交给最高的主权者来决定:“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超自然启示,说明这是他的法律,也没有以这种方式说明公布这种法律的人是他差遣来的,那么除了根据其所发布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那种人的权威以外,他就没有义务服从。也就是说,除了根据国家赋托给主权者(唯一具有立法权的人)身上的权威以外,根据任何其他权威他都没有义务要服从。”[4]306主权者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时控制每一个臣民的行为,而且渗透到了信仰的领域,而这一切的目的始终是为了维持和平。然而卡尔·施米特却在这“一统宗教和政治之主权权力的登峰造极处”,看到了断裂,正如《利维坦》第三十二章所说,主权者诚然可以强制他的臣民服从,使他不用行动或言辞表示自己不相信主权者的话,但却无法让臣民不依照自己的理性去思想[4]292。主权者在外在认可的领域拥有绝对的裁断权,但个别人在内心信与不信,则完全遵从于他们自己的私人理性。施米特认为霍布斯在这里埋下了政治领域“思想自由”的祸乱种子,尽管在霍布斯那里,它只是作为绝对主权的后援条件,但是经过斯宾诺莎等犹太政治思想家的发展,它最终取代了公共和平与主权国家的迫切性,成为现代中立国家的前提与原则,从而束缚住了绝对主权。霍布斯强调保护与服从、命令与风险承担、权力和责任之间古老而永恒的内在联系,反对任何只进行统治却不承担责任、提供保护的间接权力。但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使他一手建构的“利维坦”国家遭到肢解,现代中立国家陷入到间接权力统治的灾难之中[2]93-126。那只强大的海上猛兽因此被肢解殆尽了。
四、结论
霍布斯对人性的理解与对政治现实的观察,使他认为人性天然地就有引发战争的倾向,从而彻底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论断。由于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先验的客观秩序,且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威,因此孤立的个体们必然会陷入无止境的战争状态中去。为了结束这种悲惨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看中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一最强烈的激情,在死亡恐惧的驱使下,人们缔结契约,将他们的“自然权利”转交给一个绝对主权者,从而进入政治状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人造国家”①在《利维坦》的“前言”中,霍布斯就将“国家”比作一个“人造的人”,政治共同体来自于人的技艺(art)而非自然(nature)。而“寿数有限的人所造成的东西没有可以永生的”,所以作为人造物的国家必然会走向衰朽和死亡,正因为政治共同体缺乏自然根基,它的延续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延长这个“人造的人”的生命,使他“免于因内发疾病而死亡”才成为霍布斯思考的重心。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49。。主权者利用自己手中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以及人们对惩罚的恐惧,震慑住人类会导致战争的天性,从而维持和平。霍布斯提出了一种与古典传统截然不同的人性图景,以此为基础,他通过严密的推论证明了:倘若人性真是如此,那么,假如想要保持和平与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就必须存在一个最高的绝对主权。而任何试图限制和分割主权的行为,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与解体、和平的崩溃与战争状态的复归。
我们回头寻找霍布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预设,那是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使得霍布斯不相信在人之上存在任何客观的秩序与规则,不相信诸种善存在一个自然的等级制,而人的理性能够找到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客观答案,统治灵魂中的激情和欲望。正是因为如此,霍布斯否认政治生活能将城邦引向一个共同的最高善,从而将政治哲学关注的重心由“最好政体”转移到了“如何维持和平”上,并意识到如何抑制战争、维持和平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难题。也正是因为如此,霍布斯放弃了古人改变灵魂结构的教化之道,而致力于以最大的激情“恐惧”压服其他会导致战争的激情,以主权者的决断取代对“真理”的探求。霍布斯是成功的,他的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实践,并为现代国家的建立与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原则指导;但霍布斯也是失败的,他的根本预设决定了在他设想的国家中,纵然人与人相互残杀的内战和意见之间永无止境的争论能被终结,但霍布斯没有想到,所有人内心精神的内战会在后来的中立国家中站到了前台,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并永远失去了在“国家”中得到解决的可能——“真理”的问题从此在政治的维度里消失了。
[1]昆廷·斯金纳.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2]卡尔·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渠敬东.现代政治与自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5.
[4]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5.
[6]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4-56.
[7]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Leviathan:War and Peace in the Theory of Hobbes
Luo Shiwen1,Yao Xiaoyu2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state order,but his"sovereignty theory"at the core of state theory came from his unique insights-issues of war and peace.Through the"state of nature"theory,Hobbes tried to express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war,that is,in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political authority,people's irreconcilable subjective misunderstanding for the good and evil triggers continuous wars.It is the only state sovereignty on behalf of the state that could make people's passion under control and give a unified standard for the good and the evil.Hobbes took fear as the base for peace and created a brand-new political principle that differs from that of classical tradition.
Hobbes;theory of state;Leviathan;war;peace
D091.4
A
1000-8284(2015)01-0064-05
〔责任编辑:常延廷 巨慧慧〕
2014-10-09
罗时文(1974-),男,江西崇仁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