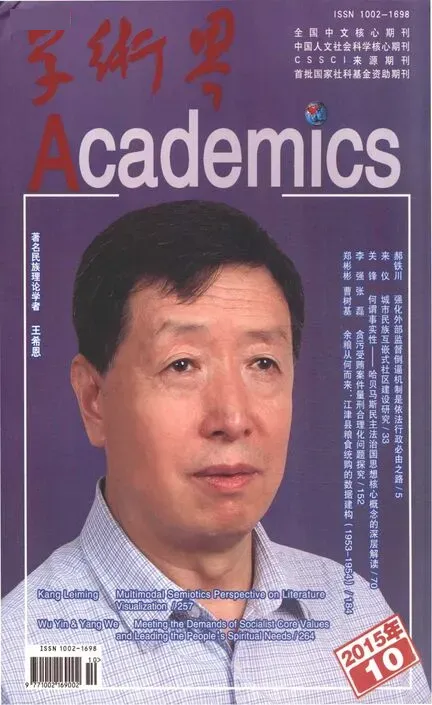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的文化回归〔*〕
○汤 琳
(合肥学院 外语系,安徽 合肥 230601)
一、美国华裔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是一个极富现代性和政治性内涵的概念,与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西苏认为女性“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写作不但可以“实现”妇女解除对其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写作是“妇女夺取讲话机会”的标志。而且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对于传统的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进行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1〕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代表了整个女性团体的集团意识,女性文学是作家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个人的精神结构”的创造,是她那个集团或阶级共有的观念、价值、舆论导向、理想结构的体现。〔2〕
美国华裔文学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但是真正地让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读者与评论界取得一致赞赏的,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大量涌现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从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到以自传见长的二代女作家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历经长时间的奋斗,在前辈文学创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叙事文本,把“一个女性主体(美国华裔女性)在文学中由长期缺席、不在场到逐渐出席、在场的过程”〔3〕鲜活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与英美女性文学的发展相一致。大致历经了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对英美女性文学发展研究时所区分的三个阶段,即模仿期(1840-1880)、反叛期(1880-1920)、自我发觉期(1920-现在)。〔4〕水仙花的代表作《春香夫人》,带有明显的奥斯汀的写作风格,阅读的过程中,全书所使用的文学象征,也容易使人联想起霍桑和亨利·詹姆斯;〔5〕1945年黄玉雪的《华女阿五》用自传的方式完成了一部“改善华人形象”的书写;其后,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继续了传记书写的传统,但是她们作品的主题,已经转向探讨二代华裔如何在美国主流社会获得一席之地的文化认同问题;而20世纪末出版的伍慧明的作品《骨》则直接对三代华裔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些美国华裔女性的作品,在美国文学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认为汤亭亭发表于1976年的自传《女勇士》,是一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用实验性写作手法自我建构和解构的女性文学作品。〔6〕这部小说获得当年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奖项,被美国《现代周刊》评为70年代美国文学最优秀奖,被列为美国高校必读书目。
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的采借和重构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所取得的成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从本体而言,她们的叙事文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采借与重构,以及她们所采用的后现代拼粘、戏仿、零散叙事及元小说等创作手法,既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又顺应当时美国读者的阅读偏好,同时还迎合了当代文学评论的时代要求。
(一)采借中国传统文化
在西方文学史上,涉及到的华裔形象最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莫过于代表“黄祸”的傅满洲和被“阉割”的华人男子陈查理了。前者是英国通俗小说家萨克斯·洛莫尔从1913年到1959年创作的,以傅满洲为主要反面人物的十多部“傅满洲博士”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在欧美世界里,这一华裔移民形象几乎就是“恶魔天使”的代名词,是20世纪西方“黄祸”的化身,在很大程度上,这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对当时中国的想象,是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巅峰造物。陈查理则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创作于1925年系列小说中的一名华人探长,与傅满洲不同,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陈查理缺乏男子汉气概,是西方世界臆想出来的“非性化”、从属性、边缘性的东方智慧与模范族裔的代表,贴着文化驯化的标签。但是从本质上来讲,陈查理与傅满洲一样都是西方世界对于华人形象的主观扭曲与歧视的人为产物。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新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势必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重建工作,其中要务就是要纠正主流话语中被歪曲的华裔形象、同时创建新的华裔文学形象、书写华裔自己的英雄传统和神话。〔7〕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这一时期担当起了这样一个重任,而且获得了成功。
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副标题是“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直接把中国人传统的“鬼”文化入题,全文还改编了花木兰、蔡文姬等历史名人的故事。谭恩美的第一本小说《喜福会》中四对母女多年的冲突,均是围绕着母亲们的麻将桌展开;第二本小说《灶神娘娘》讲的是母女因文化所产生摩擦的故事,题目里所言的“灶王爷”,是只限中国传统神系的人物。而被汤亭亭誉为“美国华裔文学之母”的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很多的笔墨都放在了中国烹饪细节上,甚至书中还罗列了“咕咾肉、芙蓉蛋”等当时流行的菜谱,这对于华裔以外的读者具有格外的吸引力。〔8〕
严格来说,没有哪一本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可以在不采借本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就可以取得西方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宛如大地之母盖亚一样,为她们提供着用之不竭的力量与创作灵感。
(二)采借西方传记叙事
传记作为一种常见的西方文学体裁,本是西方基督徒对自己皈依上帝心路历程的记录,是地道的白人的文化产物。在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五千年以来,即便是那些受到万人敬仰的孔孟鸿儒,都不敢轻易采用传记这一文体进行创作,自传就更不用说了。
但美国华裔女作家凭借着女性为主体的传记创作,建构了一个女性权力主体,使得代表第二作者的叙述者公开“说话”主体的在场身份,更加明确了其作为“作者代理人”的叙述权威,因而使得作者的叙述声音也更为强大,〔9〕更有利于作者将自己的价值观,用来作为对文本中的其他人物、事件进行衡量和评价的标准。因此,也更容易引导读者随同这些传记的女性人物叙事者,进入到文本故事中,使得文本真实性获得更大程度的信任。某种程度上说,由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于传记体裁的运用,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一直是西方文本言说的“他者”的地位,一举跃升为言说“自我”的主导。
因为传记文体通常采用“同故事+故事内视角”叙事视角,使得这批女作家的传记作品中,女性叙事者的叙事视角合法化,且完全处于文本中心位置。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传统的第三人称视角;汤亭亭的《女勇士》故事文本由五个看似无关的故事组成,更是杂糅了“异故事+故事外视角”“同故事+故事内视角”“异故事+故事内视角”等各种叙事视角;谭恩美的《喜福会》讲述的是四个家庭的故事,所以采用的是群体家族叙事模式。但是,无论这些文本叙事视角发生了多少变化,这些视角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于女性观察者,从女性视角的角度,进行的是女性叙事。
可以说采借西方文学的传记叙事文体,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取得成功的一个明智之举。这帮助她们不但超越本族前辈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又超越了像她们一样的从事创作的欧美文学女前辈们。审视欧美女性作家创作传统,我们不难发现,她们要么取一个男性化的笔名隐藏写作,要么模仿前辈男性作家的写作风格;在创作的理念上,她们或是在物质上要求一个“自己的房间”,或是在精神层面上杀死“天使”或者“魔鬼”。〔10〕与之不同的是,为了进入自己希望融入的美国主流社会,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一方面努力摆脱着具有浓重的传统封建父系文化的家庭束缚,另一方面,又凭借着自我的艰苦奋斗,作为“个人”“女人”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然而,她们的作品问世之后,就遭受了来自她们同时代的美国华裔男性评论家,譬如赵健秀等的猛烈批评。
不可否认,客观上看来,传记书写本身的优势,更有利于把身处异国他乡的二代华裔,早期试图逃离本族文化、一味认同他国文化,然后又回归本民族身份认同,同时吸纳美国文化的优质要素,趋于成熟的整个成长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也更有利于显现她们在居住国文化中相应的身份变迁的独特属性。从这一层面上看来,美国华裔女作家们的自传文体、女性话语声音,最有利于她们自由地驾驭和控制着文本的叙事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中的其他成员,突破男性话语的“囚笼”,而且还最终帮助她们建立起了一个隶属于自己的话语家园的第三空间。
(三)重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除了自传文体为美国华裔女作家招致许多批评以外,她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类采借,也成为她们作品评论的另一个颇具争议的层面。
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是汤亭亭《女勇士》出版以前流传最广的一部二代华裔的作品,为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被制作成特别节目,在270多个电视频道播出。〔11〕这本自传基本创作思路,一直践行的是黄玉雪为了“帮助人们理解美国华裔,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善良、真诚的”的创作初衷。为此她精心地筛选自传的内容,以便树立正面的美国华人形象。〔12〕书中的女主人公“阿五”怀有一颗强烈的欲进美国主流社会的勇气与决心,勤奋刻苦,竭力纠正当时被扭曲的华人形象。作为二代华裔的代表,她已经不再满足囿于唐人街的一隅,积极地接触她的前人试图逃离的全新世界,发现并积极赞扬他们的优点,努力融入其中。她的文本以对普通华人质朴的个性与生活的描写,来吸引美国读者的关注。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显现出与传统华人女性大不相同的思想与认知,开始与美国女权主义者的观念保持一致,大胆而积极追求人生的成功和西方社会的认同。
汤亭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更为彻底。她的代表作《女勇士》故事文本的五个互不相关的故事碎片,分别以主人公“我”和家族中另外三个女人“我的姑姑、姨母以及母亲”为主人公。其中“白虎山学道”一章,将花木兰的故事嫁接到主人公“我”的身上,出兵打仗以前,她的父母重演了历史上的“岳母刺字”的典故。她虽身为女性,不但能带兵打仗,还具有超人的胆识,“见到皇帝,我们砍下他的脑袋”;〔13〕实现了人生理想以后,她重又回归家庭,恢复传统女儿娴静柔顺的“耕耘纺织,生儿育女”〔14〕的田园生活。
《女勇士》中的“我”是出生于美国的二代华裔,接受的是地道的美国教育,但是却生活在唐人街。处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很难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陷入既疏离于中国文化,也难于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纳的现实困惑。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野蛮和愚昧。她对中国文化批评道:“中国人怎么能保持他们的传统?他们甚至都不让你去注意那些传统,在聚会上大吃大喝,孩子们还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收拾完了桌子。大人们愚昧,逃避,不让你问任何问题……”。〔15〕同时“我”感到华人移民的言谈举止粗鲁不雅,因此“我”希望自己能变成地道的美国女性。〔16〕
但是汤亭亭对于华裔女性形象的重构,并没有局限于对她们身份认同的困惑的描述。在《女勇士》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讲述了中国西汉这位20岁就被迫离开故土远嫁匈奴,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琰的故事。她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一直坚守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最终还学会了对“野蛮人”音乐的欣赏:“她把歌从野蛮人那里带了回来,其中三篇之一是《胡笳十八拍》,流传至今。中国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仍然演唱这首歌曲……”。〔17〕以此,汤亭亭建构了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和谐共处、相互交融的美国华裔理想的生活世界。
三、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
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借助本族传统文化的资源,运用后现代的文本创作手法,创作出来的叙事文本,在学界一方面被誉为高超的书写技巧,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便认为汤亭亭的《女勇士》是后现代元小说的一部重要作品。但是在另一方面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美国华裔男作家们,却视汤亭亭的作品是一种对本族文化的叛变。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直以来女性文学叙事所面临的尴尬境遇。
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英国社会学家霍尔在讨论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定位和重新定位时,指出相较于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场所”。〔18〕同样,在面对本族的父权,美国的白人,甚至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话语权威时,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在场也必然是被压迫的场所。“任由广西在乡愁的定义上开一道门/爷爷跨不出去/父亲跨不回来/我侧身小立/门槛之上”是南洋作家陈大伟的一首小诗,为那些散居的华裔女作家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痛苦生活和写作状态做了准确的注脚。〔19〕
(一)面对男性世界的女性文学
众所周知,千百年来,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对待女性与女性文学并不那么友好。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就认为“妇女既‘内在’又‘外在’于男性社会,既是这个社会中受浪漫主义理想化的成员又是被遗弃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存在本身就扰乱男性规范的社会秩序,“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妇女是被符号、形象和意义所代表和确定的,然而,因为她们也是这一社会秩序的‘否定’”;“(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力量”。〔20〕因此,女性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站在男性世界的对立面,带有明显的叛逆性和解构性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华裔女作家在文本创作时,为了能够在美国文化语境中获得一席之地,的确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在异质的美国文化语境下,呈现在美国华裔女作家文本中所涉及的经典的中国文化传统,经由时间及空间距离的隔阂已然变得模糊。在她们的文本中,无不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书写的疏离、厌倦和背叛,但同时又显现出因无法割舍而带来的诸多痛苦。但是经过纠结的身份焦虑以后,伴随着近代史上民权运动的崛起,美国的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开始越来越觉醒。为了使美国华裔在美国的艰苦奋斗、努力生存的族裔经历,不至于消弭在美国的主流宏大叙事中,她们的文本叙事更大篇幅地开始投入对于自我身份情节、民族意识的积极思考与探索。
但是在这些女性作家最终找寻到自身发展的途径之前,她们的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权宜之选和犹豫彷徨,直接导致了来自像赵健秀这些美国华裔男性评论家的猛烈批评。赵健秀谴责黄玉雪文本中涉及的奇异中华文化遗产,和模范少数族裔华人的刻板形象,指责汤亭亭之流的自传文体是华裔作家的媚外求荣,在屈服于白人权威,在自传中贩卖中国文化的同时,又故意将中国文化描写得诡异、残忍,这无疑使自传成为助长主流文化霸权的工具。〔21〕
虽然赵健秀的言辞过于激烈,显得些许偏颇与主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她们的本族读者,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美国华裔女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不断流露出来的对自己身为东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身份的利用。令人欣喜的是,这些逐渐在美国主流文学领域取得认可的华裔女性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力量的崛起,终于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不是她们的负担,而是她们成功的资本,强大的祖国是她们坚强的后盾,在汲取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后,她们才得以以一个自由的个体身份融入到美国社会。
(二)面对白种女性世界
美国华裔女作家除了要面临男人与女人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以外,她们还面临着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于“他者”的压迫。黄玉雪因为《华女阿五》的成功被命名为最能代表美国亚裔群体的妇女,超过30多种美国或国际性的名人录将她收录其中。〔22〕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读《华女阿五》,不难发现作品文本处处可见来自异域语境的文化压迫。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文本所描述的华人淘米煮饭、带孩子、筹备婚礼、使用中药治病以及年终的祭祀祖宗大典,无不美好迷人,其目的明显是为了迎合当时一般美国读者对于华裔的某些看法。从文本叙事的基调来看,全文温和的措辞、平和的语气,无不显出模范移民的逆来顺受、自我克制的好脾气。面对种族歧视的侵扰,她们自愿地保持沉默,最大限度地克制自我,不去挑战来自美国社会的不公与偏见。我国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学者吴冰在其《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中指出,《华女阿五》的成功,其外因是当时有利于华人的国际形式和美国政治的需要,其内因是作品迎合了喜欢“异国情调”,对中国和华人一无所知且“兴趣有限”的美国读者的口味。〔23〕
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在美国学界和华人学界所引发的激烈讨论,也很好地表明了美国华裔文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这本小说的创作,汤亭亭是界定为小说文体的,但是精明而唯利的美国出版商们却是从作者的华人女性身份、文本的东方神秘气息嗅到了金钱的气味,极力地劝导汤亭亭以非小说自传的文体出版。结果却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神秘存在的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而故事文本中互不相关的故事碎片,无论如何都是与自传有巨大差距的。然而,这一点被那些怀有宗主国心态和对东方畸形认知的白人读者和评论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他们俯瞰他者文明的视角下,这本书就最终成了一本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书”,中国人眼中的一本“美国书”。
四、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的文化回归
毋庸置疑,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其后出现的美国多元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获得了华裔男性作家和其他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都为之侧目的成就。而纯粹的女性言说是不足以使之获得如此巨大声誉的,她们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她们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大胆书写与文化回归。
(一)错位的中国书写
1990年初版的《希思美国文学文选》把那些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多元文化背景下创作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文学作品中的“自我”,定义为“错位的自我”。它提出无论是在文化思想发展与相互碰撞还是在丰富的经历两方面,人们普遍从思想上体验到异化的困惑与不安,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24〕可以说,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之前,有关中国的书写,在西方世界里无一不是被冠以错位的身份、错位的声音。
世界近代史上,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除了存在其文化边缘的两个被扭曲的华裔男性——傅满洲和陈查理以外,还有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地》中所创造的“拖着辫子”、愚昧无知的“王龙”这一中国农民形象。从一个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整部作品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传教士心态,仿佛中国当时所有的普通百姓都是需要保护与拯救的对象。赛珍珠怀着一颗西方的白人仿佛就是救世主的心怀,饱含怜悯地看着这些在宗教信仰上“未开化”的中国人。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主流世界对于我们五千年的中华东方文明既好奇又无知,同时还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优越感在俯瞰。
这一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乃至政治上的原因。在20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十年的历史中,无论是饱受西方侵略的腐败满清政府,还是给日寇铁蹄蹂躏了十几年的中华民国,都给世界留下了积弱积贫的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美国成为世界的一个拥有终极话语权利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经历了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反文化运动等大动荡、大变革。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历经20多年的奋斗,中国人民彻底地摆脱了历史上那个衰弱的祖国和无能的政府形象。在联大欢迎中国的大会上“乔冠华的笑”,可以说是当时自信、自豪、充满力量的中国形象的象征。
在自我意识大幅觉醒之后,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叙事更多地展现了对华裔文化身份的思考,记叙了海外华人的成长与蜕变,更多地回归到对中华文化的叙事本源。至此,历经了从被忽略、被边缘化,到被关注、并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后,美国华裔女作家和她们的文学叙事,在美国文学上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二)中华文化回归
美国华裔作家,尤其是其中的一大批女作家,是具有鲜明的多重文化符码的群体。她们出生、受教育并生活在美国,具有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文化浸染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在她们的私人空间里,家庭生活多是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而在公共空间里则被无所不在的西方文化所包围,她们身上体现的是异质文化既冲突又交织的这样一个现实,一再地强化她们作为华裔女性多层面的双重身份,和其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与“他者”地位。
剖析自我的这个过程势必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是阵痛之后,美国华裔女作家们最终意识到,无论是她们之前的早期华裔作家们,对自身作为移民所受的不公待遇或愤怒或悲痛的书写,还是后来者为取悦西方人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创作风格,都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华裔文学取得西方社会的认可。直至1945年,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一举成为华裔女性文学中成名最早、销路最好的作品,才改变了这一局面。黄玉雪的创作虽然还是一个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世界局势发展,以及当时美国当局在政治上的考量。可是从根本上来讲,由于她的作品向“对东方有限了解”的西方世界展现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才得以使她的作品获得美国大众关注。
这一成功法门,被其后其他具有敏锐感知的美国华裔女作家们注意到,并一起效仿。然而,如果不是由于20世纪以来国际形式的日星月异、中国力量的奋力崛起,从而更多地吸引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聚焦中华文明,想必她们的文学叙事是无法获得现如今的成绩的。而这些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叙事作品的创作,开始大量借力中华崛起的力量,其创作的主题自然而然地从以前的家族秘闻、日常起居、母女言说的叙事,逐渐过渡到大量采借中华文化精华,来展现中国文化的母题。
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华裔美国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中国文化符号,事实上既不具备原汁原味的中国原生性,也不是完全西化的文化产物。它们的呈现是这批女作家们在西方语境下所采用的一种写作策略。因为她们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可以使她们的文学创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她们的华裔身份既是她们进阶的一大困难,同时又是最大的助力。崛起的中国力量、古老的中华文明,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们文化认同的力量的源泉、成功的保障。
放眼21世纪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势必引领文化全球化的到来,文化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日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核心竞争要素。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的文明,无数的文化传承,蕴藏了中国人博大精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新世纪对中华民族崛起最具贡献度的软实力。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全球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责任与目标。
注释:
〔1〕〔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195页。
〔2〕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
〔3〕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9〕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57-58页。
〔5〕〔8〕〔11〕〔12〕〔22〕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6、155、149、154、162页。
〔6〕〔美〕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982页。
〔7〕卫景宜:《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关公”与“花木兰”》,《华文文学》2003年第3期。
〔10〕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屋及其他》,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13〕〔14〕〔15〕〔16〕〔17〕〔美〕汤亭亭:《女勇士》,李建波、陆承毅译,张子清校,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38、41、168、9、192页。
〔18〕〔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19〕胡晓红、莫翠华:《“戏仿”——华裔作家汤亭亭自我赋权之话语策略》,《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20〕〔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21〕张琼惠:《从“我是谁”到“谁是我”:华美自传文学再现》,何文敬、单德兴编:《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年,第72页。
〔23〕吴冰、王立礼编:《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24〕齐小新:《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