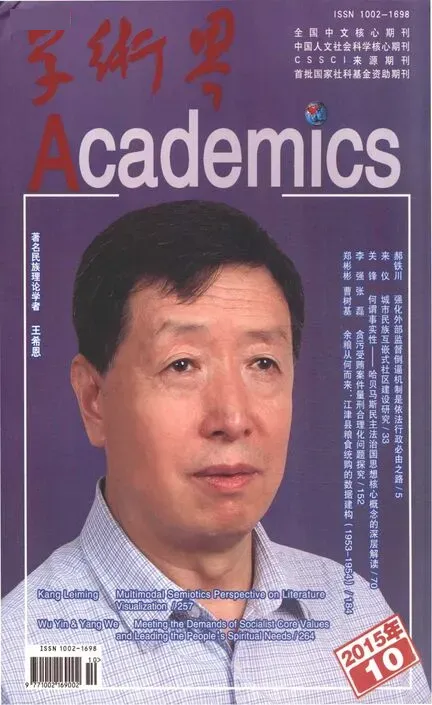辩证法的内涵革命〔*〕——重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 高广旭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学界早已进行了广泛研究。近年来,对于“颠倒”问题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研究路向:一种是“哲学观”的研究路向。强调“颠倒”既是对辩证法理论基础的重构,更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视域”的革命。〔1〕另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独断性质低于黑格尔哲学的“过程性思维”水平,“颠倒”的实质是从旧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层次跃迁。〔2〕这两种研究路向对于我们透过“颠倒”问题正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但该研究趋势存在的问题是,它只强调了“颠倒”的“哲学革命”意义,却忽略了辩证法作为内涵逻辑的理论性质对于破解“颠倒”之谜的重要价值。辩证法的内涵逻辑性质表明,“颠倒”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解释原则的“翻转”,更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理论内涵的“革命”。
一、辩证法的生命内涵革命
辩证法的矛盾思维方式源自生命本身内蕴的生死矛盾,超越有限的生命实体以求索永恒的生命意义是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固有内涵。因为辩证法在其直接性上首先表现为以生命的辩证存在方式作为反思视角来求解事物的意义与价值。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涵“颠倒”首先体现在对辩证法生命内涵的重新诠释。
生命观点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自然哲学》中强调生命是自然性的理念所达到的最高形式,更体现在《逻辑学》中对于理念生命力的强调。黑格尔非常看重思辨逻辑作为一种生命力逻辑的优越性,在《逻辑学》的导论中,强调思辨逻辑不是“毫无精神”的“畸形”和“逻辑的枯骨”,而是通过表征精神的自我运动获得“内容”和“含蕴”的“纯科学的方法”〔3〕。之后,黑格尔更明确地强调:“假如逻辑所应该包含的,不外是空洞的、僵死的思想形式,那末,在逻辑中,便根本不能谈到像理念或生命这样的内容。”〔4〕可见,黑格尔对于生命的理解总是与思辨逻辑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关注的总是思维中所把握到的生命或生命的概念形态。
黑格尔的上述生命观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生命观的影响。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人被看作是理性的动物,只有理性生命才是人的真实生命,只有理论生活才是人最幸福的生活方式。相反,人的感性生命和感性生活则被认为是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好生活的坚实保障。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让人摆脱感性生命的束缚,立足理性生命的思辨能力,构筑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理论世界。
与黑格尔及其传承的西方理性主义生命观相反,马克思认为,确证人类生命的真实性不能依靠理性思辨,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才是确证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合法领地。马克思的这一生命观早在其博士论文中便已确定,之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升华。
众所周知,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着重强调了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偏斜理论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是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最为重要的改造。马克思为何对此格外关注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从原子的偏斜运动中看到了偶然性对必然性的反抗,看到了生命的自我意识对命运实体的对抗,一句话,马克思从这里看到了人的自由。马克思指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并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意识方面那样,关于原子也可以这样说,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5〕可见,以偶然性对抗必然性、以感性存在反抗理性逻辑的辩证矛盾观点,成为青年马克思对于生命矛盾和生命自由最为原初的认识和理解。
马克思的上述生命观在之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类哲学”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这就是,人类生命的辩证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人以独特的“类”的方式存在,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可见,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作为一般生命形式的动物只以生存的尺度存在,是受自然和感性限制的受动性存在。另一方面,马克思更强调作为特殊生命形式的人类不仅具有动物的生存尺度,还具有人的生活尺度,即人是在自己有意识的创造活动中把自身的生命意义建构起来的对象性存在。而这种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生活的活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那么,人的何种实践活动与人的“类存在”本质相契合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明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辩证生命观的进一步升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8〕“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体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的诸种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具前提性和基础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对人按照自然尺度生存的证明,创造了人作为自然存在者存在的生存条件,更是对人按照人的尺度生活的证明,创造了人作为社会存在者的人类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早期所提出的偶然生命对抗必然生命、生存的自然尺度和生活的人的尺度相统一等生命观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升华。人类生命的辩证存在方式体现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的个体性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存在辩证统一,人类个体生存的偶然性目的与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必然性目的辩证统一。
通过对不同时期马克思生命观的梳理,我们看到,马克思是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确证了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即人类生命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能动性与受动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等矛盾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辩证法并不是脱离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神秘公式,而是以确证人类生命固有的矛盾性意蕴为内涵的实践逻辑。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传承的理性主义生命观的“颠倒”,不仅确证了人类生命的真实存在方式,而且“颠倒”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辩证法的生命内涵。
二、辩证法的历史内涵革命
马克思对辩证法生命内涵的革命为克服黑格尔历史观的虚无主义困境奠定基础,因为黑格尔的历史观正是建立在其生命观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只能依靠某种神圣实体来诠释,黑格尔把这种生命观与其历史观联系起来,强调历史是人类生命获得神性升华的过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异化的人性生命与完满的绝对生命相和解的过程。但我们认为,当历史被黑格尔拔高为人趋向绝对的过程时,生命与历史的真实关系就被托举到了思辨的虚空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随之陷入虚无主义的囹圄之中。因此,摆脱黑格尔历史观的虚无主义纠缠,重建辩证法的历史内涵,构成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又一重要任务。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以寻求事物存在的最高原因及其基本原理为旨趣,寻求的方式是通过对终极存在的逻辑化论证,建构起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寄托。但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数千年努力在当代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黑格尔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成为众矢之的。正如美国哲学家怀特所言: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10〕那么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病症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海德格尔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认为,理性形而上学建构的精神家园由于缺乏感性世界支撑必然倒塌,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病症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乃是形而上学本身;……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11〕这里,海德格尔深刻揭示了虚无主义发生的形而上学根源。那么,当黑格尔把历史思维方式引入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中时,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质是否得到克服了呢?
我们认为,黑格尔以历史辩证法构造起来的历史形而上学实质上仍然是虚无主义。虽然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是由理性辩证法的基石堆砌而成,而且黑格尔自己也强调历史的实质是“理性的狡计”,但是卡尔·洛维特却指出,黑格尔历史形而上学及其理性辩证法基石隐匿贯彻的是一种神学逻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实质是把“信仰的眼睛转化为理性的眼睛”,“救赎历史被投影到世界历史的层次上。”〔12〕而且我们看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自己也强调“解释历史”就是“描绘”所谓“神意”的“计划”。〔13〕可见,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实质是理性神学的历史观,神学是黑格尔历史观的隐匿前提,而这必然会动摇黑格尔历史形而上学的理性存在论根基。因为理性辩证法不过是神学救赎逻辑的傀儡和工具,历史形而上学并没有跳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一体化的形而上学逻辑。因此,黑格尔通过历史辩证法所建构起来的历史形而上学仍然是虚无主义的。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呢?如何瓦解形而上学对历史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维方式的禁锢呢?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既没有遵循德国古典哲学后期肇始的非理性主义路向,也没有选择回到康德的理性二元论路向。而是一方面,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强调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既不是神灵的“授意”,也不是理性的“狡计”,而是人类满足自身自然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4〕另一方面,从辩证法的否定性本质出发,强调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既不是理性的越界滥用,也不是无人身理性的自我运动,而是对于现实事物的批判性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5〕基于这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当马克思把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从神意计划“颠倒”为物质生产,把辩证法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时,就为历史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维方式注入了崭新的内涵,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理念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的旧世界观。
通过“颠倒”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以这种新型历史观为解释原则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在这种新世界观看来,历史的实质不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世俗表现,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也不是末日审判和精神救赎,而是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前提和结果成就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内涵并不神秘也不应该被神秘化,它就是人类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能够“颠倒”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唯心史观并克服其导致的虚无主义,就在于它以人类生命的辩证存在方式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辩证法。正是以这种实践辩证法作为理解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才描绘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其视野中的历史才既不是经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事实堆集,也不是思辨唯心主义意义上的主观想象。进而,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也才没有变成抽象的理性思辨,而是既内涵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又跳出历史的经验事实之外,成为推动历史发展与表征历史规律的历史的内涵逻辑。
作为历史的内涵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并不是人类观念史的内涵逻辑,而是人类生活史的内涵逻辑。辩证法作为人类生活史的内涵逻辑,其理论目的不再是扬弃意识的诸异化形式以实现精神的自我提升,而是通过表征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实践关系,揭示个体实践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对立统一的历史关系,并在对这两组关系充满张力的把握中,真实确证人类生命的辩证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了新的理论内涵,这就是在现实的实践批判活动中历史地解答人类的自由之谜。
三、辩证法的自由内涵革命
辩证法的生命内涵革命和历史内涵革命共同指向的是辩证法的自由内涵革命。因为人类超越有限的生命实体去寻求永恒的生命意义所成就的正是人的自由。同时,人类生命的生死矛盾在时间性的历史思维中获得诠释,也印证了历史是人类超越自然生命来确证自身作为自由生命的重要平台。因此,辩证法的自由内涵革命构成破解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之谜的理论归宿。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不是抽象的主观任意,而是意味着个体超越主观任意融入到理性绝对之中:“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16〕所以,黑格尔批判近代形式自由只注重自由的边界意识,而忽视了绝对自由突破自由边界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当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的界分揭示出,僭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界限往往会导致“自由的辩证法”:当作为个人信念的积极自由强行推广到公共领域时,必然会造成对他者消极自由的损害,即自由的初衷却导致了非自由的后果。
如果说按照以赛亚·柏林的逻辑,黑格尔的绝对自由观过多强调积极自由对于消极自由边界的突破,容易迷失在“自由辩证法”的漩涡之中。那么,马克思则实现了对于“自由辩证法”的超越。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虽然始终以求索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可能为旨趣,但是马克思的自由观却既没有陷入现代实证主义的相对主义困境,也没有陷入后现代哲学所批判的宏大叙事历险,而通过对辩证法生命内涵和历史内涵的重新确证,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由辩证法”的悖论。
一方面,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命内涵保证了人的自由不是消极自由意义上的没有根基的批判和否定,而是人作为“类存在”这一完整生命形式的复归。对于马克思而言,求解自由之谜的钥匙,不能是无批判、非反思的实证主义,它只能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加以寻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显然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极大影响,这就是,客体的真理性不是科学实证意义上与主观性的外在符合,而只能在辩证法所要求的主体对客体的否定关系中加以实现。由于辩证法是一种非实在论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辩证法的自由观主张在主客体关系的整体中实现主体自由。
尽管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辩证法只能是主客体关系的逻辑,但遗憾的是,关系辩证法还是被前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庸俗化为实体辩证法,辩证法的自由内涵被扭曲。关于这一现象,梅洛-庞蒂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庸俗的实在论者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简单替换为物质概念。物质通过激发我思的能动反映,实现不同于黑格尔的新的客观性,进而想象出一种物质辩证法。物质辩证法所导致后果是:“这一权宜之策改变了马克思的洞见:全部哲学从物的辩证法的角度看都落入意识形态,幻想甚或欺骗之列。”〔17〕卢卡奇也认为,如果不把主客体的实践关系纳入到对辩证法的核心理解之中,而只是停留于二者的直观理解,那么其“科学性”导致的必然是对辩证法的肤浅和平庸理解,对批判和革命作为辩证法核心本质的遮蔽和背离。〔18〕可见,物质实在论的弊端在于,它导致辩证法作为表征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成就自由的逻辑,被庸俗化为客观的自然规律和实证法则。更重要的是,当以这种被庸俗化辩证法再去理解历史时,马克思原本由实践辩证法支撑的辩证历史观也被庸俗化为绝对的历史观。这种绝对的历史观表面上看似坚持客观性立场,但实质上却是建立在主观意志上的相对主义拼凑。结果,历史相对主义的意志战争走向了以赛亚·伯林批判的私人强权意志对公共权利边界的僭越,自由随着历史辩证法的庸俗化走向了对自由的背叛。
另一方面,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内涵保证了,人的自由不是积极自由意义上的绝对性宏大设计,而是在人类有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自发生成。历史对于马克思而言,并不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历史进程所做的抽象思辨,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看到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差别,即黑格尔强调,辩证法不是思维对实在事物的反映模式,而是事物在主客体否定性统一中的整体性生成。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在主客体关系中完成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自我生成,但他认为这种生成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意识活动,而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对马克思而言,辩证法的主客体关系是现实的实践关系,这种实践关系表现为历史性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辩证生成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辩证生成是一致的。从而我们认为,正是以这种“辩证生成”的一致为前提,马克思的历史观才从根本上超越了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9〕由此观之,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不是被预先设定的思辨规律,而是在人的具体生存活动和生活关系中自发生成的历史总体。历史之所以具有客观的规律性,并非是某种神圣逻辑先天预设的结果,而是具有生命能动性的现实个人自发创造的结果。不是逻辑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逻辑。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辩证法作为诠释和实现自由的逻辑,既是人的实践辩证法“塑造”的结果,也是人的历史辩证法“批判”的结果。作为实践辩证法“塑造”的结果,它不是纯粹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内在标准与尺度的积极性自由。作为历史辩证法“批判”的结果,它也不是纯粹的积极自由,而是批判一切导致人的非自由状态的异化形式的消极性自由。通过述诸于寻求历史辩证法的实践辩证法支撑,马克思从根本上“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自由观,破解了自由辩证法的悖论。进而,马克思重新确证了辩证法的自由内涵,即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张力关系中回答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可能。
综上,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生命观,马克思重新确证了辩证法作为生命内涵逻辑的实践基础;通过揭示黑格尔历史观的虚无主义实质,马克思重新确立了辩证法作为历史内涵逻辑的历史根基。以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生命内涵和历史内涵的“颠倒”为基础,马克思既实践地“建构”了人类的生命自由,又历史地“解构”了扼杀人类生命自由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进而,马克思辩证法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统一中,重新诠释了辩证法作为自由内涵逻辑的真实意义。
注释:
〔1〕崔唯航:《重思“颠倒”之谜——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问题看辩证法本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李兵:《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再阐释》,《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
〔2〕孙利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段方乐:《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所蕴含的哲学变革》,《齐鲁学刊》2011年第2期。
〔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4-35页。
〔4〕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5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页。
〔6〕〔7〕〔8〕〔9〕〔14〕〔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57、147、147、171、153页。
〔10〕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
〔11〕《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774-775页。
〔1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13〕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16〕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3页。
〔17〕梅洛-庞蒂:《哲学赞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5页。
〔1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