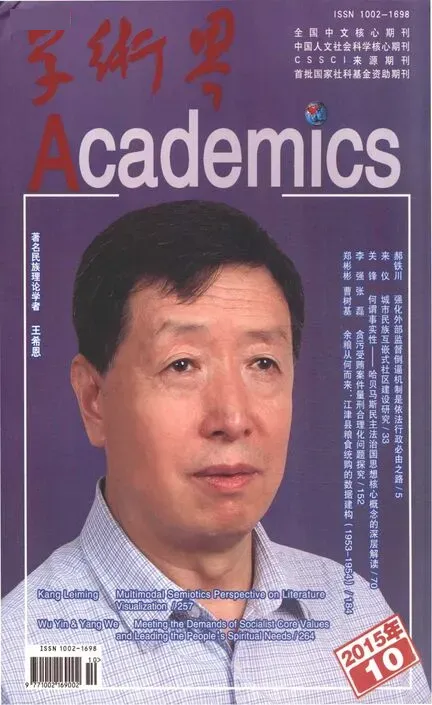论历史叙事中的想象〔*〕
○贾鹏涛,宋 良
(1.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2.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英国史家卡莱尔说:“历史是过去的生活——‘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图表和公理,而是身着黄色外套和马裤,两颊红润,内心充满激情,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个性特征充满活力的人的历史。’”〔1〕既然历史是一个“身着黄色外套和马裤,两颊红润,内心充满激情,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个性特征充满活力的人”,那史家应如何将“这个人”的这些特点在历史叙事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这里,历史想象就扮演了巨大的作用。叙事的生动有趣,基本上得益于史家通过推理展开的丰富想象。这里就引出一些问题来,此类想象性叙事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何种想象性叙事既符合史家“言之有据”的家法,又能使叙述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此类想象性叙事引起的理论问题有哪些?这都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一
一段文字要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家的想象。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范例。那么具体到历史学中的具体事件上,想象性的叙述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笔者将以“淝水之战”为例来分析一下历史著作中此类想象的表现形式。在阅读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教科书、断代史、细说体和演义体中关于“淝水之战”的叙述时,笔者发现历史教科书〔2〕和其它严肃的学术性史著〔3〕中关于“淝水之战”的叙述,不管诸位史家是用文言还是白话,基本都完全忠于史料,没有溢出史料之外的话语。“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真正做到了“言之有据”。而在通俗史书中,史家的叙述虽然也有史料做支撑,但出于趣味性和通俗性目的的考虑,史家就会添加进一些额外的叙述,而这额外的叙述中可能就有史家的想象了。因此,相比较而言,想象性的叙述在通俗性的史著中较多。为了明显清楚地达到本节的目的,所选的叙述皆来自通俗性的史著。
在有关“淝水之战”的叙述中,各位学者所依据的史料大致都来自《晋书·苻坚载记》和《资治通鉴》,因此,笔者先将学者依据的史料抄录如下,再将原始史料与通俗史著之间的历史叙述做一个比较。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读者也就大致可借“淝水之战”看出此类想象在史著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它特点。
《晋书·苻坚载记》:融于是麾军却阵,欲因其济水,覆而取之。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王师乘胜追击,至于青冈,死者相枕。〔4〕
《资治通鉴》: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阵后呼曰:“秦兵败矣!”〔5〕
在抄录完《晋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史料后,下文笔者会选择二段关于“淝水之战”的不同历史叙述,并逐一分析其中的想象性叙述。
材料一:二十几万人的队伍,后面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为何要后退,却听到朱序等人在阵后大叫:“秦军败了!”便大起恐慌,争先恐后乱逃起来。中间的见前后都在退却,也跟着乱奔。前面后退的见后面已乱,以为后边遭到袭击,也一下乱作一团。这一场面,虽然史籍上没有这样细写,但大致情形是可想而知的。……晋军上岸进攻时,阳平公苻融仍在阵前东奔西跑,喝令士卒收住脚步,但自己却因马匹跌倒(可能是被自己的士卒撞倒的),被晋兵杀死。晋军乘胜追击,冲过寿阳,直到三十里外的青冈,方才收兵。秦军乱逃,自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路上、田里、河里,到处都是尸体。〔6〕
“细说体”是黎东方开创的一种新的叙述题材,它的底本是黎东方早年的重庆讲史。黎东方在重庆以史学家的睿智和妙趣横生的语言讲历史,从各种史书中引用材料,以生动活泼、丰富有趣的语言吸引了无数的听众,以至于出现了听众竞相买票来“听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学者马先醒概括得更加明白,他说:“‘细说体’的本义,是用口讲说在先,笔之成篇在后。因此,其文其质,均别具特色:其文在说,在细说,生动精彩,引人入胜;其质在以真人实事,深入浅出,古籍记述与环境景物,结合对映,使听者、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闻目结,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7〕黎东方生前完成了《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和《细说三国》。为了完成“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出版社又邀请其他学者来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沈著就是其中之一。虽说诸位学者与黎东方的叙述风格可能会有差异,但多少也能从中看出细说体的一些特点来。就拿语言的通俗易懂来说,相对《晋书》和《资治通鉴》上的叙述,沈著的文字更为清晰明白,做到了黎东方细说体的“文字干净利落、明白晓畅,使得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8〕的要求。
较为明显的是,相比较《晋书》和《资治通鉴》,沈著则多了一些发挥。如《晋书》上是“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资治通鉴》上是“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沈著就成了“二十几万人的队伍,后面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为何要后退,却听到朱序等人在阵后大叫:‘秦军败了!’便大起恐慌,争先恐后乱逃起来。中间的见前后都在退却,也跟着乱奔。前面后退的见后面已乱,以为后边遭到袭击,也一下乱作一团。这一场面,虽然史籍上没有这样细写,但大致情形是可想而知的。”;《晋书》上是“死者相枕”,沈著叙述成“路上、田里、河里,到处都是尸体。”从这些比较中可以发现,文中的一些叙述将文言文意译成了现代文,这是史家对史料的通俗化处理。此外,还有一些是作者在设身处地理解史料后的想象性叙述,如对前秦军如何后退的描写。
材料二:那晋军已控骑飞渡,齐集岸上,一面用着强弓硬箭,争向秦兵射来。秦兵越觉着忙,竞思奔避,忽又有一人大呼道:“秦兵败了。”于是秦兵益骇,顿时大溃。苻融拍马略阵,还想禁遏部军,偏部众不肯回头,晋军却已杀到,急得融无法可施,拟加鞭西奔,那知马足才展,忽然倒地,自己不知不觉,随马坠下。说时迟,那时快,晋军并力杀上,刀枪并举,乱斫乱戳,将融葅成肉泥。〔9〕
蔡东藩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通俗史家,他以“演义”体来写历史,一生完成了13种历史通俗演义,《两晋演义》为其中之一。蔡东藩的13种历史通俗演义与许廑父续写的《民国通俗演义》40回以《历朝通俗演义》出版。此书1935年初版就销售了10万册,到1936年已经出到了第四版。〔10〕可见,此书在民国年间影响颇大。因为是通俗演义,所以蔡著的语言文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趣味性强、引人入胜。蔡东藩并没有因为是以“演义体”来写历史,就如稗史随意随性乱说,他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维,不尚虚诬”,〔11〕对比《晋书》和《资治通鉴》就能看出。也正因为是以“演义体”写历史,其中哪些是想象性描述更值得我们关注。
同样,蔡著除了意译史料外,还有一些推测想象。如《晋书》写苻融被杀,仅有“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蔡著则有“苻融拍马略阵,还想禁遏部军,偏部众不肯回头,晋军却已杀到,急得融无法可施,拟加鞭西奔,那知马足才展,忽然倒地,自己不知不觉,随马坠下。说时迟,那时快,晋军并力杀上,刀枪并举,乱斫乱戳,将融葅成肉泥。”就“苻融被杀”这个情节来说,史书仅9字,蔡著达到了99字,其细化历史的程度可见一斑。而文中“苻融如何被杀”就是蔡东藩的想象性描述。
行文至此,笔者就此类想象性叙述的表现方式作一简单小结。
第一,在通俗的史著中,虽然二位史家都用了想象性的叙述,但想象性叙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沈著是在前秦军败退时的场面上大下工夫,蔡著是在苻融被杀处颇多着墨。由此也可看出,由于原始材料记载的内容有限,因此,其中就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史料包含着多种描述方式,但当史家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描述中,就变成了仅有的一种可能性的描述了。即关于同一段史料,史家的想象性描述就会出现不同的侧重点。
第二,沈著对于前秦败退时场面所进行的想象性描述是有交待的,他说:“这一场面,虽然史籍上没有这样细写,但大致情形是可想而知的。”读者看到后也自会明白这部分是史家想象而来,这一类史著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是较为严肃的通俗类著作。而蔡著则没有讲明,如果读者不去查找蔡著叙述依据的原始资料,读者就可能把他的所有叙述当成了历史事实,至于哪里用了想象性的叙述读者更不可能知道。沈著对于前秦战败想象性描述较浅,而蔡著的描述则较为强烈。
第三,此类想象性是尽可能使叙事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且让人有读其文就能想象到要描述人物的神态、性格以及当时的场景。以色列学者里蒙·凯特在《叙事虚构作品》中区别了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简单的叙述方式,一种是丰满想象的叙述方式。他说,“比较一下‘约翰对妻子生气’与‘约翰盯着妻子,皱着眉头,咬着嘴唇,捏紧拳头,然后他站起来,砰的一声推开门,走出屋子’。第二个描述比第一个描述更戏剧化,更生动,因为他提供了更详细的描述,把叙述作用降到一架‘摄影机’的作用,把人物生气这个事实留给读者自己推断。这样,通过提出了最大信息和最小限度的信息提供者,就获得了模仿事实的幻觉。”〔12〕想象性的叙述也扮演着类似的功能。简单的叙事给出的信息量少,而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对细节的描写,则让整个叙述充满血肉,生动形象,给读者“模仿”的幻觉,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易于理解作者所要表现的形象。这种想象也就是麦考莱所说的使史家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13〕柯林伍德称这种想象是“装饰性”的想象。〔14〕
二
历史学是一门讲究有事实根据的学科,“言之有据”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管是专业的史家还是通俗类的史家都得遵守这个原则。上述想象性叙述是增加了一些材料中没有的东西,那么这种叙述方式是否违背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如果没有违背,那么这种叙述方式的合理性在哪里?即在历史叙述中,何种类型的想象性叙述是史家认可的,何种是史家不认可的。
就笔者看来,上节所引的二段想象性叙述虽然程度不同地做了一些史书上没有的描述,但基本上还是受史料的约束,只不过是史料以外意思的延伸。可以说,此叙述是史家在整体理解史实后对于史事的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推测,如苻融被杀,苻融既可能被晋军砍杀,也可能是被晋军的弓箭射倒,自家的士兵、马在混乱中将其踩死,或者有其它可能性,而蔡著选择了第一种。可见,只要有材料依据,想象性的叙述虽然有时会溢出材料,但只要其叙述合情合理,史家就是可以接受的。
史家不能接受的是,虽叙述有一些史料作为依据,但由于文学色彩太过浓厚,已经超出了合理想象的范围而达到了文学虚构。历史小说就是如此。说起历史小说,这自然让我们首先想到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是小说,但由于它是依据史书《三国志》所写,因此就有学者说它的叙述是“七分实事,三分虚事”。这里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举例分析。在第4回,曹操杀董卓没有成功,逃到中牟县,县令陈宫问明情形后,就和曹操一起逃奔。到了成皋,夜色已晚,曹操就准备和陈宫一起去故人吕伯奢家过夜。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事情:
二人到庄门下马,入见伯奢,下拜。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你太紧,你父避陈留去了。贤侄如何到此?”操告以前事:“今番不是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言罢,与操曰:“贤侄相陪使君,宽怀安坐。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以待使君。”言迄,上驴去了。操坐久,闻庄后磨刀之声。操与宫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操曰:“不先下手,吾死矣!”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杀死八口。搜至厨下,见缚一猪欲杀。陈宫曰:“孟德多心,误杀好人!”操曰:“可急上马!”二人行不到二里,见吕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抱果木而来。伯奢叫曰:“贤侄何故便去?”操曰:“被获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宰一猪相款使君,何憎一宿?”操不顾,策马便行。又不到数步,操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将伯奢砍于驴下。宫曰:“恰才误耳,今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亲子,安肯罢休?吾等必遭祸矣。”宫曰:“非也。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15〕
如此生动的语言描写,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残忍的性格特征。而这段叙述是有材料依据的,到故人吕伯奢家,把他家里的人杀掉,是来自《三国志》裴松之注《魏书》《世语》以及孙盛的《杂记》。《魏书》说曹操带数人到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他的儿子和宾客要打劫曹操,“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说吕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热情招待,而曹操“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则说曹操听见吕伯奢家准备餐具的声音,“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16〕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是在裴松之注的基础之上做了形象化地描写,也就是装饰性地想象,但显然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了虚构。比如,裴松之注中并没有记载杀吕伯奢,而罗贯中则虚构出曹操半路碰见吕伯奢,就将吕伯奢也杀掉;还有史料中只是说放曹操的是中牟县的一名功曹,不是县令,这位功曹是否叫陈宫,史料不曾记载。按照情理推论,曹操是不可能与陈宫一起出现在吕伯奢家的。〔17〕可以看出,罗贯中为了描写的形象感人,为了烘托出曹操“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自私残忍的本性,从而进行了虚构。
由上可得,通过比较原始史料,我们就可发现史家的叙述哪些是想象出来的,哪些是史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判断哪些想象性叙述是合理的,哪些想象性叙述已经超出了史家认可的范围。不过有些叙述读者很难找到原始材料在哪里,但凭借常情来推测,似乎这样的叙述也不被史家认可。如在写蔡东藩的一篇小传里,为了说明蔡东藩以真实为其史著的目标而辛勤地搜集材料,学者写到:“每当街头贴有政府通令报告,蔡东藩必摇摇晃晃出现在那里:他左臂挽着一只竹篮,篮里放一方砚台,一只‘滴水’,一段墨。右手执一支狼毫,几将眼镜贴到墙面上,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写着墙上的文字。一袭打着补丁的蓝布长衫,一双洗得发白的圆口布鞋,一缕灰白的头发随风飘扬,甩在他窄窄瘦瘦的额头之上,一滴清水鼻涕,摇摇欲坠地挂在他的鼻尖下面。”〔18〕此段想象性叙述把蔡东藩搜集材料时的一举一动刻画得是细致入微,生动形象,有如作者亲见。这段叙述可能是有文字材料作为依据,但根据常情想来,描写得过于深入细微,则其中少不了虚构的成分。美国学者彼得·盖伊说:“在虚构的故事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存在。”〔19〕因此,这种叙述生动形象,但过于深刻描写的叙述似乎史家也不能接受,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文学虚构了。在文学中,虚构性的想象是可以被文学家接受的,但在历史学中,则绝对不被史家所允许。
与此同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叙述要生动形象,无疑就需要史家的想象力,那么史家应该如何把握想象力的尺度呢?即如何使历史叙事是合理的想象而不是虚构呢?英国史学家麦考莱已经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20〕可见,史学家必须在想象和材料之间找到一个表现完美的“黄金分割点”,否则极有可能是沦为文学虚构。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叙事既要生动感人,又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历史的真实性,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对于史家实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虽然对于史家来说,要使历史叙述达到如此完美的效果很困难,但在史学实践中,“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创造出这些效果(叙述的艺术、赋予情感以趣味,赋予想象以图画的艺术)而不损害真理,这一点可以通过许多优秀的传记得到充分证实。这类著作获得巨大声誉,值得历史学家深思。伏尔泰的《查理十二》、马蒙特尔的《回忆录》、博斯威尔的《约翰逊传》、骚塞对纳尔逊的叙述,这些著作即使是最轻浮、最懒惰的人读起来也津津有味。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一本这样像样的著作出现,流动图书站前便会人头攒动;书店就会拥挤不堪;新的书籍还没来得及切边,报刊杂志的栏目里就充斥着它们的摘要。”〔21〕经过时间的洗礼,叙事高手的这份榜单里还可以加上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22〕、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23〕以及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凯撒的《高卢战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25〕、麦考莱的《英国史》〔26〕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27〕。史家似乎应该“虽不能至,吾向往之。”
三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人的历史意识不强,且古代文字用的较少,所以很多历史知识都是凭借口语在传播。口耳相传的事情,在传递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传递者删削,无趣无味的内容被传递者不断删减,同时传递者又会在原来的事件中添加一些自以为有趣的或者是想象的内容。因此,吕思勉说:“凡近于口语的文字,其叙述一定很详尽,而且能描画入微。”〔28〕历史经过口语的多次传播到形成最终的文本时,所成的叙事自然、生动、形象,能吸引读者,所讲出的故事也会情节曲折,感情丰富,内容饱满。而中西方的早期史书,无论是修昔底德的《历史》,还是《左传》《史记》,它们语言风格的口语化程度都比较强烈,史事都讲得是绘声绘色。英国史家麦考莱在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时说:“有的历史段落很长,几乎相当于莎剧中的一幕;他的叙述是戏剧性的,其目的是为了造成舞台效果。无疑,某些真实对话内容可以为历史学家获知。但是,那些发生在遥远年代和国度的事件,如果真发生过的话,它们的细节也绝不可能为他们所知,但他们也讲得绘声绘色。”〔29〕麦考莱的评论可谓至当,此评价《历史》的话语放到《左传》《史记》上依然有效。
由于早期的历史记载是真实与想象的混合物,且它的原始记载早已不知所踪,因此要分辨出这些记载中哪些是真实的内容,哪些是传递者添加进去想象的内容就特别困难了。既然如此,就极有可能出现学者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会出现不同的看法。这里以《左传》中鉏麑杀赵盾为例。晋灵公不行君道,赵盾多次劝诫,晋灵公还是不改,晋灵公对赵盾的劝诫感到厌烦,就派鉏麑刺杀赵盾。鉏麑清晨赶到赵盾家,却看到赵盾早早起来,因为上朝时间还早,坐在那里打盹。鉏麑不忍心杀赵盾,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30〕学者钱钟书认为鉏麑死前说的这句话是不可能有别人听到,因此这句话是左丘明设身处地、依照人物的性格虚构想象出来的,类似后代小说、剧本中的旁白。他说:“上古既无录音之工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五回王济川亦以此问塾师,且曰:‘把他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31〕可见,钱钟书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有意思的是,史家吕思勉的一段文字似乎在反驳钱钟书的观点。但需要马上指出的是,当然这段文字不是针对钱钟书的,因为吕思勉的分析在前,钱钟书的分析在后。吕思勉认为当时叙事的详略有一定的法度,如果和叙事主体无关,史家是不会添加其它内容进来,这是当时做文章的一种体例。因此,吕思勉认为鉏麑自杀前的这句话应属史家实录。他说:“曩尝见某笔记谓《左传》载鉏麑数语,何人闻之,实为千古疑案云云。夫《左传》之记此事,但欲以见赵宣子不忘恭敬,鉏麑之勇于就义耳。夫《左传》之此数语,已足见两者而有余,其它无关本旨,设更记之,即成赘词,故皆可以删削《左传》之记赵宣子假寐,乃以见其不忘恭敬,非以见鉏麑之乘其假寐而往贼之也。宣子为国正卿,岂得一人假寐,左右无伺候之人,且传又未言宣子始终假寐,至鉏麑欲往贼之,而尚未寐也。鉏麑之语,安得无人闻之,此等评论,直乃不直一笑。”〔32〕由此得出,关于同一件史事叙述的真实性,吕思勉、钱钟书两位学者是持不同的看法。这种现象在早期的史著中特别多,“鸿门宴”和“指鹿为马”都被吕思勉等史家指认为是一种传说,是虚构想象出来的。〔33〕如果持此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些材料史家似乎不应该用在历史研究中,但情况恰恰相反,很多史家在研究楚汉之争、刘邦或者项羽时仍然会用这些材料。那么,碰到这种情形史家应如何处置呢?麦考莱评价希罗多德的话放到这里依然有效,他说:“无疑,他对伟大事件的记述是忠实的。或许许多较小事态的描述也是如此,但是究竟哪些描述是真实的,就无法确定了。虚构的事情是如此之有似事实,而事实又如此有似虚构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对许多有趣的细节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怀疑,只得永远不置可否。”〔34〕
自20世纪历史学科学化以来,现代的史家则很少采用上述叙述的方式,他们用很多的脚注、引用语来表示自己的叙述都是言之有据,他们知道史家“无权为了叙述的生动有趣,就可以加入那些并不现实存在的而只是想象中的描写、对话和高谈阔论”。〔35〕不过知道归知道,在近现代史学中是否存在史家虚构想象的记载可能成了其他学者研究的依据呢?这个问题没办法正面来回答,只能用历史假设来回答,因为史家在没有发现该记录是虚构想象之前一直会以为它是真实的。比如,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开上海去北京,跟随胡适一起离开的罗尔纲有一份叙述,该叙述如下:
“1930年11月28日,全家从上海迁北平。我随行。人们认为特务会在车站狙击胡适,我这个书呆子却睡在梦里。这天上午八时,我随胡适全家乘出租车从极司非尔路到了上海北车站。我跟胡适步入车站来送行。满以为胡适广交游,今天一定有不少亲朋到车站来送行。别的且不说,胡适夫妇与上海金融界巨子徐新六夫妇最相好,连两家孩子也彼此相好。胡适还有一个很好朋友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与胡适的关系更好得不用说了,半个多月来,汪原放同亚东图书馆的人到胡适家帮助装书箱捆行李,忙碌不停。可是这些人,今天连影子都不见。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我心里嘀咕着。已经走到头等车厢,胡适看着他两个儿子和胡师母上了车,正踏上车梯,我忽然听到对面那边站台上有人大叫胡校长。我和胡适都掉过头来,只见一个中国公学同学,边跑来边说:‘学生会派我来送行,请胡校长等一等,要照个相。’原来那位同学在车厢对面那边站台上远远地站着,等候胡适到来,见胡适要上车时才喊叫。他跑近了,匆匆把照相机对着胡适拍了照,就立刻飞快地跑出了站台。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究竟是怎么一个场合。……”〔36〕
罗尔纲的这份记录叙述真切,又有那么多的细节描写,以至于在没有发现它是虚构前,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用麦考莱的话说就是他“虚构的事情是如此之有似事实”。相比较古代历史没有其它可参照的史料,近现代史料保存较多,史家可以通过其它材料来证明这份记录是虚构出来的。通过比较《胡适日记》得出这份记录是虚构想象的产物,余英时先生感叹道:“这是他(罗尔纲——笔者注)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被后人当成实录了。”〔37〕可见,虚构想象而成的历史叙述极有可能被其它学者当成历史事实且被接受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下来的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历史叙述。
在某一个时期,虚假的、不真实的历史被我们接受下来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这种形式的历史似乎也可算是一种特别的“虚构想象”。这里以斯大林为例,关于斯大林有过三种叙述,第一种叙述出现在斯大林活着时,他是十月革命的唯一组织者、领导者,是反法西斯的卫国英雄,是英明的领袖和导师。在德国侵略者兵临城下,莫斯科面临灭顶之灾时,他照样举行庆典并发表演说。许多战士呼喊着他的名字,向敌人发起冲锋,终于使侵略者溃不成军;第二种叙述是出现在他刚死,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他冷酷无情、专制残暴,使两千多万人蒙受不白之冤。列宁的战士被杀光,科学家被关进集中营;第三种叙述出现在斯大林死去多年后,他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他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来又领导卫国战争。他的儿子被德军捕获,德军提出用他儿子交换保卢斯元帅,斯大林断然拒绝。〔38〕第一种叙述斯大林是以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形象出现,第二种叙述斯大林是以一个一无是处的魔鬼形象出现,第三种叙述斯大林是以一个较为人性的正常形象出现,可以看出,关于斯大林的叙述是出于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接近历史中真实斯大林形象的过程,这固然是值得称赞的。但毋庸讳言的是,有两个阶段我们是将“虚构想象”出来的斯大林形象当成了历史上真实的斯大林。在古代,出于人类的历史意识不强,很多历史记载中都含有一些虚构想象性的叙述。也由于没有其它相关材料做参照,导致后代史家无法分辨出哪些内容是历史事实,哪些是添加进来的叙述。因此,后代史家对这类记载只能是“不置可否”,这似乎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在近现代,人类已经有足够强的历史意识,保存下来的史料更是多如牛毛,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类“虚构想象”的叙述呢?换言之,这类“虚构想象”的叙述是由于史料不足呢还是有其它社会、时代原因?是出于史家自己的主观行为呢还是社会、时代使得史家不得不为?如果是出于史家自己的主观行为,那么抛弃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而要虚构想象叙述的史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社会、时代使史家不得不为,那么这类现象能反映出社会、时代什么样的一般情形呢?这类现象的出现多少是出于学术的原因,多少是出于非学术的原因呢?
四、结 语
历史学是一门必须言之有据的学科,因此,史家会引用大量的史料,引用其它学者的经典话语,用大量的脚注作为自己论点成立的凭证。在传统史家看来,引语、注脚等修辞常被看作蛋糕上的糖衣,糖衣是不会影响到蛋糕的味道、形状、大小。但是通过上文的举例分析,我们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修辞不仅影响到了蛋糕(历史)的外在形式,而且影响到了蛋糕的内在质量。换句话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并不像传统史家认为得那么经纬分别,互不影响,而是彼此影响、相互缠绕在一起。历史叙述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的、书写的问题,它还与历史学的真实性、客观性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修辞不仅关系到历史书写的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以及内容结构,而且还可能关系到史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价值观和相关的利益等因素。基于此,出现上述的三种斯大林形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就像赫克斯特所说:“为了传达一种所增加的知识和意义,真正的历史学原则要求这样一种修辞,它对于唤起能力和范围来说,要以牺牲其普遍性、精确性、控制性和准确性为代价。”〔39〕就这层意义上来说,后现代对形式与内容的看法对于史家认识历史书写还是非常重要的,而海登·怀特将自己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形式的内容》着眼点就是这个问题。至于形式与内容更详细的讨论,显然溢出本文,需另辟专文。
注释:
〔1〕卡莱尔:《论历史》,刘鑫译,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0页。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2-283页;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第349-350页。
〔3〕劳幹:《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6页;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8页;刘精诚:《两晋南北朝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第63-66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234页;范文澜:《中国通史》(二),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6页;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严耀中:《两晋南北朝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傅乐成主编,邹纪万:《魏晋南北朝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83页;张鹤泉:《魏晋南北朝史:一个分裂与融合的时代》,三民书局,2010年,第123-124页;李定一:《中华史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第187-188页。
〔4〕《晋书》卷一百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8页。
〔5〕《资治通鉴》卷一百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3361-3362页。
〔6〕沈起炜:《细说两晋南北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8-159页。
〔7〕马先醒:《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黎东方,《细说秦汉》,2002年,第394页。
〔8〕邓广铭:《〈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邓广铭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9〕蔡东藩:《两晋演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
〔10〕蔡福源:《奇举有方 丹心无限——蔡东藩和他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江淮文史》2000年第2期。
〔11〕蔡东藩:《唐史演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自序第2页。这类著作,读者也可以参考李唐的《魏晋南北朝史》,李唐的著作是历史小丛书中的一本。这套小丛书是一套通俗小书,师法蔡东藩。李唐认为蔡著虽然已经简略,但仍然“于许多材料舍不得割弃,仍感繁多,不是太短的时间,所能通篇涉猎的。”(见该书序言)这套丛书有:《上古世》《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和《辽金元史》。李唐:《魏晋南北朝史》,香港宏业书局,1981年,第67-69页。
〔12〕里蒙·凯特:《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95页。
〔13〕〔21〕〔29〕〔34〕〔35〕麦考莱:《论历史》,《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0、273、262、262-263、268页。
〔14〕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36页。
〔15〕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页。
〔16〕陈寿:《三国志》上册,裴松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7〕黎东方:《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
〔18〕汤雄:《蔡东藩小传》,陈志根主编:《蔡东藩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9〕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20〕麦考莱:《论历史》,第260页。屈威廉也对史家的想像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历史的魅力就在这种结论的诗意分析中。但是,历史的诗意不是由任意漫游的想像力组成的,而是由追求事实、关注事实的想像力组成的。”转引自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如其所说地述说历史:不顾事实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张志平译,新史学第五辑《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陈恒、耿相新主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22〕吕思勉认为《左传》中的《邲之战》叙事最佳,吕思勉说“凡叙事也,能叙出其所以然,乃觉得有精神。叙战事,必使读者知其所以胜败,此篇于两军胜败之故,可谓了如指掌,而其叙晋军内部情形,则出于伍参口中,叙楚军内部情形,多出于晋人口中,则不唯见两军胜败之故,兼可见两军中智谋之士,皆能都敌,其审矣。”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28页。
〔23〕梁启超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叙事颇出彩,能感动人。他说:“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两次就不愿意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不过尔尔,而看上去令人感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2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译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艺术性又表现在他叙述的生动性和表实性上。他本人是一个参加实际活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又在许多地方作过实际调查。无论他叙述一个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一个战役,他都能使读者如身历其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译者前言第27-28页。
〔25〕罗素曾说:“我模糊地记起吉本的书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查到了这一段。这位专横的夫人立刻变得活灵活现。吉本对她已经有了好恶之感,而且想象出了生活在她的宫廷里会是什么样子。他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写的,而不只怀着记述已知事实的冷静愿望在写的。”罗素:《论历史》,何兆武、宵巍、张文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62-63页。奥克肖特也指出吉本的想象力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吉本不仅要知道一个事件如何发生,还要想象它发生的情境,叙述人物时也一样。并且举了皇帝朱利安从莱茵河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将军贝利萨留两个例子说明。奥克肖特:《历史是什么》,王加丰、周旭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121页。
〔26〕虽然古奇认为麦考莱对欧洲大陆所知是有限的且文风是粗暴的,只不过是一个通情理和有文化的庸人。但是他仍然承认《英国史》实现了麦考莱自己的期许,即几天之内取代年轻淑女们桌面上最新的时髦小说。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耿淡如译,1989年,第493页。
〔27〕古奇认为麦考莱这本著作“通过一种高度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量,他竟使读者对他书中景象的感受和他本人同样真实。”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第526-527页。
〔28〕〔32〕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第676、809页。
〔30〕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658页。
〔31〕钱钟书:《管锥篇》(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71页。
〔33〕吕思勉认为指鹿为马和鸿门宴全是想象编造的故事,不足信,并指出鸿门宴的“重重事迹,无一在情理中,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36〕罗尔纲:《胡适琐记师门五年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8-99页。
〔37〕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笔者认为余英时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参见拙作:《对胡适一段公案的定案——补证余英时先生的洞见》,《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38〕刘兴雨:《追问历史: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39〕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陈新译,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