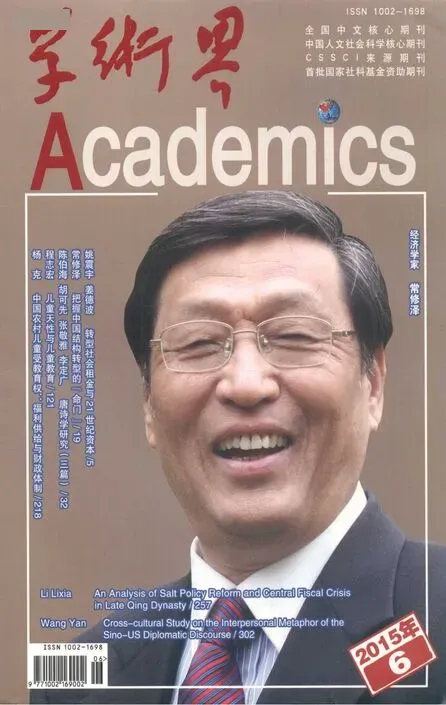儿童天性与儿童教育〔*〕
○ 程志宏
(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天性的概念
目前,关于“天性”还没有一种非常权威性的、广泛接受的解释。
《心理学词典》上解释天性是“有机体天生的或遗传的特性或特征。”〔1〕
《实用教育大词典》上解释“‘天性’是‘天然的品质或特性’、‘自然赋予’。从上代继承下来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感受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2〕
《教育大辞典》(简编本)上注解“天性”即“人的先天本性。语出《荀子·儒效》‘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3〕
马克思将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首先肯定了人的这种自然性“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的属性”。马克思曾以自然遗传的观点,指出人具有自然力、生物力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4〕
刘晓东认为“天性是人身上的自然性、宇宙性,它是自然意志、世界意志、宇宙意志”,“它的内容是本能、无意识和意识的先天形式以及部分意识,这部分的意识也是作为本能与无意识之镜的意识,是对本能与无意识的意识,就像肉身有自我复制的欲望和生长的能力一样,精神也有自我复制的欲望和生长的能力。精神的成长与创造,与肉身的生殖与成长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它们是人的本能,也是自然的意志。”〔5〕
本文将天性视为自然对人的发展的规定性,也是人身上的自然属性,也就是夸美纽斯的“自然法则”“种子”、裴斯泰洛齐的“自然天性”、福禄贝尔的“神秘本能”(福禄贝尔分为四种:活动的本能、创造的本能、艺术的本能、宗教的本能)、蒙台梭利的“内在教师”、杜威的“本能”(杜威分为四种:社交的本能、制作的本能、研究和探索的本能、艺术的本能)等。
二、天性是不可教的,需要敬畏和保护
1.天性是不可改变的,需要敬畏
天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秉赋,“它含有一切遗传的东西,一切起点,一切人体中存在的东西。”(弗洛伊德)人不是一张任凭文化涂写的白纸,他是一个富有活力和特殊结构的实体,当他自身适应时,他是以特殊的、确定的方式反应在环境的,如果人像动物一样,通过改变自己的本性,自动地适应外在环境,并适合生活在他所唯一能适应的特殊环境中,那么,他就会进入专门化的死胡同,这种专门化乃是每一种动物的命运,于是,人就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人自身能在毫无冲突的情况下,适应违背他本性的所有环境,那么人类也就无历史可言。人类的进化植根于人的适应性,植根于他的本性中无可毁灭的某些特征,这些特性强迫他永久无止境地寻求更适合于他内在需要的环境。天性是使人在各种情况下保持自我的依据。天性是不可教、不可改变的,我们应对天性保持敬畏。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介绍了郭橐驼丰富的植树经验和高明的种树技术:他“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视仿慕,莫能如也”。至于种树的诀窍,“郭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孽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郭橐驼认为树木的“天性”就是:“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其漪也若子”“其置也若弃”,种树一定要做到“不害其长”。郭橐驼懂得树木的天性,正是对树木的天性保持敬畏,“不害其长”,顺着树木的自然天性去栽培,从而保护和发展了它的生机,收到了“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他种树“无不活”的诀窍。所以,“其置也若弃”,看似不管不问,无所作为,其实非也。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是顺应自然,不作干扰,这正是郭橐驼的过人之处。他种树的全部秘密在于顺天致性,即尊重树的自然天性和成长规律,保护树的自然潜能并使其充分表达出来。而其他种树的人则不然,他们违背了树木生长的天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表面上好像很关心,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以致于摧残了树木的本性,扼杀了它的生机。这样的种树人多像溺爱子女的那些成人们!
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也以隐喻的方式告诫我们:过多干涉、干扰、束缚儿童,反而使儿童这一幼苗无法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更无望成为栋梁。教育应当尊重儿童的自然本性,应当给予儿童自由成长的空间,应当使儿童这棵小树柔嫩的树干和枝条自由地享受阳光雨露。
2.天性是潜在的,需要保护和激发
天性是不可改变、不可教的,但是天性也是需要保护和激发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暴风雨会把它摧毁;幼芽需要阳光,但曝晒会使之枯萎;天性亦如此。儿童的成长需要成人的帮扶,儿童的成长离不开教育。
夸美纽斯一再强调:“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只需把那暗藏在身内的固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并重视每个个别的因素就够了。”“万物确乎都已存在人的身上:灯、油、火绒,以及一切用具都已具备,只消他善于擦出火星,点上火,点好灯,他便立刻能够看见,能够充分享受上帝的智慧放在他身上和世间的稀有的珍藏。”〔6〕
蒙台梭利也认为儿童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或内在潜能,这种生命力是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按照遗传确定的生物学规律发展。
面对这些“种子”“内在生命力或内在潜能”,教育的任务不是给孩子所有他们要学的东西,而是唤醒和激发,并使之循着儿童自身的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的发展,正如福禄贝尔所说:教育的目的是唤醒人类内在的精神本性和力量。
孩子的天性是需要引导的。教育者要拥有农民种庄稼的心态,在合适的时机给庄稼施肥、浇水、灭虫,精心呵护之下,终会有丰收之果。
三、保护天性就要保卫童年
卢梭:“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7〕
童年是人生最自然的时期,是天性保存得最完全的时期,是潜在人性内容最完整的时期。马拉古奇曾说过:大自然下令,人类的幼仔期在所有动物中应当持续最久的时间。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是因为大自然知道多少河流必须跨越,有多少小径必须重新走过,大自然让成人与幼儿有更正错误的时间、克服偏见的时间、幼儿可以掌握他们自己呼吸的韵律,重塑自己、同侪、家长、教师和这世界的形象。〔8〕他劝导人们:“成人必须团结一致,反对给予孩子过度的压力,反对让孩子匆忙地脱离童年的做法。”〔9〕
考古专家已经意识到:有些极富价值的宝库,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不宜开掘。面对童年,面对儿童的天性,在我们对早期教育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热衷的时候,似乎对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表现出莫大的主观和自信,甚至还表现出莫名的牺牲与冒险精神。相反,西方国家对早期儿童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等诸类问题的思考和选择,常常表现出更多的犹豫和慎重,即便是经历了18世纪中叶以来教育的理性时代,教育已经充分沐浴在“自然、自由”的氛围之中,他们在对儿童早期教育的选择上还是显得小心翼翼。对于儿童的教育尤关谨慎,不恰当地“开发”、“开掘”不仅不利于儿童的茁壮成长,而且可能会令其受伤甚至毁灭。
人为地压缩儿童的童年,使得儿童的童年期过于匆忙,儿童被迫去成长,而且成长过快、太迅速,势必严重影响儿童正常、健康地成长。因此,保护天性就要保护童年。
1.“童年的消逝”
童年期有其自身的意义,像哪吒那样生下来就会跳、会跑不一定(甚至可以说一定不)是好事。早开花的树反而凋谢得快,而晚一点开花的树却得到较大的力量和耐久性;早熟的果子只能当天有用,却不易保存,而晚熟的果子却可以常年保存。
但是,我们从生活中悲哀地看到:童年期正在消逝,儿童的生活不断受到成人生活的侵蚀;儿童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儿童作为人,正沦为某些外在力量任意把玩的对象、任意加工的原料;儿童的天性、儿童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没能够得到应有的礼遇,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异化”,教育成为某些成人手中的“工具”,也成为儿童身上的“枷锁”。这种现象在早期教育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前早期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恰恰是我们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忽视儿童内在天性,无视儿童需要和原发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当前早期教育中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识字、英语、才艺等正规的学业学习,过分强调训练,过分符号化等现象,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过分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倾向……事实上,儿童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他们自己的最佳时间内学会那些童年期的常规任务的。他们获得惊人的知识、语言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储备,这通常并不需要成人专家或学院式教育的帮助。但是,当他们的潜力因额外的任务而被开发得太早时,问题就出来了。因此,重新审视教育,重新关注童年、儿童的天性、儿童的生活方式、儿童的现实生活地位,赋予儿童教育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已经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1)过早专门化训练
曾经有人问过弗洛伊德,以前维也纳街头到处可见的擦鞋童后来都做了什么?这些鞋童精明世故,能言善道,因而颇得顾客欢心。弗洛伊德思考了片刻,回答道:“他们后来都变成补鞋匠了。”艾尔金德非常赞赏弗洛伊德的回答,从某方面来说,这些鞋童成长得太快,以至于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的人格特质过早被定型,几乎没有给未来人格的发展预留任何的空间。过早专门化训练不利于儿童的系统的成长、整体的发展。如果我们不适应儿童的天性,任凭我们的教养推动儿童超越其自然的水平,这种做法对儿童的正常成长并无益处,反而可能导致长期发展的受阻。
皮亚杰认为,人为地推动儿童超越其自然的水平,无异于训练动物在马戏团中表演杂技,这种做法对儿童的正常成长并无益处,反而可能导致长期发展中的阻滞。有时候,文火慢熬要远胜于猛火强攻。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儿童发展的较慢速度也许有利于最后更大的进展。”〔10〕
费歇尔(Kurt W.Fischer)等人提出了“成长与发展的非线性动态模式”,不仅证明了皮亚杰的有关思想,而且进一步揭示出,在某种行为上的不当刺激所导致的短期变化,会对人的整体成长系统产生弥散性的影响,使整体发展脱离平衡状态,并且在接受不当的催早熟刺激的那个领域,产生较为低下的发展水平。
费歇尔等人指出,当成长速率过于高涨时,可能导致系统成长的紊乱无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了导致稳定地平衡地系统地发展,应保持比较平衡的成长速率,使得成长过程呈相对平衡的趋势。〔11〕由此可见,教育和干预所提供的支持性影响应当是适应有度的,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应当是适中的,这样才有利于系统的成长、整体的发展。
洛伦兹也强调非专门化和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是人类的关键特征,过早专门化是不明智的。从根本上讲,儿童成长得太快,他们的心理过早地结构化、定向化,也就不可能为进一步的发展留下空间。
21世纪的今天,中国教育市场里许多人吆喝着“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两个半世纪以前,卢梭却告诫人们:“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他称此为“最重要的和最有用的教育法则”。“按照自然的进程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正好同你实行的教育恰恰相反。在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具备种种能力以前,不应当让他们运用他们的心灵。因为,当它还处在蒙昧的状态时,你给它一个火炬它也是看不见的,而且,在辽阔的思想原野中,它也不可能找到理性所指引的道路,因为那条道路的痕迹是这样的模糊,就连最好的眼睛也难以辨认。所以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你开头什么也不教,结果反而会创造一个教育的奇迹。”〔12〕其实,卢梭上面的话并不是主张浪费童年时光,而是批评那些类似“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他其实也是主张教育的,他主张的教育是“消极的教育”:“你必须锻炼他的身体、他的器官、他的感觉和他的体力,但是要尽可能让他的心闲着不用,能闲多久就闲多久……所有这些延缓的做法都是有利的,使他大大地接近了最终目的而又不受什么损失。”也就是说不要让儿童成长得太快,不要进行过早的、专门化的训练,“如果延到明天教也没有大关系的话,就最好不要在今天教了”。〔13〕
(2)过度开发
早期的过度训练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很深刻的。在《奥林匹克赛会历年优胜选手题名录》中,先在儿童竞赛中得奖,随后这个选手又在成人比赛中得奖的人,总共只有二三例,原因是明显的早期训练中的剧烈运动损耗了儿童选手们的体魄。〔14〕
喜而不语,不是说高兴不能分享,而是不能为了自己高兴,而让别人不痛快。《菜根谭》中说:“淡泊之士,多为浓妆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喜而不语,说的更是不张狂自傲。
教育也是如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认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学记》中说:“学不躐等也”,意思是学习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由简到繁,不能跳跃。这些说法,非常契合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
然而观诸今人,往往却是“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定授以三百字,常恐其精神力量有余”。很多教师和家长,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一天培养出个“神童”,这明显是对教育规律的违背。在如此教育方式下,资质较差的固然会被拖垮,资质较好的同样也会被拖垮。
2.让孩子享受童年
事实上,我们对于儿童阶段的基本认识就需要反思。我们常说童年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要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一切为了将来。但童年本身呢?童年有没有自身的价值?童年算不算人生的一部分?
卢梭认为那种“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在”的念头,“简直是发了疯”。这是因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童年的光阴就更是短暂得不能再短暂了,是“稍纵即逝的时光”。在卢梭看来,童年是儿童的极其珍贵的财富,我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去剥夺这笔“财富”,童年的生活是有价值的。那种轻视儿童现在的做法,导致了儿童在其童年受尽了折磨和痛苦,享受不到儿童应有的欢乐。因此,“既然是不能肯定目前的痛苦能够解决将来的痛苦,为什么又要他遭受他现时承受不了的那么多灾难呢?”〔15〕所以,在目前就把儿童弄得“怪可怜的”,而“好歹终有一天使他获得幸福”的希望,“这样的远虑是多么糟糕”。苏霍姆林斯基也宣称:“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这不是对未来生活的准备时期,而是真正的、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16〕
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享受童年,而不是逼着他们把这段人生牺牲掉,牺牲给成人社会和他们自己的“不定的”未来。
四、教育的本质在发现天性并引导其成长
当前的儿童教育通常并不是遵循和顺应儿童的天性,而是打着“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旗号,通过给儿童灌输一些知识、技能来戕害儿童的天性,发展儿童的“潜能”。这种做法错误地把儿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外向内填塞的过程,这样的儿童教育正是刘晓东所批评的“向儿童填输许多东西——这等于是向井里拼命填东西。填到最后,井里再也没水了,孩子的心灵也就失去创造力了”。〔17〕
1.儿童的天性如同“自给自足”的“种子”
夸美纽斯率先提出了著名的“种子说”:“在我们身上自然地播有知识、德行与虔信的种子。”“把来到世上的人的心理比作一颗种子或一粒谷米是很正当的,植物或树木实际已经存在种子里面,虽则它的形象实际上看不出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种子如果种在地下,它便会向下生出根芽,向上长出嫩枝,嫩枝凭着它们的天生的力量日后便可长成枝柯与树叶,垂着绿荫,点缀着花儿与果实。”他强调,“人不是一块可以随心所欲雕刻的木头;他是一个不断地塑造着自己的活的形象。”〔18〕
裴斯泰洛齐也赞成夸美纽斯的论断,认为儿童的天性就如同“一颗小小的种子,它含有了大树的形状和特征,被种在土里,整个的大树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有机体,它整个的发展均存在于其种子和根部。人就好像是一颗大树,在新出生的孩子身上隐藏着在其整个一生中所要展现的本领。”〔19〕
2.教师像“园丁”一样,发现并顺应“种子”成长的规律
夸美纽斯认为一位教育者就是一个园丁,他照料着花木,但总是尊重他们成长的自然(天性):“自然世上的人的思想形象难以看到,但是可以把它比做草木的种子核仁。因而,人没有必要从外界得到一切,而是要使隐藏的内部的一切得以展开和表现。”“教师的职责无外乎是在他们思想上耕耘播种,小心地浇灌上帝的花木,这样便能发展和成长。”〔20〕
裴斯泰洛齐声称正确的教育如同园丁的艺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呢?它就如同是一位园丁的艺术,在他的照看下,百花齐放,万木争春。人对花木实际的生长没有任何作用,生长的要素寄存于小树木之中,园丁种植浇水,但是上帝让其生长,教育家也同样如此。他不能给人任何一点力量,他既不能给他人生命,也不能让他呼吸,他仅仅能注意不让外来的暴力损害或打扰他,他要关照让发展沿着固有的规律前进。”〔21〕
福禄贝尔指出,儿童是花木,教师是园丁。“我们给动植物以空间和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存在于他们身上的法则、规律,它们能茁壮成长。对幼小的动植物要耐心,不能采用拔苗助长的办法,因为任何相反的做法都会打扰它们纯洁的展开和良好的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幼小的人类个体却被当作一块蜡、一堆泥,可以由人去任意捏造……对葡萄必须剪修……尽管是小心翼翼地剪修,可是如果园丁在劳动中不能够被动地注意遵循植物的自然规律,也难免毁掉藤架。……在处理自然界的事物时,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可是在处理人时,我们却迷了路。而在两者中起作用的力量却是来自同一源泉,遵循同一规律。”“教育的任务在于促进儿童的自我活动和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挖掘儿童内在生命的潜力。”〔22〕要完成这些任务,促进儿童“内在本质力量”的和谐发展,教育就必须依据儿童发展的规律,遵循儿童的天性。
近年来风靡世界的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就把教养的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瑞吉欧的成功经验表明,只有教育符合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兴趣与需要、儿童发展的规律,只有教育的“大纲”符合儿童的“大纲”,才能成为成功的教育。
3.教育还要引导天性的成长
把儿童比作种子或花木,把教师比作园丁,这是一种类比。实际上,儿童比种子或花木要复杂得多,教师的工作比园丁也要复杂得多,尽管它们拥有共同的或共通的规律。
裴斯泰洛齐指出,人类与动植物的生长作为生命现象有其一致之处,但是人类又不同于动植物,“人类生命的真正源泉、人类善恶的真正源泉是从人类感觉的自我和感觉的环境中吸收过来的,而不是依附于人的躯体;它超越了一切肉体的羁绊,它是自由的。”〔23〕当树木处于旱或涝的状态时,是否浇水、排水取决于园丁的意念,也就是说,树木的死活取决于园丁的安排。但是人不同,人可以意识到外部的一些影响并加以自我调整。总之,“树木不能自我帮助,人能”,因为人是自由的。〔24〕人的成长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同时,人面对同一环境又可以有一定的自由选择,从而主动地参与自我塑造活动;花木对于园丁是受动的,而儿童面对教师则有其积极主动的一面。因此,相对于园丁来说,教师不仅要发现并顺应“种子”成长的规律,还要指导天性的成长。
蒙台梭利虽然强调儿童体内存在“内在教师”“精神胚胎”“有吸收力的心智”,强调儿童通过“工作”达到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和谐,获得自我发展。同时,在蒙台梭利看来,在儿童的自由活动、自我教育中,教师并不是无所事事,她对教师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一,具备观察的素质,了解儿童的特点。她说“观察时等待”是教育者的座右铭,观察是幼儿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和研究的唯一一本书”。其二,善于指导或引导儿童。她说:“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刺激生命——使儿童自由发展与开展”〔25〕。她要求教师成为“有准备的环境”的“保护者”和“管理者”,成为儿童的示范者,成为儿童作业的促进者,成为良好纪律的维持者。其三,成为学校与家庭、社区的联络者和沟通者。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有自己的“大纲”,他指出学前教育是否成功,取决于“教师的大纲变成儿童自己的大纲的程度”。如果成人或教师的大纲偏离了儿童自己的大纲,是断然难以实现的。他极力批判分科教学和超前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让儿童在学前期便完成学校大纲,就是说,授予儿童每门学科的按其逻辑编排的系统的知识,那么很明显,我们永远也不会完成这个任务——即将传授知识与使这个大纲变成儿童自己的大纲结合起来。”〔26〕但是,他认为教育不能“只是充当发展的尾巴”,不应消极地适应儿童智力发展的已有水平,而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不停顿地把儿童的智力从一个水平引导到另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他指出“只有那种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良好的教学。”〔27〕因此,他提出“最近发展区”理论,要求教育者创造“最近发展区”,帮助儿童从“独立水平”迈向“帮助水平”。其追随者进一步提出支架式教学(scaffolding teaching)理论,其本质在于:以“最近发展区”作为教师介入的空间,为儿童的学习提供支持,促使儿童主动而有效地学习。在这个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儿童学习的有效性,教育者必须参与到儿童的学习过程中去,不断提出挑战性任务和必要的支持,激发其心理机能的运作和转化。
五、教育应帮助儿童获得幸福
儿童教育要为儿童的可持续性发展服务,而这个过程应该是幸福的,并且儿童教育的最终极目标是要使儿童过上幸福的生活。人类生生不息的努力、奋斗,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文明,都是为了使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幸福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感受,一切与人的身心健康成长相关的积极感受才是幸福的。那些与儿童的身心发展相一致的活动都会给儿童带来幸福。对于儿童来说,学习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因此,教育能否给儿童幸福,就成了他们整个生活是否幸福的主要标准。
幸福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与优越。在音乐剧《欢乐公主》中,在妈妈柔佳看来一个芭比娃娃价值几百元,小乌龟只值几元钱。而对于女儿欢欢来讲,喜欢就是快乐,拥有小乌龟比拥有芭比娃娃更幸福。所以成人必须了解儿童的天性,了解儿童的兴趣需要,发现儿童的生命法则。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儿童是否幸福取决于当前的活动是否满足儿童的天性需要。不同的生命阶段有着不同的需要,成人的需要不能代替儿童的需要。儿童有自己发展的需要,杜威说“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与规律的世界。”〔28〕
要使儿童愉快地接受教育,要使教育愉快地为儿童所接受,就要认识儿童发展的天性和需要,不要强迫儿童去接受违背其自然本性的东西。“一切违抗儿童成长内在力量的、外在强加的活动对儿童来说均无幸福可言的,甚至是不幸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成人的干预使儿童没有充分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同时,我们也可以认定,成人的努力——朝着儿童生命潜能成长方向的努力,能使儿童更好地拥有幸福。”〔29〕
教育要在遵循儿童天性的基础上使儿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儿童教育的过程应使儿童感受到幸福,儿童教育是为了儿童幸福的生活。愿祖国的儿童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如阳光下的花儿,幸福成长!
注释:
〔1〕〔美〕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2〕《实用教育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3〕《教育大辞典》(简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29年,第67页。
〔5〕刘晓东:《论教育与天性》,《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4页。
〔6〕〔18〕〔20〕〔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年,第74、28 页。
〔7〕〔12〕〔13〕〔15〕〔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28、96、97、73 页。
〔8〕〔美〕C.Edwards,L.Gandini,G.Forman:《儿童的一百种语文》,罗雅芬等译,台湾心理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9〕〔意〕Loris Malaguzzi等:《孩子的一百种语言》,张军红等译,台湾光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页。
〔10〕杨宁:《幼态持续、发展的原发性和早期教育》,《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30页。
〔11〕刘晓东:《儿童教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14〕刘晓东:《教育者应当学会等待》,《早期教育》2002年第10期。
〔16〕〔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唐其慈等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1年。
〔17〕刘晓东:《解放儿童》,新华出版社,2002年。
〔19〕〔21〕〔22〕〔英〕伊丽莎白·劳伦斯:《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纪晓林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65-166、21、210 -211页。
〔23〕〔24〕〔瑞士〕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夏芝莲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3、322 页。
〔25〕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26〕〔27〕〔前苏联〕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成球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86页。
〔28〕赵祥麟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76页。
〔29〕虞永平:《幼儿教育与幼儿幸福——对幼儿教育的一种反思》,《幼儿教育》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