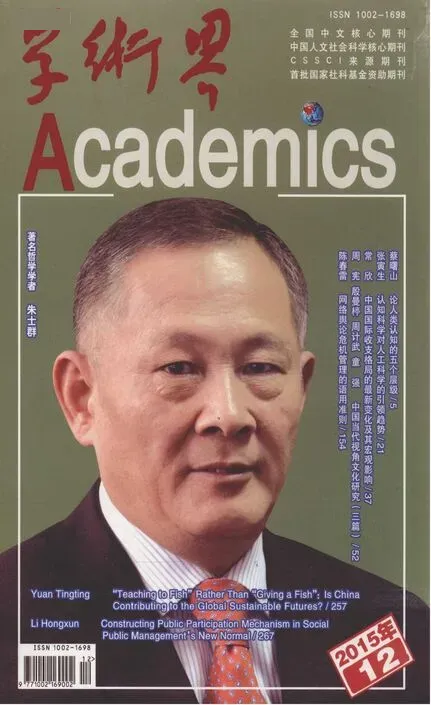新媒体时代宗教传播的新态势及社会风险〔*〕
○戴 燕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2.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2012年12月12日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发出了他的第一条推特,该行为明确地传达出罗马教廷在对新媒体保持多年保留态度之后意欲在数字世界中建构宗教领地的决心。推特信息发布之后的影响力之大(转发量达到120万次,甚至超过当红明星贾斯丁·比伯)〔1〕足以使这次新媒体传播行为成为宗教传播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一部宗教传播史,其实也是一部媒介发展史。作为人类社会最初的宇宙棱镜,宗教正是通过各种媒介——口口相传、书写印刷、壁画雕塑、广播、电视以及WEB1.0的互联网平台,传播其教义理念,给予行动者心灵慰藉,同时也实现了群体认同并最终在异质行动者之间构建起跨界的信仰共同体。
正是得益于对层出不穷媒介的有效利用,宗教才始终在世界文化谱系中保持着优势地位。据统计,当今世界60亿总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1%。〔2〕
然而,由于宗教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亚文化等有着天然相互纠缠的内在发展脉络,宗教在解决人类终极困惑的同时也导致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这种伴生现象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焦点。WEB2.0时代的媒介极有可能将上述现象推至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峰值水平,从而酝酿出难以估量的风险。正如梵蒂冈教宗在2008年的世界传播节上所言:“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可以为人类的益处提供未曾有过的机会,但也有可能掘开未曾有过的邪恶的深渊,当传播工作失去伦理的依据,避开了社会的控制,就会陷入约束人的自由和生活的危险之中”。〔3〕故而,他慎重地提醒神职人员:“在数码领域,对神职人员而言,更重要的是心灵而非驾驭媒体的能力”。〔4〕当宗教借助于新媒体步入佛陀所言的“一多互摄、重重五尽之因陀罗网”的华严境界时,如何管理我国6.32亿网民,5.27亿手机网民,〔5〕让新媒体时代的宗教传播保持正面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试图梳理新媒体环境中我国宗教传播的新态势并分析其中酝酿的社会风险。
一、新媒体背景下宗教传播特点
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描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意味着传授者都是开放的、不可测的,原有的角色壁垒趋于消失,信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流动模式滑出推送人设置的边界,沿新媒体塑造的社会网络到达任意对象,由此必然带来信息的编码和解码方式、影响力、覆盖面、信众结构等一系列变化。
1.弘法者具有极高的媒体自觉,新媒体使宗教传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2010年8月30日,武汉归元禅寺“归元隆印”微博在线开通,日前收听人数突破200万。2012年4月26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分组论坛之“佛教弘法的现代模式”在香港举行。健钊长老表示,弘法者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将弘法内容细化,对症下药,弘法利生,将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精神传给各种人群。
截至目前,腾讯微博上宗教类用户5255个,新浪微博宗教类用户约409个。其中“延参法师”微博粉丝数高达3257万,微博发送数为23435个,单次阅读量和累计转发量均令人惊叹。如果再加上微信、易信及QQ用户,每天通过新媒体接触宗教信息的人员恒河沙数。除此之外,依托于各类移动终端的宗教类应用工具不断被开发、使用,在苹果的应用商店里运用中英文对主要宗教进行搜索之后,显示基督教的应用列榜首,有500多个;其次是佛教,有200多。
“对于技术相对落后,内容资源却很丰富的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的优势就在于一种面向全世界更多人的24小时不间断的交互式内容传播。这种海量信息储存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让新媒体的优势进一步扩散”。〔6〕
借由新媒体的功能,宗教传播能实现即时信息分享、跨越文化阻碍、突破制度壁垒,在不同背景群体中进行教义传播。和以往的任何一种媒介相比,在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如果将他们(宗教、道德、权威、传统价值以及政治意识形态)通过精神传输的习惯予以电子物资化,他们的威力将会倍增:电子传教士与互动式基本教义派网络比起那种遥远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面对面传输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更有效率、更具穿透性的教化形式。”〔7〕
2.传播对象空前异质化,宗教多维传播结构开始形成,跨界“宗教共同体”在新传播结构中快速聚集并开始从“想象”迈向“现实”
曼纽尔·卡斯特曾预言道:“在这样一个没有控制、令人困惑的变迁世界里,人们倾向于围绕着‘原始认同’而重新编组:宗教、种族、地域、民族等。”〔8〕
后麦克卢汉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互联网的内容,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网的内容,而且使用因特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因为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一样,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换言之,上网的人是因特网的内容。”〔9〕当人开始成为信息的节点时,传教士、信徒、教会组织、QQ、微博、微信、宗教网站走到一起,形成跨越传统和现代的多维传播结构:从教会组织到信众;从单向度的网页宣传到多维度的新媒体分享;从一对多的信仰建构到多对多的抱团分享,信息在不同个体中实现了病毒式传播。
多维传播结构的到来,宣告了神职人员主导的垂直传播结构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宗教世界社会结构的改变。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社会结构是人在各种关系中不断排列组合的结果。现代化的发展促使社会成员的个体化追求日益强烈,彼此间的疏离也日渐明显,这使得信息在关系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当多维传播结构让信息超越了种族、资本、身份、角色等因素,在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中流动时,信众群体认同的路径改变了。
梵蒂冈作为宗教界的前行者,除了拥有自己的网站,还与Facebook、Wiki Cath等社交网站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且建立Pope2you网站整合其在各种社交网站中的资源和内容,配合教会推广。帕典尼神父认为:“借着Pope2you,我们尝试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讯息的内容和教宗的工作,不仅是告诉青年一些消息,而是要与他们一起体验、生活。”〔10〕在我国,宗教传播对新媒体的运用也毫不逊色。归元禅寺通过微博、义工交流群、善缘义助学子群构建起虚拟互动平台,群主与群友在新媒体上共同学习佛门经典并时时分享。事实上,新媒体OTO的互动模式不仅为亿万信众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帮助对象找到精神依归,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而且因为可以跨时空传播、消弭物理世界的局限,“想象的共同体”借助新媒体信息聚合实现从线上走到线下,从而为“现实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可能。在过去几年中,归元禅寺依托新媒体平台组织了几百场OTO的活动,成功地实现归元禅寺的宗教推广。
3.新媒体助力宗教信徒的群体结构向年轻化、知识化方向提速发展
Google Buzz上的一位传道人感慨道:“社交网络把不同的朋友圈混合在一起,让我的教会弟兄姊妹看到我工作中的劳苦愁烦,……可以说,SNS让我们在一个无缝的处境当中表达信仰如何渗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11〕新媒体传播以个体为中心,具有极大的自由度、丰富的信息内容,其个性化、人性化的传播特点,更易于达到让“上帝体现在细节里”的传播目的。随着宗教传播主体媒体自觉意识不断觉醒,其传播策略迅速从单纯“信徒取向”的“信仰传播”向“大众取向”的“入世传播”转变。正如《福音时报》的编辑所言:“保罗使徒教导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要谦卑下来,进入福音对象的内心世界”,〔12〕与其他的宗教传播媒体相似,《福音时报》将商业、家庭、环球与教会、神学并列作为主要栏目设置,所有资讯被设计为一键分享到各个社交媒介。
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4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0.7%,50岁以上网民比例还不到8%。中专以上学历人群占到总人群的51.7%。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5.9小时。青年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好奇心强、价值观尚未稳定,自我同一性形成过程中容易茫然、焦虑、混乱、精神空虚,且一旦认同某一文化,该群体又容易因为极强的自信心产生文化中心主义现象。作为社会的未来、新媒体的积极使用者,青年群体自然成为宗教新媒体传播的主要目标。伴随宗教新媒体传播策略的调整,我国宗教信徒正在提速迈向年轻化、知识化。2010年中国宗教蓝皮书指出,我国44.4%的基督徒信教年龄在35至54岁之间。来自南京的调查也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到总数的53%。〔13〕2012年教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实证研究”课题组对7所高校的调查结果显示52.1%的大学生接受宗教在文化上的影响,7.8%的大学生表示有皈依某种宗教的想法。〔14〕归元禅寺自从2010年调整了传播策略后,信徒由原来的四多,即“老人多、妇女多、病残多、文盲半文盲多”,逐步向年轻化、高学历化人群发展。
我国的宗教传播正呈现出2010年3月17日《中关村在线》转述的预言:网络兴起对宗教界或许是个福音,特别是对懒得进教堂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网络宗教信仰的兴起,让年轻人既能信仰,又不用早起到教堂做礼拜,创造出“教堂2.0 时代”。
4.媒体经营门槛降低,宗教传播迎来人人是“上帝”的“去魅”时代
威尔伯说:“宗教力量之所以高妙伟大,绵延不绝,独一无二,其精髓要义,就在于它是一门灵性体验的科学。”〔15〕为此,宗教惯常采用“权柄”和“权场”结合再现神秘力量的方式达到传播的目的,传播中心被锁定在寺院、法师手中。
新媒体时代的技术赋权正在打破这一宗教传播的历史传统,传播中心分散化趋向日益明显。斯达克和芬克认为,即使是面对宗教,人们的理性精神依然发挥作用,他们“在追求彼世回报中,愿意接受一个排他的交换关系”,但是“会寻求最小化他们的宗教代价”。〔16〕新媒体技术降低了使用者的知识成本和经济成本,这对用户具有极大的诱惑,但其深层原因却是新媒体能在虚拟社会中提供社会成员建构新人际关系的可能,助力信众突破我国阶层的固化状态。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宗教网站、论坛、QQ群,法师及信徒的博客、微博、微信,APP应用甚至宗教用品网站出现了井喷。
与此同时,我国的宗教传播也迎来了韦伯所言的“去魅”时代〔17〕。2004年复旦大学“网络时代的宗教”学术研讨会提出:“网络宗教发展到极致,就会形成一种虚拟宗教,其没有组织实体、没有场所实体,除了教主之外,一切仅存于网上,由此,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新创一个宗教”。然而“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18〕“修辞幻象能够将一大群人带入一个象征性现实的综合戏剧。”〔19〕WEB2.0时代,新媒体改变了上帝与人之间的神授启示关系,正如梅洛维茨所言“有了电子媒介,群体就失去了对自己后台情况的独有接触,并能看到其他群体的后台行为。”〔20〕当前,数字压缩确实化解了我国宗教信息传输的瓶颈,但客观上也使宗教的神圣性加速逝去,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开始缓慢消融。
二、新媒体时代宗教传播状态的社会风险
新媒体迅速俘获用户芳心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功能给用户带来新的体验,即:传播主体的匿名性、传播行为的主动性、传播信息的建构性、传播效果的放射性。匿名性降低了传播主体对被追责的担忧,提升其使用的愉悦感;主动性为传播主体提供自我展现的平台,助力其突破社会刻板印象塑造个人形象;信息的建构性为传播主体释放精神世界,获得与外部世界的链接提供机会;而传播效果的放射性则能让传播主体的声音放大,提升个人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然而,当“人人都是麦克风”时,极端性、冲突性、情绪性、群体性和难控性也开始粉墨登场,成为新媒体时代传播的伴生特征。这些特征放置在我国社会结构背景的宗教传播框架中,更是孕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值得警惕。
1.新媒体与“信仰至上”的结合,加剧宗教传播中“群体极化”现象,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宗教传播是传播主体借助传播媒介宣传某种教义、理念,旨在让传播对象接受并践行该教义理念的行为。不同的传播媒介在展示、传递宗教教义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新媒体的副作用之一是传播内容的随意性,信息的真伪无人关心,源头不明的信息在传播主体转发、评论、点赞等行为下一样进行病毒性传播。而且,传播主体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往往采用情绪化的语言对信息进行再加工,观点越偏激、表达越感性,越能获得网友的关注,病毒性传播的强大力量让独立、理性的声音淹没在一边倒的狂欢中。这势必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加剧。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言,“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1〕拉塞·斯皮司与其同事通过研究也发现:“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更加突出,大约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22〕
自带群体极化风险的新媒体遭遇到宗教文化后,风险翻倍,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这是因为,“信仰至上”是宗教的基本原则,在客观上,信仰体系维系了社会稳定,“它使社会沟通成为心灵沟通,把所有个别情感融合成一种共同情感”,〔23〕但是,每一种宗教都宣扬自己的教义才是绝对真理,当高歌信仰神圣性的信息在新媒体传播圈中以“入世的”“反复的”“互动的”“多点对多点”的方式进行传播时,宗教的排他性被强化了。然而“对上帝的过份虔诚会导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视为理想,把对神的牺牲和谄媚看成是美德。”当“一个太窄的心灵只有可容一种感情之地,在爱上帝的感情占有了这颗心时,这种感情就把一切爱人类,并为人类效用的心除掉了。”〔24〕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儒家文化的兼容并蓄、中华民族的温和友善以及政教合一不是我国社会的传统等因素,我国没有出现如西方基督教新旧教派之间、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之间势如水火的冲突和斗争。但新媒体加剧宗教传播群体极化的客观现实也会造成或加深社会群体之间的区隔,特别是像“微信”这样强调圈群、小众、互动传播的媒体,极其容易在圈子内部形成舆论合力,且能将舆论合力变为线下的行动力。因此,在新媒体时代,需要更加密切关注宗教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以及其他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构稳定的文化结构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2.新媒体“把关人”角色的缺失给邪教组织可乘之机,加剧宗教传播监管难度
大众传播时代,记者、编辑及媒体从业人员处于社会信息流通网络的核心位置。他们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能够运用专业知识过滤、筛选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新媒体时代,信息“把关人”开始大众化,媒介的开放性带来他律日趋式微,然而“网络不能分辨真实与虚假、偏见与客观、琐细与重要,一旦错误信息送上网络,追回和纠正几乎是不可能的。”〔25〕这使得新媒体中宗教教义的真实面目扑朔迷离,来自境内外的各类宗教组织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神秘主义、反社会、反传统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大行其道,正如埃瑟·戴森所言:“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26〕
根据警方统计,1990年至2014年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了百余起暴恐事件,造成各族群众、公安民警、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0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近期落网的涉暴力恐怖犯罪嫌疑人,都有着通过互联网和多媒体卡等载体观看暴恐音视频、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学习制爆方法和体能训练方式的经历。这些暴恐分子还通过QQ群、短信、微信以及非法讲经点交流制爆经验,宣扬“圣战”思想,密谋袭击目标。〔27〕
2014年5月28日发生在山东招远震惊全国的故意杀人案,就是邪教组织“全能神”一手炮制。“全能神”教于1989年由“呼喊派”骨干赵维山创立,仅仅在2001年11月,全能神在国内的信众就达到30万人,经过20来年的发展,“全能神”组织人数达数百万。“全能神”之所以发展异常迅猛,在于其特殊的传播策略。在传播内容上,以赵维山为代表的邪教组织往往借合法宗教的“壳”推行邪教教义,如“全能神”首先号召传播对象信基督教,然后踩在合法及信教自由的基础上宣扬“全能神”是传播福音最好的选择;在传播媒介上,除了选择传统媒介,更是有效利用新媒体“把关人”缺位、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等特点。赵维山为发展和控制国内的信众,通过互联网以电子邮件形式从美国向国内发送指令,据报道,这些电子邮件,大都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加密,加密达到二十多级,接受者有专门密码进行破译。出于对新媒体传播的重视,“全能神”邪教组织,在其组织结构中特别设立电脑组部门。2012年12月,青海警方捣毁的“全能神”多处窝点中,除了常规的宣传品外,还收缴了一批电脑、扩音器、手机等传播工具。
根据凤凰网的调查,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型媒体实施宗教极端犯罪十分突出。我国公安机关目前已侦办煽动分裂国家和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型媒体实施宗教极端犯罪案件11起。〔28〕因为邪教组织的危害性,我国政府一直将其列在重点监管范围。但是加密电子邮件,层出不穷的新媒体聊天工具,各种类型的APP,日益发达的移动互联技术让信息的即时追踪、辟谣变得日益困难,监管难度非常大。
3.新媒体时代宗教传播效率高,传播对象年轻化、知识化趋向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站前站长、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前主管大卫·艾克曼,在2003年出版的《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造中国以及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一书中,主张西方应用基督教驯服中国,并预测“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这一预测让人心惊,也因此引发学界对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变化的关注。
201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宗教的现状与走向: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提出我国基督教信徒有3300万。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了由金泽和邱永辉主编的《中国宗教报告》,其间提到:中国基督新教人数为2305万人,其中受洗的是1556万人。此外,还有来自不同渠道的、从几百万到1亿3千万落差巨大的各种估算人数。尽管数据缺乏一致性,但都不约而同反映出我国基督教信徒激增的事实。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无疑有媒介的力量。
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宗教传播策略的调整除了继续增加宗教信徒的人数,更带来宗教信徒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具有更大的潜在风险,因为是群体结构而不是单纯的群体数量决定了社会系统的演进。尽管各个渠道的统计有一定差异,但各方的数据均显示,新媒体时代宗教传播对象日益知识化、年轻化。在新媒体的助力下,知识分子、大学生甚至更为年轻的群体成为宗教渗透的主要对象。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开展“中国大学生媒体接触与消费行为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智能手机拥有率达95.9%,“微博”使用率为71.1%,“微信”使用率为82.3%。〔29〕每天海量宗教信息通过这些媒介到达尚不具有分辨能力的青少年群体。信息发布主体多元:有正规的教会组织、网络宣教士,活跃于网络的基督徒,还有大量的“神棍”与“网络水军”,信息内容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对青少年群体主体世界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困难。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30〕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转型期,价值体系多元结构的并存分散、弱化了主文化的影响力,教育的工具理性化难以给主体心灵带来慰藉,现代化的发展在赋予主体丰富选择权的同时也带来选择的无所适从性。个体精神世界无可奈何地坠入碎片化、支离破碎的状态中。与此同时,青少年对自我认同、彼岸世界、普世价值、终极关怀的好奇与探索却从未停止,反而因为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而更为强烈。然而,我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对新媒体缺乏敏锐性显得乏善可陈。内容和实效性严重不足且传统、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内心共鸣,手段上依然以单向说教式为主,缺乏互动,难以激发青少年的主动性。美国“大使命中心”的刊物曾载文指出,“网络是神所赏赐的媒体”。〔31〕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苍白给蓄势已久的宗教新媒体传播留下可乘之机。
4.新媒体助力宗教更为便捷地侵入公共领域,宗教的反世俗化进程对政治稳定构成挑战
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曾成功地将在权力领域发生激烈冲突的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诠释终极价值的宗教系统与干预生活世界的政治系统的剥离有力地维护了政治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权威,因为“如果没有合法性,一个统治者,一个政权或者政府体系就很难得到处理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长期的稳定和良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32〕
但是,宗教却并未放弃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和入侵,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便通过凸显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或者“去私人化”进入全球复兴状态。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坚定预言,伴随社会的理性化、现代化发展,宗教必会因世俗化而走向衰微。而今却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那种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世俗化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一些地区甚至比以往更具有宗教性。”〔33〕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宗教复兴必然会重构社会结构、影响社会变迁进程。社会学家卡新鲁华认为,“现代性理论和世俗化理论都只为宗教留下边缘和私人化的角色,但世界各处的宗教传统拒绝接受这种角色。多个社会运动涌现,不是有宗教性的本质,就是以宗教的名义挑战那些首要的世俗领域……这些持续竞争的结果之一就是私人的道德和宗教领域的再政治化,公共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新规范化。”〔34〕
面对宗教的全球复兴,中国政府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及2004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上,通过反复论证,提出四个适合我国历史文化的宗教问题处理政策,即: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对宗教的角色边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宗教与政府的功能边界进行了明确的定位。
然而,新媒体时代科技与宗教的全新组合则可能模糊上述边界,为宗教在社会结构版图中获得新的位置赋予更多的力量。基督教中国的著名网站“约拿的家”为适应群体新的生活方式,陆续推出“圣经软件”“微看圣经”等APP,伊斯兰教近期上线“礼拜助手”APP,拥有中阿两国语言,中文版还特别设置“朝觐报名”和“朝觐事务”等栏目,解决中国教徒因语言障碍无法参与线下活动的困境。相比对传播对象生活方式的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宗教传播似乎比以往更热衷在文化、经济公共领域甚至政治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以“旷野呼声”基督教网站为例,导航条除常规的宗教类名目,还有文学、家庭、视频、时评专栏等很生活化的栏目。
时评专栏中的文章无一例外通过评论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热点事件宣传基督教。内容时时更新,最近备受社会关注的《穹顶之下》已经被作者一番论证后引申为应当通过信耶稣解决诸多问题。类似的还有,姚贝娜去世、司马南移民美国、易中天讲座、上海踩踏事故、官员腐败等等民众关注热点,均成为宣传基督教的素材。“旷野呼声”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每一篇文章都能实现一键分享到各大社交网站。这些文章彰显了宗教在公共领域的立场及欲求,而新媒体是其有效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通过有序开展宗教领袖参政议政等方式释放了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正能量,也因此建立起西方民主国家都难以实现的信仰与理性对话系统,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相关法律、制度界定了宗教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美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宗教必须有限度地影响公众生活,宗教的王国应当建立在人心向善上,若宗教与某个政治联盟,就会陷入权力纷争;宗教经营的是安慰和希望,而不是政治权力、控制和利益。〔35〕运用新媒体进行的宗教传播正在动摇已有的平衡。
三、结语:对新媒体时代宗教传播的思考
宗教在我国社会的历史更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始终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未能在传统社会中获得稳定的纵向结构性地位。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异常强大的封建社会权力代际传递系统及匹配的儒家文化消解了外来的和底层社会的力量。所以,我国的宗教未能像西方社会一样,通过动员普通大众形成与主流文化系统的对峙进而进入到纵向权力结构或者成为社会领域中独立的力量,而是一直作为权力的附庸或群体亚文化存在于我国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较低的社会分化现实以及执政党的追求保留了宗教在个体层面的自由和组织层面的非自由,从而在客观上既维护了权力的合法性又尊重了社会成员的精神慰藉,宗教依然以力量分散的子系统面貌深度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国宗教的这种特殊位置不仅有效地弥补了其他系统的功能缺陷,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新媒体时代,我国宗教传播的嬗变可能打破上述的平衡,来自不同背景的弘法者敏锐地捕捉到新媒体的赋权功能,并依托新媒体迅速建立起新的传播策略:构造多维传播结构、对青年群体精准传播、推动“想象共同体”向“现实共同体”迈进、确立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故而,新媒体赋予宗教前所未有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与此同时,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群体极化”性、匿名性导致信息的“难辨性”、交互性带来的“超强动员能力”、即时性造成“监管的滞后性”等特点在遭遇到宗教信仰之后可能成为酝酿社会风险的沃土:在这里居心叵测的邪教拥有可乘之机,背景各异的社会成员因信仰结成新的社会群体,主流文化系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宗教更容易突破边界渗入到其他社会领域。上述的任何一项特点,都是对稳定社会系统极大的挑战。
本文认为,保持我国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我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是确立新媒体时代宗教位置的前提,为此,面对新态势和新风险,需谨慎处理以下关系:
1.单个社会成员的宗教信仰自由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社会成员出于对彼岸世界、自我归属的原始需求通过新媒体了解宗教信仰、选择宗教派别、开展心灵层面的宗教皈依及相关活动,属于个体的自由。但有组织的宗教派别借助新媒体聚拢、号召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性实务,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要坚决予以杜绝。
2.作为亚文化的宗教与独立的宗教权力场域。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因其善念、善心和善行,在抚慰心灵、消解文化冲突、实施人道救援等方面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是我国社会文化谱系的重要成员,应当予以支持。同时,宗教权力场域的划定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历史情境,作为以神为核心的象征权力系统,其活动的内容应当是终极关怀,活动的边界应当止步于伦理的追求,对其他领域的任意介入都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为此,一方面,须建立宗教舆情监测系统,通过实时监测拦截境内外不良信息,阻止宗教的越界行为,过滤错误言论,净化虚拟空间,既保证社会成员的需求得到正当满足又能维护社会系统的内在平衡。另一方面,须完善主流文化的传播机制。面对新媒体时代宗教传播的汹涌之势,最有效的方法是以疏代堵、多元展示。普及宗教的基本知识、揭示宗教的基本特点有助于受众理性选择;丰富主流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通过建立新媒体传播机制联动线上与线下的活动,让受众由被动变主动,在多元价值体系相互碰撞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
注释:
〔1〕互联网资料:http://www.cnbeta.com/articles/219130.htm。
〔2〕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中国宗教学术网,2010年12月2日。
〔3〕转引自许正林、乔金星:《梵蒂冈网络传播态势》,《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4页。
〔4〕《罗马教宗鼓励神职人员试水网络新媒体》,《中国天主教》2010年第3期,第49页。
〔5〕《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第34 次调查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6〕李强:《新媒体:传统媒体强劲的竞争对手》,《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4期。
〔7〕〔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5页。
〔9〕〔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10〕梵蒂冈为青年创立的网站,http://www.h2onews.org/index.php?option=com content&view=article& aid=18337。
〔11〕基甸:《社交网络与基督徒》,http://www.inlord.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39:2011-06-11-07-57-04&catid=127:2010-03-12-15-15-33&Itemid=551。
〔12〕《福音与科技:进入新科技下禾场灵魂的内心深处》,http://www.gospeltimes.cn/news/17675/。
〔13〕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课题组:《关于南京宗教的调查与思考》,《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张承安:《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实证调查及其分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5〕〔美〕肯·威尔伯:《灵性复兴——科学与宗教的整合之路》,龚卓军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64页。
〔16〕〔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德〕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慕尼黑的演讲。
〔1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2、154页。
〔19〕〔美〕E·鲍曼:《想象与修辞幻象:社会现实的修辞批评》,转引自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20〕〔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逝的地域》,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21〕〔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美〕Patricia Wallace:《互联网心理学》,谢影、苟建新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23〕〔英〕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98页。
〔24〕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第632页。
〔25〕〔美〕斯坦利·J·巴伦:《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和文化》,刘鸿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27〕互联网资料:http://news.sohu.com/20140711/n402080803.shtml。
〔28〕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40529/40521880_0.shtml。
〔29〕杨雪睿:《中国大学生手机上网现状及其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8期,第120页。
〔3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1页。
〔31〕《网络宣教》,《大使命双月刊》2008年第10 期,http://www.gcciusa.org/Chinese/b5_publications/GCB/2008/Oct/P01.pdf.
〔32〕〔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41页。
〔33〕Grace Davie,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SAGE Publications,2007.
〔34〕Casanova,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5-6.
〔35〕马继孔、陆复初:《爨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2-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