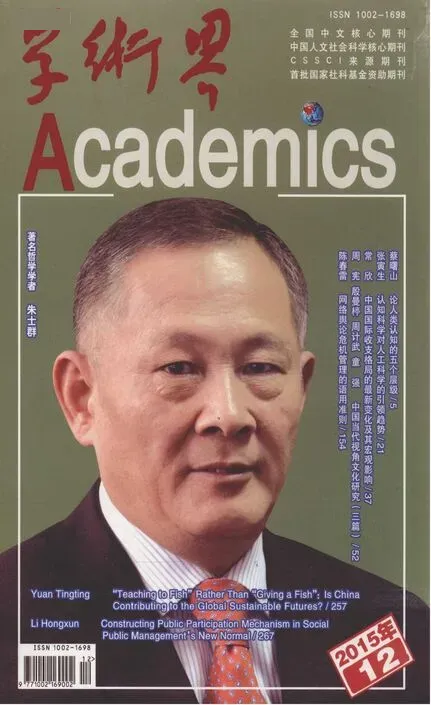当代城市景观形象的变迁〔*〕
○童 强
(南京大学 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仍然很传统。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的城市、城市景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往昔城市的对比,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当代城市空间及其景观的实质。
中国当代的城市生活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包括了很多方面,诸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增长以及消费观念的普遍流行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城市日趋功能化。
传统城市当然也会为居民提供工作、居住、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方面的条件,但总体上商品化程度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层次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有公交车,但人们的住所距离工作地点都不太远,大多是步行可以到达的范围。人们外出时,依赖步行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鲁迅曾提到早年在南京时从下关走到夫子庙的经历。前工业化时代的美国许多城市相对也很小,人们可以轻易地横穿整个城市,被华纳称之为可以“步行的城市”。〔1〕大体上传统城市还是一个半自给自足式的生活聚落。
但现代城市,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功能系统网络,集约化的功能区,一个时刻需要保证其功能正常运转,能够输出各种功能的地方。许多学者都赞同城市就是增长机器的观点,〔2〕我们目前也是把城市的经济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城市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功能化,功能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方式。人们需要居住,城市提供住宅;人们需要饮用水,城市提供自来水管网系统;人们需要出行,城市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人们需要连接互联网,城市提供各种接入口;人们需要交往和心理安慰,城市给人创造出始终在人群之中的感觉。当然,理论上讲,人们得到城市功能系统服务的代价,就是必须为城市功能系统服务。传统城市也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但相比较,现代城市的功能服务已经高度专业化,具有复杂的管理系统控制和强大技术力量支持等特点。
伴随着城市的转型,城市景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试从传统城市景观特别是街头景观是什么样、现代城市景观是什么样、发生变化的关键是什么等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景观变迁。
一
首先来看传统城市,传统城市距离我们并不远。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城市都还是非常传统的城市。传统城市空间分区比较模糊,具有有机的特征,街头比现代城市更能保持景观的多样性,呈现市场及日常生活的场景。
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分离,职务领域与生活事务、职位所拥有的财产资源与私人物品相分离。〔3〕所以,现代城市总是按照特定功能进行规划分区。传统城市,工作场所与居住空间,大体上是分开的,但距离很近,有时甚至紧紧连接在一起,难以区分。西方前工业化城市中的职业街区,手工业(金属加工、木工艺制作、纺织等)者的住所、作坊和贮藏室就是处在同一个楼房里,作坊在沿街的一楼,主人的居室在二楼,顶层则是贮藏室和雇工、学徒及仆人的住处。〔4〕中国传统城市中也有许多类似的布局,但不是西方垂直的结构,而是水平的结构。房屋沿街的门面房作为商铺或者作坊,商铺后面是店主的住处,再往后则是加工后场、仓库、雇工的住处等,房屋的后门大多临河,临河的房屋又称为河房,货物通过船只运送到商铺的后门,直接进入仓库。虽然也有功能区域的划分,但划分总是相对的,由于空间上的密集、相近、毗邻,因此各种不同的功能空间事实上是相互交错重叠,空间的分割与延伸呈现有机的特点。
居住与手工作坊空间上的靠近,造成了街头特有的市场景观。学者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城市的研究揭示其街区空间与景观上的特征。当时的“街头不仅作为市场,实际上也成为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繁华商业区后面的居住区,成了产品的生产地。……在小街小巷总是民居和作坊间杂,而且在每一居所总是在制做什么东西卖”。〔5〕“全城商业和居住区域并不隔离,因此任何地方都是居住区,街上到处都是小孩、鸡禽和猪豕”。“商业区的主要街道干净整洁,商铺装饰华丽,总是挤满了购物的人群。而一般的小街小巷却简陋肮脏,精英阶层很少光顾。”〔6〕居住与工作场所虽有分别,但也是交错在一起,相间使用。
街道的基本功能虽然仍是交通,但它连接着商铺的房子,所以也是自由市场,既有月市,也有日常市场。除了在房屋中的店铺之外,还有街头露天的小贩小摊。商人、小贩在街头出售商品没有什么限制。一些街道都是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果市、花市、柴市等。一位西方人观察,不同的街道通常是不同的交易,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由此形成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7〕不仅是成都,诸如南京等城市,许多旧街巷的名称如颜料坊、箍桶巷、弓箭坊都可以看出其作为市场、作坊的历史。作为重要的商业空间,街道首先集中展现出商业景观。
建国以后,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以至于城市的居住和生活功能的发展颇为缓慢。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还是延续着传统的空间格式。城市的轻工业、商业都不很发达,小型企业、商业分布在城市的居民区当中,城市整体的功能化程度不高。从基本的空间模式上来看,生产与居住虽然是分离的,但两者的距离非常靠近,有时甚至是融合在一起的。一些“大单位”独立使用地块,除了建有工作用房、工作场地,还为本单位职工提供住房以及食堂、浴室、商店、菜场、礼堂等生活配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空间,特别是居住区域就是按照不同的单位来划分,单位建房,并分配住房给本单位员工,单位成为城市居民工作、生活空间的统一体。〔8〕
传统城市,街头作为公共空间,不仅呈现各种手工作坊、市场景观,也呈现民众日常生活的景观。这主要因为中下层民众,居住的房屋狭小,邻居们的住房又彼此毗连,人们的生活簇拥在一起。许多生活内容都从严格意义上的自家空间外溢到街头巷尾、路边空地、公用院落等这类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间里,展现在这种公开或半公开的空间中。正如19、20世纪之际成都城市的目击者所说:“在穷人区,人们生活在低矮的房子里,由于室内空间非常小,所以诸如吃饭、做手工、休闲等日常活动,都不得不在室外进行。虽然那些背街狭窄,却经常塞满了货摊、小贩、桌子、临时搭的棚。”〔9〕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长期城市住宅建设的滞后,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都非常紧张,居民们已经习惯了在家门口的巷子、空地或者院子里吃饭、纳凉、晾晒衣服,女人们聚在一起择菜、聊天、织毛衣、洗衣服,邻里彼此交流信息、情感、观念,孩子们在弄堂里玩耍,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在这类公共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是可以看到的,是可以听到的,是可以闻到的,它们构成了传统城市相当普遍的景观。只要你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你自然每天可以看到它真实的景观。
二
其次我们回顾四周,看看中国当代大城市的特点。中国当代大城市的分区,功能明确,技术力量支配强大,但城市区域景观也因此趋于单调,传统景观的多样性已经很难再见。
现代城市功能分区的观念非常明确。建筑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基于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观念,分析城市的不同功能,给予每个功能以明确的空间分配,并在交通道路、居住区以及工作场所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城市中物与空间都体现出特定的明晰的功能。如道路仅仅是作为实现单一化通行功能的装置,他正是按照这种现代性的纯粹功能思想把道路划分为7个等级系统。甚至印度昌迪加尔的植被也被分为六个种类,“每一种都有一个明确的功能”,〔10〕功能概念成为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原则。
现代城市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功能概念的影响。如今的城市大多以功能为主进行规划分区,如商业区、金融区、休闲娱乐区、开发区、产业园以及住宅区,由此形成不同的空间区域。
区域内部功能决定景观,商业区不可能建成码头、村落式的景观。传统城市除了少数区域功能特征比较明确,如中心商业区、公园等,大多数区域各种功能空间如厂房、住宅、小商店等总是交织在一起。现代城市功能分区后,功能的输出、功能的满足成为区域核心的目标。
更进一步来说,现代城市的功能系统都是高度专业化技术的结果,技术支配的场所,不能不呈现技术强力支配的景观。这为城市景观带来了两方面后果,一是集中化,为了适应技术的需要,我们上下班最好是集中在高峰时刻乘坐地铁,这样效率最高。购物也是集中在大型购物中心,或者移至网上,但时间要集中在诸如“双十一”这样的特殊时刻,这样也给技术批量处理带来方便。二是专业化。专业化就是专门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控制的垄断,其他非专业人士无法介入这一专业领域。最有意味的例子莫过于城市道路。由于城市居住与工作地点相去较远,现代城市对道路通行提出很高的要求——无法依赖人自身力量解决而只能求助于技术解决的事情。于是城市出现了地铁、轻轨、高速路、高架、隧道等各种通过技术手段提高通行能力的装置。道路不再是传统时代,人们可以随意走动、驻足聊天、摆摊设点,甚至挤点路边堆放货物的空间,而是成了技术支配的专门化、管道化的功能装置。它是机器,是大型交通设备。随着通行能力的提高,道路越来越专业,它排斥了其他功能兼容的可能性。地铁只能是地铁;高速路只能是高速路;为了实现高速、量大的交通,快速道路只能用于汽车通行而禁止一切行人和非机动车辆上路。
而传统城市中,道路面对的是慢速、量小的交通,通常只需能够满足步行、低流量的车辆的通行即可。它有相当部分的功能实际上是生活空间的衔接与外延,特别是小街小巷,传统城市布满了很多狭窄的小巷。城市的道路系统网络是从最宽的主干道延伸到稍窄一些的大街,再从大街延伸到细小的巷子。这些细小的巷档弄堂是城市循环末端的毛细血管,只有这些末梢能够深入城市生活的肌体之中,渗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当中。
这一切在专业化、管道化的道路机器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道路的本质已经变化,两者也呈现出不同的功能景观。新式的小区住宅模式彻底根除了以住的毛细血管,街道作为一种民众生活场景消失了。在一个半公共、半公开的空间中,个体自由安排布置表达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三
最后我们讨论,从传统城市到现代城市,造成景观变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归根到底,当然还是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人的行为模式改变了;二是城市空间的社会本质发生了改变。
从古到今,社会结构、人的行为模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汉书·食货志》记载古代到了冬季,农民回到城邑中居住。“妇人同巷(里中道路),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是说,邻里女性,到了夜晚都会“相从”,集中起来从事纺织工作。一个晚上有半天工作量,这样一个月就能有四十五天的工作量。但是劳作本身并不仅限于劳作,为何女性要集中起来夜绩呢?这样可以省夜灯燎火的费用,不仅节省,而且还能“同巧拙而合习俗”,女性干活过程中,相互学习技术,所谓“同巧拙”,而且通过相处说话交流,女性能够维持统一的习俗与观念。不难看出,人的行为并没有简约为单纯目的的行为,抽象为单一的功能,而是保持整体性,劳作行为与情感、理智、习俗、观念、共同体因素等各方面都有关联,劳作保持在人生全部意义之中。
但现代功能分区要求人们配合相应的功能行为,也就是说,不仅空间功能化,而且人的行动也功能化,景观也功能化了。当人进入商场时,功能分区的特征要求出现在这个区域的人,只有相应的功能化行为——购物,才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购物过程中,事实上包含着休闲、交往、自我认同等多方面的功能,甚至仅仅只为打发时间,但在一个专门购物的场所,人们的行动至少被空间功能规定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专门在商场中睡觉、散步,没有人会理解那是发生在商场中最典型的行为。在一个功能化的空间中,人们功能化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景观,而这个景观仅仅从功能上就可以得到理解与解释。随着功能分区的明确,现代城市各种区域景观单一而蕴含贫乏,就在所难免。
另一个方面,城市空间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传统城市空间虽然有充分的定义,但在其边缘、缝隙地带,城市监管不力,这使得民众能够在自身周边空间,形成自身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景观。相反,现代城市空间,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是高度而严格定义的,功能分区界限明确,民众介入或参与景观营造的可能性降低,参与的范围收缩,城市整体景观趋于单一。
空间定义的弱化,使传统城市空间保持某种程度自发的生长性,进而在景观方面呈现出混杂性、多样性。传统城市许多空地和边缘地带的权属、功能、使用等状况都不甚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规定,但城市监管比较薄弱。明代谢肇淛《五杂组》卷三记载当时南京路边店家都逐渐溢出自家的范围,扩展到马路边,当时路宽九轨,“蚕食而充拓之”。于是为政者勒令拆违建,“欲复当时之故基”。时为官员的谢肇淛却以为大可不必:“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攘攘也?”他认为路边是无用之地,百姓占据使用完全合情合理,与我们今天对空间的看法完全不同。1949年前,外来移民划船到达上海后,就沿着苏州河沿岸以“滚地龙”的形式定居下来,〔11〕可证当时有空间占用的可能性。各大城市非常庞大的棚户区形成之初都因为空间定义与监管的极度宽松所致。这种情形对于现代城市已经不可能了。现代城市空间界定与管理非常严格,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受到监管,清除占用、拆除违章建筑的力度都非常强。
传统城市空间界定与监管存在各种松动,城市空间因此能够形成有机生长的格局。这里所谓“有机”,主要强调城市生长过程中顺应社会自然,减少人为干预的程度。传统街区之所以充满魅力,也正在于城市低度规划的特点。它有一定的安排,但安排又不是死板固定的。它有规划,但规划的刚性很低。它是应对生活各种变化而“生长”出来的自然形态。空间不够,房主会在楼顶上加盖一层;侧墙也会延伸出来一个小房间;较宽的过道又因为两侧房屋加宽而变得异常细窄,等等。城市会因为这种自治自主的生长,呈现出空间景观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城市街景可能并不是仅仅一个开发商、政府规划设计部门就决定了的事情,它可能涉及到所有与这个空间有关的居民,每个人都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空间形态。另一方面,这样的空间格局有一个缓慢而自然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同样是任何规划都无法设计、想象的。然而正因为这种生长,城市空间显现出历史的印迹。空间格局随着时间缓慢发生变化的印迹以及不同时代建筑的多样性,不仅避免了单一规划、一个时代建筑所带来的风格单调,〔12〕更关键的在于它保留了城市历史的真实。
在这里,可以看到现代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蕴含正在转变。
“公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对公众开放的各种场所都是公共空间,从公用电话亭到公共浴室,从公路到公园。当然,“公共”本身的含义非常复杂,有时只是“免费”的同义词,有时却是“花了钱,人人都可以进去得到相关服务”的场所,如公共交通、影院以及游乐地方。“公共机关”,并不是公共交往的场所,而是办公场所。它们之所以具有公共性,在于它们所担负的为全体民众服务的职责。法庭所具有的公共性,在于它代表了民众而进行的公正的评判,而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公共性,则在于它代表了公众的舆论。〔13〕市民广场除了可以供人休闲散步之外,还需要发展更深刻的空间含义,即它应该是一种基于广泛对话、交往以及共同实践基础上形成共识的公共领域。
对于外在世界来说,景观具有公共性。景观语义是建立在景观公共性基础之上的。仅仅是个人的观看,它不能构成景观。通常所说的城市景观,总是暗含着它的公共性。而这一公共性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有着连带关系。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或明或暗地显示出自身政治、社会或者道德的蕴含,并且强迫公众接受。正如斯克鲁顿所说:“一座建筑物可以作为看得见的历史连续性的象征而矗立,或者作为强行宣告的新奇要求而挺立。”〔14〕城市景观以建筑为主,所以,景观总是某种能够被群体共享的景象。
景观通常具有较大的尺度,卓越的形象,这是其公共性的保证。正因为建筑、设施、城市艺术品等具有卓越的品质、相当的规模,才可能在一般意义为众人所观看,进而获得其公共性以及相应的语义。但景观公共性又有其边界,特别是现代城市,其公私分界非常明确。这使得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景观在现代城市空间中被遮蔽了,比如晾衣物就在现代城市中被各种法规禁止,不能随意摆设摊点,私家店铺的门头也受到市容方面的约束等。城市的面貌变得越来越硬性、刻板化、几何化。
但传统公共空间、公共景观却是耐人寻味的。它是公共空间,人们可以自由介入这样的领域;它呈现为公共景观,即人们可以看到它所呈现的景象。它的公共性,在理论上讲,包含了所有的人,这是所有人融入其中的那种公共性。
不同于现代城市,传统街区、院落等都是公私交界处边缘的、模糊地带,而非高度定义的区域,城市的统制、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在这些模糊的区域人们可以自由地延伸、延展自己的生活,个体能够自行安排,布置而不太受城市方的管束。市民的私人生活溢出到公共空间中,或者说市民在公共空间中并非自觉但却保留着某种表达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公共空间是市民相互之间,相对可以自治、自我管理的领域。
这种公共性不是人们显示个人独特风采和不可替代的卓越性的场所,不是一种展示伟大、万民膜拜的空间,〔15〕它只是平凡生活的延伸,只是显示与其他人在一起的方式,它是共同的“看我、我看”的模式,保持差异,但却并不标新立异,因为所有人都与我一样富有个性,但终究没有因为个性与差异把我从那种生活的整体性中脱离出来。它只是特定区域中平常生活的平常表达。我们以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独特的公共性。它是传统城市景观多样性、丰富性的重要来源。对于市民来说,他们从未意识到正在参与景观建构,他们只是不得已、吃力地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客观上城市空间景观却由此形成了令人很难预先设想、设计的情景。这也是传统城市虽然破旧,但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城市中,我们看到空间公共性实际上意味着民众以某种个人特有的方式介入公共景观的特征。这种介入甚至与现代城市中仍然存在的空间私有化不同,私有空间,如带有院落的私家别墅、私营厂区、承租或购买的商铺等,这些空间也是民众介入公共空间的一种方式,但无疑受限于自身的功能性质,如商铺无论如何都是应付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的空间。“相比之下,原来在街道上和其他公共场所举行的社会习俗行为和街区活动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公共秩序的各种正式条款”。〔16〕尽管民众并不是在全部意义上理解自身介入的含义,但客观上恰恰是这种普遍的介入,使城市景观保持着某种生活的本真性。
在街区房屋还是自建房时代,整个街区的房屋因为建造者、修建时代的不同,而使公共空间呈现多样性、多元因素。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各地兴起各种“社区营造”运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保存传统街区建筑、恢复传统的社区生活。〔17〕我们以为,传统街区、街屋之所以对现代民众仍然保持魅力,就在于街区景观包含着往日社区生活的印迹,它们代表了“前功能化时代”的生活方式。在功能化城市中,人们的行为正在被功能化空间分解、规范、衡量。
总之,描述从传统城市到现代城市街区景观变迁的目的,并不是试图恢复到旧时代,而是给功能化时代空间景观提供一个自我批判的参照尺度。实际上变迁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一切商品化的冲动。空间功能化的背后正是包括大卫·哈维在内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空间商品化的进程。城市必须努力开发土地和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空间不专业化、功能化分区,它的商用价值就降低。区域按照功能定位有利于投资者对土地和空间未来收益的准确计算。在完成了空间中物的商品化过程之后,空间本身也进一步商品化,这意味着城市中所有土地与空间都是可以分割、加工、包装之后加以出售的商品。区域内部再细分为各种可售的功能场所(服装专卖,还是食品店),或是细分为各种可售的、价格不等的住宅空间。正因此,城市空间,特别是街区、街道两侧空间,更是不可能随意占用、挪用的地方,新的空间生产方式将古老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一同驱逐。
注释:
〔1〕〔2〕〔美〕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M.Orum):《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49页。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0页。
〔4〕〔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6页。
〔5〕〔6〕〔7〕〔9〕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40-41、43、43页。
〔8〕黄志宏:《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
〔10〕摩歇·巴拉希:《城市的观念》,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2页。
〔11〕林拓、〔日〕水内俊雄等:《现代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住宅、生态、治理》,上海古籍出版,2007年,第4页。
〔12〕〔英〕蒂耶斯德尔等:《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张玫英、董卫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4〕〔美〕史蒂文·布拉萨:《景观美学》,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16〕〔美〕P.M.霍恩伯格、L.利斯:《都市欧洲的形成:1000-1994年》,阮岳湘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1页。
〔17〕〔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2007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