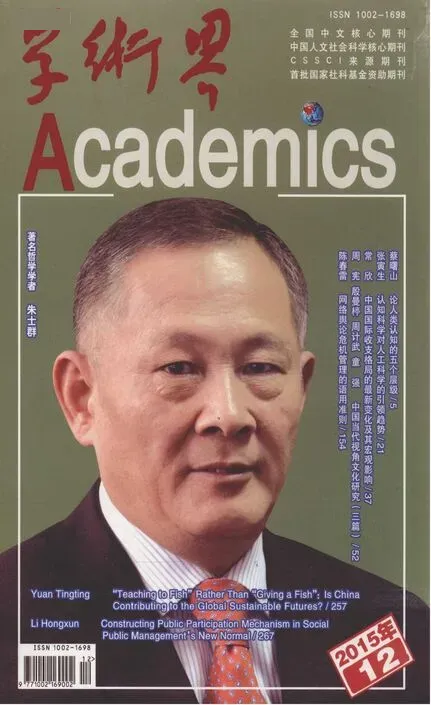革命形象的祛魅〔*〕——先锋艺术的症候性分析
○周计武
(南京大学 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告别革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既响应了合理化的现代性诉求,也开启了形象“祛魅”的进程。我们首先会诊断政治偶像在革命时期建构的社会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毛泽东形象“走上神坛”的视觉模式。然后,我们会阐释两个有代表性的形象类型:毛泽东形象和天安门广场。这两类形象在革命时期处于“符号等级制”〔1〕的顶端,享有庄严、神圣的崇高地位。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表征模式中,它们往往处于视觉空间的中心,倾向运用冷暖、明暗的对比和戏剧性的构图,来突出革命形象的光辉伟岸,供人们敬仰、膜拜。然后,我们会从美学风格上分析形象祛魅的症候——躲避崇高。
一、政治偶像的建构
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尤其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之后,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的形象,就成为各种类型的艺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母题。从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摄影、浮雕、纪念章中英俊、睿智、刚毅的革命形象,到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中质朴、亲和、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的领袖形象,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庄严、神圣、伟岸的“红太阳”形象,毛主席形象在理想化、典型化、戏剧化的视觉修辞中不断圣化为一种政治偶像(idol)。政治偶像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供人膜拜的政治形象。它源于偶像崇拜,是崇拜者通过想象性的移情对伟大人物的情感依恋与社会认同。毛泽东形象之所以会成为政治偶像,是历史性的选择也是政治性的建构。
首先,它具有深层次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中国自古就有偶像崇拜的传统,从史前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到传统社会中的皇权崇拜、圣贤崇拜,再到近现代社会中的英雄崇拜与领袖崇拜,层出不穷。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偶像崇拜源于崇拜者对神秘力量产生的一种视觉上的敬畏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无论是古老的巫术仪式,还是传统的宗教仪式,乃至世俗化的美的仪式,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的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2〕人类对幻象的依恋与膜拜是长期文化积淀的产物,它并不会伴随信仰的衰落和“世界的祛魅”而消失。在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本我依然需要强大的超我或父亲形象。因为“人类发现很难弃绝古老的超我,没有神他们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他们把对智力和道德的抱负都转而寄托于古老的父亲形象之上,让他披上新的伪装——这伪装满足了理性的需要——再次统治人类。即使科学和理性已经把神逼退到了银河星系之外,而天堂也只不过是被阳光照耀的氧气和臭氧而已——这是不适合众神居住的——神还是在理性所不能接受之处统治着,他还居住在人类心灵的潜意识领域。”〔3〕如果没有神灵,那么我们就再造一个神灵。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倾听我们诉说,帮助我们脱离人生苦海的偶像。
其次,它是卡里斯玛型(charismatic)统治合法化的需要。韦伯认为,社会统治是能够让被统治者乐意服从的命令结构。人民之所以服从命令,是因为它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合法化来自上层,但合法性则是人民的赠品。换言之,政府的统治是否合法,需要来自人民的授权与承认。按照韦伯的观点,合法化统治有三种类型:传统型、卡里斯玛型与法理型。毛泽东时代的统治属于第二种。卡里斯玛型权威是一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禀赋的人。”〔4〕
权威依赖于领袖的卓越功勋与人格魅力,依赖于追随者“对启示与英雄的信仰,对一种宣示(Manifestation)——无论其为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学问的、政治的或其他各式各样的宣示——之意义与价值的情绪性确信,也奠基于英雄性——无论其为禁欲的英雄性、战争的英雄性、审判官之睿智的英雄性、巫术性施为的英雄性或其他各类的英雄性。此种信仰,是将人‘从内部’革命起来,再依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事物与秩序。”〔5〕领袖要赢得追随者的崇拜与服从,必须首先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必须首先从内部实行思想的革命,改变人们的信念,继而改变世界。要改变人们的信念,政治宣传和思想说服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宣传与说服能否有效果,不是依赖于理性的推理,而是依赖于词语与套话能否唤起“伟大壮丽的幻象”,在视觉上吸引人、感染人。具体的手段有三种:断言法,即简洁有力的断言或口号;重复法,即不断强化某种信念、说辞与形象;传染法,即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介来传播形象、宣传信念,形成舆论。〔6〕
毛泽东政治偶像的建构过程不仅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手段,而且在数量、规模与手段的多样性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政治动员和大众自发的效仿行为,反复运用可技术复制的像章、标语口号、大字报、招贴画、宣传画、红太阳歌曲等视听手段和程式化、概念化、公式化的艺术语言,以及各种仪式化的视觉表演,毛主席政治偶像的崇高地位得以不断建构与强化。
从偶像建构与形象传播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乃是一种不断神化与升华的圣像运动。首先,毛泽东形象的生产者,无论是学院派艺术家,还是民间自发创作的工农兵学员,都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狂热的偶像崇拜投入制像的。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它表现的不是艺术家的个性化情感,而是集体性的政治化情绪。艺术个性消失于一种集体风格之中,共同缔造了一个虔诚的神圣世界。其次,毛泽东形象普遍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征模式,戏剧化的构图、纪念碑式的人物造型和高度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视觉图式。在构图方式上,毛泽东形象处于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画面背景要么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么是霞光万丈的红太阳,要么是群众欢呼的红海洋。这种戏剧化的构图人为缔造了一个充满“幻觉”的神圣空间,走向了假、大、空的编造和歌功颂德的矫饰。再次,制像技术的可复制性,为毛泽东形象的批量生产和大规模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强化了毛泽东作为人民群众的大救星和红太阳的光辉形象。最后,作为象征性的政治符号,毛泽东的画像与塑像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成为婚丧嫁娶中的膜拜对象——以拜神的目光和仪式化的虔诚来瞻仰。以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1967)为例,它的公开发表与全国性的政治宣传是“作为一道政治命令来下达”的,“当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时候,还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迎接。”〔7〕因此,毛泽东政治偶像的确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偶像崇拜双向建构的产物。
二、政治偶像的祛魅
如果说视觉形象的“祛魅”是光晕消散、距离消解的解构过程,那么政治偶像的“祛魅”则是消解偶像的神性与重构偶像的人性的双重过程。其策略是升格与降格。升格把世俗的、日常的、卑微的符号,如未雕琢的木头、艳丽的花朵、名牌汽车、福娃、时尚女郎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被严肃地展示、歌颂和膜拜。这从反面消解了神圣与禁忌。与之相对,降格具有“贬低化、世俗化和肉体化的特点”,它“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8〕毛泽东形象的降格旨在消解其神性与威严,重构世俗、平凡的人生,使一代伟人从天上重回人间。这是我们要重点分析的前卫策略。
在改革开放的后革命时期,政治偶像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第一次祛魅发生在80年代,是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以先锋文艺为主力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革之后,告别、反思、消解革命艺术范式及其等级化的政治符号体制,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它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政治化、文艺大众化的工具论文艺观和“唯我独尊”的革命现实主义模式;主张从“表征什么”“如何表征”两个方面重构现实主义模式,突破僵化、虚伪的“高大全”“红光亮”模式,消解革命文艺的戏剧化矫饰风格,突出艺术的启蒙价值和人道精神。这种视觉真实的重构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偶像崇拜的社会心理,因为从黄克平的木雕《偶像》(1978)、《沉默》(1979)开始到“85美术新潮”期间,毛泽东形象似乎一直是艺术界不敢触碰的雷区。不过,这种视觉真实的重构依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9〕
第二次祛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王广义、余友涵、李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打破了短暂的沉寂,并最终在政治波普艺术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政治的波普化旨在用波普化的艺术语言把革命时期的政治形象与现代流行的商业符号结合起来,以此表达某种荒诞、戏谑的意味。这次祛魅的过程具有双重性,它不仅要祛掉政治偶像的“神性”之魅,而且要祛掉从“85美术新潮”开始到“后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凸显的精英文化之魅,理想主义的“崇高”之魅。换言之,它既要“去政治化”,也要“去精英化”。不过,当代先锋艺术对政治偶像的去政治化过程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具有政治与思想解放的双重意义;它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去精英化过程本身,也具有精英的、小圈子的艺术特性。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王广义的《红色理性——偶像的修正》(1987)和《毛泽东——红格1号》《毛泽东:P2》(1988)到余友涵《招手的毛泽东》(1995)、薛松的《轮廓系列》(2005),从刘大鸿的《四季》(1991)、杨国辛的《参考消息》(1992)到李山的《胭脂系列》(1992-1997),从祁志龙的《消费形象31号》(1995)到罗氏兄弟的《欢迎,欢迎系列》(1999),我们见证了毛泽东形象不断被修正、变形,不断被符号化和艳俗化的“祛魅”过程。
首先是形象的去神圣化,即通过形象的修正、变形、抽象等策略来消解偶像的“神性”。以王广义的《毛泽东——红格1号》(1988)为例,它以黑白灰的冷色调褪去了毛泽东画像中的自然色,并把原本应为毛泽东画像底层的方格置于画像的表面,完美的比例、醒目的红色,不仅强化了画面中冷暖色调的对比,而且把画面的表层空间同背景中的画像“区隔”开来。这是一种自我解构的隐喻,因为红色方格既建构也消解了毛泽东偶像的政治性。与红色符号一样,它属于政治符号。但是,它们都属于过去的时代,是即将被历史掀开的一页。再以刘大鸿的《四季》为例,它挪用了文革时期熟悉的毛泽东形象,并把它与年画中的福娃、京剧中的扮相、国画中的山水和消费时代的汽车、麦当劳等消费符号并置起来。众所周知,毛泽东形象在革命文化中是常见的能指,其所指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1966)。在《四季》中,这种能指与所指构成了一级符号系统,并与其他视觉元素一起构成了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即革命政治话语的隐喻或象征。当其形象作为革命时期的视觉资源被挪用到改革开放的消费社会语境中,它实质上已经成为被掏空了历史意义与政治价值的符号,一种空洞的能指。作为空洞的能指,脱离革命时期整体语境的毛泽东形象,与消费社会的商业符号一样,仅仅是散落在文明废墟上的碎片。这些碎片的并置,穿越时空,导致了语境的错位与存在的滑稽感。它既唤醒了政治话语的记忆,也掏空了符号隐含的政治意义,使其降格为空洞的能指。
再次是形象的世俗化,即以平视的视角刻画政治偶像的世俗人生和日常生活中的音容笑貌,来消解偶像的“不可接近性”。隋建国、王文海的《睡觉的毛主席》(2004),以人性化的视角和写实的笔法,逼真地呈现了毛主席的日常生活——睡觉。用日常行为的“日常性”来取代政治偶像的“神圣性”,打破了偶像的“禁忌”,消解了偶像与观看者之间的距离。与之类似,尹朝阳的《遇见》(2004)以超现实的手法、冷静的构图和平视的视角,虚构了我与毛泽东在郊外的意外相遇。观者的视线与画面中的我以及毛泽东远看的视线,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毛泽东的形象是视觉注意的中心,但他看起来比近景中的我,要小得多。这种大小的对比是透视法产生的一种幻觉。不过,这种幻觉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具有社会心理的真实性。作为视觉隐喻,它暗示我们超越了偶像膜拜的阶段,已经能够以平等的视角、人性化的眼光,与领袖平等交流了。
三、广场的凡俗化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多重编码的视觉符号。作为特定的能指,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所指,联系着现代革命与政治变迁的记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二·九”到开国大典,从“四五”运动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广场始终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政治舞台,指称着革命、进步与变革,指称着激情、正义与铁血,指称着政权、真理与合法性。如戴锦华所言,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广场“联系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革命’与政治的记忆,其自身便是‘中国版’的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实践。”〔10〕与领袖形象的命运相似,广场形象在新时期同样经历了凡俗化的过程,即从神圣的政治空间降格为世俗的人文景观。
告别革命是“祛魅”仪式的第一步。赵半狄的《听我说》(1992)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视觉隐喻的空间。画面背景中的红色云彩、天安门和红光满面的毛主席画像,与前景中用白、褐、灰着色的一对青年男女,以冷暖色调的对比构成了典型的三角形构图。在广场上行走的年轻人与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形象隔着一道具有透视效果的围栏。围栏拉开了两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距离是建构偶像与神性的基础。但此处的距离却具有疏离、隔膜的政治意义。年轻女子穿着白色衬衫、白底黑色斑纹的裙子,身体前倾,后腿抬起,嘴巴微张,若有所诉,似乎要退出“剧场”,具有戏剧舞台般的雕塑效果。年轻男子上身裸露,下身穿褐色大裤衩,打着黑色油纸伞,目光向外,正走出画面。因此,这是一个“离心”性的构图。画面中的年轻女子、青年男子与天安门及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形成了三种不同方向上的力。这种张力结构既呈现也消解了人民与领袖之间的距离。它是一种告别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仪式,一种告别革命、告别政治的仪式性寓言。
在王劲松的《天安门前留个影》(1992)中,空荡荡的舞台被身着休闲服、略带微笑的游客占据了。这件作品戏谑性地模仿了孙濨溪的《天安门前》(1964)。它挪用了蓝天、天安门、红墙、巨幅毛主席画像与天安门前的人群等视觉元素。但是,主席画像不再处于画面的视觉中心,它被人群中的游客形象部分遮蔽了,只留下模糊的轮廓;通过平涂手法,天安门与游客不仅共处于同一个平面之中,而且天安门与人群各占一半的画面,大大缩小了二者之间的比例,从而使天安门不再庄严、高大;摆着各种站姿、面露嬉笑,随意自然的游客置换了原作画面中身穿节日盛装、满面红光、身姿笔挺、洋溢着自豪的工农兵形象;僵硬的笔触、单一的色调不仅使画面中的形象显得呆板,失去了原作的生动逼真,而且使整个画面变得凝滞,消解了原作此时此地的光晕。革命记忆中充满激情与热血的天安门广场,褪去了革命的色彩与政治的光辉,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供人观光、消遣的景观。无论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还是留影以资纪念,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都化为了一种装饰性的符号。这种符号掏空了政治记忆的沉重与庄严,沦落为标志性的景观。
如果说,赵半狄、王劲松通过挪用革命时期的宏大图式,暗中置换其中的视觉元素,来达到消解广场形象的视觉效果,那么,张晓刚的《天安门》系列(1993)、宋冬的《哈气》(1996)和苍鑫的《交流之四·天安门》(2000),则通过个性化的微观视角,以仪式性的庄严唤起并重构了广场的集体记忆及其视觉形象。集体记忆是集体情感与社会心理的一种重构性回忆,旨在用现在的视野与观念重塑过去,抵抗记忆的断裂与遗忘,实现自我救赎的目的。〔11〕张晓刚的广场形象是凝重的、焦灼的、悲怆的,空无一人、起伏不平的广场和一块块似乎被撬起、被烧焦的地板石,在炭黑、蓝灰、白灰层层晕染下发出惨淡的白光,与银灰色的天空交相辉映,同血红、晕黄、暗紫色的天安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激情的、热血的、万众参与的革命记忆在政治的焰火中化为灰烬,成为哀悼的废墟、遗弃的丰碑。与张晓刚内敛性的冥思不同,宋冬选择在寒冷的冬天用自己的热血之躯,匍匐在广场上40分钟,不停地向地面哈气,以肉身化的方式来检验政治气候的变迁,寻找自我与广场记忆的血脉联系;苍鑫的《交流》脱胎于1996年开始的《舔》系列,旨在通过用舌头舔广场的萨满式行为,来重建与广场记忆的个性化交流,实现过去与现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与融合。这种个性化的方式是私密的、冥想式的,广场形象在视觉建构中既是艺术家哀悼与怀念的对象,也是重构与反思的客体。在社会转型期的语境下,广场是在场的缺席者,只能用肉身化的体验才能唤起集体性的革命记忆与阶级体验,重建艺术家与过去想象性的文化认同。
伴随革命时代的渐行渐远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广场虽然继续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磨灭的角色,但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被掏空了隐含的革命色彩与政治意义,成为一种空洞的能指和供人观赏的景观。在岳敏君的《大团结》(1992)中,远景中露出一角的天安门城楼与标语,同画面中心不断重复、超大比例、眯眼傻乐的憨傻群像,构成了尖锐的对比。俸正杰的《时光隧道二号》(1998),旧上海月份牌年画中的青年恋人正在广场上拍摄婚纱摄影,程式化的表情、姿态、着装与画面中红黄相间的天安门形象并置,产生了穿越时空的错位之感。卢昊的装置《花鸟虫鱼鱼缸》(1999),将天安门做成亚克力鱼缸,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将家庭日常用品鱼缸与象征国家意识形态的天安门进行了功能意义上的叠换。在这三件作品中,天安门广场都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景象并置或置换,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神圣与世俗、崇高与卑微之间的界限,使前者沦落为当代生活语境中的装饰性图案或人文景观,失去了革命形象的庄严感。
四、躲避崇高
如果说,崇高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艺术在美学形式上的重要特征,〔12〕那么,躲避崇高,转向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则是90年代先锋艺术的重要症候。如王蒙所言,这是一种失重的艺术,一种把各种语言、各种人物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不表现“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欣赏者高尚之物,“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艺术。〔13〕躲避崇高,是先锋艺术在美学风格上对理想主义的清理及其对悲剧英雄主义的反动。在视觉形象上,它不仅要祛政治偶像的魅——去政治化,而且要祛精英形象的魅——去精英化。在表征策略上,它受惠于存在主义思潮和超现实主义对人生荒诞感的体验和对现实陌生化的处理。它不是如其所见,而是如其所想的那样表征内心深处隐秘的、个性化的真实体验。笔者认为,躲避崇高与其说是美学风格上的刻意反动,不如说是对文化英雄形象深层次的祛魅,因为它不仅要祛革命政治的魅,而且要祛精英文化的魅。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形象的碎片化、脸谱化与平庸化。
生活在现代意味着生活在永恒的过渡、短暂与偶然之中,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偶然性碎片、孤独、焦虑之中。〔14〕如果说知识分子在上世纪80年代扮演的是一种具有忧患意识的、激情燃烧的启蒙者角色,那么知识分子在上世纪90年代所体验的是一种历史断裂的创伤与英雄主义失落的迷茫。面对破碎的真实和不断边缘化的境遇,知识分子文化英雄的形象开始支离破碎。张晓刚的《黑色三部曲:惊恐、沉思、忧郁》(1990)以视觉隐喻的方式表征了英雄形象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断肢残体是作品的中心形象:身首异处,消瘦、憔悴的面孔,因恐惧或放大、或低垂、或紧闭的双眸,躺在书本上的小孩头颅,断臂、断手、匕首、展开的书与信封、皱褶的窗帘和血红的丝带,在黑白灰与红色的鲜明对比中,以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塑造了陷入创伤与冥思之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种因过度的震惊而惊恐、忧郁与沉思的形象。展开的书本与空白的信纸是文化知识无力、苍白的隐喻,是无言阐释时代的寓言。在三联画的视觉形式中,书本、信笺与断臂、匕首的并置又构成了图像叙事的转喻——意识形态暴力施虐的社会根源在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文化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但在文化知识贬值甚至成为意识形态禁忌的时候,知识分子何为?他们既不能成为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在与大众结合的过程中启蒙大众、领导大众,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也不能像爱德华·萨义德式的“业余知识分子”那样,不同任何阶层合谋,以多重边缘的文化身份和多元的文化视角对社会进行独立的批判。彷徨于无地的挫败感与无力感折磨着他们,使其陷入无尽的忧郁、莫名的恐惧与痛楚之中。这是一种缺乏精神寄托而心理缺失的受伤,一种失去了批判指认性而陷入被害妄想的集体受难意识。
形象的脸谱化是形象祛魅的另一种表征。脸谱化是指人物形象在容貌、表情、仪态、风度与身体形态刻画方面,以及在色彩与构图类型上程式化、简单化的造型行为。当代先锋艺术,尤其是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与艳俗艺术,倾向反复运用某种个性化的脸谱符号来表征内心的困惑、迷茫、不安与焦虑,如曾梵志的面具、张晓刚的血缘家庭照、方力钧的光头、岳敏君的傻乐、杨少斌的肉搏、毛旭辉的意淫、毛焰的痛楚等等。这些视觉形象在视觉语言上具有风格主义与学院派的倾向,表征了异化的人格心理,是社会心理被意识形态扭曲的症候。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语言上的革新,也不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以方力钧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光头形象为例,它往往在蓝天、白云、大海等诗意风景的衬托下,成为画面压倒性的重心——具有泼皮感的光头,张大、变形甚至扭曲的嘴巴,细长的、眯成缝的双眼,无意义的表情。这个形象比较暧昧,很容易让人想起罪犯、军人、和尚、尼姑,乃至文革时期武斗中的“黑五类”形象。然而,画面剔除了任何历史的痕迹甚至人性的痕迹。纯净、鲜亮的色彩、非表现性的笔触,强化了画面的平静和冷漠。这里的光头仅仅是无阴影的透明,没有任何叛逆的暗示;眼睛有目无光,视若无睹,失去了欲望与好奇;嘴巴与其说是吼叫,不如说是无聊的哈欠。显然,这是一个脸谱化的空心人,一个没有内心世界与精神体验的脸谱符号。张晓刚《大家庭系列》(1994-2005)中的人物形象具有类似的特点:看似凝视实则空洞无物的目光,看似表情丰富实则千篇一律的面孔——细长的眉毛、直挺的鼻梁、平直的嘴唇和文弱清秀的鹅蛋脸。这种“空心人”有着一致的精神谱系,但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因为“他既不是英雄式的主人,也不是一个卑微的奴隶;既不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15〕
如果说形象的碎片化源于整一性的丧失,形象的脸谱化源于内在性的丧失,那么形象的平庸化则源于思想性的丧失。平庸意味着无所事事,碌碌无为,随波逐流。平庸之人整日沉迷于闲言碎语、猎奇窥视之中,既没有独特的个性与判断力,也缺乏勇于担当的责任与勇气。当代先锋艺术家主要选择两种视角来表达平庸,“一种是直接选择‘荒唐的’、‘无意义的’、‘平庸的’生活片段;另一种是把本来‘严肃的’、‘有意义的’事物滑稽化。”〔16〕我们把前一种称为无聊,后一种称为傻乐,这是形象平庸化的两种重要表征。
无聊是理想幻灭、价值缺失、意义失落所引发的一种厌倦、颓废的心理体验。其实质是一种梦醒之后无梦可做、无所事事的价值空虚感。无聊之人往往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他们不再相信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以拯救社会或文化的虚幻努力,也自愿抛弃了艺术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转而以平视的视角凝视周围庸俗的现实,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消解过于沉重的意义枷锁。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处在瞬间的、怡然自乐的非历史状态,一种既没有激情也不颓废,既没有被荣耀眷顾也没有被耻辱铭刻的状态。在情欲的投射下,偶然的现实碎片瞬间被力比多点燃,照亮了无意义的生活画面。这种对平庸生活方式的认可,及对空虚、无聊和情欲的冷静展示,主要表现在刘小东、喻红、宋永红等新生代艺术家身上。
在宋永红的油画《真实的幻觉》(1992)中,艺术家以冷漠的旁观窥视着公交车中百无聊赖而又装模作样的“色情”场景:坐在车后面的一对年轻人相互拥抱着,一个穿着时尚的女郎扭过头在偷看;画面中心的光头男青年正要掀开身边女人的上衣,窥视她的乳房,而女人双目紧闭,半睡半醒;光头男的右边是一个穿白色汗衫的中年男人,他闭着眼,仰着头,嘴巴微张,一只手紧紧抓住另一只手的手腕,似乎在意淫。这是由看与被看、窥视与偷窥建构的一种流动着情欲的暧昧画面。淡黄的光线和层层推进的明暗对比,使整个画面沐浴在超现实的幻境之中。这是时间凝滞的虚幻一刻,它横亘在禁欲主义的过去和享乐主义的未来之间。欲望的压抑和压抑的欲望以白日梦的方式呈现在暧昧的张力结构之中,暗示了被意识形态扭曲的心理症候。与宋永红对情欲的刻画不同,刘小东擅长挖掘庸俗生活碎片中焦灼的无聊感,来表达艺术家内心深处的困惑、怀疑与反思。以油画《烧耗子》(1998)为例,画面的远景是延伸向远方的小河,小河的两岸绿树成荫,与远处的小桥、小桥上的电线杆和中景中的楼房、路上偶遇的行人构成了一幅祥和安逸的风景画。画面的焦点是两个西装革履、留着中分头、无所事事的年青人,左边年青人身材略瘦,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拿着底端还在燃烧的木棍,眼睛斜视前方,嘴角带着笑意;右边年青人身材略胖,双手悠闲地插在裤兜里,低着头看着地下。在两人洋洋得意的目光交汇处,一只烧着的耗子正在向画面的右下角逃跑,它的尾巴与后半身一直在燃烧,燃烧的表皮甚至发着光,似乎发出吱吱燃烧的声音和毛发烤焦的味道。这显然是两个年青人的得意之作,他们挡住了耗子逃向河里的去路,让耗子在无处可逃的煎熬与惶恐中挣扎。画中的年青人正在凝视这个杰作,不仅凝视耗子的惊恐、挣扎与奔逃,而且凝视即将燃烧的画面,因为在耗子的前方就是画家的签名和绘画日期。体验小小暴力带来的生命乐趣和日常的残酷戏剧,似乎成为年青人烧耗子的全部意义。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一种在无思想、无判断的碌碌无为和不可救药的迷茫中犯下的恶。
傻乐是莫名其妙的乐,是在不该乐的时候乐。陶东风认为,“傻乐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出于无知。”〔17〕前者是清醒者的自嘲,是一点正经也没有;后者是愚昧者的麻木,是傻呵呵的乐。后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艺术家社会批判的对象。与“独异个人”或“精神界之战士”不同,他们缺乏反省和忧患意识,是一群碌碌无为、喜欢围观与传播流言的庸众或看客。与之不同,前者是没落的文化英雄主义者,“看透一切”的玩世现实主义者。面对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无常,他们是泼皮的、迷茫的、无聊的、幽默的,但绝不是可以瞒和骗的。他们不再相信英雄的壮举、崇高的伟业和伟大的措辞,而是转而探寻人生中的复杂和混蛋、偶然和无意义的一面。他们怀疑一切,但韧性十足,能在无意义的现实中利用一切机缘来加强调侃、嘲讽与自嘲的话语强度。
傻乐形象最早出现在耿建羿的油画《第二状态》(1987)中。画面用黑白灰的冷色调刻画了一个极端狂笑之人:夸张的大笑,扭曲的面孔,眯成缝的双眼。这不是喜极而泣的笑,也不是爽朗自信的笑,而是高度压抑状态下的精神痉挛,一种神经质的笑。没有具体场景的暗示,没有任何历史信息的痕迹,紧闭的双眸也没有表现任何内心的心理活动。不过,因狂笑而痉挛的面孔在冰冷的画面中依然让欣赏者感到颤栗。
如果说,笑脸在上世纪80年代仅仅是偶然的个案,那么,笑脸在方力钧、杨少斌、岳敏君等玩世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典型。以岳敏君的作品为例,张大嘴巴的大笑面孔是其美学风格中重要的视觉符号。这是一种动作夸张、失去理智却盲目自信的开怀大笑。它有时以独立的面孔出现,有时以重复的集体面目亮相。这是岳敏君为自己作品量身打造的“新偶像”,但这是一个没有光晕和本真性的偶像,因为它仅仅是一个不断自我循环的模拟形象,一种没有本原的梦中幻象。它有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如《发生在X城楼的戏剧》(1991)、《狂笑》(1991)、《飞翔》(1993)等;有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如《大团结》(1992)、《大狂喜》(1993)等;有时又出现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画面中,如《希阿岛的屠杀》(1994)、《草地上的午餐》(1995)、《自由引导人民》(1996)、《处决》(1996)等。如批评家冷林所言,“所有这些场合都在这种‘自我形象’的放大夸张下变成了一场场的游戏,‘我’好像不是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而是恰巧出现在这里。”〔18〕这是一种自恋自嘲式的笑,因为紧闭的双目对一切都视若无睹;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笑,因为它出现在庄严、神圣的场合;这是一种怀疑颠覆式的笑,因为所有的社会现实都在笑声中显得可笑、荒唐、不真实。
先锋艺术品中的无聊、傻乐等视觉形象,虽然在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语境中具有质疑现状、消解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但形象的平庸化暗中迎合了大众文化“媚俗”的需求,间接弱化了政治批判的热情,容易陷入犬儒主义的泥淖,产生“平庸的恶”。
注释:
〔1〕在革命时期,整个社会是按照符号等级制来确立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所谓符号等级制是指毛泽东根据敌友逻辑的政治性原则,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人为建构的一种符号编码与解码的规则。形象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政治符号。不同的形象在符号等级制或符号场中占有的位置也不同。作为革命领袖,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一种原型符号,享有庄严、崇高的政治地位,当仁不让地占据着中心;各种英雄符号以光辉的形象接近中心;工农兵学商等群体形象离中心稍远;“黑五类”等阶级斗争的对象则处于边缘的阴影之中。
〔2〕〔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130-134页。
〔3〕乔治·弗兰克尔:《文明:乌托邦与悲剧——潜意识的社会史》,褚振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222页。
〔4〕〔5〕韦伯:《韦伯作品集III·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271-272页。
〔7〕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现代美术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8〕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5页。
〔9〕如栗宪庭所言,这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红光亮’、‘歌德’的反动,则是以四川为代表的‘伤痕美术’的骤起;对‘假大空’、‘重大题材’的反动,则是以陈丹青为代表的‘生活流’的风行;对艺术从属政治、内容至上的反动,则是以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装饰风’的滥觞。这都是在一种逆反心理的驱使下产生的,变革的核心是社会意识的、政治的。”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10〕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1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2〕在表征策略上,它大胆借鉴西方野兽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的语言,用“黑白灰”取代“红光亮”,用理性的抽象和情感的表现取代写实主义模式,用“反艺术”的观念冒险和自我献祭的前卫精神来表达内在灵魂的跃动与激情。它表征的不是供人们肉眼观看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而是供心灵之眼观看的、内在于灵魂深处的体验与追问,一种心灵的、想象性的真实或超真实。这种形式上的实验具有令人震惊的审美力量与崇高感。比如,周韶华的《黄河魂》(1981),色彩沉郁明亮,笔触粗狂有力。尚扬的《爷爷的河》(1984),用粗狂的笔触、黝黑的色块和充满张力感的形式,勾勒了黄土高原地貌与人物形象的坚韧,以直观的视觉感受唤起了那种凝重而久远的文明意识。王广义的《凝固的北方极地》(1985),以稳定简洁的构图、凝固内敛的造型和北方极地的冰冷感,确立了他的庄严、静穆的基本图式。丁方的黄土高原系列,以坚实的造型、冷峻的笔触、金属感的色彩和变幻不定的光的使用,塑造了一种超验性的精神氛围和深沉有力的悲剧感。
〔13〕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4〕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等译,何百华译校,学林出版社,2002年。
〔15〕汪民安:《形象工厂——如何看一幅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
〔16〕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95-296页。
〔17〕陶东风:《无聊、傻乐、山寨——理解当下精神文化的关键词》,《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
〔18〕冷林:《岳敏君的“自我形象”》,《美苑》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