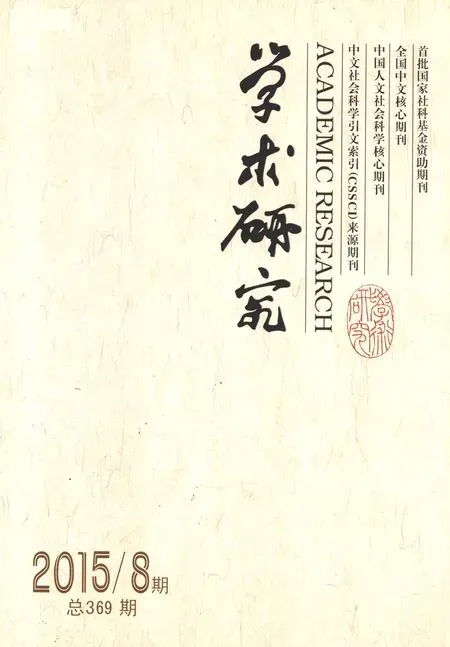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变化及其因果探析
严玉芳
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变化及其因果探析
严玉芳
19世纪,随着矿物能源的大量使用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伦敦的树木景观呈现出两种明显变化:一是主导树种的兴替;二是分布场所的扩展。这两种变化不是社会进步的自然结果,而是伦敦城市发展所致的树木生存环境变化与城市人审美、健康和卫生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因而,从树木景观变化的新视角诠释19世纪伦敦环境与人们环境观念的演变,可以丰富英国城市环境史的相关研究。
悬铃木 城市环境 树木景观
2008年4月22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刊登了一则令人瞩目的报道:伦敦伯克利广场的一棵 “悬铃木”①英国梧桐 (London plane)、美国梧桐 (Occidental plane)和法国梧桐 (Oriental plane)的学名分别是二球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 willd)、一球悬铃木 (Platanus occidentalis L)和三球悬铃木 (Platanus orientalis L),均通称悬铃木,但二球悬铃木比较常见。二球悬铃木是一球悬铃木和三球悬铃木杂交的产物。据文献记载,三球悬铃木大约在16世纪中期引进英格兰,一球悬铃木约在1636年由园艺家约翰·特雷德斯坎特 (John Tradescant)从美国引进英格兰。据亨利教授 (Prof.Henry)推测:二球悬铃木大约于起源于1670年,在牛津植物园 (Oxford Botanic Garden),一株一球悬铃木和一株三球悬铃木碰巧生长在一起,二者杂交的幼苗便是二球悬铃木,这株幼苗的茁壮生长和新奇的树叶吸引了园艺者,从而得到繁殖并传播。参见 “The History of London Plane”,Nature,June 26,1919,p.333.价值75万英磅,成为英国最昂贵的树。[1]1920年,英国树木培植学专家A.D.韦伯斯特(A.D.Webster)在 《伦敦树木》(London Trees)一书中记载:伯克利广场只种植了悬铃木。而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榆树才是伦敦唯一的常见树种,直到19世纪中期悬铃木还不多见。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已取代榆树成为伦敦最常见的树种。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它与19世纪伦敦的城市发展及相伴而生的环境问题有何联系?这种变化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对此,在英国城市环境史的相关著述中鲜有论述。②相关研究概述了城市空气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及有关人群的反应,但均未涉及树种变化及其深层原因等问题。参见Peter Brimblecombe,The Big Smoke: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don:Methuen,1987, pp.68-69;Peter Thorsheim,Inventing Pollution:Coal,Smoke and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800,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pp.33-35.而探究这类问题,既有助于认识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的演变历程与变化要因,揭示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助于深化人与自然 (树木)共生关系的历史、现实认知。因此,本文试图以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的变化为对象,在厘清树木种类与分布场所变化的基础上,
探究其变化因果,以拓展英国城市环境史的相关研究。
一
19世纪,随着用煤量的大幅增加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伦敦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伦敦的树木种类和分布场所呈现出明显变化,二球悬铃木、杨树、合欢、臭椿等逐渐取代了榆树、橡树、雪松、针叶树等,场所也从花园、广场扩展至街边、道路两旁。
1893年,有人撰文指出:榆树曾是伦敦唯一的常见树木,这可以树木命名的街道为证,街道名是获悉现在被房屋盘踞的地方过去曾生长何种树木的指南,而伦敦有诸多 “Elm Gardens”、“Elm Park”、“Elm Grove”、“Nine Elms”之类的名字;同样,以橡树、山毛榉命名的地方亦不胜枚举。总之,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伦敦的榆树满街遍地,它们在公园、街道、花园长势茂盛。[2]然而,时至20世纪20年代,曾经生长在切尔西地区的黎巴嫩雪松、兰贝斯的榆树、摄政王公园的橡树都在逐渐消失,或正在向条件良好的郊区退缩,以致雪松不再是能在伦敦健康生长的树种,海德公园的榆树遭受了严重的病害,摄政王公园里几乎难以找到一株英国橡树了。[3]
19世纪后半期,伦敦榆树分布范围逐渐缩小,而另一些树种开始大量出现,例如二球悬铃木。“悬铃木,尽管以美丽著称,但在19世纪中期还不是伦敦的常见树种,杨树、臭椿、黑桤木 (blackalder)也几乎不为人知。”[4]可是,1920年,韦伯斯特已认为不妨称伦敦为 “悬铃木之城”(The City of Plane Trees),因为它整整占据了伦敦树木总量的60%。[5]尽管榆树、酸橙树、杨树、合欢、臭椿及其他树种也比较常见,但均不足与悬铃木相匹敌,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量种植的悬铃木几乎驱逐了其他所有树种。
在伦敦主导树种更替的同时,树木的分布场所也在发生变化。19世纪中期之前,伦敦的树木大多分布在私家花园、广场等地。1887年,《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刊登的 “伦敦植树”一文认为:25年前只有少量树木出现在公园、部分广场和教堂,且以榆树为主,其树干发黑,春季刚长出的嫩叶很快便被煤烟熏染成墨绿。当时,六月的伦敦是一个令人疲倦的城市,很少有树叶可以让人们的视野感觉清新,人们也很难在公园和广场外发现一棵树木。[6]随着伦敦城的不断扩展,新增的众多街道与道路大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树叶或灌木装饰,但因旧伦敦地区的主干道不断植树,迟至19世纪80年代,这里已发生了 “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美丽变化”。[7]1896年,《星报》(The Star)也谈道:在那些足够宽阔的道路旁,已种上了小树苗,极大地改善了道路的面貌。[8]
由上可知,19世纪伦敦的树种出现了更替,其分布场所也有所扩展。上述变化与19世纪伦敦树木生存环境的演变和人们对树木用途的新认识密切相关。
二
与19世纪伦敦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环境问题改变了树木的生存环境,包括空气、土壤和局部小气候等环境因子,这些变化是导致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变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伦敦的空气污染是影响榆树等树种健康生长的要因。伦敦的空气污染并不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现象。早在13世纪晚期,因燃烧海煤 (sea coal),伦敦就已出现空气污染问题。虽然中世纪伦敦的用煤量还相当有限,但也在逐年上升,至伊丽莎白一世 (1558—1603年)统治的晚期,伦敦的耗煤量已达到年均5万吨。[9]休·普拉特 (Hugh Platt,1552—1611年)在1603年观察到煤炭燃烧过程中排放的煤烟会对伦敦城的植物和建筑物造成损坏。[10]17世纪,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伦敦家庭的主要燃料,家庭用煤连同工业用煤致使伦敦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进入19世纪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如1881—1885年伦敦的大气污染记录显示,在冬季的12月和1月,其中心地区所拥有的明媚阳光的天数只是牛津、剑桥、马尔伯 (Marlbrough)和吉尔的斯顿 (Geldeston)这四个城市同类天数的1/6。[11]
19世纪伦敦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常绿树木在冬季很快就被覆盖上一层暗黑的煤灰,它会堵塞树叶的气孔,降低树叶的二氧化碳吸收量,进而抑制营养物质的产生与流通,剥夺植物的重要 “食物来
源”。此外,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会与空气中或树叶上的水珠相结合形成亚硫酸 (H2SO3),其酸性腐蚀力会对树叶造成损害。亚硫酸对树叶的危害到底有多大?1864年英格兰皇家园艺学会(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England)的化学家奥古斯塔斯·沃尔克 (Augustus Voelcker,1822—1884年)曾谈道:煤烟对植被的危害主要归因于亚硫酸,按照多年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特纳 (Edward Turner)和罗伯特·克里斯蒂森 (Robert Christison)的实验,当其构成空气比例的万分之一时就会导致植物脱叶;而德国科学家对空气中包含少量亚硫酸时对植被影响的实验则表明,小的杉树暴露在包含两万分之一甚至八万分之一亚硫酸的空气中两个小时,在潮湿的天气里它们就会完全变白,当暴露时间更长时,它们便会死亡。[12]在大量使用含黄铁矿 (FeS2)的劣质煤的地方,煤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硫通常会波及煤烟产生地的一两英里之外,对植被造成大面积损害。
其次,伦敦的一系列建设活动逐渐改变了土壤的性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铺设道路和建筑房屋使得土壤硬化;过度排水导致土壤涵养水分不足。
城镇街道下面的土壤主要由建筑废弃物组成,其植物营养成分含量甚微,且硬度很高。尤其是在城镇的中心或商业区,因地面被建筑物和道路大面积覆盖,使得该区域土壤严重硬化,能在这种土壤环境下成功生长的树木种类极少。例如,适宜街道种植的树木在巴黎有11种,在华盛顿有12种,而在伦敦只有4种,即悬铃木、臭椿、泽西榆树和伦巴第杨树。[13]不仅如此,硬化的土壤还会阻碍空气进入植物根部,使根呼吸受阻,这通常是导致城镇街道树木死亡的重要原因。
因城市过度排水,树木生长所需的水源亦遭到剥夺。19世纪,就城市污水处理方面而言,伦敦堪称世界上排水最通畅的城市。可是,通畅的排水渠道不但排走了污水,也带走了各种类型的地表水,尤其是雨水。首都公园协会 (Metropolitan Public Gardens Association)①首都公园协会成立于1882年,首任主席是布拉巴宗勋爵,其宗旨是为公众使用而保护花园、废弃墓地、教堂、开敞空间等,参见该协会网站:http://www.mpga.org.uk/。主席雷金纳德·布拉巴宗勋爵(Lord Reginald Brabazon,1841—1929年)在回应一位匿名通信者建议伦敦每家每户种树的文章时谈道:哪怕是数小时的倾盆大雨,天空放晴1小时就足以排干降水,因雨水被吸入下水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壤就如同被挤压过的海绵一样干燥,在这种情况下,树木很难在城市健康生长。[14]因此,涵水能力不足经常成为城市树木的大敌。
最后,夏季的干旱和热浪对树木的危害也很明显。苏格兰园艺学家赫伯特·马克斯韦尔爵士 (Sir Herbert Maxwell,1845—1937年)曾指出:干热是伦敦树木面临的两大敌人之一 (另一个是烟雾),而热浪的蒸发力在建筑物和硬化道路的反射下将成倍增加。[15]由此可见,局部小气候的变化对树木的危害甚大。
煤灰、二氧化硫、土壤硬化、干热的环境决定了只有悬铃木等抗逆性②指植物所具有的抵抗不利环境的某些性状,如抗寒、抗旱、抗盐、抗病虫害等。强的树种才能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中更好地生存。那么,这类树木的生理特性是如何被发现的?
经过植物学家、园艺者对城市树种的长期观察,悬铃木、桦树等耐煤烟的树种能在城市长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由于其树干表皮定期剥落,如此便褪去了表皮所富集的煤灰等有害物质,从而防止了对它们正常代谢的影响。1884年10月6日,《泰晤士报》报道:在炎热天气的不利影响下,榆树、橡树和酸橙树等树的叶子已枯萎且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而 “二球悬铃木”的树叶依旧生机勃勃,在公园和广场甚至在伦敦最拥挤的地区,皆是如此。正因这种树木的特殊生理特征才使其在煤烟环境中继续生长,免受城镇快速扩展所导致的毁灭性影响。[16]于是,它在伦敦得以广泛种植。譬如,19世纪80年代,在泰晤士河河堤、新建道路的人行道和房屋街道,以及公园和广场的空地等处,人们种植了数千棵悬铃木幼苗。
总之,因城市煤炭消耗或建设活动酿成的煤烟、土壤硬化和干热等因素共同导致伦敦树木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结果,一些不耐煤烟、硬化土壤和干热的树种逐渐消失或退缩至伦敦郊区等环境状况良好的地区,而抗逆性强的树种则逐渐取代之,成为伦敦的主导树种。当然,这一替代性变化既与树木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树木本身的生理特征相关,也与19世纪伦敦人对树木用途的新认识相关,这一点在树木分布场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
在19世纪早期之前,伦敦是绿意盎然的,树木曾普遍装饰着伦敦的花园与广场:
在伦敦,从十二世纪起市民的花园里就有树。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四法学院和伦敦同业公会种植了大量的树。而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穆尔菲尔德 (Moorfiled)被夷平,开辟成林荫道,使它成为伦敦第一个城市公园。……王政复辟之后,植树成为平常之事。当时的插图表明,纵横交错的林荫道不仅分布在伦敦蔬菜花卉市场、林肯律师学院广场以及皇家花园,而且出现在许多广场和大多数公共大楼的外面。[17]
在1748年的一位瑞典游客眼中,“伦敦几乎家家户户花园里种树,几乎每个广场都有榆树。”[18]
19世纪伦敦的城市发展促使房屋、街道与道路大量涌现。18世纪伦敦的房屋和人口并未迅猛增加,至该世纪末因商业发展导致伦敦出现了拥挤现象,之后持续增长并贯穿整个19世纪。据1739年的伦敦死亡周报表 (the Bills of Mortality)记载,当时有95968栋房屋和5099条街道,而从1839—1849年,仅仅10年间新建房屋数便达到64058栋,新增街道1642条。[19]又如,在1834—1846年的12年间伦敦新增1200条街道,年均增长100条;[20]在1844—1850年的7年间,新增街道200英里。[21]伦敦房屋、街道急剧蔓延的现象曾被英国著名插图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 (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年)称为“房屋进军”。[22]
“房屋进军”的过程吞噬了大量花园与广场。18世纪中期以来,富裕家庭修建的房屋多数都附带后花园,伦敦边缘的房屋还有前花园。此外,18世纪伦敦兴起的住宅广场也逐渐实现了绿化。①相关研究参见Henry W.Lawrence,“The Greening of the Squares of London:Transformation of Urban Landscapes and Ideal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83,No.1,1993,pp.90-118;Henry W.Lawrence,City Tree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the Renaissance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Virginia: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6,p.77.但是,在房屋建设或道路拓展的过程中树木被清除,花园大量消失。英国作家雅各布·拉伍德 (Jacob Larwood, 1827—1918年)在1867年写道:伦敦的 “去乡村化”过程年复一年地推进,无数的树木和花园在房屋建筑浪潮面前消失了,而剩余的植物则被煤烟和污浊空气所摧毁。[23]因人为砍伐和城市环境恶化的双重威胁,私人空间的树木量不断减少,而新增道路等公共空间却没有及时种植树木。
19世纪中期在伦敦树木量锐减的情况下,残存的古老树木也面临被砍伐的威胁。这时,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树木 “情结”逐渐被唤醒,保护古老树木的呼声悄然兴起。1846年4月10日,《每日新闻》(Daily News)刊登了弗雷德里克·特伦奇爵士 (Sir Frederick Trench)写给 “树木和森林委员会”(The Commissioners of Woods and Forests)首席专员林肯伯爵 (Earl of Lincoln)的信,对接连被砍伐的伦敦古老树木深感痛惜,他再三恳请林肯伯爵务必保护它们,并殷切希望在未获得他批准的情况下树木不能再被任意砍伐。[24]次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便以妙语呼应这一保护古老树木的举动:“特伦奇爵士代表皮卡迪利的榆树和切尔西的栗子树给林肯伯爵写了一封动人心弦的紧急呼吁信,我们以伦敦所有麻雀的名义感谢他!”[25]
不久,伦敦植树问题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19世纪70年代人们对树木重要性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城镇及其周边植树的愿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26]那么,这种强烈的愿望是受何种因素的推动而产生的,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有关树木功能的科学新认知是这种愿望产生的重要动因。对植物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记述,可追溯
至17世纪英国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 (John Evelyn,1620—1706年)的 《驱逐烟雾》(Fumifugium)一书,在该书中他谈到植物散发的怡人芬芳能极佳地改善伦敦空气。[27]19世纪中期,树木能净化空气、增进健康的新认知更是不断涌现。1866年,有杂志报道:“无论是由于艺术还是卫生,无疑,在大城市,大型树木都必不可少。它们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贡献甚大。任何一种植物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方面都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树木不但在固碳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有减弱煤烟、灰尘的好处。”[28]1868年,英国植物学家利奥波德·哈特利·格林顿 (Leopold Hartley Grindon,1818—1904年)在 《旧英国的树木》中极力赞扬树木的卫生功能:
树木是人类居住的经济世界的清洁员。它通过 “吸收”过程,即从空气中吸收碳,经过特定的加工,被转化为木材或其他物质……使空气维持在一个适宜人们呼吸的状态,草本植物对此贡献甚大,但木本植物的贡献更大,因为它们有更大的体积和树叶面积。供给呼吸的或在山巅豪饮的新鲜空气,如同看不见的空气美酒,而我们却很少考虑空气的清洁和健康来自于繁盛的树木。同样,我们也不会想到去感谢树木。今天在英格兰呼吸的空气可能在千里之外的树木就为我们净化了。如果风从北方吹过来,我们也许要感激斯堪的纳维亚的山毛榉,如果风从西方吹来,可能正是北美的木兰树襄助了一臂之力……自然界中的每一棵树木都对空气有益。[29]
1876年,《英国建筑师》(British Architect)载文对城镇树木的功能作了更全面的描述:“植物不但美丽,而且实用,它们是空气的清道夫,吸收人体释放的浊气。植物可以清新视野,带来精神愉悦,也可振奋精神,释放香气让人欣喜。在树阴下散步可消除疲惫,最终给人注入一股对造物主的感激之情。”[30]1879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社会科学大会上,来自伦敦的一位医生报告了他近30年的实验及其结论,并证明在住房附近植树非常有益于人体健康。[31]总之,“树木有益于净化空气的问题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不只是在英格兰,而且在整个欧洲亦是如此”。[32]
在上述新认知的推动下,伦敦人的植树呼声此起彼伏。1858年,有人倡议在伦敦的教堂墓地和开敞空间种树,理由是树木不但可以美化街道、愉悦身心,还可以净化空气。[33]1868年,英国建筑师亚历山大·麦肯齐 (Alexander M’Kenzie)写信给 《泰晤士报》,倡议在泰晤士河河堤北岸种树。[34]19世纪70年代末,还有人倡议在伦敦分发盆栽灌木以建立园艺之家,认为如果伦敦的每户家庭都拥有一小丛带刺灌木、一株薰衣草或天芥菜,伦敦的空气质量将会得到显著改善,并且身居伦敦中心区域的200万人将能呼吸散发到空气中的芳香。[35]1878年,一位对植树感兴趣的绅士捐献1000英镑给伦敦的10个教区,希望每个教区用100英镑在伦敦最需要树阴的地方栽种悬铃木。[36]
尽管一些人对树木的益处已有认知,且植树呼声不断,但在19世纪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伦敦却未大量植树,出现这种认知与现实相矛盾的原因何在?
早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著名园艺家、植物学家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 (John Claudius Loudon, 1783—1843年)在新建房屋附近的小径旁栽了一颗槭树 (Sumach),这一行为很快遭到了地方检察官的反对,理由是树木会遮住道路并使路面潮湿,影响路人通行。劳登的邻居也声明在多雨的天气里,经过树下时淋到雨滴让人感觉不悦。最后,劳登被迫将这棵槭树连根挖掉。[37]甚至到19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城镇街道植树遭到了伦敦地方当局的坚决反对,并被斥为 “情感的创造”。[38]这种抵制主要是出于植树存活率与财政方面的考虑。譬如,一些绅士的植树捐款遭到某些教区的拒绝,因为他们担心栽种的树木一旦死亡或遭破坏,便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来重植。[39]而这种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初,伦敦树木的生存环境非常糟糕:煤灰、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缩短了榆树等树木的存活期,每年春季新植的树木经过冬季煤烟的熏染后便丧失了活力,在生长条件相对恶劣的街道或道路旁更是如此。
此外,也有人认为城市植树不利于健康。在19世纪的英国,医学领域经常强调新鲜空气和阳光因子之于健康的重要性,并认为潮湿环境是滋生瘴气与传播疾病的重要诱因,即 “瘴气致病理论”,该理
论成为阻碍在街道旁植树的认知障碍。1867年有报道认为,树木离房屋太近不利于健康,它们会产生潮湿、遮蔽阳光、阻碍空气流通等弊端,枯叶腐烂释放的浊气也会导致疾病。[40]在1883年8月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 (International Hygiene Congress)上,一位成员认为街道树木不但会阻碍空气流通,还诱使人们只躲在街道的阴凉处而避开阳光,因此出于健康的考虑,不应该在城镇种植更多的树木,而应该移除现存的所有树木。[41]
尽管19世纪后期仍有人坚持 “瘴气致病理论”,但是在植物学家的实验结果以及社会舆论的共同影响下,植树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推行。为克服伦敦不利的城市环境以提高树木的成活率,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等纷纷建言献策,有关城市植树的著作或文章不断出现,为城镇植树的方法、树种的选择提供指南。[42]在其推荐树种名单中,悬铃木、杨树等抗逆性强的树种位居前列。另外,他们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指导城镇科学地植树。譬如,1887年英国植物学家乔治·布尔杰 (George Simonds Boulger,1853—1922年)在伦敦学院所做的演讲中谈道,在伦敦植树要因土制宜,并希望林业部能尽快成立,以指导人们在由气管、水管、电缆和下水道构成的底土上种植何种树木才能旺盛生长。[43]与此同时,政府与民众的主流态度也逐渐转向赞同植树。一方面,虽然在劳登挖掉槭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对街道植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是政府面对日益强烈的植树呼声,开始采取措施在伦敦实施植树计划;另一方面,伦敦人也被欧洲大陆城镇的美丽所吸引 (在欧洲大陆,树木被大量种植在广场和街道上),植树观念逐渐传播,植树行为获得支持。[44]此时,常有文字见诸报端指责某些人对植树的漠视态度,并积极呼吁植树。[45]在城市植树弊大于利的观点也受到部分专业人士的反驳,某大学教授通过列举树木的诸多益处,大胆地做出与国际卫生大会不一样的结论,并强烈推荐在街边植树。[46]
在提倡植树观念的同时,植树实践也开始了。1876年,在麦肯齐的指导下,首都公共事务会员会在泰晤士河河堤开展了植树活动。1882年成立的首都公园协会在城市植树方面功不可没,它不但在伦敦新辟的公园里和新建的道路旁植树,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呼吁伦敦地方诸郡委员会参与街道植树。[47]
四
科学指导和舆论压力的共同作用,促使自19世纪70年代末大量树木得以在伦敦种植。1892年,《哈德斯菲尔德每日纪事报》(The Huddersfield Daily Chronicle)报道:根据对伦敦17个地区的调查显示,只有三个地区树木稀少,另外14个地区公路旁的树木量为14700株,其中5158株是由委员会和教区所植,5323株由道路建设者或其他人所植。[48]1895年,美国芝加哥的 《每日国际海洋》(The Daily Inter Ocean)也对伦敦公路旁蔚然壮观的树木进行称赞:仅仅在伦敦城的公路旁就有14700株,这还不包括公园的树木。[49]在九榆树站,每日有100辆装满绿化植物的卡车到达。在1900年12月底的某一周,伦敦共购入圣诞树、冬青和槲寄生 (Mistletoe)等树木3700吨。总之,伦敦的街道、道路等公共场所的树木量在逐渐上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悬铃木的普遍种植,伦敦的树木景观却逐渐呈现出单调性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譬如,悬铃木在街道、道路和公园等处反复出现,以致韦伯斯特认为,悬铃木这种单调重复的景观应该加以修正,而且近年来它已受到诸多指责。[50]其理由有二:一是悬铃木的果毛进入空气对人体的呼吸器官等有害;二是20世纪初伦敦空气质量的改善已能支持多样性树种的生长。[51]
关于悬铃木的危害性,早在1597年的 《草本志》(Herball)中就有记载:如果不慎吸入悬铃木的果毛会导致气管不适,乃至引起咳嗽和嗓子哑的症状;如果它飘入眼睛或耳朵,也会有害视听能力;19世纪时劳登也指出:悬铃果破裂后的针毛飘到空气中,会引起令人厌恶的咳嗽,数周都难以消除。[52]1910年,沃尔辛厄姆勋爵 (Lord Walsingham)写信给 《泰晤士报》呼吁人们关注悬铃木有害的一面,他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悬铃木较多的地方,咳嗽、角膜炎、咽喉异样等健康问题也较多。为了证实悬铃木与这些症状的关联,他咨询了剑桥的亨利医生,亨利医生经过试验后确证,悬铃果破裂后,果毛的确会飘散到空中并污染空气。[53]1914年,有人写信给 《泰晤士报》,称悬铃木的球果是一种刺激性果实,
会致使伦敦患支气管炎和鼻腔黏膜炎的人数上升,尤其是经常到公园玩耍的儿童会患上这类炎症。[54]
这样,到20世纪初,当悬铃木成为伦敦的优势树种且其副作用日益显现之时,出现指责之声也就在所难免。例如,位于伦敦中西区的一栋有名的官邸,其中一些居住者提出要离开住所,理由是住宅周围的悬铃木果毛会刺激喉咙和眼睛,有害健康。[55]
与此同时,因消除煤烟措施的执行——如使用燃气、改善壁炉和提高煤炭燃烧效率,到20世纪初年,伦敦某些地区的煤烟状况已得到缓解,空气质量已经改善。譬如,在临近泰晤士河的低地区,家庭燃气的供应已大幅降低了煤炭的消耗量,由此也减少了令人厌恶的煤烟和煤灰,所以在相对清洁的空气中其他树种也能生长。[56]此外,人们对伦敦的单一树木景观也感到乏味。
值得注意的是,到19世纪末,伦敦私人空间的树木量在急剧下降。1890年有报道认为,虽然伦敦的道路等开敞空间逐渐得到绿化,公共空间的树木量在上升,但这远不及已丧失的绿地与树木面积,所以一升一降的变化是得不偿失的。[57]当人们所拥有的主要是被区隔了的城市公园时,生长于城市有限土壤上的树木仅由极少的专业人员管理,公众却成为旁观者。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伦敦树木分布区域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一种 “疏离”。
综上所述,19世纪伦敦的树木景观曾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主导树种的兴替与分布区域的扩展。这一变化不但凸显了该世纪伴随伦敦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体现了人们改善城市生存环境的多元化尝试。所以,20世纪初悬铃木等树种在伦敦大量出现,乃至单调重复景观的形成,不是社会进步和启蒙降临的自然结果,而是在自然选择和人类认知的共同作用下,英国人长期努力经营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在改善伦敦人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曾带给他们新的烦恼。因此,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得失问题,实在是一个需要多方面、辩证地看待和对待的问题。
[1]Sophie Borland,“Britain’s most expensive tree valued at 750k”,The Telegraph,http://www.telegraph.co.uk/news/ earth/earthnews/3340392/Britains-most-expensive-tree-valued-at-750k.html,January 10,2015.
[2][4]“London Trees”,The Spectator,Vol.71,No.3403,1893,p.365.
[3][5][50]A.D.Webster,London Trees,London:The Swarthmore Press,1920,p.7,p.1,p.1.
[6][7]“Tree Planting in London”,The Morning Post,Issue 35938,August 25,1887,p.3,Gale Document Number: R3211754205.
[8]“Trees in Towns”,The Star,Issue 53,May 2,1896,Gale Document Number:R3210928294.
[9]Peter Brimblecombe,The Big Smoke: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don:Methuen, 1987,pp.5-22.
[10]Hugh Platt,A New,Cheap and Delicate Fire of Coal-Balles,London,1603,p.B.4.
[11]布雷恩·威廉·克拉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王黎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4页。
[12]Augustus Voelcker,“On the Injurious Effects of Smoke on Certain Building Stones and on Vegetation”,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Vol.12,1864,p.150.
[13]Augustine Henry,Forests Woods and Trees in Relation to Hygiene,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19,p.46.
[14]The Morning Post,Issue 35634,September 4,1886,p.9,Gale Document Number:R3212483189.
[15]Herbert Maxwell,“London Trees”,The New Review,No.60,1894,p.582.
[16]James Nasmyth,“The London Plane Tree”,The Times,Issue 31257,Oct 6,1884,p.4,Gale Document Number: CS67553094.
[17][18]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04-205页。
[19]Stanford’s New London Guide,London:Edward Stanford,1860,p.28.
[20]“Growth of London”,The Ohio Observer,Issue 29,July 29,1849.
[21]“Growth of London”,Greenville Mountaineer,Issue 42,February 22,1850.
[22]Michael Rawson,“The March of Bricks and Mortar”,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7,No.3,2012,p.844.
[23]Jacob Larwood,“Trees and Gardens of Old London”,Once a Week,Vol.3,No.65,1867,p.356.
[24]“Trees and Fountains”,Daily News,Issue 69,April 10,1846,Gale Document Number:BA3202824331.
[25]Illustrated London News,Issue 206,April 11,1846,p.237,Gale Document Number:HN3100014241.
[26]Nathan Cole,The Royal parks and gardens of London,London,1877,p.67.
[27]John Evelyn,Fumifugium,Exeter:The Rota,1976,p.A4.
[28]“The Use of Trees in Large Cities”,The Wesleyan-Methodist Magazine,No.1,1866,p.75.
[29]Leo H.Grindon,Trees of Old England,London,1868,pp.1-2.
[30]“Trees in Towns”,British Architect,Vol.5,No.126,1876,p.275.
[31]“Planting of Trees in Towns”,Daily Evening Bulletin,Issue 19,October 29,1879.
[32]William H.Ablett,English Trees and Tree-planting,London,1880,p.1.
[33]W.H.J,“London trees”,The Times,Issue 23065,Aug 06,1858,pg.9.
[34]“The Thames Embankment-Rus in Urbe”,The Times,Issue 26186,July 25,1868,pg.11.
[35]W.Mattieu Williams,“Economic gardens for London and other smoky towns”,Journal of Society of Arts,Vol.27, 1878,p.376.
[36]“Tree Planting in London”,The Times,Issue 29301,Jul 8,1878,p.7.
[37][44][55][56]A.D.Webster,Town Planting,Trees,Shrubs and Herbaceous Plants,London,1910,pp.48-49,pp.54-55, pp.8-9.
[38]Examiner,16 Dec.1876,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http://ncco.tu.galegroup.com/tinyurl/5iF73,March 17, 2013.
[39]“Trees in London”,The Times,Issue 29778,Jan 15,1880,p.11.
[40]“Trees and Health”,Bow Bells,Vol.6,No.144,1867,p.316.
[41][46]“Trees in City Streets”,St.Louis Globe-Democrat,Issue 260,February 5,1883,p.2,Gale Document Number: GT3004137084.
[42]“Tree Planting in Towns”,British Architect,Vol.10,No.17,1878,p.160.
[43]“Tree Planting in London”,The Huddersfield Daily Chronicle,Issue 6324,November 9,1887,p.5.
[45]“The Trees in Open Places”,The City Jackdaw,Vol.4,No.207,1879,p.404.
[47]“Trees in London's Streets”,Architects Magazine,1900-1907,Vol.3,No.35,1903,p.233.
[48]“Trees in London”,The Huddersfield Daily Chronicle,Issue7872,October 24,1892,p.4,Gale Document Number: R3211488220.
[49]“Tree in London Highways”,The Daily Inter Ocean,Issue 189,September 29,1895,Gale Document Number: GT3001586966.
[51]“Trees in London Streets”,The Times,Issue 40798,Mar 10,1915,p.7,Gale Document Number:CS119080042.
[52]Mark Heron,“The Plane in London”,The Gentleman’s Magazine,No.259,1857,p.277.
[53]Lord Walsingham,“Plane Trees and Disease”,The Times,Issue 39266,May 7,1910,Gale Document Number: CS219871911.
[54]H.D.O’neill,“Botanical Colds”,The Times,Issue 40502,Apr 20,1914,Gale Document Number:CS151716500.
[57]“Trees in London”,Journal of Society of Arts,No.39,1890,pp.79-80.
责任编辑:郭秀文
K561.4
A
1000-7326(2015)08-0100-08
严玉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