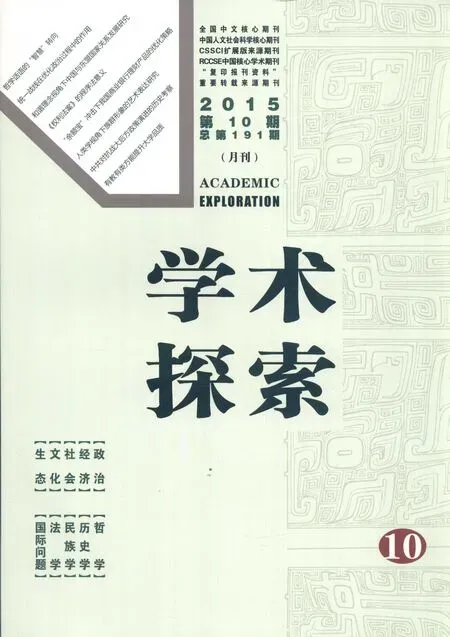哲学话语的“智慧”转向
胡朝阳,梁 忠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哲学话语的“智慧”转向
胡朝阳,梁 忠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爱智慧”作为古希腊“philosophy”的词源释义,与中国儒家经典对“大学之道”的论述,互补性地为“轴心时代”的哲学奠定了“智慧”的话语。中、西哲学在各自发展历程中均偏离这一话语。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现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话语的重要转向,同时体现了向轴心时代“智慧”话语的自觉回归,亦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话语的综合创新树立了典范。陈卫平、张汝伦等人对“智慧”说的阐扬,体现了“智慧”话语在新世纪的重要发展。
哲学;话语;智慧;转向;回归;综合创新
按正常的逻辑,问题总在事物的发展中得到解决。然而,随着中西哲学的不断纵深发展,何为哲学、哲学为何的哲学元问题却日益困扰着哲学界人士。尽管伟大“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家曾经互补性地指出了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旨趣,然而在各自的哲学发展长河中却并没有接续和围绕这一旨趣展开哲学致思,而是形成许许多多脱离人类精神追求旨趣的哲学概念、哲学体系和哲学话语,进而使得当今的许多哲学家,特别是中国的哲学家们,深陷“何为哲学”、“哲学何为”的困惑之中。冯契的“智慧”说及“智慧说”哲学体系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自觉回应,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值得重点注意的话语转向,同时也是向“轴心时代”哲学本义的话语回归,它为人类精神的最高追求从而为今后哲学应有的精神旨趣贞定了更为合理的方向。
一、哲学话语的历史回归
从词源释义的角度,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y)”其意为“爱智慧”,即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然而,对于何谓智慧,却没有进一步的阐释。后世学者把古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作为对“爱智慧”的注脚,认为“爱智慧”即为认识自己,或者说从认识自己开始。但是,“爱智慧”就仅仅是认识自己吗?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的关系怎样?认识自己和世界又有何目的和意义呢?在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y)”概念及相关论述中难以找到确切的相关内容。
倒是同属伟大“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对人类精神的意义追求做出了比较完备的表述,此表述或许正好可以成为古希腊“philosophy”(爱智慧)的意蕴和内涵。在中国先秦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关于人类的精神、智慧之学无疑是相对于日常生活技艺的“小学”而言的“大学”。儒家经典《大学》对人类精神的意义追求有完备的表述,它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被儒家奉为圭臬的人类精神追求的“三纲领、八条目”。在此纲领、条目中,虽然没有出现“哲学”字样,但“大学”、“大学之道”诸词,清楚地表明这是为学和学问的最高层级,其层级的高度相对于古希腊的“哲学”一词来说,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与亚里斯多德时代的“第一哲学”概念的层级大致相当。而且,“八条目”以“致知”为基础、根基,为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开端和出发点,与阿波罗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意义上,对于同处“轴心时代”的中、西文化来说,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y)”、“爱智慧”,与中国先秦时期《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在概念与内涵上具有互注的效果,从而有助于对世界哲学史上“轴心时代”的“哲学”概念之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追求智慧,而追求智慧则一方面在于求知,即格物致知(包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另一方面在于运知、用知(“知”的运用),即在于以所求得的“知”来进一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最终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目的和境界。前者体现的是认知,后者体现的是认知所指向的目标和所应具备的价值追求;认知是价值追求的基础和出发点,价值追求则为认知和实践提供原则、方向和意义。明乎此,可以显见,古希腊哲学的核心话语是“智慧”,而同处伟大“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儒家哲学的核心话语同样也是“智慧”,而且正是中国先秦的儒家经典为此“智慧”界定了清晰而完整的内涵。
然而,西方哲学自柏拉图构建其“理想国”开始,其哲学话语就开始偏离“认识你自己”的“爱智慧”的话语。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古希腊的哲学话语中已经几乎看不到“智慧”的身影了,当此之时,不仅哲学话语淹没于“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之中,而且被奉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也无非是由逻辑概念构成的所谓“理念”世界、“本体”世界。“认识你自己”被遗忘了,“智慧”话语消失了,不仅科学而且哲学所充满的是对逻辑、本体、自然、物理等的广泛讨论,尤其是与人自身及现实世界相分离的逻辑概念的世界——ontology(本体论)——被捧上哲学的最高宝座。哲学成了脱离现实、脱离生活、忘怀“自己”的纯粹逻辑的游戏。
此后,从普罗提诺到奥古斯丁,从安瑟伦到托马斯·阿奎那,整个罗马、中世纪的哲学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笼罩下沉浸在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所构造的关于上帝存在的“神性”话语之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以及现实中人自身的精神及生活实践,完全消弭于对上帝的皈依和对神性的论证之中。
到了近代,笛卡尔的“沉思”和康德的“批判”把人们的哲学致思从天国、神性拉回到了经验的人世和人自身,人类“理性”成为哲学的核心话语,甚至成了哲学的代名词。但是这种“理性”的哲学话语,由于不具备“智慧”所应具备的人类精神的追求指向,故而成为一种为理性而理性、为知识而知识的认识论、知识论,且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脱节,从而无法与伟大“轴心时代”的“智慧”意蕴相提并论,而沦落为一种徒具工具功能的单纯的知。这种为知而知的“知”,对于人类精神的终极追求和旨趣,对于人类的最终福祉来说,无法排除其“南辕北辙”之嫌。
正是因为看到了为知而知的“理性”已经带给人类巨大的实际祸害,故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兴起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以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相抗衡,故而现代西方哲学交织在与科学主义对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非理性”、“反理性”等话语之中。尽管“非理性”、“反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潮对“理性”的科学主义有一定的救偏补弊之功,然而,“非理性”、“反理性”也仅仅涉及人类精神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故而难言其具备“哲学(philosophy)”、“爱智慧”所蕴含的人类精神的终极追求。而且“非理性”、“反理性”的哲学话语还从根本上反对、排斥人类理性,与“智慧”本义也不兼容。可见,西方现代哲学仍然没有重新响起“智慧”的话语。倒是19世纪的马克思曾将哲学称之为“人世的智慧”[1](P223),并且将世界、人生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出了哲学向“智慧”话语回归的第一先声。
在中国,先秦以后的哲学同样偏离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人类精神的追求旨趣,从而偏离了原有的“智慧”话语。两汉哲学致力于构造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秩序和三纲五常的人间秩序。魏晋时期,以对宇宙本体玄思为核心的“有”、“无”之辨成为哲学的中心话语。隋唐佛教哲学对成佛、出世的沉迷,将现实之知及现实生活抛于脑后,“佛性”、“般若”成为哲学的流行话语。宋明以降,虽然张载、朱熹等人对“格物致知”作过专门论述,但哲学的主线是以对“心”之本体(以“理”为本或以“心”为本)的探求取代对宇宙本体的玄思,“天理”、“良心”成了哲学家以致普通民众的口头禅,“格物致知”也仅仅作为去除“人欲”以使“良心”发显、“天理”流行的方法和途径而已,“修齐治平”、“亲民”、“止于至善”的价值追求不复存焉,最终结果是封建纲常取代了对物对人的认知,忠孝节义取代了为民谋利的价值旨趣。
到了现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依傍西洋哲学来诠释、梳理中国古代哲学,并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但均与“智慧”话语相距甚远。冯友兰的“新理学”热衷于构建与现实生活脱节的“不合实用”、“无用之用”[2](P13)的“理”的概念和世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企图把世界建立在“体用不二”的本体之上,通过“翕辟成变”,来论证其万法“唯识”的理论,同样脱离现实的生活世界。金岳霖的“知识论”虽然体现了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但对人类精神的追求旨趣同样惘然无所指,尽管他在《论道》一书中意识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精神追求是“道”,但其所论述的“道”却仅仅是“式—能”的纯粹形式。一句话,中国现代哲学中充满的也只是“理”、“唯心(唯识)”及“知识”等话语,而不是“智慧”话语。
然而,在这些话语之外,有一派哲学,立足于社会现实斗争的实践,致力于认识事物客观规律并用之于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实际的哲学,却具备了“智慧”话语的实质内容,这就是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正是建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认识辩证运动理论的基础上,会通中西哲学史上的各种“智慧”元素,而生发出来的体现了轴心时代“智慧”本义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以“智慧”为其核心话语,对“智慧”作了集中、系统的论述,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话语的重大转向,同时体现了向伟大“轴心时代”奠定的“智慧”话语的自觉回归。
二、哲学话语创新的典范
冯契是按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次序提出并阐述其“智慧说”哲学体系的。以“智慧”为核心,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围绕三个基本关系而展开:一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这是冯契“智慧”哲学首先关注并重点考察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冯契阐述了他的广义认识论,提出了其“转识成智”的理论;二是智慧与方法的关系问题,这即是冯契所称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3](P37)所要解决的方法及方法来源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冯契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的学说,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辩证逻辑方法体系;三是智慧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智慧的追求旨趣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冯契提出了著名的“化理论为德性”的学说,把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最高追求旨趣贞定为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培养和“自由人格的联合体那样的社会”[4](P340)的建立,从而构建了独具一格的价值学说和道德哲学体系。在冯契哲学体系中,其“智慧”说贯彻于其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及道德哲学之中,“智慧”成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主线和核心话语,其哲学体系也事实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智慧”体系。冯契的“智慧”体系会通了中西,贯通了古今,吸纳了此前最新的哲学话语成就,从而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进行新时期中国哲学话语的综合创新树立了典范。
在广义认识论中,冯契把认识论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3](P47)冯契认为,前两个问题是关于知识经验的问题,后两个问题是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即关于智慧的问题;前两个问题是西方哲学所主要致思的问题,而中国古代哲学则更多地探索了后两个问题。而在其广义认识论中,冯契把这四个问题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人类在对这四个问题的认识上体现为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两次质变、两次飞跃,体现为一个完整的辩证运动、辩证发展、辩证统一的过程,从而打通了知识与智慧的界限,会通了中西哲学不同的致思路向,同时也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论争及作为该论争在中国现代哲学之折射的科玄之争作出了理论总结。
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冯契将“转识成智”的佛教命题进行改造并运用到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的论述,书写出其广义认识论最具创新性的篇章;另一方面,将类、故、理的中国古代逻辑范畴和理性直觉融汇于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之中,构建了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现代辩证逻辑方法论体系。
在价值论和道德哲学方面,“智慧说”哲学体系在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即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关于“性与天道”的终极玄思,以及培养理想人格崇高“德性”的精神旨趣,融汇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理论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培养立足于“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理论,这无疑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富有创新性的成就。
不仅如此,冯契“智慧”哲学还吸纳了中国哲学自现代以来最新的哲学话语成就:一是“实践”说,另一是“反思”、“境界”说。
一方面,冯契的“智慧说”哲学把实践作为贯通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动力因素,认为广义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都是在人类实践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另一方面把实践作为认识是否把握具体真理的检验标准之一;而且,“智慧说”哲学还把以实践的最高表现形式——“自由劳动”——为基石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培养作为其“智慧”的最后追求。这样,冯契“智慧说”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话语吸纳为自己“智慧”话语的基石、动力和追求,从而成为其自身生命的重要部分。从哲学史的眼光来看,抓住了“实践”,无疑就抓住了哲学的生命线;相反,脱离实践的哲学以及其他一切学问,都只能是人类思维的“无根树”。
同时,“智慧说”哲学还吸纳了冯友兰“反思说”、“境界说”的哲学话语。冯契认为:“由于反思,人把握了逻辑规律和逻辑方法,也是由于反思,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了,人对自我有了越来越明白的意识。人凭意识之光不仅照亮外在世界而且用来反照自己,提高了人心的自觉性,加深了对人的本性的认识。”[3](P216)又说:“哲学的核心是性与天道的学说,而讲性与天道,不仅在于求真,而且要求穷通。哲学要把握会通天人、物我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培养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德性,哲学要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揭示人生的最高境界……”[3]P(423~424)很明显,在冯契“智慧说”哲学中,“反思”成为把握逻辑规律与逻辑方法、提高人的自我意识和人心自觉性的主要方法之一,“境界”成为穷究天人之际、达到终极关怀之极致的表现形式,二者都被吸纳成为“智慧说”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使得其哲学成为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哲学体系。从而,“反思”、“境界”的哲学话语成果不仅得到继承和改造,而且成为“智慧”哲学话语的有机内容,从而被赋予了更新的意蕴内涵。
三、“智慧”话语的弘扬与发展
20世纪末,陈卫平先生在对冯契、庞朴、汤一介、张世英、王树等哲学家的哲学理路进行梳理后,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哲学是文化的精华,因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近20年来人文学科中较有成果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总趋势,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从‘认识史’到‘智慧说’。”[5]并对新世纪哲学话语的走向作了前瞻性预见:“可以说从智慧层面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是对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应和总结。由此,我们也可以预计进入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大概是进一步讨论中国哲学的智慧是什么,以及这种智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是什么。”[5]
此后,冯契“智慧说”哲学思想不断被哲学界广泛阐发和弘扬,“智慧”的话语随之而流传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对冯契“智慧说”哲学较早作出系统阐发的当属西北师范大学的陈晓龙先生,他在《转识成智——冯契对时代问题的哲学沉思》一文中,从时代精神以及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多个角度,对冯契“智慧说”哲学作了系统阐发和深层揭示,[6]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先生在《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一文中,也系统阐发了冯契的广义认识论,[7](P42~43)湘潭大学王向清先生在其《冯契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一文中,也对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作了集中阐发。[8]
值得注意的是,对冯契“智慧说”哲学的研究,近年出现了一个批判创新的动向。张汝伦先生《创新、超越与局限——试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9]一文体现了这一动向。张汝伦先生在其文中充分肯定了冯契的广义认识论,肯定冯契在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特色,以及会通中西并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有机组成部分等方面的独特贡献,认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素融为一体,代表了中国大陆学者在20世纪下半叶后认识论研究上的最高成就”。[9]并认为:“冯契还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智慧给予系统论述的哲学家,他将智慧等同于哲学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以智慧学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关于智慧的思想。”[9]
接着,张汝伦先生从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及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出发,对“智慧”的内涵和功能作了深入辨析。他认为,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是认识关系,而是存在关系或实践关系;与其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毋宁说认识是实践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他提出,智慧不是性与天道的“理论”,而是性与天道的“发用或功能”;智慧“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是“实践之道”;智慧应当具有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的功能。[9]基于此,张汝伦先生指出冯契“智慧说”存在两方面的理论缺憾:一是冯契的“智慧”只是理论,而不是实践的智慧,不是实践之道;二是冯契只强调“智慧”培养德性的功能,而未涉及智慧的判断功能,忽视了智慧作为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的机制。[9]
认为冯契“智慧说”哲学不是实践的智慧,似乎并不公允。因为在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中,不仅认识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实践,而且在转识成智后“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中,指向改造世界的实践——“自由劳动”——实际上已经内蕴于“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培养之中,且作为理想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存在。这样,实践不仅是认识和智慧的基础,而且是理论和智慧的指向,尽管这一指向因内蕴于理想人格的培养而未被凸出。当然,张先生立足于实践的本体主义立场,把认识看作是实践的要素之一,而不把实践仅仅看作为认识的基础,自有其理论深意。
张汝伦先生的后一个批评,即认为冯契“智慧”哲学忽视了智慧作为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的机制,显然比较中肯。因为“智慧”之为智慧,不应当仅满足于“自证”,不应当自得自足,而应当一方面经受实践的检验,同时也具备鉴别、判断其他命题、理论之真、假、善、恶的判断功能以及明白清晰的判断标准和机制,否则所谓“智慧”就有可能成为独断论者的极好借口,或者成为遁世者的妙理玄音。而冯契的“智慧说”哲学虽然谈到了价值评价问题,[3]但对于如何进行价值判断、是非判断的标准和机制等问题,则浅言辄止,无法为人们进行判断提供“智慧”指导。况且,冯契把评价标准归结为是由“我”掌握、由“我”运用的,而把“我”又最终归结为主观性的“良知”、“良能”,[4]从而实际上取消了评价的的客观标准。
张汝伦先生基于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以及实践的本体主义立场,对冯契“智慧说”所作的深度辨析,使我们一方面明了冯契“智慧说”哲学及“智慧”话语对中国哲学发展作出的独特功勋,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智慧”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张先生对“智慧”内涵的独特解读及其对实践本体立场的凸显,以及对价值判断、是非判断机制的强调,这可以看作是冯契开创的哲学“智慧”话语在21世纪哲学征途挺进的一个强音。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冯契.冯契文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冯契.冯契文集·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陈卫平.从“认识史”到“智慧说”——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6]陈晓龙.转识成智——冯契对时代问题的哲学沉思[J].哲学研究,1999,(2).
[7]杨国荣.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A].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王向清.冯契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J].哲学研究,2010,(10).
[9]张汝伦.创新、超越与局限——试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J].中国哲学,2011,(8).
The“W isdom Turn”of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HU Chao-yang,LIANG Zhong
(Philosophy Colleg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Love ofwisdom”which is the etymological paraphrase of“philosophy”in ancientGreek and the elaboration of the“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by Chinese Confucianestablished complementarily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wisdom”in the“Axial Age”.But in the later history,both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Western partner deviated fromit.“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wisdom”by Feng Qiembodied the important turn and conscious regression to the discourse ofwisdom in the“Axial Age”since the Chinesemodern history.It created themodel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philosophy too.And the state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uch as Chen Wei-ping and Zhang Ru-lun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wisdom”discourse in the 21st century.
philosophy;discourse;wisdom;turn;regression;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B014
:A
:1006-723X(2015)10-0001-05
〔责任编辑:李 官〕
胡朝阳,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学和中国现代哲学研究;梁 忠,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