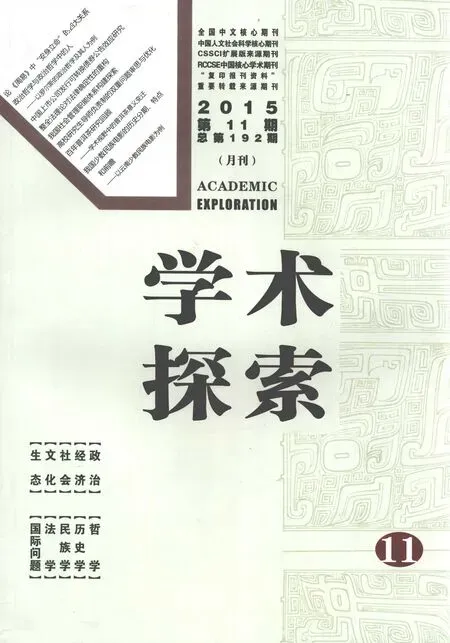南宋绘画图式对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的影响
南宋绘画图式对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的影响
王莲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南宋画家们把观察方式由整体把握趋向深入细节并由远观转为近视, 开创了以少胜多、空灵深远的格局。宋代理学的发展,使中国画构图技法更加完善并有了全新的突破。宋元时期中国禅宗极盛,禅宗和宋元文化的输入使得水墨画在日本风靡一时。此时,日本水墨画对南宋的摄取除了审美意识外,更重要的是绘画图式。我国南宋绘画简洁的构图——以小见大、以少见多、以简代繁、以空代实,使单纯的画面充满生机,与日本民族空寂、闲寂、禅意等日本传统美学形态承袭融会并深深地影响着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的发展。
关键词:南宋绘画;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
作者简介:王莲,女,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美术研究、民间美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
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受益于中国画在各方面的营养,中国绘画的许多元素被日本吸收、同化,并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组成部分。日本水墨画在生成、模仿、发展、成熟、创新的各个阶段,无不受到中国绘画的直接影响,经过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移植、消化、吸纳,从而创造出日本民族的水墨画,本文所述就是南宋绘画图式对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的至深研究。
一、南宋绘画图式的新突破
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对南宋绘画的摄取除了审美意识的选择外,还有包括室町幕府文化发展的战略、足利将军的权威等其他复杂因素所致的可能性。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由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其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镰仓时代封建割据取代了中央集权,王朝贵族没落,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并需要自己的文化,而日本始终把文化上的借鉴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便积极摄取中国宋元文化。宋元时期中国禅宗极盛,禅宗和宋元文化的输入使得水墨画在日本风靡一时。虽然北宋宫廷样式的“院体画”达到了顶点,元代士大夫“文人画”也很发达,但日本吸取的并不是宋元绘画的全部样式,更多的是接纳了在中国绘画史上从技法方面来看是属于文人画家对立面的南宋“院体画”、从声誉中来评被认为是默默无闻的“小画家”的南宋禅画。
宋元时期可以说是日本水墨画的摇篮期,当时日本并没有水墨画,还保留着唐代重设色的传统。中国画由工笔设色演变到水墨技法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而日本并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可以想象,当初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充满光影变化的水墨画时,一定是受到极大的视觉震撼。南宋简略却又笔墨层次丰富的画风,尤其是快速、不假思索的泼墨画法很近乎20世纪表现主义及抽象表象主义的潮流,日本人选择它,更为显示其重视表现性的审美情趣。可见,表现主义不仅是美术史上的一个具体流派,而且更是一种艺术倾向和人文精神;不仅出现于20世纪初的欧洲,在八百年前的宋元时期的中日本水墨画中就已经存在。但当时的日本并不是系统地而是相当踌躇地在采用,是默庵、可翁、良全等这几位画家奠定了日本水墨画笔墨技法的基础,至少是在禅宗的范围内。
构图是中国绘画中的一条重要的美学法则。宋元时期,中国绘画的构图已趋成熟,北宋的“全景山水”和南宋的“边角山水”“折枝花鸟”,可以说是宋元时期章法构图的最主要的形式。构图是西学东渐后的外来专业术语,在中国传统画论中称之为“章法”“布局”。
唐代绘画就非常重视构图,《山水诀》(传唐王维所著)中“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凡画林木,远者疏平,近者高密”[1]等诸多论述,对山水画构图中的远近、高下、虚实、深浅等空间处理都有了明确的总结。
到了宋代,中国画的构图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郭熙是山水画实践与理论的集大成者,其著作《林泉高致》对“三远”理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山水画构图美学理论的成熟。他认为“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按徐复观的理论观点是,郭熙所总结出的构图原则“三远法”,使把庄子的“逍遥游”的精神自由、解放思想及魏晋玄学在人生中的实践落实于山水画之表现成为可能。[2](P264)
纵观宋元画史,“全景”和“边角之景”构成了这个时期绘画的主流风格,其极度的“丰实”与“空灵”,占据了我国传统美学最高境界的“两元”。北宋基本是以壮美的全景图式贯穿了整个的时代,而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以后,南方地区与北方的山川相比更多的是平缓的丘陵山地。画家们的观察方式由整体把握趋向深入细节并由远观转为近视,开创了以少胜多、空灵深远的格局。宋代理学的发展,使绘画的视角从“以大观小”转向了“以小观大”,马远、复圭的“一角”“半边”取景法,使中国画构图技法更加完善。南宋绘画边角小景与北宋绘画的气势雄浑有了明显变化,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四大家为代表的院体绘画,弃置北宋以来的全景构图而转向选择某一角度、某一局部的边角式构图。这种大量留白的局部构图虽被戏称为“残山剩水”,但在艺术审美上却自成风格,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富于灵性,在图式上有了全新的突破。
二、南宋绘画图式对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之影响
宋元时期中国水墨画东传日本,而章法构图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的全景山水图式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共鸣,而南宋边角图式却漂洋过海为日本画坛所吸纳。南宋院体图式以近景、小景取材,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虚带实的“边角半边”与日本人偏爱的空寂与幽玄之美感不谋而合。日本人从画中细微的题材、精致的表现以及暗含遐想空间的深度内涵中领悟到了禅机与诗意,很自然地走向了精确设计的概念,富有禅宗意境的简略布局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
《鹭图》是早期日本禅宗画家默庵灵渊的代表之作,*默庵灵渊(?~1345)是入元画僧中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14世纪20—30年代,他在中国各大禅寺巡礼,求法于元代名僧江正印、祥符绍密等人门下,后来成为中国的住持。高斜的树干上栖停着一只鹭在寒风中抖擞,其锐目闪光盯住水中的鱼,使画面静中有动,画面下方并没有画鱼,而是留下一片空白。简略的构图,将“画眼”集中于鹭鸟身上。同时,这只鹭鸟也将观者带向远方,使画中之势伸向旷远宁静的天空,给人一种无穷尽的感觉。这种留白并非是简单的虚“无”,而是一种充实的“无”,使作品的意韵延伸到画面以外,大胆使用的留白让画面富有清新、寂静的格调,同时使主体元素在此环境中亦能得到突出。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不拘形似,画面常呈现出一片虚白至上的境界来描绘自然的生命,尤其是南宋绘画勇于突破全景程式构图,大胆剪裁画面而画边角之景(或山一角,或水一涯),画面留下了大幅的空白以突出主体景观,表现空濛的空间及浓郁的诗意,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寒江独钓图》(传为马远所作)就是很好的画例。画面上仅有一位老者独坐舟端垂钓,舟的另一端高高翘起,简约数笔便勾勒出人物专注的神情。最微妙处还在于小舟的四周不着一笔,留下大片的空白给人无限的空间感觉妙不可言,淡远空灵禅味无穷。大量留白的局部构图是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构图的一大特色,一张画往往只画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空白不画要比有画处更给人以无限遐思。
日本画家铁舟画过若干幅《芦雁图》,*铁舟德济(~1369年),日本著名的禅僧梦窗疏石的弟子,于13世纪30—40年代入元。并尝试了各种构图形式。画芦雁以秋冬景居多,其清旷荒寒之境较受中国文人之推崇,是宋元花鸟画常见的题材。例举铁舟的三幅《芦雁图》,一幅是北宋全景式构图,另两幅则是南宋边角特写式构图。前幅注重画面的整体感和结构的严谨性,画面复杂并在变化中求统一、运动中求均衡,使有限的画面包容尽可能多的艺术语言,一群芦雁在高空飞翔,它们有规律的节奏韵律给人以抒情诗般的艺术享受。画中尚有近二十只芦雁在水边芦苇丛中戏水,意态悠闲颇有野趣。芦苇叶片皆是淡墨,微风中摇曳的疏疏落落的芦苇隐现于大块面积的渲染之中,芦雁在大笔画清淡水摊的衬映下越发显得精神。此画是日本早期水墨花鸟画中值得重视的一幅,它标志着在意境创造、布局、气氛、笔墨、层次关系上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般地说,饱满、繁多的景物画面会增加整体布局的难度,若要使繁多归一,必须使物象与情感、造型与笔墨乃至色调浑然一体,其层次还要清晰有序给人以鲜明整一的感觉。该画以“雁”为主体,以芦苇、湖水为背景,在主次、浓淡、刚柔等组合关系上无拖沓混浊之现象,可以推断是经过一番苦苦探索、反复推敲后的一种超越,非高手难以驾驭。而后两幅,则为一角取景、景物大大减少,重点以两只芦雁为描写对象。一幅表现了两雁在折芦之中,一雁已息落,一雁盘旋将下;另一幅两雁栖于湖水岸边,相望相依富有天趣,宛如一对旅外的伴侣。边角特写式构图的笔墨更加简练,因此,对于笔墨技艺要求很高,画中的每一笔、墨,包括墨色的干、湿、浓、淡都要有所变化。这两幅边角特写式的芦雁构图笔墨不多,芦雁形象删繁就简,虽大胆落墨但墨色单调,显露出画家笔墨功力还不够深厚;从大写意的泼墨芦雁及几棵芦草的点缀上亦可以看出其浓淡、枯润、疏密变化还欠佳。[3](P161)
南宋盛行的“折枝花鸟”构图如同山水中的“边角之景”构图一样同属于以少胜多的简略图式。所谓“折枝”构图就是折枝或截取树木花草中最美的一角(或一段)作为表现的主题,追求以少胜多,绘画“四五枝”却能胜过“千万朵”的效果。
“折枝”一词最早见于唐人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妙品》中对边鸾的评价:
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蝉,并居妙品。[4](P23)
在画面中,折下花枝的摆放方式比全株式花卉要自由得多,它打破了唐代花鸟画常用的竖向中轴对称式构图旧模式,向斜向非对称构图发展而成为一种典范。在宋元画史中,“折枝”构图的成熟是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折枝”构成法则运用灵活,结构组合丰富而变化,内涵深广且法度严谨。折枝式构图是宋代花鸟画最常用的构图形式,宋以后则日趋程式化了。
十四世纪,大量宋代花鸟画传入日本后便风靡起来,并成为后世一再表现的图式。
《墨梅图》是三联幅成套作品,该作品只知道由白云惠晓题赞,却不知道作者是谁。白云惠晓于圣一国师之后前往中国,师从断溪妙用,弘安二年(1279)归国,殁于永仁五年(1297),由此可推断出制作本幅作品的大致时间。这套三联幅作品,中间一幅画的是出山释迦,左右画的是墨梅图各一幅。右幅是在印有花纹样的蜡箋纸(一种涂了蜡的纸)上,使用了没骨画法表现的折枝墨梅图。关于三联幅的作者说法不一,有说左幅是中国人画,右幅是日本人画的;有说是白云惠晓在中国画的说法;有从三幅作品不同的纸质方面来考证,认为该作品应该由中国传入后再题赞的。
折枝构图往往截取最有代表性、最优美、最精彩的部分入画。以近景出现,不能有较大的动势变化,因此更注重在小小的构图中巧妙地布置画面,使其均衡得势,以平稳为主,平中有势。而这幅折枝墨梅图一波二折式、“V”字形图式,一枝墨梅花从画幅右中侧入画,以一波二折之势向横倚出枝,末梢又自然分出上下两小枝,几朵梅花点缀枝头。该画构图截取了最精彩的一枝墨梅加以描绘,以一枝联想全株尽显曲线美之变化。此构图贵在得势,即有物象富有生机之势,又有均衡之美,取势传情,生动自然,是宋代折枝构图中经典的构图图式。[5](P151)
日本大板正木家藏的《墨梅图》,画面的左上方有一长枝弓形竖向折枝墨梅,搓错的枝丫,枝繁花茂,千蕊万朵,有张弓弩拔之势,充分表现了寒梅怒放的神韵和风骨。布局上以密取胜,并做到了密而不乱,繁而有韵。枝干挺秀,穿插得势,构图清新悦目,沿袭了元代墨梅图式。墨梅浓淡相宜,花朵的含苞、渐开、盛开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机盎然,显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笔力挺劲,虽不设色,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动地刻画出来。该画明显受到了元代文人画家王冕墨梅的影响。清代朱方蔼曾说:“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煮石山农(王冕)始易以繁花,千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王冕画墨梅,尤其是画枝干,十分注重质感的表现,用笔顿挫得宜,笔力遒劲。有时画枝梢,一笔拉到几尺长,停而不滞,一气呵成。枝的梢头露出了笔的尖锋,笔墨洗练。王冕画梅画花的功力很深,他将杨补之的一笔三顿挫,改为一笔二顿挫。勾勒梅花如铁线圈成,用笔不飘浮,严谨而逼真。[6](P39)
活跃于镰仓末到南北朝时期的日本画家可翁,*可翁(1270~1345)与默庵是同时代的道释画家。关于他的生平还知道得很少,有说原为日本东福寺禅僧,于1317年入元留学,曾在中国修禅12年,归国后主持万寿寺、南禅寺;也有说根据其画上“仁贺”的印章以及画风来推测,他应该是诧磨派专职画家。诧磨派是从平安末期到南北朝前后出现的由同姓的画家组成的画派,他们的俗名多为“为”、而法名为“贺”。他们的遗作几乎都是吸收了宋元水墨画风格的佛教绘画。是一位善画竹、梅的日本画僧。其《竹雀图》明显借鉴于宋元折枝构图图式,[6](P150)尤其是学牧溪甚多留白,一枝横生的竹枝倾向一侧,扩大了画面的空间感,画面空间处理就像是经过精密仪器测量过似的恰到好处,体现出可翁构图高超的把握能力。
日本水墨画的边角、折枝构图显然是受到南宋的影响,这种“以小观大”的思维模式与北宋“以大观小”正好相反,体现了对细小事物的宽宏与精研。这种小中见大,精细不苟的绘画图式作为程式在日本曾风靡一时,而日本传统文化中优雅精致的审美意识正铺就了以秀丽精工、简洁洗练见长的南宋画风在日本勃兴的温床。通过以上的范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南宋绘画简洁的构图,以小见大,以少见多,以简代繁,以空代实,使单纯的画面充满生机,与日本民族空寂,闲寂、禅意等日本传统美学形态承袭融会,深深地影响着宋元时期日本水墨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维.山水诀[A].詹景凤.画苑补益[C].朱竹院藏.明抄本.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田中一松.水墨美术大系.普及版第五卷可翁.黙庵.明兆[M].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78.
[4]朱景玄,温肇桐.唐朝名画录[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
[5]郭熙,林泉高致[A].山水训见.詹景凤.画苑补益[C].朱竹院藏.明抄本.
[6]田中一松,米沢嘉圃.原色日本の美术第十一卷水墨画[M].东京:株式会社小学馆,1984.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ainting Schema on
Japanese Ink Painting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NG Lian
(Art and Design Institut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225009,Jiangsu,China)
Abstract:The change in painters’ observation angle from overall grasp to delicate detail, from far view to close look set the high-efficiency painting style that was deep, quiet and free.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mproved the composition techniques of Chinese painting as well as a new breakthrough. Besides,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the heyday of Zen. The introduction of Zen and Song culture made fashion of ink painting for some time in Japan. The intake of Japanese ink painting from the South Song Dynasty included the painting schema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he simple and vivid pattern of Chinese painting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ncounter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aesthetic form of emptiness, leisureliness and Zen, which had genera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ink painting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paint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Japanese ink painting
〔责任编辑:葛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