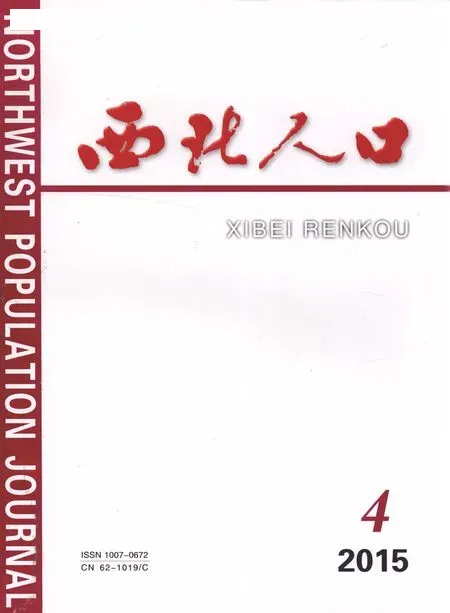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研究——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
丁 波,王 蓉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武汉430079)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研究
——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
丁波,王蓉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武汉430079)
农民工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群体的身份标识,他们对定居地的选择是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是对定居地是否适合自己的考量,同时也是对自身资源再认识的过程。本文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将农民工群体视为“理性人”,分析他们选择定居地的影响因素,并将这些影响因素划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进行研究性阐述,研究得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对定居地的选择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农民工;理性选择;城镇化;公共服务;
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群体,他们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2013年底全国农民工2.6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农民工对定居地选择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是基于外出农民工根据自身的综合情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笔者引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部分内容对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进行分析,阐述外出农民工选择定居地时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虑。
一、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相关文献回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对定居地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对城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关注已早,并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社会融入、农民工群体意识、农民工对城乡发展影响等方面,而对农民工定居地选择的研究则大多数采用实证调查的方式。夏怡然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异地打工、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影响较明显,而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1]。费喜敏、王成军首先运用推拉理论从理论上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然后利用河南省汝州市187个外出打工农民样本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得出农民工收入越高和年龄越小越倾向于在打工城市定居;外地人子女入学受歧视和老家经营的耕地面积大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打工城市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中心镇与对照组地级市或县城比较,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意愿会下降的结论[2]。黄庆玲、张广胜依据2012年辽宁省不同层级城市65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访谈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去向、原因及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男性、25岁以下者、已婚者、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者、在中小城市务工者、来自打工城市附近县城农村的打工者及来自东北3省外的务工者倾向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定居[3]。张笑秋、陆自荣视人口流动为“行为”,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包含迁移心理学的人口迁移理论为指导,采用“农民工流动调查”调研的数据,使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的因素[4]。叶鹏飞以多个省市区的调查数据为依托,对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定居地选择受市场、文化心理和制度三种因素影响,这其中,市场因素使起主导作用,但仍受制度因素的影响[5]。续田曾通过北京市的农民工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农民工选择是否在城市定居是一个根据教育水平的正向的自我选择过程,但是在个人能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另外,发现参与社会保险能够使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显著提高,而社会资本似乎并不会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造成影响[6]。
以上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地区外出农民工的调查资料而做的实证分析,研究外出农民工选择定居地时考虑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的大小。实证分析能够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时影响的各种因素,但较少用理论作为支撑来研究外出农民工选择定居地,而且缺乏用理论分析外出农民工选择定居地时的基本考量。本文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论视角研究外出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同时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等因素在外出农民工定居地选择的影响情况,并以理论反思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排以至于更好的服务于外出农民工进行定居地选择,最后以农民工定居地选择为突破点分析农民工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
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反思
本文认为农民工在对定居地的选择上是基于对自身条件和对定居地收益成本的综合考虑。农民工群体选择定居地的理性决策,他们首先需要考虑自身条件、家庭成员状况和自己的社会交往情况,其次是要考虑选择的定居地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或者是何以更好的让他们生活;从这样来看,农民工是属于社会中的“理性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理性行动、行动系统、理性行动层次、行动系统中权威与信任关系等方面构成。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与经济学结合对社会行动进行分析的理论,它曾引起社会学界极大的关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行动者在综合多种影响因素背景下,做出对自己价值最大化的行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是基于理性考量而产生的行动,这些行动一般都是以最小的成本付出作为获取更大价值的前提。科尔曼在阐述理性选择结构时,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由两个分析层次,一个是行动者的行动层次,一个是社会系统行动的层次。科尔曼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它由众多的社会行动者的理性行动组成;与此同时,这些社会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是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规范约束下进行理性行动,并获取效用的最大化,这便使单个的理性行动者建构成具有层次和体系的理性选择理论[7]。本文主要利用的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微观层面对外出农民工定居地选择进行分析,而相对较少涉及理性选择理论的系统层次方面。
(一)科尔曼眼中的理性行动
理性选择理论顾名思义是以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为起点,以社会行动者的理性行动为基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行动者有不同的选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价值和效用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者会进行理性的选择行动来达至这个目的。“经济人”是经济学对社会行动者进行理性行动的描述;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行动者的理性行动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除了考虑经济因素之外,还会考虑行动者的情感因素、文化因素和交往因素等等,这种理性行动是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焦点。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获得价值最大化”的理性行动假设,一是为了提高理论的观察水平,二是有利于保持理论的可塑性。这样一来就能够把经济学中的一些模型和分析方法运用到理性选择理论中去。科尔曼认为,以理性行动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尝试解释大部分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二)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
理性选择理论的行动系统不仅仅只有社会行动者,它还有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源”,这些资源是社会行动者行动的前提和条件,没有“资源”社会行动者将无法与其它社会行动者进行行动和交换。社会行动者通过控制自己或者他人的资源来实现自己所追求价值和效用的最大化。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资源”包括多个方面,“资源”可能是行动者的知识或者专长,也可能是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行动系统内容是,有多个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行动系统中活动,他们都是在进行理性的行动,目的是实现价值或者效用的最大化,同时,这些社会行动者拥有一定的资源和掌握使对方价值最大化的资源,社会行动者们进行一定的交换和理性行动,并相互支持和发展。科尔曼关注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实现期待的价值最大化或者帮助他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过程[8]。
(三)理性行动的层次
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行动在不同的场域中,所进行的理性行动亦是不一样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目的是追求对自己来说效用的最大化。而这个目的在不同的层次,就会有不同的理性行动。理性行动根据由低到高追求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理性行动[9]。三个层次的理性行动目标不同,生存理性是考虑自身以及身边行动者生存状况理性行动,经济理性是追求经济目地的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而社会理性是在追求前两种理性基础上更高的理性行动,社会理性是实现自身和社会满足的理性行动。
(四)行动系统理论中权威与信任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系统层次的系统行为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目的,而以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科尔曼通过研究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来描述系统层次的社会系统行为,以此来解决“微观到宏观的转变”问题[10]。科尔曼认为,社会行动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往往会将自己的某些资源和自身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他人,从而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威结构。同时,由于管理方便,权威的支配者会将其所能支配的一些资源委托给有一定经验的代理机构,由他们来管理和使用这些权威,因此,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简单关系就发展为三方及三方以上的复杂的行动关系,社会权威结构得以产生。信任关系也是由行动者转让某种资源开始的,但是它所转让的事物有所区别,信任关系强调行动者做决定时需要考虑一定的风险因素。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发展容易形成不同于社会行动者的代理机构,这种代理机构是为社会行动者的集体目的而得以存在的。同时,代理机构会将个体的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系统层次连接起来,使社会行动者的社会交换有了系统层次的意义,伴随着一系列交换规范的产生,社会系统得以建立和运行。
三、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及理性分析
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分为回老家和留在打工所在地,而回老家又可分为回到所在农村和回到所在城市。外出农民工选择回老家或者留在打工所在地都是根据对自身资源“理性”考量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外出农民工自身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定居地与家乡的距离、定居地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打工所在地的接纳和排斥情况等。这些影响因素有些属于生存理性,有些则属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一)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是农民定居地选择的根本原因
科尔曼认为,理性的社会行动者会按照有利于他们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的选择理性的行动,其中,他们考虑各方面不同的信息和条件,做出最佳的理性行动。外出农民工属于“理性人”,他们选出外出务工是为得到安全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们对选择定居地的基础是能够保持他们基本的生存和经济发展。因此,外出农民工对定居地的选择首要考虑的是其自身和家人的生存发展,其次,是考虑能够让自己得到一定经济发展[11]。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得出,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会首先考虑自身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等,这些影响因素使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最基本的条件,将会直接决定外出农民工是否留在打工所在地。年龄会影响农民工对定居地的选择,较多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到异地进行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可能选择回家定居。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外出农民工做出定居地选择的决策,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要多,这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给予他们较高的谋生手段,从而促使他们更可能选择到有竞争力和高生活质量并存的定居地去生活,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则可能会选择低竞争力的定居地。收入水平是农民工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外出农民工是否能够留在打工所在地或者其它城市。收入水平低的农民工最有可能选择回老家,他们的低收入水平无法支撑他们在打工所在地一直生活居住,而回老家是选择回所在农村还是城市则需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他们有能力留在打工所在地,同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到其它城市进行发展,高收入水平会给予他们多样的定居地选择机会,这时他们所考虑的不再是基础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而是追求更高水平的社会理性的满足,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已婚外出农民工相较于未婚外出农民工选择回老家定居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因为已婚外出农民工在定居地进行务工大多会将家庭整体迁移,而家庭迁移的成本会高于单身农民工迁移的成本,这导致已婚外出农民工选择回老家定居的预期成本将高于在务工所在地进行定居的预期成本。上述各种影响因素能够直接决定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它们是影响外出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因此,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是农民定居地选择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定居地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行动者在进行理性选择过程中,除了考虑社会交往和社会满足对自身的影响之外,社会行动者还会考虑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发展状况对人们的心理和理性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外出农民工在选择定居地时,他们会受到一些社会结构因素比如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情况、打工所在地的接纳和排斥情况、定居地公共服务供给等的影响与制约。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行动者都是拥有一定的资源,他们将其资源与别人进行交换,得到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又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行动者有时并不只是考虑利益后果,因为每个行动者都是社会人,所以他们还考虑一些感情因素等在进行理性选择的时候。
外出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除了考虑上述基本的影响因素外,它们还会考虑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之外的社会理性,如社会交往状况、打工所在地的接纳和排斥情况、定居地公共服务供给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是外出农民工必须所要考虑的,因为作为社会人除了基本的生活,还应有社会性的生活和心理的需要。社会交往状况间接影响着外出农民工对定居地的选择,通常以家人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农民工容易有确定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因为定居地的选择是需要和家人集体商议,而不是一人独自的决定,因此,和家人商量的结果将有助于这些农民工进行定居地选择。而平常与务工所在地的本地人交往越密切的外出农民工,他们则更越愿意定居在打工所在地。打工所在地的接纳与排斥则影响外出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打工所在地,在打工所在地感觉被接纳的外出农民工更愿意留在打工所在地,而在打工所在地受到歧视或排斥的外出农民工大多选择回老家或者去其它城市发展。这种内心的接纳与排斥对年轻农民工选择定居地表现的尤为突出,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接纳自己的定居地或者回老家。定居地是否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是外出农民工选择定居地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定居地如果能够提供均等的、全面的、优质的公共服务,它将吸引大量的外出农民工选择在此地定居生活。公共服务基本包括基础实施、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外出农民工能不能在定居地享受到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外出农民工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决定外出农民工是否能过上与定居地当地人一样的生活,特别是居家定居的农民工,他们会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外出农民工在定居地都能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那么户籍制度则显得不是非常重要。另外,也会加速我们国家城镇化的进程,推进更多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
(三)信任:农民工选择定居地的基础
农民工根据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考量来选择不同的定居地,这是农民工对不同定居地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信任定居地的过程。科尔曼认为,行动者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得不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控制权转让给他人。在做出转让控制权的选择时,行动者会考虑转让所包含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将会直接影响行动者是否对被转让者有信任关系。如果行动者对自己资源控制权的被转让者有信任的话,那么就会把自己的资源交给被转让者,从而形成转让者和被转让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一旦多个行动者将自己的资源控制权转让给同一被转让者,那么这个被转让者与这些转让者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威关系。由于为了让资源更好地利用和利益最大化,支配者往往把这些资源委托给代理机构,转让者、支配者与代理机构之间形成信任关系。农民工在选择定居地之前,会考虑定居地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所想要的生活以及影响他们选择定居地各种影响因素的大小,而一旦做出定居地决策时,表明农民工认可了定居地,并信任定居地所给自己带来的资源。农民工为了获得效益的最大化,把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带到所在定居地,这是基于在信任定居地的基础上。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部分内容,将农民工群体视为“理性人”,分析他们选择定居地的影响因素,并将这些影响因素划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农民工定居地的选择是在考虑自身综合资源和定居地的实际情况后做出的决策,这一选择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过程。研究发现,农民工选择定居地,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资源,它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等在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次是农民工考虑定居地是否适合自己和家庭生活,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交往情况以及能否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最后是定居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情况,定居地能否提供农民工所需求的公共服务是影响农民工选择定居地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关键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力在于农民工的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缩小城乡之间差距,推动农村向城市的发展,同时也体现着社会公平正义;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利用其在外地打工学习到的知识和经验以及资金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城市内部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定居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共服务,这能够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直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农民工进城补充城市发展的动力,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分析不仅是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深入的研究,更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民工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研究。
[1]夏怡然.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3):35-44.
[2]费喜敏,王成军.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4 (3):40-44.
[3]黄庆玲,张广胜.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意愿探析[J].调研世界,2013(7):29-33.
[4]张笑秋,陆自荣.行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人口,2013(5):108-112.
[5]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2011 (2):153-169.
[6]续田曾.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0 (3):120-128.
[7]谢舜,周鸿.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J].思想战线,2005(2):70-73.
[8]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430.
[9]祝平燕,晏华.“非诚勿扰”女嘉宾的择偶观分析——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1):17-64.
[10]周鸿.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简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3):101-104.
[11]刘军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4):77-82.
New Urb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grant Workers to Settle Down to Select the Will of the Study:Based on Colema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erspective
DING Bo,WANG 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Migrant worker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ur modernization drive to a group’s identity,their choice of settle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Migrants settled choice is whether to settle for their own reasons,is also a process of its own resources between.In this paper,in the perspective of Coleman’s rational choice theory,the migrant workers as a“rational man”,analysi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land they had settled,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are divided into existence rationality,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social rationality to carry on the investigative,study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as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 the choice is not only an individual behavior,it will also promote the equal basic public services,and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migrant workers;Rational choice;Urbanization;Public services;
F323.6
A
1007-0672(2015)04-0118-04
2015-01-27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倒城乡二元结构下微观社会基础重构”(14YJC840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11JBGP038)阶段性成果。
丁波,男,安徽铜陵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王蓉,女,山西长治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