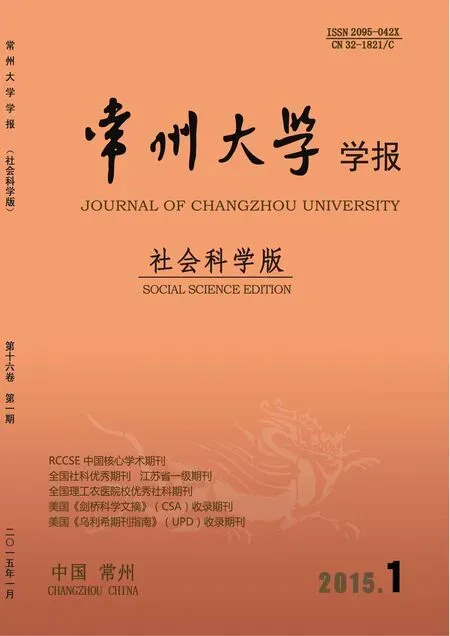汉语字母化现象的生态语言学解释
韩 燕
(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常州213164)
汉语字母化变异现象是指在汉语中夹杂外文或非汉字字符的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字母词,即“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1]字母词这种“异类”的面目迎合了人们力图求新、求变的心理,但也挤压了本民族语言独特的创造新词汇的能力。外来语言大规模涌入会对本民族语言造成一定冲击,引起群体语言的发展、变化、变异乃至语言规则系统和结构的变革,影响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因此,了解语言文字变化的动向并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就尤为迫切。
一、语言变异的生态学研究现状
国外方面,由语言接触造成的语言借用和变异现象一直是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从生态性角度通过生态学和语言学交叉形成的跨学科语言学研究范式对语言借用和演变现象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生态语言学观点强调语言是一种生态现象,具有生态性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生态规律。目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语言多样性及保护濒危语言问题,语言人权问题,语言的自由性问题。语言多样性观点主张语言权利及语言的多样性,尤其主张少数民族应保持其母语的独立性及活力,以芬兰社会语言学家Tove Skutnabb-Kangas为代表。语言多样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突显了保护濒危语言及“弱语言”的重要性。英国语言学家Crystal在《语言灭亡》一书中告诫人们:世界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中只有600种暂时还处在安全状态,至21世纪末,整个世界将被少数几种语言所统治。[2]语言人权问题的核心理念是“语言帝国主义”、“语言谋杀”以及维护语言人权,以丹麦学者Phillipson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英语的强势传播导致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产生。美国语言学家Wiley则指出西方国家在各种文化机构、技术、语言和文化实践中的优势地位造成英语与其他语种的等级关系和英语对其他语言实质上的不平等和剥削。[3]语言自由性问题以澳大利亚批评应用语言学家Alastair Pennycook和Blommaert及Christopher Stroud等语言自由派为代表,他们对语言人权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语言应被理解为一种自由流动的,依赖不同语境而充分调动的资源。
国内方面,李国正在20世纪80年代就尝试用生态学原理研究汉语问题,考察汉语语言系统各元素之间,各元素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之后范军俊和陈立中等进一步对语言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多种语言和谐共生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究,包括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生态语言学理论的探索、从语言生态危机入手对我国濒危语言问题和相关语言政策的探讨等等。此外,学者们也对全球化背景下汉语和外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辜正坤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英语目前已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第二语言,这造成了汉语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弱化,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及汉语进行保护并发扬光大,同时扩大对外传播。
综上,国外对语言演变的生态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英语对其他语言的影响上,而国内从生态学角度对汉语受英语的影响度研究比较少,对外来词的讨论也比较宏观,尚未触及汉语字母化倾向这一具体问题。
二、汉语字母化的生态语言理论背景
(一)语言进化与汉语字母化的合理性
语言进化规律是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施莱歇尔(Schleicher)1863年在其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提出的。在他看来,语言同世界上其他生物形式一样,也会经历从发展到衰亡的过程。语言的发展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以缓慢渐变的方式完成的。到了21世纪,美国社会语言学家Salikoko Mufwene教授从“生态学”视角更新了语言进化观。Mufwene把语言进化理解为个体间为适应交际策略、交际需要而产生的重构过程。这一过程与生物学中的遗传重组相似,在自然竞争和选择的作用下会产生与原先个体相异的变体。[4]88这些变异的产生适应了社会生活与交际需求的发展与变化,成为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汉语词汇也同样会通过新旧词汇的交替以及借用吸收外来词汇等形式实现语言的更新转化。每一个汉语词汇的发展和变异,对汉语的发展乃至整个汉语生态系统来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因此,汉语字母词作为汉语的一种变异形态,它的衍生过程,可以看作语言进化发展的过程,也是汉语本身不断发展进化的表现。
(二)语言生态环境与汉语字母化的变异性
生态语言学把语言视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主张从语言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相互依存和作用关系出发分析研究语言。如同生物为适应环境需要不断调节自身的结构功能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进化一样,语言的进化也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变异及重构过程来适应一定的生态环境。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语言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从外部环境来看,语言重构以语言接触为生态环境,该环境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语言演变的结果。从内部环境来看,语言的内部生态因素也可以相互作用从而推进语言的重组。[4]89-91汉语字母化的衍生变异实质是汉语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生态环境对汉语的改造,也是汉语内在语言结构及规律的发展变化推动的结果。
(三)语言生态保护与汉语字母化规范
生态学家将维护环境权益的公平性作为重要的生态伦理原则。[5]语言污染是目前语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为保持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语言在与社会同步的发展中会发挥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功能,调整各要素之间的协同进化从而保证语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一功能主要通过使用语言的人来实现。因此,要保持汉语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需要对汉语字母化进行规范引导。汉语字母化的规范原则可以参考以语言环境公平为核心的生态语言环境观:“提倡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合作原则,以消除言语交际双方的不公平;提倡利益平衡的双赢原则,以消除交际利益主体的不公平;提倡个体整体协调一致的原则,以消除语用个体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不公平;提倡当代人与后代人语用利益并重的原则,以消除跨代不公平。既要维护公平有序的语言交际环境,形成代内语言环境的公平,又要保证语言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代际之间语言环境的公平”。[6]
三、对汉语字母化的语言生态思考
(一)汉语字母化的生态性
语言的变异可以促进语言生态环境的生态化发展,因此语言变异有其生态性的一面。汉语对字母词的吸收并不是拿来主义,会根据字母词的使用背景和汉语自身的特点对字母词进行本土化改造。通过这种本土化改造,汉语丰富了自身的语言元素,实现了自然选择的替代,也同时改造了字母词的异质因素,使其更具有汉语特点,进而融合成为帮助汉语发展的新成长元素。汉语字母化的生态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多样化。汉语引入字母词促进了汉语语言的多样性。首先,新的音素和发音方式增加了汉语语音系统的多样性。以“IQ”和“三K党”为例,“IQ”中的“Q”读[kiu]。[kiu]这个音节是汉语中没有的,突破了普通话声韵配合中的“舌根音g、k、h不能跟i或i起头的齐齿呼韵母拼合”的规律。“三K党”中的K读[kei]。该音节在普通话声韵配合表中也同样是找不到的。[7]79其次,外文字母和汉字共存的现象增加了汉语词形构成的多样性。第三,新的表达方式增加了汉语词义表达的多样性。比如我们今天用来联通世界各个角落的网络既可以用“互联网”来表示,也可以用“internet”来称呼。
2.自然选择。汉语在吸收使用字母词的过程中会根据汉语自身发展规律和语言环境对字母词的成分进行自然选择使其适应汉语的语言系统,主要表现在两种替代改变上。第一种是语音替代,即用汉语的音位替代外语语音。汉语在音译外来词时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的汉语音位,就会用相近的汉语音位改造外语词的读音。[8]比如“VCD”中的“V”在汉语中经常会被读成[wi:]而不是[vi:],因为汉语普通话语音中没有辅音[v],所以就用相近的[w]音代替。此外,汉语声调的加入以及外来词重音的消失也是一种语音替代。第二种是词义替代,即对字母词的词义进行增删或变更其附加的语义色彩。一些字母词进入汉语后,虽然其语言形式得以保留,但为了适应汉语的表达需要,词义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英文字母“N”只在数学上表示“不定的”或“无穷尽”的含义。但进入汉语后,该特定含义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应用中,并成为年轻人的流行口头语,强调“很多”的概念,像“今天的作业N多”、“我有N个想法”等。
3.协同进化。汉语对字母词的融合使得字母词直接参与到汉语语法中,并呈现语素化倾向,实现与汉语本土语素的共生互利、协同进化。例如,表示“金融中心”的词“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人们把住在CBD作为自己的梦想。于是就有了“CBD后花园”、“CBD后院”、“CBD卧室”等词语。在这些词中,“CBD”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构词语素。
(二)汉语字母化的非生态性
语言变异如果发生在不同语系之间,互相共生发展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由于汉字与字母文字不同的构造体系,汉字与字母混用的情况如果长期处于没有规范的状态下,汉语语言体系就会出现失衡的状态。目前汉语在使用字母词时表现出来的非生态性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缺乏规范统一性。首先,目前汉语中的字母化现象比较混乱,既有汉语拼音,又有英文字母。虽然汉语拼音也是借用了拉丁字母的形式,但主要作用是辅助汉语学习。其发音与拼写结构与英语字母完全不同。目前这种混杂使用的状况使得字母化现象变得更为复杂。以新闻传播媒体为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周报》等报纸的报头都是采用汉字加汉语拼音拼写的方式;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环球时报》等报纸的报头则采用汉字加英语翻译的方式。虽然都是字母,但汉语拼音和英语分属于两种语言体系,这样很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此外,各种大型考试名称的字母略写也比较混乱,以“CET”和“HSK”为例子。“CET”是英语“College English Test”的首字母略写,代表的是大型全国性英语考试“全国大学英语考试”。而“HSK”则是“汉语水平考试”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略写。有意思的是,用英文缩写表示的CET考试对象是国内普通高校的中国学生。而用汉语拼音缩写的HSK考试对象是外国汉语学习者。对于这种全国性的大型考试,命名上本应该比较统一。但目前两种南辕北辙的命名方式却着实让人有些看不懂。
其次,汉语字母词的读音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呈现出随意性和混乱性。例如在“CT”一词中,字母“C”的读音就有好几种,包括英语读音[si:]、汉语注音[xi:]、京音[sei]等[7]77。而对于像“RMB”这样由汉语拼音缩略而成的字母词读法也各异,有人按英文字母读,也有人直接用汉语读成“人民币”。面对字母词的读音规范,学术界争论不断。有人主张用汉语拼音给字母词注音,以使字母词真正进入汉语词汇系统。[7]80也有人主张既然汉语字母词主要由英文字母构成,还是应该按照英文字母音来读,而对来自汉语的字母词则作区别对待。[9]
2.缺乏控制度。当前字母词的使用有泛滥的趋势。许多文艺作品,甚至是新闻报道中都夹杂着大量字母词,一般以缩略词居多,且往往没有汉字注释,给读者阅读造成困难。比如“ICU(重症监护室)”、“OEM(原始设备制造商)”、“TMD(战略导弹防御系统)”、“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词,如果不附加注释,一般人很难理解其含义。再比如下面这段新闻报道:“预计2011年以后,蓝光BD光盘的销售额将超过DVD,成为新的增长点。蓝光BD企业连续推出DVD所没有的、消费者一见就想用的新功能,如BD-JAVA,BD-Live,3D等,将实现市场向蓝光的快速推移。”[10]这段文字中,字母词几乎占到了整段文字的一半,给读者的阅读带来极大困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互联通讯的广泛使用,网络语言中使用的字母词泛滥趋势更为明显。因为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及丰富性,网络语言往往具有简单经济且标新立异的特点。字母词正符合这些特点。因此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很多极不规范或表意不明确的字母词,如ZT(转帖:转载别人的文章)、GG(哥哥:男朋友)、BS(鄙视)、I服了U(我服了你)、3Q(thank you:谢谢)、IOU(I love you:我爱你)等。这些字母词虽有一定的便捷性和趣味性,但有些造词随意、表意晦涩,如果渗入到书面语中,会给汉语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隐患。此外,网络语言中还会使用字母词表示一些低级趣味或带有色情意义的内容来逃避监管,比如TMD(他妈的)、KF(开房)等。这种字母词的泛滥更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3.缺乏稳定性。作为汉语中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字母词既会受到汉语本身的语言规范和发展的影响,也会受到后来新词汇的冲击。因此,汉语中的字母词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更新换代较快。对第5版和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比较统计后可以发现,第6版比第5版总收录字母词数量增加了60条,删减了3条。具体为:通信科技类删除2条,增加20条;政治经济类增加19条;文体生活类,增加15条;教育图书类,增加4条,删除1条;生物医药类,增加2条;军事类,无变化。[11]可见,字母词的的引入和使用范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当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时,它的使用寿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收录的新词“EPT”(“出国进修人员英语水平考试”)到第六版就被“PETS”(“全国公共英语登记考试”)所取代了。再比如像“BP机”(“无线寻呼机”)在八九十年代曾大出风头,风行全国。如今随着手机的普及,除了个别专业领域,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2007年3月22日中国联通正式关闭30个省区的寻呼业务,标志着寻呼业正式退出舞台。《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修订虽然仍保留了这一词汇,但这个词的实际使用已经越来越少,特别对年轻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
此外,一些在网络中创造出来的新字母词,或由于失去流行性,或由于造词牵强、晦涩难懂,也很快被淘汰或者发生词义转移。因此,字母词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后续更多新词的涌入,会有更多的字母词被淘汰。
四、结语
字母词的出现及使用给汉语语言系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虽然汉语需要吸收外来先进元素来充实自身并不断发展,汉语字母化的吸收也符合汉语言文化包容性的和开放性的特点,但如果对这一现象放任自流,可能会导致语言发展的失控,引起群体语言的变异乃至语言规则系统和结构的变革,影响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但是,短期内完全杜绝字母词的使用既违背了语言自然发展的法则又不符合语言发展变化渐进的规律。因此,掌握好一个适当的度,给予字母词的使用规范性的引导非常重要。《第一批推荐使用外语词中文译名表》(共10组外语词及其中文译名),已经于2013年9月13日由外语中文译写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推荐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用规范的外语词中文译名。该专家委员会将分别发布第二批、第三批《推荐使用外语词中文译名表》。希望这能成为汉语字母化有序、规范、生态化管理的良好开端。
[1]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2(1):85-90.
[2]Crystal D.Language Deat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98.
[3]李建华,钟玲,叶湘.语言的文化接触及其后果:基于汉语与外语关系调查问卷的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41-150.
[4]陈治安,马军军.《语言进化生态学》评述[J].当代语言学,2004(1):88-92.
[5]黄知常,舒解生.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68-72.
[6]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60.
[7]贾宝书.关于给字母词注音问题的一点思考与尝试[J].语言文字应用,2000(3):79-80.
[8]李彦洁.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72-73.
[9]沈孟璎.浅议字母词的入典问题[J].辞书研究,2001(1):30-38.
[10]孙寿山.莫让字母词扰乱汉语语言环境[J].新华文摘,2010(21):146-147.
[11]韩燕.字母词的现状及未来:基于第5版和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比较研究[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2):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