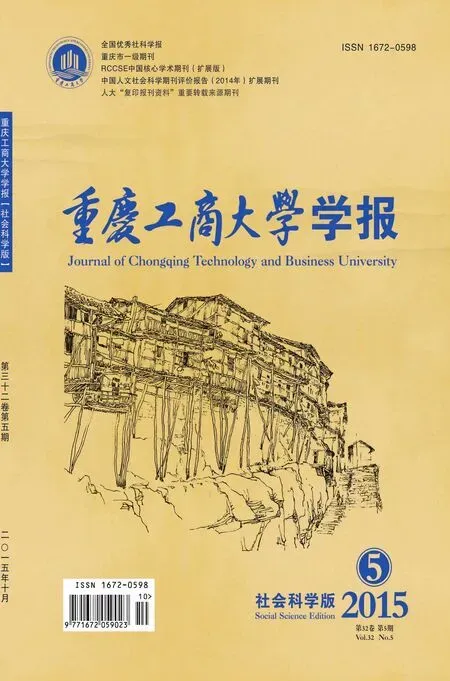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情结书写*
袁玲丽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230009)
朱光潜生于清末皖西南桐城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自幼便对语言文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六岁进入父亲的私塾,十六岁时考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时考取了香港大学,由此告别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皖西南天地。故乡桐城的田园山地和风土人情构建了童年、青少年时期朱光潜对于世界最初的直观认知,而这些成长经历、记忆中的印象与认知感受,又在岁月的洗练中逐渐沉淀,转化成一个个典型的形象和意象,成为他一生创作时取之不尽的素材库。细读朱光潜的诸多说理文,不难从中发现频频出现的乡土人情、乡村风俗和田园风景书写,这些凝聚了朱光潜故土情结的乡村田园场景和意象,在参与说理的同时,也展示了一幅清末民初皖西南山村民居的传统风貌,营造出了一种质朴氤氲的自然气息。
一、皖西南乡土人情
戴·赫·劳伦斯说过:“每一大洲都有它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吸引力——随你怎么叫它都行。然而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1]20世纪初的皖西南山村依然是传统的男耕女织乡村生活,在童年朱光潜的眼里,最勤苦耐劳的当属一年到头耕种在土地上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寒来暑往,从不得歇。家中的男孩,尤其是长子往往被寄予厚望,犹如每年预留的稻种一般珍贵。男人们在外辛劳耕种时,女人们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闲暇时纺织绣花。女子的针线盒是家庭的必备品,里面的针头线脑缝补起农家人生活的艰辛,而点缀于其中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则是平淡生活中一抹亮丽的色彩,衬托出农家女子的心灵手巧,也寄托着青年女子对未来的憧憬。这家中凝聚着温情和希望的针线盒,曾给幼年的朱光潜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乡下姑娘难得能有一件漂亮衣裳,压在箱底,一般是舍不得穿的。朱光潜在提到自己住在北京时情愿去后门大街而不去北海时比喻道:“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的一件漂亮衣,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2]65这件漂亮的衣裳在姑娘时还是可以偶尔穿出去应场的,然而,一旦嫁为人妇为人母,这当年曾被无限遐想过的衣裳则只能压在箱底,成为一份成长的怅惘见证了,这种心情恰如创作者多年后翻看自己最初的作品。
乡土社会地域空间明确,人员结构相对稳定,乡村农事生活单纯,在乡情的维系下,人们共同遵循业已成为传统的礼仪和秩序,相互恪守本分,彼此耳熟能详,“这是一个都‘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3]。熟悉是从长时间多方面接触的过程中培养出的一种亲密感觉,恰如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生词,朱光潜写道:“对付生词就象对付陌生人的面貌,你碰见一个陌生人,下定决心要把他记住,盯着他看一天两天不放,就能把他记住吗?他是一个活人,你要记住他,就得熟悉他的生活,看他怎样工作,怎样聊天,怎样笑,怎样穿衣吃饭,如此等等,久而久之,你就自然而然地熟悉他,知道怎样去应付他了。”[4]14乡村又是个封闭的小社会,乡里乡亲沾亲带故,一个新人要想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必须要尽快攀亲结友,在朱光潜看来,新知识的学习如同是走进一个乡村的新客,村里的熟人越多,牵涉面越广,他融入的可能性就越大,他的地位也就越稳固。相反,如果他进村之后,不能同任何人发生关系,他就变成众人眼里戒备提防的陌生人,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更无法发挥他的能力或者有所作为。只有攀亲结友,彼此交往,产生联系,相识相知,才能共同构筑一个融会贯通的知识网络。
二、皖西南乡村风俗
朱光潜家附近有个集市,每逢年节,附近几个县的农民、小商贩等都聚集到这里来买卖物品,赶集市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件热闹事。朱光潜在谈到人生会面临种种选择时比喻道:“人投生在这个世界里如入珠宝市,有任意采取的自由,但是货色无穷,担负的力量不过百斤。有人挑去瓦砾,有人挑去钢铁,也有人挑去珠玉,这就看他们的价值意识如何。”[5]222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集市上出现的各种人也是朱光潜观察的对象:有暴发户,处处以多为贵,时时不忘装点门面,借此机会来炫耀自己的家私;有商人,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本以为富足,一夜之后,满集市人都喧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惶恐、忐忑而又心有不甘;也有明明是一个穷人,却要摆出富贵架子,滑稽可笑中又透着一丝可爱,这形形色色的赶集众乡亲。
除了赶集,乡村生活中另一件乐事要数看戏了。作为黄梅戏的故乡,清末民初的桐城活跃着大批黄梅戏戏班。一到农闲时节,便有各个戏班在桐城山村巡回表演。有演员坐在村民家堂屋板凳上清唱的“抵板凳头子戏”,也有在农村乡场表演的“围子戏”,在一块地势略高的平坦场地上,表演者载歌载舞,村民们围在四周观看,演员下场后也站到台下观众中去,你方唱罢我登场,非常热闹。从最初搭在村头简陋的“门板台”戏,到后来走向城市的“新舞台”戏,演戏与看戏的场面、演员与观众各自投入的神态曾深深印入少年朱光潜的脑海:人生就是一部戏剧,既要有人演,也要有人看,演戏与看戏是两种基本的人生态度。
朱光潜自小便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他的父亲和伯父在家门口无意中挖出两个瓦瓶,兄弟俩对着瓶子研究了很久,后来又切磋了一整天,作了一篇“古文”记,贴在瓶子上。父辈们运用文字时的字斟句酌与严肃郑重,使得少年朱光潜对于文字产生了一种神秘意识,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自如地掌握语言的魔力。这个桐城少年模仿能力很强,在他看来学古文别无奥秘,只要熟读范作多篇,头脑里甚至筋肉里都会浸润下那一套架子,下笔时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扶乩手,扶乩是曾在中国民间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一种古老占卜术。积累了十几年文言文家底的朱光潜一度在古文世界里游刃有余,然而,不久之后的白话文运动却令他产生了切肤之痛,仿佛一夜之间持有货币贬值即将破产。而当他终究接受并逐渐运用白话文自如创作时,最初的紧张与担心也在发生着改变:“最初好比放小脚,裹布虽扯开,走起路来终有些不自在;后来小脚逐渐变成天足,用小脚曾走过路,改用天足特别显得轻快,发现从前小脚走路的训练工夫,也并不算完全白费。”[6]114裹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一个陋习,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依然普遍。裹脚布因其对人性的摧残而终究会被扯开,文言文也因其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表达需要而终将被白话文取代。在朱光潜看来,文言文与白话文并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白话文是从文言文演变而来的,“我们如果硬要把文言奉为天尊,白话看成大逆不道,那就无异于替母亲立贞节牌坊,斥她的儿子为私生子,不让他上家谱。”[6]243上家谱是乡村社会认祖归宗的一种仪式,立贞节牌坊则是对女子在丈夫死后贞节行为的一种表彰。
三、皖西南田园风景
田园山川,清风明月,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乃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不同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不同的山川河流也就孕育出了不同的人文和地理文化。位于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的桐城,山地、丘陵与河道交织密布。少年朱光潜曾经为了求学,每日早晚数小时行走在这皖西南的山水田园间。不上学时他曾在村头池塘钓鱼,瞪半天也看不见浮标幌影子,偶然钓起一只寸长小鱼,虽不能满足一咽,却也要快乐半天。蓝天碧水,浮光掠影,蜜蜂采蜜,蚂蚁搬家,自然界四时更替中的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在朱光潜的眼里都是有趣的,充满生机的,流淌在多年后回忆时的笔端。
在谈论人生时,朱光潜写道:“人好比一棵花草,要根茎枝叶花实都得到平均的和谐的发展,才长得繁茂有生气”[5]228。人的情感思想就好比是花草的生机,生来就需要足够的空间宣泄生长,需要自由的园地与丰富的滋养,才能最终发芽开花。如果用沉重的砖石压着它们,仿佛墙角生出来的草木,得不到阳光与空气,便容易变得黄瘦萎谢,即便偶尔能破石而出,也会失去自然的形态。人生经历好比是土壤,文艺则是这上面开出的花朵,见证人生的春华秋实,又反过来滋养着心灵和思想,使人们的各种情感得到生长,如同草木在阳光下蓬勃多姿。人生离不开文艺的滋养,当人们的性情怡养在文艺的甘泉中时,便可以脱去尘世的辛劳,得到片刻的精神解放,这种感觉如同是在清泉里洗一个澡,或者是绿树荫下歇一会儿凉。人生是可以艺术化的,不计较、少抱怨,“如草木在和风丽日中开着花叶,在严霜中枯谢,如流水行云自在运行无碍,如‘鱼相与忘于江湖’”。[2]126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时,整个宇宙便成了一曲融会贯通的交响乐。
文学创作也是朱光潜频繁谈论的话题。在朱光潜看来,文学是人生土壤上缔结的花朵,创作者的潜能有如一颗种子,为了能发芽、开花、结果,创作者需要辛勤耕耘,他需要读各家书,博取众家之长,“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7]244他得甘于守住那份等待的寂寞:“蜗牛的触须,本来藏在硬壳里,他偶然伸出去探看世界,碰上了硬辣的刺激,仍然缩回到硬壳里,谁知道它在硬壳里的寂寞?”[6]16他需要培养趣味,趣味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流动的水才不会腐化,趣味的培养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6]25他需要对周遭保持敏感,普通人的心灵可能受到强烈地震撼才会产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6]148不仅如此,他还要能在沉静中沉淀下这种感悟,并用恰当的语言准确地描述,普通人的情绪常如暴雨后的河床,夹杂着污泥和朽木奔腾,来势汹汹,去无踪影,“诗人的情绪好比冬潭积水,渣滓沉淀净尽,清莹澄澈,天光云影,灿然耀目。”[6]38这一番等待、耕耘、滋养、呵护、静候之后盛开的文艺之花,璀璨绚烂,流畅自然,读起来令人身心愉悦,浑身筋肉也仿佛是在奏乐、在泛舟。而那些音调节奏上有毛病的文章,读后“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6]221皖西南农村做饭以秸秆和柴木为燃料,十天半月下来,灶膛中的锅身会沾满厚厚的秸秆和柴火灰,需要将锅端到外面倒扣在空地上,拿铲子贴着锅身,顺着顶点的锅底向贴地一圈的锅沿刮锅灰,一铲子下去,一堆烟灰随之滚滚落入地面,一圈刮下来,地面便是一个烟灰画出的深浅不一的圆。在孩子的眼里,尽管这声音很刺耳,场景却煞是壮观有趣,声音与画面的融合,定格为少年记忆里有关故乡的温馨场面。
四、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情结
在朱光潜诸多的说理文中,不难发现那些经常情不自禁出现的乡土情结书写:种子发芽,蜗牛伸触须,农民撒稻种,姑娘拣丝线绣花;草木芬芳,蜜蜂采蜜,农闲去看戏,女子翻看箱底衣;流水行云,蛛丝轻弹,厨子刮锅烟,少年垂钓池塘边;还有那热闹的赶集、神秘的扶乩、松开的裹脚布和肃立风中的贞节牌坊,出现在朱光潜说理文中的这众多乡土情结书写,汇聚起来可以还原出一幅三维的皖西南山居图。这些乡村风景与风俗人情见证了一个桐城少年的成长求知岁月,又透过少年的一双眼睛沉淀积累,打包进记忆的行囊,伴随他行走天涯。不仅如此,多年后,当它们再次经过记忆的加工从笔端不经意间流出时,它们早已生根发芽,出落得一副新模样,也担负起了新使命。
成年后的朱光潜为了梦想离家前往城市,他先是在武汉待了一年,后来在香港学习生活了五年,毕业到上海任教两年后考取官费留学欧洲,辗转爱丁堡、伦敦、巴黎等地求学八年,获得文学博士后受聘于北京大学,除了因抗战被迫离京,余生一直定居在北京。李欧梵在谈到中国现代作家早期生活时分析道:“离家入读大城市的新学校,代表了最早的双重解放:首先是从传统社会的自然环境中解放出来;其次是从传统道德标准与社会习俗整套礼仪体系中解放出来。”[8]走出乡村小天地、一步步奔向大城市的朱光潜是满心喜悦的,这种感觉在他读惯中文后初学英文时也曾有过,然而,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轨迹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中,铸造了他的生活习惯、认知方式乃至价值取向,身体的解放却难以改变心理的思维定式。多年后,当朱光潜回忆起在武汉的一年岁月时,最难忘的只有洪山的紫菜薹、蛇山的梅花和江边的书店。香港大学的生活是相当有趣的,足球、网球、辩论赛,他连看的兴致都没有;全校仅有的两个女生和他是同班,他却从没有将她们当作女子看待;这个别人眼里寒酸的“北京学生”最喜欢的事情是和另外两个“哲人”在午后顺着小路爬到学校后面的山顶,呼吸清新的海风,眺望远处岛屿上青葱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房屋,疲倦后再顺着另一条小路返回学校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从欧洲回国住在北京慈慧殿三号时,他在院子里挖了一片地,种几棵芍药,栽几株丝瓜、玉蜀黍和西红柿,淹没在自生自长的杂草丛中也不去管它们;为了赶走清晨惊扰他香甜美梦的老鸹,他竟然去买了弹弓去射它,后来弓子坏了只好作罢;看门老太婆捧着长烟杆、闭着眼睛听车夫讲故事,虽无瓜架豆棚,却俨然是一幅移植到城里的乡村太平岁月图画。
武汉、香港、上海、伦敦、巴黎、北京、成都,成年朱光潜在都市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目之所及、挥之不去的依然是那和乡土沾边的记忆里的乡村图画。即便是小时候曾觉得单调无味、每天早晚都看到的乡下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多年后回忆起来也令他无限留恋。这浓郁的乡土情结,如同故乡给游子下的蛊,早已深入他的骨髓中,占据了他的记忆空间,自然会频繁显现于他说理设喻的笔端。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9],在一个人所有的心灵现象之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他的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是他随身携带,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境的意义的载体”,他的记忆也绝不会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从他毕生接受到的、多得数不清的印象中选取出来记忆的内容,“肯定是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极具重要性的事件。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那山、那水、那人,还有那记忆里的童年,那些熟悉亲切的生活经历,纵然离乡千万里,总在游子的心头萦绕,在不经意间想起,浮现于朱光潜创作时的思维瞬间。
出现在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风景与民俗风情,是记忆中故土和家园情结的自然再现,不仅是成年朱光潜离开山村奔赴城市生活的必然,也是他的文学和美学旨趣的间接书写。作为京派文学的领军人物[10],朱光潜和沈从文、废名、凌叔华等京派作家一样,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推崇文学和美学思想的静穆境界、距离感和移情学说。周作人曾经说过,人是“地之子”,不能离地生活,要忠实于脚下这块地:“……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11]静穆于脚下的土地和江上的青山是一切生灵的慈母,泯化一切忧喜,亲切宁静,守护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于是,说理设喻语言中的泥土和自然气息也是朱光潜的文艺主张。不仅如此,在朱光潜的眼里,宇宙间的许多真谛往往都寄寓在一些极其平常细微的事物中,稍不留神便会被忽略,只有像日神阿波罗一般,才能静观诸生,既能察觉其中的哲理,又能领略到一种置身事外的永恒之美:“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5]62这样一种静观默察的态度,使得他能处处发现乐趣、吸收生机,时时触机生悟,如同“地行仙”一般怡然豁达。万物皆自得,那记忆里纷扰的众乡亲、静穆的山川树木,在他的眼里都成了自然图画,都是小说,都是他信手拈来设喻说理的绝妙素材。
五、结语
“童年记忆的乡土是一片毫无异己感、威胁感的令人心神宁适的土地,也是人类不懈地寻找的那片土地。”[12]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田园山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成年朱光潜非常重要。曾经的生活故事,凝聚了浓郁的乡土情结和家园情感,因而自然会频频出现于他创作的瞬间。出现于说理文中的乡土情结书写是作家潜意识中存储意象在说理瞬间的智慧火花,是事与理相通时的灵光闪现,因其隐蔽,更加率真,一旦生成,弥足珍贵。当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学者成为背井离乡的游子时,故土和家园便成为他游走城市的随行行囊。恣意文字、畅谈美和人生的背后,难以掩饰的是他对故乡山水和淳朴自然生活方式的深深眷恋,回归的冲动也就成了诉说不尽的话语。不仅如此,童年记忆在作家的心里形成了一座来往自由的桥梁,连接过去和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频繁辛苦地拜访童年生活,“只是想探索一条捷径,直抵现实生活的核心”。[13]借助一双慧眼,存身文字中,这份沉重的故土情结和家园意识寻得了暂时归属;凭着作家的笔,定格文学中,清末民初皖西南山村风土人情的一个剪影得以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保存。它不仅是朱光潜一个人的心理情结,也是深植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存在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之中的一种情结,这种情结“不仅与自己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在一起”。[14]于是,在设喻说理的彼时和解喻感悟的此时,个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中实现了双重交汇,作者和读者都得以跨越时空抵达各自的视觉和心灵家园。
[1]戴·赫·劳伦斯.乡土精神[M]∥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30.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10)[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
[4]刘世沐.怎样学英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14.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1)[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6)[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5)[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52.
[9]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曹晚红,魏雪萍,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58.
[10]文学武.朱光潜与京派文学[J].浙江学刊,2012(2):79-85.
[11]周作人.地方与文艺[M]∥自己的园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6-127.
[12]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21.
[13]苏童.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J].中国比较文学,2012(4):96.
[14]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