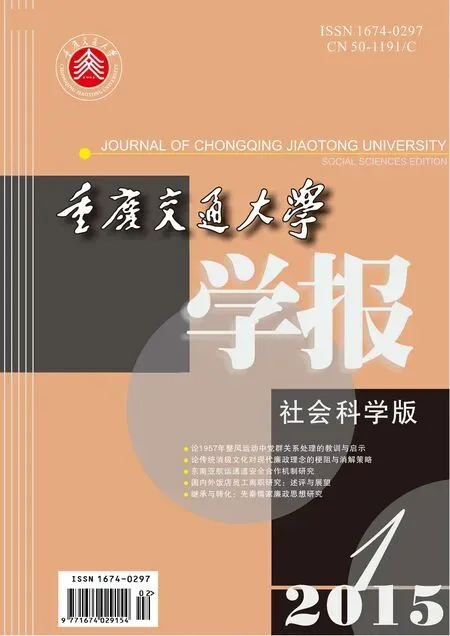日常生活的奇趣化表现
——论《天地》杂志散文的话语特色
满 建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日常生活的奇趣化表现
——论《天地》杂志散文的话语特色
满 建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下,《天地》杂志适应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所刊登的散文关注饮食男女等主题,发掘日常生活意义,肯定日常生活价值,并通过引用、拼贴、陌生化、庄谐并出、雅俗对照等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表现,营造出奇特有趣的话语风格,形成了特殊语境下现代都市的独特话语。
《天地》; 散文; 日常话语; 奇趣
20世纪40年代,上海市民社会渐趋成熟,现代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使得文学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沦陷区的动荡局势使得朝不保夕的市民失去了崇高感和悲剧感,淡化了诗意的追求,无力关心宏大主题,转而去追求“一刹那的安慰与排遣”[1]458,从日常生活领域品味生命的意义,表现日常生活、传达市民趣味的散文受到文化市场的欢迎。《天地》散文以关注饮食男女主题为主,表现日常生存状况,肯定日常生活价值,使得日常生活成为独立表现对象,成为特殊语境下现代都市的日常话语。
一、“以常人地位说常人话”:写作姿态的日常生活化
考察《天地》散文的话语方式离不开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一方面,在日伪严酷政治迫害和舆论控制下,作家无法在宏大主题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有龟缩到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战时经济政策带来的严峻压力使作家为了谋生需要放低姿态,关注日常生活,根据读者市场需要进行商业化写作。此外,主编苏青的女性性别也影响到了《天地》散文的话语姿态。
如果说上海“孤岛”时期进步文化人还可以利用租界的中立状态表达自己的呼声的话,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后,这种有限的言论权也失去了。日军采取极端恐怖的手段,加紧搜捕和杀害抗日文化界人士,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命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据统计,仅1939—1941年间,上海就有20名进步记者被暗杀,日军把砍断的手或手指寄到报社,将被害者的头颅挂在路灯下示众或扔到路边的排水沟里[2]。这种残暴的行为使得沦陷区的文人完全失去了表达政治诉求的可能。为了生存,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无奈选择。
上海沦陷后,日军和汪伪政权实行了战时经济控制政策,还对市民实行计口授粮配给办法,又强行征购米粮以供应战争需要,导致上海物资紧张,物价飞涨,市民经常食不果腹[3]。苏青慨叹难以生活下去:“米卖四万多元一石,煤球八万左右一吨,油盐小菜件件都贵,就说我一个人吧,带着三个孩子,外加女佣之类,每月至少也得花去十几万元钱,做衣服生病等项费用,还不在内。至于我的收入呢?办杂志不亏本已经够开心了,赚钱简直休想……然则——如何生活下去呢?我是只好希望:‘船到桥头自然直。’”[4]在此情境下,作家不坐以待毙,就要按照商业化的模式来进行写作。上海的文化消费市场经过开埠以后长时间的孕育以及30年代的极度繁荣后,40年代已经比较成熟,不断成长起来的市民读者在日伪高压统治下,需要有一定趣味的文学作品来满足其日常文化消费需要,为沦陷区作家的商业化写作准备了条件。在谈到写文章的目的时,苏青说:“但是心里还难过的很:因为那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而是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呀”[1]432。功利化的写作目的势必让作家放下精英姿态,不谈高深哲理,不抒圣贤性情,认同日常生活的价值。
《天地》散文作者的日常写作姿态还与主编苏青的性别有密切的关系。在苏青看来,女性对于日常生活更为关注。以看报为例,男人多为了虚荣了解国家大事,因此好读社评,而女人“爱看什么看什么,只拣与自己日常生活切身有关的记牢,卫生酱油,先施牙膏,这些广告在她们看来也许比李维诺夫辞职消息更为重要”[1]385。创办《天地》前,苏青经常向《古今》投稿。这个杂志是以男性作者为主的严肃杂志,文化格调较为古雅。苏青以女性作者的身份把日常琐事、饮食男女话题引入《古今》,使得《古今》添了几分烟火气息。《古今》的写作实践凸显了女性身份之于日常生活的意义,坚定了苏青在《天地》上提倡女子写作和关注日常生活的决心。她在《天地》上提倡女子写作的理由有写作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影响女子家庭工作、女子爱道东家长西家短等等,都是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的。
在《〈天地〉发刊词》中,苏青写道:“编者原是不学无术之人,初不知高深哲理为何物,亦不知圣贤性情为何如也,故只求大家以常人地位说常人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之不厌”[5]。这样就把话题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从而得到读者的认同。在苏青看来,《天地》的作者不限于文人,写作并不应该成为文人阶级的特权,各个阶级都可以有文人存在,才能产生出好作品来,因此她指出《天地》的执笔者可以是农工商学官,也可以是农工商学官太太。这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了写作姿态日常生活化的重要意义。显然,作者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本身。文人和普通人的身份差别消失了,纯文艺作品和一般文章的界限消失了,只要是表现无处不在有价值的日常生活,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好作品出现。
苏青的这种写作态度通过主编《天地》杂志变成了对作者的要求。《天地》散文作者大都模糊自己的作家身份,予且说“社会之大,谁都是文人,谁都不是文人。我终年转换的拿这红蓝黑白四色的笔,也不是文人”[6]。在《天地》上发表过数篇幽默散文的正人说:“不佞份属男性,自非例外,惭愧之余,所愿声明者,不佞所写全是游戏文章,兴到为之,用以娱人娱己。余之作品,绝非文学,不佞本身,更非作家也。”[7]作家在放低写作姿态的同时,将日常生活本身置于最为重要的地位。纪果庵这样来认识自己的写作:“唯生活到底是生活,我不会作诗,不会作小说,尤无天才,而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低能人,因此代表老实人讲一些不中听的老实话。若是说这种文章太无味,也不绚烂,那则我之该死也。”[8]认识到日常生活的作用,认为其中蕴含着味道和绚烂的色彩,正是把日常审美化,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那样:“艺术无所不在。所以说艺术死了,不仅仅是因为对艺术卓越超凡的批评已经消逝,而且还是因为现实本身已完全为一种与自己的结构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现实已经与它的影像混淆在一起了”[9]。
就常理来说,杂志的发刊词置于创刊号最显赫的位置,说明该杂志的宗旨、性质及意义,具有宣传导引作用。但是在予且笔下,《〈天地〉发刊词》却充满了现实功能意义[10],这就消解了该杂志的神圣意义,使之成为满足办刊者需要的物质载体。对苏青、予且这些作家而言,无论是办杂志还是写文章,都出自现实功利需要,这种需要是合理的,因而无须摆出架子,突出其崇高意义。这种姿态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大异其趣,与30年代京派散文追求的高雅精神趣味也不合拍,更近于《论语》《宇宙风》等林氏刊物的理想,正是日常思维制约下的行为。
二、“人情总应该是差不多的”:日常生活的呈现方式
“布达佩斯派”美学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认为,人类日常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人类生活的可变部分,另一部分是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不变部分,它 “包含了所有活着的人所必须共享、所有死去的人所曾经共享以及所有未出生的人所必将共享的一切东西”[11]。苏青在《〈天地〉发刊词》中谈到:“我以为在天地之间做一个人,人事或有不同,人情总应该差不多的。”[5]《天地》散文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就是日常生活中相对永恒的“差不多”的永恒不变的部分。苏青从自身熟悉的日常生活出发来写作散文,并有意识地将这种写作倾向在《天地》上推行。该刊21期所刊登的217篇文章,大多数围绕市民生活中衣、食、住、行、恋爱、结婚、生育等日常话题展开,其中第7-8期的“生育特辑”和第20期的“衣食住特辑”两个特辑集中体现了这种倾向。
《天地》刊载的这些散文以敏锐的视角深入到市民日常生活深处,反映了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撞庵的《甘和苦》写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甘苦;小鲁的《吃》津津乐道各种不同吃的乐趣;汪昱的《盲肠炎者的自白》写自己被庸医无故割掉盲肠的就医经历;丁谛的《闲话商人》写商人的赚钱之术;禾人(苏青)的《买大饼油条有感》写知识女性买大饼油条被人看到后引起非议的感想。即便是谈名人,《天地》散文作者也将他们置于日常生活中,描写其鲜为人知的世俗生活。许季木的《谈拿破仑的晚年》写的是滑铁卢之败后被英国政府送到圣海列那岛上与世隔绝的晚年日常生活;小凡的《记大人物的癖好》结合西方政要的个性谈论其爱好。
《天地》散文作者认为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断在作品中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在《天地》散文作者看来,宏大的目标都是虚伪的,饮食男女才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他们往往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看成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在散文中反思日常生活种种的不合理处,并指出其重要价值:“观乎上述种种,可知国人于衣食住三者之诸欠合理。亦以见国人之不明事理,不辩是非,于日常生活之必需,犹复如此,他且不必问矣。胡适之有云,‘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语虽偏激,实有至理”(有心人《衣食住》)。
《天地》散文作者还善于从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和哲理。虽然孩子的接连出生会带来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但霜叶在文中这样写到:“我记得有一次回家得很晚,开了电灯,看见躺在孩子壁垒中的妻子的睡姿,很有一点诗样的享受,只要我有百分之一的诗人的天才,我准会写出一首美丽的诗来,我觉得这情景是美的,有诗情的,也有画意”(《群小》)。他们经常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在文中畅谈多子之乐(予且《多子之乐》),列举住在都市公寓中的无穷趣味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谭维翰从给孩子洗手、揩面、穿鞋、换衣、讲故事这些日常生活细节中体会出无限的快乐,还从多子并未使得自己经济状况变差升华出浅显的生活哲理:“人总有一点惰性,有了孩子可以使做父母的人振作起来,这倒是有意想不到的美德,我们不该讨厌孩子,只应感谢孩子”(《为父者言》)。
《天地》散文在对日常生活描写中表现了身处战乱境况下市民的世俗理想和追求。战争使人们面临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他们不再追求宏大的理想,仅表现出结束战争、回复到常态的日常生活的渴望:“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非常快快的过去,恢复了我们能应付的常……我们没有一份力量,可以旋转乾坤,化戾气为祥和,飞机炸弹潜艇之工作,我们委实是没有力量制止的,我们所要求的,只是非常状态的寄生虫们,也能恢复一些‘常态’”(潜之《常与非常》)。在战乱中,他们即便有一些梦想,也是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显得尤为世俗:“战后沪上房屋奇缺,敝人之做所谓三房客已六年于兹矣,寓所狭隘小窗,受尽房东瘟气,尤其余事,故而存下一个妄想:一旦多下几个钱,定要造一所真真的所谓‘花园洋房’,窗子定须开得多,园子务必造得大”(实斋《谈窗》)。
《天地》散文表现出市民阶级实用的、利己的价值观念。他们毫不讳言自己对实利的追求,承认人的物质需要的合理性。这种实利的观念甚至渗透到爱情当中,市民在恋爱的时候往往把神圣的爱情和世俗的物质需要联系起来。予且认为:“在从前,婚姻是一件终身大事,焉得不谨慎将事。如今,婚姻已经成为生存手段,焉得遇事挑剔,来关闭自己的幸福之门?这一种变迁不能说是不大,更不能说和以前相差不远。婚姻如此,恋爱的方式,手段,性质,结果,遂亦不得不和以前不同了。”(《我之恋爱观》)在实利思想的影响下,市民多采取中庸的处世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种种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处世哲学。霜叶从坐车中领悟到:“精明的人,或是抢先的人,未必一定占便宜,有时反而吃了亏。反过来说,不精明而不抢先的人,有时反而实惠。不过精明的人和抢先的人,心理上总觉得自己占优势地位:既生而精明,复抢着了先。可是那里想到事实偏不如此。”(《坐车哲学》)这些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不崇高,但务实;不纯粹,但本真。
《天地》散文对日常生活的表现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古代的文以载道,还是“五四”及其以后的启蒙、救亡口号,散文主要表现的是政治、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而《天地》散文把表现对象转到以个人为主体的日常生活领域,关注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生儿育女、男女交往等基本内容,展示了人们生活中最为本真的一面,让人们认识到了世俗生活本身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三、“只要你谈得有味道耳”:日常生活的奇趣化表现
苏青在《〈天地〉发刊词》开头就写道:“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耳。”[5]在把《天地》杂志内容拓展到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同时,又提出要“谈得有味道”,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表现。为此,《天地》散文采取了一系列吸引读者的话语策略。
首先,打破散文文本的封闭状态,将其看成是一个开放系统,通过引用或拼贴等手法形成互文关系,使文本在相互指涉中产生意义,甚至将文学文本和实用文本混融,增加趣味性,让读者读出“味道”来。
苏青在《〈天地〉发刊词》曾提出作者不限于文人,所刊登的文章也不限于纯文艺作品。但是由于散文文体具有开放性,完全可以通过拼贴等方式使不是纯文艺的作品产生出意味来,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文化消费需要。如《天地》第7-8期推出了生育问题特辑,其中有苏复医师的《节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无论是从作者的身份还是从文章的题目来看,都像一篇科普类文章。但是该文从一开始就侃侃而谈古今中外种种节育或促进生育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经过作者有机组合和重新阐述后插入到文本中,与后文的科学节育措施相对照,产生出新的意义指向,既将严谨的科学话题拓展到了生动丰富的历史生活领域,又有一定的人文思考,所用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叙述的生动性让人读来兴致盎然。此外,柳雨生的《节育之难》一文在进行探讨时插入的笑话、周越然的《婚姻与生育》在议论中插入的故事,都冲淡了科学话题本身的严肃性,使之妙趣横生,消遣性大于科学性,成为文化消费的一种。
《天地》散文中另一种典型的语体交融形态是体裁互文,即作者在散文文本中加入其他体裁文本,使得散文语体变得更为丰富,同时产生意义指涉。予且的《我之恋爱观》就是一例。“观点”是一种理念化的形态,如何将之生动地述说出来?首先他申明人的恋爱观是容易变化的,为真实展示自己恋爱观的变迁,他结合自己的写作道路和对社会的认识,在散文文本中大量植入先后写作的《小菊》《凤》《两间房》等小说文本来演示自己恋爱观的变迁。显然,小说是虚构文本,大量拼贴到散文文本中,会“将两种陈述分开,使得读者不得不暂停下阅读,把目光投射向另一个空间,另一种方式的话语”[12],这样一方面把爱情观阐述得更为具体,增加了散文阅读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将已固化在小说文本中的爱情观念和自己在时代中的感知相互印证,使变迁的流程更加可信。
此外,《天地》中刊载了不少奇文,不仅打破界限,将各类文体杂糅,甚至将文本和表格混合,用别出心裁的形式谈论某种世相人情,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如第14期以吃书人为名发表的“Edible Edition”一文。作者托词说因无准确译文而用英文名作为标题,实则是为引人注目;在文中声明该文是博士考试论文的大意,并为该文多次加注,使文本呈现出庄重的形态,内容实际上是讨论怎么印一种可以吃的书,并在后面插入了一个滑稽的菜单,这样在文本内容与形式、文本形式和形式之间造成巨大的反差,在戏谑中对文坛和社会现状有所针砭。苏青在《编者后记》中评论道:“本期发表此篇,立论奇,写法奇,且趣味无穷,而说笑中均有至理,诚不可多得之佳作也。”[13]苏青一向选稿很严,该期又因纸价飞涨仅刊载11篇文章,在此情况下选入此文且大加赞赏,充分说明了《天地》对文体的重视。接下来的第15-16期又刊载了同一作者以散淡的人为名发表的《出妻表》一文,文体形式更为奇特。从文名来看,是对封建时代“七出之条”以及诸葛亮《出师表》的戏仿,内容则将计就计,设计成一张表格,以独特的文体形式揭示了社会中某些家庭女性只是一种代用品的现状,多则历史典故在文本中运用,与表格内容指涉,暗指“妻子”这一身份至今没有得到改变,通篇采用表格的直观形式一目了然,让人在忍俊不禁后深入思考。
其次,《天地》散文常常打破常有的思维模式,将日常生活陌生化处理,或反其道而行之,说出惊世骇俗的言论;或庄谐并出,或雅俗对照,营造出奇特有趣的话语风格。
《天地》散文所表现的日常生活发生在人们周围,重复琐碎,平淡无奇,为使得散文“有味道”,引起读者的注意,作者常常采取逆向思维,打破日常生活的机械性,使之产生奇趣。对于《礼记》上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人们习以为常,但是苏青将之断句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突出了女性欲望的合理性,奇趣就产生了。与之类似的是,正人在《疏女经》与一般介绍如何取悦女人的经验相反,该文谈论取厌女人的基本原则以及实行的细则,包括什么样的言论最能取厌女人,如何在路上、饮食店里、戏院里,在房中、在月下等场合取厌女人等,可谓奇特之至。再如,依照惯常思维看,言语不通无疑会阻碍人们的正常交流,给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是苏青的《论言语不通》却从自己的日常经验出发,侃侃而谈言语不通就不会得罪人、照样可以达意、可以得到“情之正宗”的恋爱,这种反其道而行之又建立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生存感悟,无疑会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
《天地》散文的这种奇趣还表现在谈论严肃话题的时候引入世俗的比喻,使之充满了烟火气息。节育本为一个科学问题,但是东方髦只却在《不孝有弍》一文中将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和尚与尼姑、嫖客与娼妇,显得不伦不类;但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世俗化比喻,在吸引市民读者注意力的同时,形象地阐明了节育的必要性。该文在对庄重的科学“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大胆引入世俗化的比喻和言说方式,从而将科学娱乐化,满足市民的消遣需要。《天地》散文常常运用庄谐并置、雅俗对照等手法,将日常生活和重大时事或风雅韵事放在一起谈论,产生出幽默的效果。如第18期的《自言自语》一文在谈论男人给女人零花钱时,把家庭日常生活的金钱往来和重大的经济政策及分配投资联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无独有偶,正人在谈到女人惧怕衰老时,不仅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以及“人老心不老”两个词义更改了,而且用“闪电进攻、按兵不动、停战言和、移交、拉锯战”等描绘军事的词语来揶揄女人对衰老的抗拒。《天地》散文还善于将日常生活事件进行雅俗对照,从而产生某种幽默的效果。在《群小》中,霜叶写到自己的孩子出生时说:“拿我自己来说,除了第一个孩子由当事人双方同意‘决定’养之外,其余的几个就像诗人的名句一般,所谓‘偶得之’,根本不是存心要养”,把意外生子的世俗生活与诗人作诗的雅事比照,让人解颐。
《天地》散文为追求“有味”的话语方式,打破文体的封闭状态,在文体形式上不断创新,以新奇的思维方式表现日常生活,营造幽默趣味的言谈方式,既体现了散文作者对于日常生活本身的认同,也体现出了适应读者大众阅读需要的追求。《天地》散文的这种追求对后来散文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南方周末》和上海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开辟了许多专栏,刊载了大量女性散文。无论是关注日常生活的内容,还是发表的表现形式,都与《天地》散文有一脉相承处,被称为“新海派女性散文”[14],证明了其生命活力。
[1] 苏青.苏青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329.
[3] 刘轶.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1942年—1945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07:93.
[4] 苏青.如何生活下去[J].天地,1945(17).
[5] 苏青.发刊词[J].天地,1943(1).
[6] 予且.予且随笔[J].天地,1944(4).
[7] 正人.从女人谈起[J].天地,1944(13).
[8] 纪果庵.夫妇之道[J].天地,1943(3).
[9]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0.
[10] 予且.我之恋爱观[J].天地,1943(3).
[11]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危害?[J].国外社会科学,1990(2):61-66.
[12] 贵志浩.话语的灵性——现代散文语体风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90.
[13] 苏青.编者的话[J].天地,1944(4).
[14] 周红莉.论1990年代后新海派女性散文[J].江苏社会科学,2007(6):122-126.
(责任编辑:张 璠)
Manifestation of Conceit of Everyday Life On Discourse Features of the Prose inTiandi
MAN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the occupied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n the 1940s, catering Shanghai people’s needs for cultural consumption, the essays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Tiandimainly concern the universal themes of human being, such as the natural instincts and essential needs of men,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aily life, affirming the value of daily life, thus representing daily life through the writing techniques of reference, collage, defamiliarization, making the solemn and witty tied together, comparison of the elegant and the popular, etc. A strange and interesting speech style is created and a unique discourse of modern metropolis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is formed.
Tiandi; prose; daily discourse; conceit
2014-05-23
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都市文化视阈下的海派散文研究”(SK2014A398);宿州学院教授(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上海现代传媒与海派散文”(2014jb08)
满建(1978-),男,安徽宿州人,宿州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6
A
1674-0297(2015)01-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