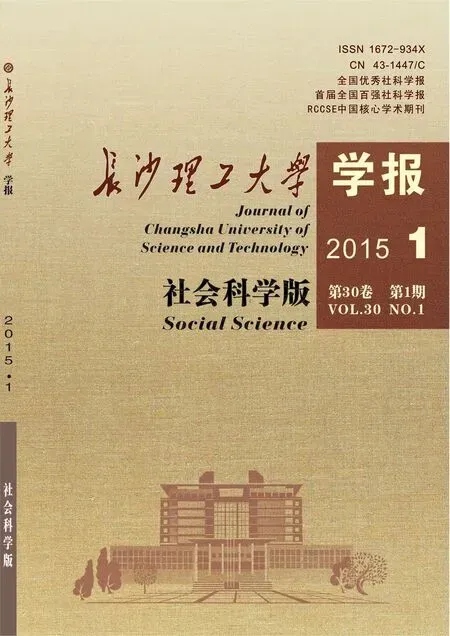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价值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价值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去除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傲慢,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具有三层方法论价值:一是使“主观”的社会科学走向“客观”;二是“宏观”的社会分析走向“具体”;三是“微观”的社会研究走向“真实”。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价值
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作用,往往被视为学术不自由、人格不独立,这其中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有学理上的混乱之处,笔者试图做点澄清。
一、“主观”的社会科学如何做到“客观”
大家知道,社会历史领域离不开“主观性”,可如果建立不了“客观性”标准,该领域的研究就无法成为科学。因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致力于寻找历史的“内在必然性”,黑格尔称之为“客观精神”,马克思称之为“历史规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把这种“客观性”视为非个人意志的产物。而马克思以后的所有不赞成马克思的探索,几乎都试图以“个人”(及其意志)来说明历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波普尔。韦伯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为“只能支配外行和浅薄人的头脑”[1](P19)予以断然拒绝,而波普尔则指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希望将历史变成个人主观意志的“任性”,因此不约而同地将“客观性”定在了历史地积淀于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上。在韦伯看来,历史领域的“客观性”只能是深藏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1](P6)
但是,把渗入每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其表现形式就是“普世价值”或“良知”)作为历史“客观性”的依据,存在着明显的“软肋”:尽管人类的道德理想、价值追求有一个“向善”的指向,有跨民族、时代的共同性,但历史从来不是按人们的内心愿望“直线式”发展,而是曲折、跌宕、出乎意料地发展的。用“普世价值”去设定历史的人,无法说明曾经的“价值共识”总是不断被颠覆的历史事实,无法证明我们今天究竟是处在历史的“高点”、“低点”还是“拐点”,因而无法证明今天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从历史趋势上看是否属于“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无法证明该价值观(比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高于其它价值观的优先性。
大多数人的“诉求”、“认同”并不能作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客观决定力量,甚至可以说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前一个阶段大多数人“诉求”与“认同”的颠覆。因为前一阶段大多数人“诉求”与“认同”往往造就了那一个时代的秩序,不颠覆这种秩序,就无法为新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可以说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以颠覆曾经的“普世价值”为前提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2](P236)资本主义是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的颠覆。科学社会主义也必然要用“消灭阶级”、“共同富裕”、“劳动解放”等价值追求,对资本主义的价值共识进行颠覆,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为何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原因。
同样,“良知”也不能成为历史的客观坐标。虽然“人同此心”,但心并不能阻挡“人心不古”,不能破解“人心叵测”、更不能揭示“人心向背”。“良知”是否天性、“天良”能否发现、“天理”是否能容,于人于事都难以定于一规,只能听凭见仁见智、可信可疑、毁誉随意;“良知”为天性还是“习得”,“致良知”如何可能,争了几千年也没有争明白。以此为据,能有真正的历史科学吗?
因此,在我看来,“人性诉求”并不是决定历史趋势的主导力量和根本原因。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韦伯)都承认价值观的相对性(只是他称之为“积极的相对主义”),既然如此,它就必然有使之成立的更为根本的缘由。在今天一些人看来,自由的价值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可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种“逃避自由”的情况,则一再出现在历史的记忆中。恩格斯就引证过德国农奴在17世纪放弃“自由”、寻求领主保护的史实,说明个人意志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3](P440)(注:三十年战争的时间为1618-1648)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社会的最高价值只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而不是所谓的“自由”,因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所能实现的自由,就只能是资本的自由、金钱的自由,而不是个性自由。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可能进入个性自由发展的时期。
因此,从人的主观意志与价值诉求来寻找社会科学的客观基础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客观的生产力状况才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标准。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因此“主观”的社会科学要做到“客观”,关键在于研究的出发点与研究路径,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实的物质生产状况,研究路径必须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物质生产实践。
二、“宏观”的社会分析如何做到“具体”
对于宏观的社会问题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视其为空洞的“宏大叙事”而加以拒斥,或者通过“概念的具体”而加以应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否定整体认识社会的可能性,因而拒斥“宏大叙事”而沉溺于“局部工程”的认知、“细小叙事”的把玩,绝对的相对主义和“碎片化”则成为其特征。排斥了对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识,也就失去了历史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的依据。这是当代思想混乱和价值缺失以致道德危机的根源。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缺乏“大气”、“大手笔”的成果已成为当今许多人的忧虑,以至于我们不仅不能深刻洞察历史的未来,甚至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等现实问题也一筹莫展。美国对外政策焦点研究所副所长费弗在《下一个马克思》一文中是这样感叹的: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从而使左派和右派同样大吃一惊。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这一期盼折射出近年来“碎片化”研究的浅薄和无效,足以发人深省。当然,用概念代替现实、以逻辑剪裁历史、靠想象设计未来的抽象整体性研究,也于事无补。唯一可行的是开辟出具体地、科学地整体认识社会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可能给我们以启发的地方。主要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社会科学要做到“具体”,就必须打破抽象化的陷阱,提出具有能指的“具体概念”。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用抽象的整体否定具体的部分。比如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理直气壮,但是脚下的土壤其实非常疏松。因为从人类有史以来,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从来就没有现实地存在过,而现实存在的是对抗的阶级利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阶级的阶级利益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什么阶级的阶级利益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进一步说,也正是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抗,才存在着(统治阶级)用抽象的人类利益去否定某些现实利益的情形。
二是用抽象的人性否定具体的个性。资产阶级惯用的抽象化思维手段不仅表现在用抽象的整体否定具体的部分,还表现在用抽象的人性否定具体的个性。其典型表现就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状况,视为是超越阶级的永恒人性,是人性发展的顶峰,并以此作为评价其他国家是否尊重“人性”、“人权”的标准。这种做法可以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可以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使其占领“自然如此”的人性高地;另一方面是消解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使其陷入“违反人性”的道义困境。但是这种把一成不变的人性视为历史的深层根据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无论是历史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证明,人性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呈现出人性的不同状况。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性不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其表现;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可见,用抽象的人性去解释社会现象,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方式,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比如抽象的劳动、抽象的思维、抽象的人性等,把“思维的抽象”还原为“思维的具体”,“概念的具体”则是马克思主义破解资产阶级抽象化陷阱的思维方式。
第二,要做到“具体”,就必须提出可以进行分析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有改变世界的追问:这个世界什么问题需要我去改变?而不能把一切现实存在的东西看作是当然的前提,从而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次上。改良主义的谬误不在于其重视事物的修修补补,而在于其力图保存当前的事物。“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61,66)历史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终结”。尽管历史发展的方式有渐变(量变)和突变(质变)两种,但变是本质、质变是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就是准确判断当前的发展态势、努力推动事物的革命转化。
要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就必须有一系列内涵外延清晰的具体概念。概念具体是指能够正确把握和历史再现客观存在的思想范畴,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矛盾概念,而不是孤立(单一)、静止(无差别)的范畴。这就是说,具体概念的构成至少是“二”,而不是“一”,其次这“二”是又对立又统一,其动态展开过程就是现实事物变化的逻辑表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为例,作为具体概念,它既不是单一的“生产力”概念,也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概念,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就是说,脱离了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都是抽象概念,都不能准确反映现实的经济运动过程。“生产力”概念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但在马克思之前运用这一概念的人(例如德国贸易保护主义之父、经济学家弗·李斯特)并没有运用这一概念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科学的描述。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没有看到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则是统治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没有形成“生产关系”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没有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做出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具体的分析[4](P115)。
第三,要做到“具体”,还必须有一个认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深入实际,这其实是一个拆分实际、梳理问题、发现本质的过程(具体的表象蒸发为抽象规定的过程);二是解决实际,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整理、形成思路、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具体分析”就是用具体概念还原现实,实质是体现理论的彻底性,抓住事物的根本,形成可以说服人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贯彻“具体分析”的要求,我们研究任何社会问题,有两个根本界限必须分清:一是通过体制内的改良、自我调整能够加以解决的,和必须通过推倒原体制才可以解决的;二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和停滞不前的问题。我们不否定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甚至不否定某些问题的极其严重性。但是,如果问题属于两个界限的前一类,那么从总体上看就是社会凝聚力大于社会的对抗性,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大于对当下困难的不满,或者说,机遇大于挑战。这就是我们反对“中国崩溃”论的根据,同样,这也是我们反对夸大中国的发展成就,掩饰其存在的问题,灌“迷魂汤”式“捧杀”的理由。
三、微观的社会研究如何做到“真实”
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密不可分。从数学的排列组合看,似乎有四种情况:宏观、微观都科学;宏观准确、微观错误;宏观错误、微观准确;宏观、微观均失真。但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则只有两种结果:宏观、微观的具体、历史统一中的真实或不真实。也就是说,宏观分析正确,也可能出现对于某一阶段、某一局部分析不准确的情况,但这只能是暂时的,如果一直改变不了,则宏观分析也是站不住的;反之,宏观分析失真,而局部、阶段性分析有效,这也只能是暂时的,有其历史界限的,否则,其宏观分析就不能是错误的。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西方经济学微观管用,宏观失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有效,微观无效。这在一定历史界限、一定社会范围内可能成立,超出了这一范围或界限,情况就会改变。比如,将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研究,可能就会导致谬误。
现在有一个误解,似乎一谈到微观研究,就只能做定量分析,只能靠“数学模型”解决问题。其实,微观研究离不开宏观分析、定量研究离不开定性分析,仅靠抽象的数字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毛泽东早就指出,必须抓住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特点,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5]这种“不平衡”说明中国是个“异质化”的社会,其挑战和出路都在这里,而使用抽象的数字去解决中国问题就更加需要格外的谨慎。如果说,抽象的数字过去说明不了阶级力量对比、军队士气及战斗力,更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话,那么今天,抽象的数字同样难以有效观察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对于当代中国问题容易产生误判的一个原因,就是迷信抽象的数字和公式。比如,人们可以根据世界银行关于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最新报告,得出中国已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之一的结论;从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的数字,得出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甚至社会已经发生严重分裂的结论。我要说,“吉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人均GDP”、“国际标准”等等,都不是判断中国问题的最终依据,对于中国问题的话语权不在这里,而在于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欧美发达国家可以说是个均衡化、同质化的社会,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单一,因而抽象的数字能够说明问题。换言之,日均收入10美元的,生活质量肯定高于日均5美元的,而日均不足2美元的肯定是极端贫困的人口。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社会,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活法”。因此,同样的收入,生活质量迥异;收入稍高的,不等于生活质量就一定较高;在西方按“国际标准”看来简直无法生存的收入,在中国就可能生存、甚至还有一定的生活乐趣。我丝毫没有否认或忽视中国当今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意思,而是想强调,但是如果仅仅凭一些统计数字或公式概念去判断和预测中国,就必然失之偏颇。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同时,我们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如果老百姓挣的钱都用去看病了(这印证了“健康”的价值)、都被坑蒙拐骗了(“安全”很重要)、都被污染空气、水和食品了(“绿色”的价值),GDP又有何意义?单纯的GDP观点正在被改变。
如果满足于所谓的“微观正确”,不从史料的真实上升到历史的真实,必然会在两个问题上失足:一是混淆“卑躬屈膝”和“忍辱负重”的界限;另一是混淆“惨无人道”和“壮士断臂”的界限。这两个问题就现象看有相似之处,卑躬屈膝和忍辱负重都是一种“妥协”,而惨无人道和壮士断臂则都是一种“伤害”,但是两者的本质和本性却截然相反:有两种妥协,一种是维护更大的利益而作出的“必要让步”,另一种则是贪图私利而丧失道德意志的“缴械投降”;同样,有两种“伤害”:一种是灭绝人性的屠杀,另一则是展现人性光辉的牺牲。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正义”,而判断是否正义就需要科学的历史尺度,树立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坐标。由于历史是复杂的,事物的性质往往也是多重性的,因而更需要把握事物根本性质的客观标准,更需要确立这一客观标准的科学方法。
近代以来,东方社会不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近代史之争的焦点。在“西化”的观点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总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并从根本上毁灭了其原来的文化传统,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4](P762)山河破碎、积弱贫穷是这种入侵的物质后果,而丧失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则是这种入侵的精神后果。因此,我们从根本上不能歌颂、赞美西方的殖民侵略,而必须揭露和控诉这一侵略、歌颂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而离开这一基本面的所谓材料真实,都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188.
On the Value of Social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 Marxism
HOUHui-qin
(ResearchInstituteofMarxism,China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
DDeprived of ideological prejudices and pride, Marxism holds the value of three-dimensional methodology for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es. Firstly, it enables "subjective" social science to become "objective"; Second, it enables "macroscopic" social analyses to be "specific"; Thirdly, it enables "microscopic" social studies to be "authentic."
Marxism; social scientific methodology; value
2014-12-15
侯惠勤(1949-),男,安徽安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A811
A
1672-934X(2015)01-0046-06